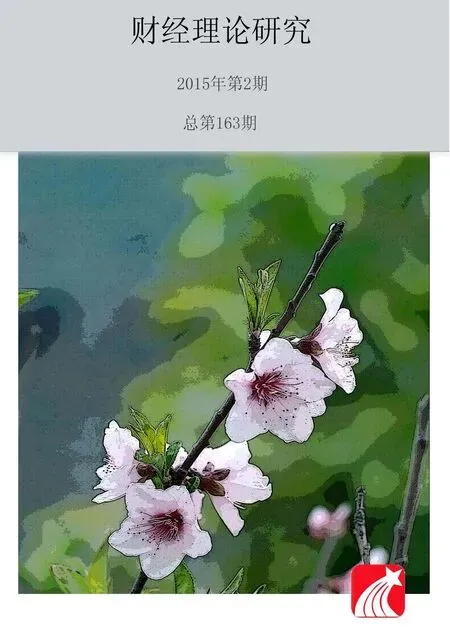从“掠夺之手”到“扶持之手”——城镇化的反思与转型
从“掠夺之手”到“扶持之手”
——城镇化的反思与转型
史官清
(泛华集团城市发展研究院,北京100070)
[摘要]政府在参与经济问题时有三只手——“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在传统的城镇化道路上,很多弊端根源于“掠夺之手”,如单向索取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对西部的掠夺、城市对乡村的掠夺、中心城市对次级城市的掠夺)、农民工及被征地农民不能融入城市社会(要地不要人、要劳动力不要市民)、透支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对环境的掠夺)。“掠夺之手”积弊的解决有赖于政府的“扶持之手”,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多处都能够看到“扶持之手”,笔者从区域协调、城乡统筹、以人为本、开放包容、集约节约、改革创新等方面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扶持之手”进行解读。
[关键词]掠夺之手;扶持之手;新型城镇化
[收稿日期]2014-09-19
[作者简介]史官清(1979-),男,内蒙古赤峰人,泛华集团城市发展研究院战略产业规划师,博士,从事经济增长、财税理论与政策、科技管理、区域经济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2
一、“手”的转变与城镇化转型
手,是经济学者为政府建构理论模型时最常用的一个喻指。亚当·斯密秉持自由放任观点,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运转良好。除了提供法律、秩序和国防安全等这些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手应当是“无为之手”。依据凯恩斯干预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府模型叫“扶持之手”,它描述了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政府的作为。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在《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运用经济学工具,提出了“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认为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为追求私利而牺牲公益①。
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承载了国家和平崛起的战略需求,受到新型工业化的带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2至2011十年间,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表现在: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常住人口增加扩展了城市市场需求规模,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近3倍,同时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50%以上,设市城市与建制镇数量迅猛增长,超过800万人口的城市超过30个,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教育、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持续较快发展,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制度藩篱逐步打破。②
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我国传统城镇化也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人口不完全城镇化、要劳动力不要市民,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城市管理压力大、社会问题突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要地不要人,城镇用地粗放低效,以物质资本大量投入为驱动要素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大量人口向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相对缓慢、空间分散、功能不足,区域均衡发展面临挑战;“城市病”和“乡村病”现象并存,城市历史积欠多、农村发展乏力,城乡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工业过度集中、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多样、交通压力大等“城市病”与劳动人口空心化、耕地荒废、公共服务边缘化、农耕乡土文化消失等“乡村病”同在;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公共服务能力欠缺,普遍出现房地产化,“空城”、“鬼城”现象普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机制阻碍城镇化健康推进,亟须转变。
传统城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大都可以在“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中寻找到一些解释。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我国正在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这将是国内外城市化宝贵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实践再结合的契机,将是转变城镇化推进思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老问题与新问题的战略性实践,无疑,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公布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该规划将成为未来几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纲领性文件,从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扶持之手”正取代“掠夺之手”成为质量增进型经济的主推手。
二、传统城镇化中的“掠夺之手”
城镇化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部分起源于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适当运用了“掠夺之手”。这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层面,更包括地方政府的层面。
(一)“掠夺之手”导致非均衡发展的城镇化
1.东部掠夺西部
东部地区在解放之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轻工业基础好,人才集中,且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人力资源等方面相对较弱。东部优先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之初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观符合区域非均衡增长的经济理论,即在一个大局中利用缪尔达尔所说的“回波效应”③,而第二个大局中运用其所说的“扩散效应”④。区别仅在于,在实现两种效应的过程中,政府是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常高,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东部都市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较发达的城市,而西部地区由于资源、人力的外流,经济处于落后的境地。尽管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政策,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个大局已经来临的迹象。但从现实来看,东西部差距仍旧在扩大,存在过多的回波效应,过少的扩散效应。
学者马述忠、冯晗(2011)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地区发展差异与整体经济规模同步增长,尤其是其中的东西部差距,几乎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过大的地区发展差异不仅会对整体经济发展构成阻碍,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西部大开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发展差距,尤其是在GDP相关的部分经济指标上。不过,过分关注能源产业、过分追求大投资可能会给西部经济带来新的问题。⑤
2.城市掠夺乡村
改革开放前,也即建国后的头三十年,国家通过对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维持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生存,其间农村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难以想象。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中国迅速演变为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以乡村社会为主体的中国社会迅速转变为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类型。
当前,中国又落入了依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怪圈,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的背后,是四千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完成了被动城镇化的历程。对农村矿产资源、耕地的无偿或低价使用,制造了更多的贫困人群,导致更多的群体性事件。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阶段有关系。一个地区的发展,要经历城乡收入差距由低水平的均衡到收入扩大、再到收入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倒U字形。这是一个规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尽管如此,我国的城乡差距仍逐步扩大,且未看到缩小的迹象。
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到了2010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3.中心城市掠夺次级城市
在2005年,建设部根据《城乡规划法》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的国家中心城市概念,将国家中心城市置于全国城镇体系金字塔的最顶端。形成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五大中心城市的格局,以及期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沈阳、西安等城市⑥。另外,区域经济中心、区域增长极等概念也在各个城市的规划中屡有提及。中心城市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仅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职能,更是国家战略或区域战略的载体。
一旦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就能有效集聚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形成经济的繁荣局面。传统的城镇化往往是权威主导,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以及单一中心的城市布局。从这个国家到省市县,都是自上而下的汲取资源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我们的城市能够繁荣的基础之一。中心城市往往成为“掠夺性的城市”。其财富、人力、资源,依靠吸纳周边的比它层级更低的城市以及乡村,把资源集聚到中心城市,形成了自身的繁荣。
实际上,中心城市的发展最终是要靠周边地市的繁荣才能真正发展的,真正的发展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倒金字塔。次级城市以及乡村的发展落后,必将阻碍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掠夺之手”导致人与地的城镇化不同步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一直遵循“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这种模式概而言之就是“只要农民的土,不要农民的人”。要地是赚钱的,要人是花钱的。其结果具有悲剧色彩,虽然我国的名义上城市化率已达53.7%⑦,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城市户籍的却只有35%左右,有19%的农民工虽然已在城市居住但却被排斥在城市体系之外,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应该享受的社保医疗等福利。
因为不承担近1.5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社保成本,我国的城市化通过征用农民的土地却付出极低的失地补偿成本,廉价低成本扩张十分迅速,尤其是不少大都市等在短期内繁荣起来。我国城市化的财富来自农民的土地,但农民却被排除在受益之外。
古典经济学先驱威廉·配第就曾说过,资本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民最重要的资产是土地,而目前的城市化征地制度廉价拿走农民的土地, 农民只能获得极低的价格补偿,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增值享受之外。我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一部分财富来源于土地和各种资源的开发,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发展城市与工业都需要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使用农民的地,目前城市发展95%以上是通过征地来实现的,而地方政府每年卖地的收入都在大幅度上涨。
在1997-2008年我国地方政府仅从土地出让金中就获得5.2万亿的收入,而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万亿元。我国的土地是国有的,但中央与省级政府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土地出让金,能够获得土地出让金的有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大量的土地收益集中在城市,农民被排除在受益之外,造成部分城市繁荣,农村贫困。不少地方都存在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目前这种愈演愈烈的“消灭村庄大跃进”,逼农民上楼,也是历史罕见。把农民宅基地转换出来用于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这种“只要农民的地,不要农民的人”的城市化已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⑧。
(三)“掠夺之手”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
城市是一个经济中最为繁荣的部分,而城市的繁荣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就业才能够支撑。但中国的传统城镇化出现了“只要劳动力不要市民”的错误路径,原因并不复杂,市民化必然要支付相应的成本。
学者张国胜(2008)在其著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中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⑨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高?针对这个问题,有几个说法:(1)2005年,中国科学院估计每进入城市一个人,需“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2)2006年,建设部调研组称,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不含运行和管理成本);(3)2009年,张国胜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认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称,“根据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⑩。
这个成本并非高不可攀,如果处理得当,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是一个天堑。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归还历史积欠的关键时期。
(四)“掠夺之手”导致综合承载力透支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单位GDP的能耗相当于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以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资源紧缺、油价上涨,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空气污染、雾霾增多……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粗放、外延式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将走向尽头,我国的国民经济与城市经济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发展不可持续的直观表现是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不可持续,实质则是经济发展方式不和谐、不可持续。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经济发展既面临着资源供给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内生动力缺乏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较快,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1。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
从城镇化发展来看,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市粗放扩张,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盲目扩张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将城镇化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土地的城镇化,在“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路下片面地快速推进土地的城镇化,摊大饼式地扩大城市边界。外延扩张式的城镇化产生了城市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表现为城市人口密度不高、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以及土地产出效率不高的问题。
而粗放式的城镇化路径导致我国土地利用产出非常低,在我国多数城市用地结构中,工业用地占到了30%左右,超过美国(7.3%)和香港特区(6%),并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图1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粗放式特征 数据来源:《中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
(五)体制机制不健全是“掠夺之手”存在的内因
以财政体制中的预算制度为例,我国实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各级地方政府预算由本级政府预算和汇总的下一级总预算组成,多数政府仍沿用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基数增长法。即,各政府部门在编制预算时是以去年的预算数据为基础乘以一个增长率,得出今年的预算申报数。这使得政府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往往夸大编制基数,既为今年争取更多的资金,也为下年编制预算提高基数,而不是经过合理、科学的测算,得出本年该部门实际应申报的预算数。
一旦预算获得批复,往往就已经超出了该级政府的恰当支出,这从法律层面上导致了当下政府部门出现铺张浪费的现象,导致税收资源的浪费。一旦年底出现预算的盈余,这部分将被上一级政府重新统筹,转拨给更需要资金的相关政府或部门,并且减少该政府下一年的预算批复。所以地方政府的选择往往是加速预算执行,绝不为人作嫁。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出现了“公地的悲剧”。
城镇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现盈余本来是有经济依据的。如土地财政,一旦收储了农民的土地,就欠了农民一个愿景,一笔未来的支出流,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处理是题中之意。但在当前的预算体制下,政府更愿意将这部分收入一次性支出,转换成为自己的政绩。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为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你能看到湖北十堰250亿元的“辟山造城”,4亿财政收入的武胜县敢于打造“东方迪拜”。
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扶持之手”
政府行为的理想状态是“无为之手”,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参与,从一次次的减少审批权限改革中,可以感受到这种状态正在临近。最糟糕的状态是政府伸出“掠夺之手”,其后果是社会和经济将面临灾难,我国传统的城镇化之路中有许多问题是由于“掠夺之手”造成的。“扶持之手”是一种中间路径,在传统城镇化积重难返的前提下,如没有政府的“扶持之手”,很难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针对这一窘境,党中央于十八大适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型城镇化会议、农村工作会议都对新型城镇化做出了一些具体的阐释: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公布,其中许多地方都体现了“扶持之手”,这也许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福音。
(一)区域协调、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规划》阐明了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认识到“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提出“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规划》的第十章《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中提出“中西部城镇体系比较健全、城镇经济比较发达、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开发区域,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农民工,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在优化全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从认识层面将对中西部地区伸出“扶持之手”。
《规划》阐明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认识到“我国农村人口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提出“城镇化总体上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为发展现代农业腾出宝贵空间。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第六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指出“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可以理解为将对乡村这一弱势方伸出“扶持之手”。
《规划》的第十二章《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中提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减少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的“掠夺之手”,实现大中小城市共生共荣的新思路。
(二)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其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 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
《规划》的指导思想开宗明义,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规划》的第三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提出“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健全落户制度、实施差别化落户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包括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包括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合理确定各级政府职责、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等。”
以户籍人口来看,我国的非城市人口仍旧占有绝对多数。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福利保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政府适时运用好自己的“扶持之手”,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增长,为可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三)节约集约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规划》提出“优化布局、集约高效,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这可以看作是政府将收回对环境承载能力的“掠夺之手”。
(四)改革创新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制度是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变量,其对经济运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学界对制度改革的呼吁由来已久,政府的历届工作会议也都大谈体制改革。在传统城镇化的推进中,地方政府更多地体现“掠夺之手”而非“扶持之手”,部分原因是改革具有的局部性而缺乏整体协同性,与地方政府利益相左的中央改革思路没有得到贯彻。《规划》强调加强制度顶层设计,消除一系列制度障碍,纲举目张。
《规划》的发展目标部分提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规划》的第七篇《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中提出“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尊重市场规律,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早在2012年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就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所改的,往往也都是“掠夺之手”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规划》让我们看到了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将消除一系列制度性障碍,真正伸出“扶持之手”。
《规划》的第十四章《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中提出“增强城市创新能力。顺应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新趋势,发挥城市创新载体作用,依托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推动城市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营造创新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和文化氛围,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可以理解为新型城镇化的出路之一,没有创新的发展方式将很难在传统的城镇化道路中寻找内生动力,创新发展模式是实现富民强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性动力。
四、结语
沿着古典主义的框架,我们期望“看不见的手”发挥全面作用,政府的手应该是“无为之手”。“掠夺之手”在我国传统城镇化道路上发挥了不当的作用,其不得不带着成就与问题走进历史。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传统城镇化“掠夺之手”的积弊,“扶持之手”作为一种折中措施,是当前政策制定者的不二之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多处体现了“扶持之手”,其作用有待时间的检验,其前景值得期待。
[注释]
①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M].赵红军译.中信出版社,2004.
②张立群.(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0/15/18249119_0.shtml.
③回波效应是由为了在发达区域获得更高的报酬而流出不发达区域的劳动和资本构成,发动的核心区凭借自己的支配地位,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吸入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这将引起不发达地区的衰落,使区域差距扩大.
④扩散效应由从发达区域到不发达区域的投资活动流动构成,发达的核心区为了保持自身的发展,不断增加向不发达的边缘区采购原材料、燃料和产品,输出资本技术和设备,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这有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
⑤马述忠,冯晗.东西部差距——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演化与分解的分析框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⑥丁伟,徐娜,胡艳凤,于小波.国家中心城市与城市的战略思维[M].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⑦数据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⑧郑风田.“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应该终结.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1125/2949789.shtml.
⑨张国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
⑩其中,远期的养老保险补贴平均约为3.5万元,住房和义务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约为2.4万元,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会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约为560元.
[参考文献]
[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2]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编著.掠夺之手[M].北京:中信出版社,赵红军译.2004.
[3]张立群.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0/15/18249119_0.shtml.
[4]马述忠,冯晗.东西部差距——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演化与分解的分析框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5]丁伟,徐娜,胡艳凤,于小波.国家中心城市与城市的战略思维[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6]郑风田.“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应该终结[DB/OL].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1125/2949789.shtml.
[7]张国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张晓娟]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rabbing Hand” to “the Supporting Hand”
——the Reflection on Chinese Urbanization
SHI Guan-qing
(C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PAN-China Group,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Government has “three hands” when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issues——“Inaction hand”,“supporting hand” and “grabbing hand”. In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many drawbacks rooted in “grabbing hand”, such as “the imbala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caused by one-way request”,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landless peasants are hard to engage into urban society”, “overdrawing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settlement of the long standing abuse by “the grabbing hand” depends on “the supporting hand”. It is evident to perceive many “supporting hands”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plan(2014-202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people-orient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ity, innovation and reforming,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supporting hands” based on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plan(2014-2020).
Key words:“the grabbing hand”; “the supporting hand”;the new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