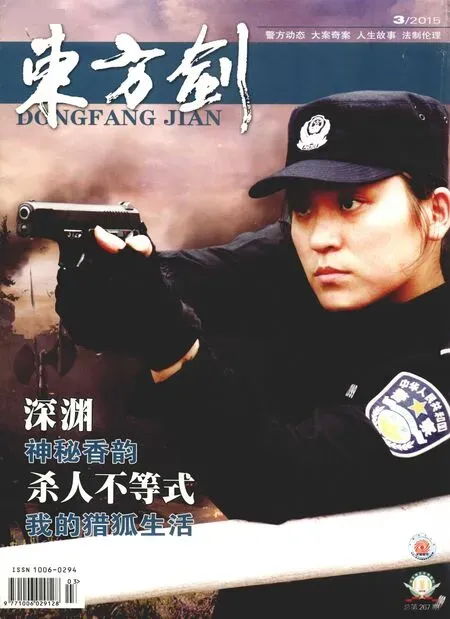神秘香韵
◆ 朱 辉
神秘香韵
◆ 朱 辉

万家灯火时分,住宅楼的窗户都亮着光。楼群像一只只巨大的复眼,窥视着什么。楼群下面无非是蜿蜒的行道灯,远处闪烁着霓虹。楼下的行人或许会朝楼房随意一瞥,但除了玻璃窗的亮度,他看不出差别。
有人说:玻璃窗仿佛楼房的眼镜。这话有点酸。其实玻璃窗全都是平板玻璃做的,度数一样都等于零。如果说有差别,全在于你和这楼房的关系。王路的家就在这楼上,两个人住。说是家,其实很勉强,简直自作多情。房子不是他的,他和一苇合住。他们不是恋人,纯属合租。当然,合租的房子也是栖息地,是每一天上班后的终点,但王路心里更愿意它是一个起点:不但是上班的起点,更是他感情或婚姻的起点。一苇挺漂亮,他喜欢。他一回去就和一苇近了,在同一套房里。他看那玻璃窗的眼神有点像个诗人了。
房子在三楼,窗户亮着,这说明一苇已经回来。他两阶一跨地上了楼打开门,没有看见一苇,她在自己的那一间里。这是个两室一厅的小中套,他们各自一间房。合租与同居是两码事,他们各吃各的,基本都在公司或在外面解决,因此一苇系着围裙把厨房弄得香气诱人地等男人回家,目前只是一个幻觉,或者是一个远景,不过远景里的男人不见得是他。他明白所有的合租都是不可长久的。尴尬难免,微妙也可想而知。这是一种临界状态,要么很快就分开,要么不久就滚到一张床上。就像两团绒絮,风一吹就散了;或者两尊沙塔,脚一跺就塌了,混成一堆。就是说极其细微的因素就可以改变这种微妙的状况。这种状况简直可算脆弱,关门的震动,走路的脚步,哪怕只是一个眼风,一声呼吸,都足以导致现状的终结——要么成为路人,要么合二为一。
王路站在客厅略发了会儿呆,顶上的小灯就熄了。他顺手打开了大灯。小灯先亮,再开大灯,这个是他的手笔。三个月前他搬来后不久,就去街上找来了这么个装置,门一推小灯先亮,避免一苇抹黑找开关害怕。这是善意,是体贴,说是讨好也不为过。王路注意到一苇第一次被小灯照亮时脸上浮现出的惊喜,他忐忑着在心里自嘲:“我这是追求的节奏啊!”但一苇只抬头望望灯,扭头看看他,说:“真不愧是理工男。你一定能算出这盏灯的电费,我来付吧。”这话听上去是领情了,可界限明确。从此他们就是最规范的合租者。
所谓规范,其实就是规矩。主要有三条:平等相待,互不侵犯,互不擅入对方房间。这是公约,并没有写在墙上,是王路入住时一苇口头宣告的。一苇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孩,语气平静甚至温柔,态度却坚决。王路本就觉得这规矩合情合理,自然点头称是。不赞同他也不能再住下去。他原先与一个同学合住一间,后来那同学搬走了,这个时候一苇强调一下规矩很有必要。这规矩或者公约十分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譬如“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就简化成了“互不擅入对方房间”,问题是房子并没有划定国界,既然是合租,有些地方就是共用的。譬如客厅,小到只能称之为走道,于是他们就都只当各进各房的走道用;厨房也简单,基本都在外面吃。问题是,肠胃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次循环,你在外面吃了你还得回来上厕所。要知道这房子的厕所还兼盥洗室、洗衣间及浴室等功用,这就更麻烦。日常问题还可以谦让回避,但碰上拉肚子之类就难免尴尬了。王路有一次拉完肚子竟发现正遇上停水,一塌糊涂无所措手,不要说一苇,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像个文明人——王路是十分重视在一苇面前的形象的。他灵机一动,只能用一苇泡着衣服的水冲了厕所。那盆衣服里没有一件是内衣,饶是如此,王路也偷了东西似的难堪。
一苇是个素净的姑娘。手上戴一串木头手串的那种文艺范儿。虽说那厕所马马虎虎算是冲过了,但王路一直坐在房间里听着水管的声音。水管一有动静他动如脱兔,立即钻进厕所把洗衣盆里的水放到原来水位,再把厕所彻底冲了一遍。他是个自爱守理的人,他守理固然是因为性格和教育,更重要的是他在乎一苇。他珍惜目前的现状——如果不能再进一步的话。原先他同学也住这儿的时候,一苇也跟她同公司的一个女孩同住,那时候倒是自然得多,偶尔一起做个饭吃吃,还凑成一桌打过牌。那两人先后走了,他和一苇就落了单;落单也就罢了,居然落成了一对,虽然目前只是一对房客。“大浪淘沙,最后留下的是两个珠子!”王路这样想着,一苇嗤笑道:“还两个珠子!我看是猪!你就是猪!”想象中的一苇娇嗔可爱,令人心动。一苇有个男朋友,在外地,来本市看过她,如胶似漆的样子,看得王路讪讪的,觉得自己十分多余。如果手头宽裕,他宁可去开房住。不过此人已经许久不来了,一些迹象也显示他们之间出了问题。首先听到的是他们在电话里争执,往往是先喁喁细语,然后声音就大起来;最近几次几乎是一上来就吵。有时她房里传出的争执会持续很久,那一定是在视频里吵,对着吵。王路心里有些窃喜,又代她着急:你可以去啊,当面说清楚嘛!她果然就去了,两天后回来,一脸晦气,板着个脸。那个男人从此再没有来过,连电话似乎都没有了——王路只能确定自己在家的时候没有。他和一苇毕竟只有晚上才在一个房子里。
那个男人王路见过的,实事求是地说,他比自己至少外形要强——王路不会丢弃有一说一的理工精神而违背事实。他早已学会严谨精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那个男人胜过一筹。那人持男版文艺范儿,头发半长不长,耳钉也有一个,说话做事看上去有点“甩”。现在不管是他甩了一苇,还是一苇甩了他,总之他们的缘分看来是尽了,王路的机缘也出现了。
明确的迹象已经出现。以前的一苇用客气做一堵墙,她走到哪里周围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画过圈,你进不去,她也不出来。就在最近,情况变化了。那天她在自己房间看电影,那音效透露,是个鬼片。她把声音调大,大概是觉得太吓人了,又调小,这下更吓人。王路发现,她把门悄悄打开了。门厅的瓷砖闪烁着明灭的光线。她怕了,需要一点阳气。这时她如若邀请他进去,陪她看,他一定会欣然而入,可惜她没有。他从门厅到厕所再进自己房间,好几个来回她依然没有理会。王路常看一些精短的小文章,心灵鸡汤那一类的,有篇文章曾提醒说:怀春的男女要注意对方释放的信息,譬如女方邀请或不反对两人去看鬼片,基本就是个有所允许的表示,允许男方在女方害怕时有所动作。可他除了看见她抱着肩缩在椅子上,信息并不明确。王路不敢造次,只能对她表示声援。所谓“声援”是真正的声援,就是打开自己房间的电脑,也放一个片子。但具体放什么,也不能乱来。她看着鬼片正怕哩,你也放一个,搞个鬼片双声道?这不是成心搞得屋子里群魔乱舞鬼气森森嘛。爱情片也不行,虽说可以顺便表示点什么,但考虑到她正失恋,这时候的任何爱情故事基本等于挖苦,至少是讽刺。最后王路点开了一部武打片,很烂的片子。结果是一苇的鬼片顺利看完的时候,他的武打还剩20分11秒。一苇走到他的房间门口,看着他,大幅度地点着脑袋,说:“你成心的吧,你!”王路也点头,因为他确实是成心的,他立即把片子关掉,以证明要不是为了一苇他确实不会去放它。一苇接着道:“你这叫成心捣乱。你这边打得乱七八糟,我还看个鬼哦!”王路刚要说你看的就是鬼,一苇自己扑哧笑了:“知道你的好心了,啊。”这显然是个善意的道谢,王路觉得云开日出,春暖花开。
那天一苇没被吓着,王路今天回来却没有这个好运了。他安装的那个体贴装置,就是那个小灯熄掉后,他打开吸顶灯,心想她怎么不在呢?她房间的灯从楼下看是亮着的,从她房门下边看也亮着,正想着她一定在房间里做什么,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正想着,动静就来了。这动静竟然是从身后传来的,厕所那里。他转过身,面前赫然是个人,顶灯下,脸上一片惨白!他后退一步,直瞪瞪地看着,那是毫无血色的白,死白,两个眼睛黑洞洞的,忽闪忽闪。王路腿都软了。
王路被吓得不轻。事后他回顾与一苇的经历,主要就是两个场面,其中一个当然是后面将要发生的一段,还有就是这一幕。其实那天是有预兆的,他从进门那一刻就闻到了一股香气,幽幽的,似有若无,却直接钻到你脑子里。那是一苇点的香,熏香,熏的沉香,据说是印尼的,加里曼丹。沉香很贵,是她前男友留下的,那小子以前跟王路吹嘘过他手上的沉香手串。他家做沉香生意,这两年沉香价格暴涨,他决定回老家帮着打点生意:这大概是他离开本市的理由,当然也是他们分手的直接原因。他们在电话里吵,声音飘入王路耳朵,但王路不能出言求证。一苇没有把香扔掉,但也难得熏。其实失恋的人不该唤回以前的氛围,但一苇偶尔又把这味道弄起来,他也无权阻止。转念一想,香是损耗品,那香线一点一点短下去,即使换一根续上,终究也会燃尽。一念至此,王路现在有时竟等着一苇燃香了,他不能否认他是盼着她那里的沉香早点烧完,但沉香的味道确实迷人也是事实。不知道她是兴致来了,或者在一些对她有特殊意义的时候才会熏香,反正今天王路一开门那味道就幽然而来。他没看见一苇,但这味道说明她应该在房间。一转身,却被吓得魂飞魄散,香气和魂魄齐飞。他看出来了,这是一苇,她最漂亮的是眼睛。一苇满面惊诧,她吓着人了她倒错愕地站在那里。她后退一步,突然捂住自己的脸,连说对不起。她说她敷了面膜是不该出来的。王路惊魂初定,有气无力地说:“你,你这个太吓人了。你把它撕掉。我现在看着还是觉得怪怪的。”一苇听话地撕了,左一片,右一片,她有点舍不得。迟疑着说:“你没见过女人搞这些吗?”王路说:“你不该从后面出来。”一苇不说话。王路说:“你在厕所为什么不开灯?”一苇说:“我又不是在厕所贴的面膜。不要开灯,你管得好宽。”王路说:“你人不在房间干嘛要关着门嘛!”一苇笑了:“你管得好紧!”王路这时已经松弛了,忍不住笑起来:“你到底是说宽还是紧啊?我不懂。”
一苇也笑了:“什么紧啊宽的,话赶话逼的。喏,撕掉了,这下没事了吧?”在撕掉的面膜的反衬下,她笑靥如花。她走进自己房间,门并不关上。 “以后我保证,敷面膜一定提前预告。”她坐在椅子上朝外面说,“我一点也不讨厌你。你挺好的。”
这话友好,而且温情。意味着他们还可以一起住下去,甚至预示着这是一个转折点。王路觉得饿。他还没有吃晚饭,本该觉得饿,但饿感比正常的要凶猛许多,于是他问:“你吃了吗?我要去吃点东西了。要不要我带点回来?”一苇说:“我也没有吃。”她在房间里说,“你看方便吧。”
约莫半小时后,客厅里拖来的一张小方桌上摆满了饭菜。有荤有素,热气腾腾,都用饭盒装着。一瓶红酒竖在桌上,两个杯子是各自的水杯。王路到了楼下的小饭馆,临时决定炒好菜带回去一起吃。区别是显然的,自己吃了带一份,那是照顾,而现在这样是超越,更像一家子的样子。一苇故意把眼睛瞪大了看看他,看看菜,不再做额外的表示,坦然坐下。两个人都饿了,碰一下杯,然后,开吃。
因为不知道一苇的口味,他有意识地叫师傅蔬菜淡一点,鱼肉不妨口味重些,这样也有个挑拣,不至于全然不合口味。一苇果然挑嘴,她鱼肉吃得很香,蔬菜只夹几筷子。这是个重口味的姑娘,据说口味重的姑娘行事比较果敢,神经也比较大条。当然他只是听说,听书上说,一苇平时的言行并没有予以印证。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坐在一个桌前吃饭,在一套房子里吃晚饭。一苇几杯酒下去,脸色酡红了,她头发绾在脑后,手臂从紫色毛衣里露出小半截,皓腕如玉。她抬起尖尖的下巴,筷子停在中途,问:“说,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王路红着的脸还是感到一热,说:“是你说看我方便的。饭馆就在楼下,有什么不方便?”“不对,饭馆不是今天才开张的。”一苇吃吃笑道,“是我今天吓着你了,你趁机请饭?”王路低着头,不看她眼睛,说:“应该是我问你啊,我应该问你,为什么今天允许我和你一起吃饭了。”一苇说:“我说过了,因为你被我吓着了。”自己嘻嘻笑起来。
王路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们这是在兜圈子,但他们现在不是兜圈子的阶段。兜圈子是情侣的游戏,他们现在应该往前走。他很想问她男朋友——不不,前男友的事,但不太敢。她是个喜欢吃肉的姑娘,食肉动物,有脾气的。不想她自己提起了这个话题。她端起杯子和他碰一下,微微一笑,问:“想知道我跟他怎么好上的吗?”王路点头,却又问:“谁?”他不是装傻,还真有点犯迷糊,酒还罢了,她点的那个加里曼丹,也像是有后劲一样,越发浓重了。沉香本是醒脑的,但和酒叠加,效果大异。
一苇接着说下去:“他本来也在我们公司,平时也表示过,我不讨厌,但也没有接受。后来到过年了,家里催得紧,那意思是我不带个人回去就索性别回去,我没办法,就让他冒充我男朋友。后来——”她看着王路询问的眼神,“后来,我爸妈倒很喜欢他,还给他包了个不大不小的红包。他不肯还我了,点着钱笑嘻嘻的,坚决不还。这违反了我们的合同,但他说这个是他应得的。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王路瞪大了眼睛,说:“你们合同写的什么?”一苇说:“哪有什么合同。就是嘴说说的,君子约定。我付了他一千元的冒充费,可他红包就是不还。我被他耍了。”王路说:“倒也不能这么说。”一苇说:“你还为他辩护!我本来以为能长久的,不想他有个机会换了工作,后来,你知道的,我们就散了。”她斜眼看着自己房间的方向,“我啊,本想等今年过年我就可以到他家去,也把那红包挣回来,嘿嘿,失算了。”她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他不对的。他一千块钱应该退给你。”王路左右手比画着,正色说,“他是你男朋友,他就可以拿红包;他不是,只可以拿冒充费。两笔钱,只能得其一。”“对啊!你怎么不早说?”一苇不讲理地瞪着他,目光顿时又柔和了,“他是个小人,不说他了。我现在喜欢君子。”
这话让王路心里咯噔一下,脑子有点轰。一时无话。两个房间的门都开着,两盏灯一南一北照过来,照在桌子上。酒已在杯中,王路端起杯子,对着桌上一苇的杯子碰一下,一仰头喝干了。一苇笑道:“最后一杯酒,我还想说句什么呢!”笑着也喝掉了。王路的脑子像用久了的眼,有点糊。他闭上眼睛使劲转着眼球,思忖着一苇刚才的话:她说那人是小人,她现在喜欢君子。那么君子是谁?是自己吗?她似乎没说自己是君子,或许她的意思只是她喜欢君子那一类的……正胡思乱想着,一苇已经给他碗里拨了饭,自己也匀了一点。两人沉默着正要吃饭,门咚咚响了两下,有人敲门。一苇看看王路。门又响了几下:“是我。”
“我”原来是房主老张,大号张文瑜,一苇在租房合同上见过这颇有功底的三个字。张文瑜五十多岁,是个艺术家——至少他给房客们自我介绍时是这么说的。他如此自我介绍也不全是为了炫耀,而是他的打扮需要解释。他留着长发,蓄着胡子,戴个耳钉,手上还戴着菩提手串,这样的装束如果不释疑可能会影响房客的租房意愿。他一进门就嗅着鼻子说:“好香!好香!”他晃着脑袋找一找丝缕的香气道,“你们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呵呵。我能闻出是星洲系的香,清凉,带点奶香,具体产地,我就不那么内行了。”王路看一眼一苇说:“她喜欢。”一苇说:“你这房子通风不好,改改味儿。”“通风不好更有家庭气氛嘛!”张文瑜的逻辑有点奇怪,但一转就转到房租上来了,“房租也公道嘛。”
每月月底,他都要上门收租。本可以让房客们把钱打到卡上,但他坚持自己上门收,借此了解生活。他房子有好几套,父母所留再加上自己购置,他于是不再上班,专心在家里写作。他主攻“心灵鸡汤”,数量惊人,拥趸众多,收入也可观。上月他来时王路一个人在家,他一时兴起就揭秘了一下自己的创作。他确实极为精深,已把心灵鸡汤分成了心灵公鸡汤、心灵母鸡汤和加药的药膳鸡汤,分别针对不同性别、年龄和特定的心理状况。滋阴、壮阳或者猛药,各有妙用。王路听得目瞪口呆,钦佩不已,因此今天见面,直接称他为作家了。“作家啊,你的房租还算公道,就是不能再涨了。”他快步回房拿了钱,把两人的房租一起付了。张文瑜略显诧异,因为以前他过来,即使两个人都在,他们也是各付各的。他笑吟吟地接过去,看看桌上的两只空酒杯,说:“两只空酒杯,一对妙龄人。哈哈——不打搅了,告退。”脑后的马尾巴一摇,转身走了。走时不忘记把门轻轻拉上。
屋里两人都有些尴尬。至少王路尴尬。王路嗫嚅道:“这家伙,你看他说的,空酒杯,妙龄人。”他这是试探。一苇道:“随他说!”不再说话,若有所思。她浅浅地吃了两口饭,放下饭碗,看着王路吃。王路不敢正眼看她,因为她这姿态太迷人,太令人想入非非了。问:“你不吃了吗?”一苇摇头,说:“再吃就胖了。胖子没人要的。”她手在肚子上轻轻一拂道,“你说我胖吗?”王路道:“不胖,正好。”一苇笑道:“狡猾!”格格一笑,站起身回房间去了。
其实不是狡猾。一苇是略有一点点偏胖,但太瘦只是穿衣服好看,脱去衣服还是一苇这样好。他觉得自己是全面地喜欢她。他默默吃完,把桌上的碗筷收拾到厨房去。“要不要我帮你?”一苇在里面道,“今天辛苦你啦。”倒似乎平时都是她洗碗的,只是今天例外。王路挺享受这个语气。他把刚当过酒杯的水杯洗干净,拿到一苇房间门口,一苇从里面出来,接过去了。
他很好奇她房间的样子。他还从来没有进去过。一苇接过杯子转身进去了,虽然没有关上门,但也没有邀请他。他很失望。正要走开,她却在里面喊:“你来。没事的,你过来啊。”
这是他第一次进来。典型的单身女的布置,特别的是这里香味更浓,一盏小香炉摆在写字台上,他带起的风吹弯了香线,很快又复原了,笔直地升上去。一苇坐在电脑前,随意点击着各式衣物,不像要买什么,只是随意看看。她头没有回,突然说:“我前天在这里看见过一个很恶心的东西。”她的QQ开着,左下角的图标在闪,她不理。声音也被她关掉了。她用手点着屏幕说:“就是在这里。”王路发懵,心开始狂跳。她这什么意思?那种“恶心”的东西王路当然看过的,而且经常看。“我看到两人在干那个事。还是现场直播!”王路张口结舌。“而且我还认识那个男的。”一苇转过了脸,脸上微笑着,上牙齿却紧紧压着下嘴唇,很怪异的表情。王路瞪大眼睛,眉头紧锁,一副受惊了的样子。他几乎已经猜到了实情,但他以为是一苇装了软件偷窥的,但他不好出言谴责。“是他主动给我看的!他这是故意恶心我让我走远!这混蛋!”一苇的脸突然扭曲了,眼泪流下来,没等王路做出反应,她已经抽一张纸擦干了。王路说:“你应该把它录下来。”“我气糊涂了,他关掉我才想起这招。”一苇恨恨地站起身说,“要是录成了,我就放到网上去!”她双手一比画,“让他红遍全球!”王路插话说:“这可不行,这犯法的。不过可以留着。”“干嘛?留着给你看啊?美死你喔!”一苇沮丧地说,“我刚才心生一计,想让你坐我旁边,打开视频也气他一下子,可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她把椅子往桌子边推推,这是个结束话题的动作。王路往后退了两步,转身出房,慢慢走向对面自己的房间。沉香味被他带出来,似乎连衣服上都沾惹上了。他等一苇走过房间门口,说:“其实我没说给我看。”一苇端着个盆,笑道:“你没说可你肯定想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你呀,有心无胆,嘿嘿。”她进了厕所,也就是浴室。片刻后她在浴室喊道:“哎,学理工的男人,你帮我一下,我弄不出热水。”
工艺原理及缺点:在以往的沉箱安装施工中,沉箱进水口阀门采用传统阀门,即通过潜水员进行拧紧或拧松转盘进行水口的关闭或打开。此进水阀门缺点在于需要潜水员进入沉箱逐个打开或关闭阀门,工序繁琐,效率低,耗时较长,且容易沉箱进水量不一致导致沉箱四角高程不一致,给安装沉箱时调平带来一定困难。
浴室已经很陈旧了。瓷砖后补过几块,设备也旧。很破的燃气热水器,一直凑合着。王路把水弄好,伸手试试洒下的热水,心里想:一会儿她就要在这里洗澡。脸一红,立即就出来了。
水声哗哗地响着,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暧昧的气氛。王路无事可做,准确地说他是什么也做不了。其实两人合租,洗澡总会有个先后的,就是说,他以前也面临过这样的局面,但他今天却格外地胡思乱想,简直心乱如麻。他先是待在房间里,耳朵竖着,期待着同时也害怕着一苇突然喊他,因为忘记洗发水沐浴液之类的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他没有机会害怕,水声伴随着人叮叮当当轻微的活动声,一切都很正常。
他忍不住走到了客厅。一苇的房间门虚掩着,他轻轻一推进去了。他蹑手蹑脚,小心得像个贼,香炉上的香线只轻微摇晃一下又变得笔直。香比刚才倒长了截,显然一苇洗澡前换过。他此后所有的动作都极轻微,但他的心被惊到了。他看见一苇的电脑上,屏保的画面竟然是一个男人,加着黑框,是遗像。他几乎立即就认出,就是那个男人,一苇的前男友。他死了?或者他这是在被诅咒?也许,这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说,一苇用这种方式把以前的情感彻底埋葬。
气氛就此诡异起来。王路悄然退出房间。他朦胧感到,今天应该是个转折点。要么,他和一苇就这么维持下去,前景不明;要么,他进一步,让这套房子里的所有的门,各自的房间的门,浴室的门,全都形同虚设。
但浴室的门关得很严实。他连走近的勇气都没有,更不用说去敲门,或者破门而入。他是个君子。心有企求的君子尤为守理。浴室里的灯光沿着门下的缝透出来,水声依旧。时间不短了,女人做什么都磨叽。王路的心渐渐静了下来,他期待着一苇洗好出来,似乎只是期待着湿发披肩身材窈窕的一苇从他面前走过。他目前能预见的只是这些。
无聊中他坐到自己的电脑前,随意浏览一些小文章。有个故事说,一对青年男女,因为与团队失落,只能单独住在山野里一个猎人遗弃的木屋里。两人虽然早有朦胧情愫,但他们各住一间。木屋很破,虽然有房门,但早已糟朽不堪。夜里,男人心中天人交战,几乎一夜未眠。他多次起身,欲伸出手推开房门,但终于遏制欲念,守住底线。第二天,女人和他都走出了房间。女人手里捏着一根长长的头发丝,说:这根头发昨天夜里拴在我的门栓上,这是我的房间所有的防卫——最小的力量就能使它崩断,可它依然完整。女人说:你在我心里的形象也是完整的,是完美的。故事的结局是:女人抱住了男人。他们走到了一起。
王路问:自己会不会崩断那根头发呢?结论是:他不知道。事实上,今晚的事件将用事实验证他的行为。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一苇洗澡的时间似乎长了点。但水声哗哗的,而且,似乎有动静。是一苇在动作。加里曼丹的味道太浓了,浓得有分量,再加上依稀飘来的沐浴液的香味,王路迷糊了。一苇洗澡的味道更迷人,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浴室的门里那仿佛可见的身体。他悄悄靠近,贴近浴室门口,并随时做好跑开的准备。他的身体已经起反应了,立即又窘得不行。如果他现在去敲门,一苇肯定要骂他流氓——是的,真是流氓哩——如果他索性流氓一回,直接破门而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当然,也许一苇会欲迎还拒,半推半就,就此鸳梦得谐。真说不准呢。
夜晚的事件正如迎面而来的列车,不可阻挡地逼近,也将不可阻挡地远去。王路突然觉得紧张,耳边的水声稳定地响着,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这很不对。当然一苇也许是在泡澡也说不定。他喊了一声,没人应;鼓起勇气敲敲门,还是没有回应。“一苇,你好了没有?我,我要用厕所!”他觉得自己的谎言很得体,立即又觉得这句话很弱智——一苇似乎喜欢开玩笑的,你说上厕所她没准就更不理你。他脑子一热,想冲进去,但是,里面什么情况他虽无法确认,可有一点却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此刻的一苇一定赤身裸体。他又喊了一声,犹豫着要不要采取措施。他冲进去,一苇一定“呀”一声惊起,抓个东西捂住自己,然后,然后他将被判定为乘人之危的小人。十有八九连朋友也做不成了。要么他离开这房子,要么她走。
王路开始慌了。他口发干,心脏狂跳。不祥的感觉攫住了他。他咚咚地敲门,边敲边喊。他几乎就要呼救了。但“救命”这两字非同小可,那一定会引来无数的围观者,万一没什么大事他将成为笑柄。他迟疑一下,飞快地冲下楼,他首先想到的是去喊那个房主张文瑜,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房子是他的,出了事他也一定会合力遮盖,不要闹大。王路冲下楼道,却突然想起他并不知道房主具体住在另一个单元的几层。只能给他打电话,可王路这才发现出来得匆忙,他手机没有带。他大喘粗气飞奔回去,找到手机拨通了房主。
张文瑜很快赶到。他一进门就深深地吸了几下鼻子,回手关上门。“多长时间了?”不等回答,直奔浴室。他一把推开王路,用力试了试门,后退两步,抬腿就是一脚。门轰一声开了,水汽弥漫,他命令道:“去把所有窗户打开!不许动开关,不许打手机!”王路颤声问:“要不要报警?”“我报了!”
王路刚打开两个窗户,那边喊他:“快过来!快把她抱起来!”
浴帘已被撩开,一苇扭曲着躺在浴缸里。花洒还在洒水,噼里啪啦打在她的裸体上。王路手足无措。张文瑜一步跨上浴缸,哗地推开窗户,厉声道:“你还不动手?!”王路明白他的误会,他一定以为自己是一苇的男朋友。王路刚想辩解,张文瑜一把搡开他,哗地拽下了浴帘,浴帘上的金属环落在瓷砖上叮当作响,四处乱蹦。他把浴帘往一苇身上一包,一把抱了起来。
王路瞪大了眼睛。他倒不是不愿意抱,只是面对一具赤裸的肉体,他一时无法下手。可怜他只在梦里和一苇有过肌肤之亲,如果来过真的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是她洗澡前他们有限地亲热过一下子,他也不会如此。这一切在张文瑜面前都不是个事。他给别人炖心灵鸡汤,自己并没有成为药渣。他有意志力执行力,拥有多套房产后毅然辞掉鸡肋工作专卖鸡汤就是一个佐证,只不过他在文章里不以此为例而已。他把一苇抱到门口,警车已经鸣叫着赶到了,这无疑证明了他的临危不乱。女人的头和双腿软软地垂着,脸色青紫,他已料到了事情的结局,神仙也无力回天。他已在思谋,这房子马上就要空出来了,怎么才能顺利地把这死过人的房子租出去。更迫切的任务是:他必须从这件事中全身而退。
他抱着一苇下楼,恨恨地瞪了王路一眼。
来了一个警察一个辅警,这是标配。辅警开着警车去医院,警察带王路回到了现场。张文瑜跟进了门,随手把围观的人关在外面。警察一进门就使劲吸溜着鼻子,他大概没有闻过沉香,他只知道煤气。但煤气的味道显然被掩盖了。他板着脸,尖锐地盯着王路。王路急切地说:“是她点的。她点的香!”王路连忙带他去看香炉。香早熄了,立着的线香塌成了一小堆白灰。很难想象如此厚重的香味是从这里散发的。张文瑜长长短短地吸着鼻子,眉头紧皱。警察想:这里一定有问题!他走到浴室,四下张望一下,目光落在燃气热水器上。“你们搞什么玩意儿?”他嘴里问着,脑子里驻留的是刚才一瞥间发现的电脑上的遗像,还有那个香炉。他心里想:这太像一个诡异的仪式了。
发稿编辑/冉利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