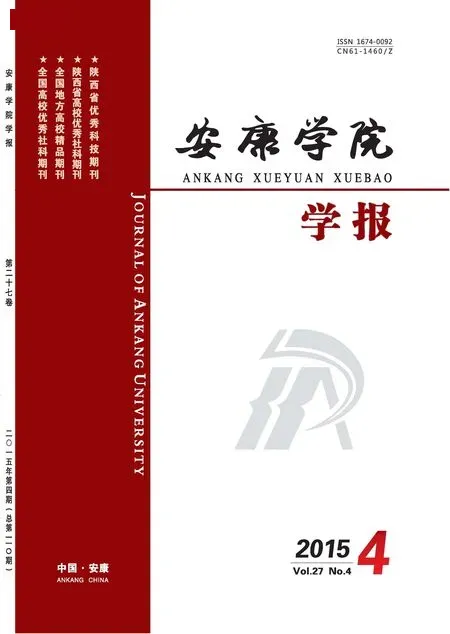《左传》中的梦境预言探析
季桂增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左传》一书凡十八万余言,记述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共计244年的历史,其内容广博,无所不包,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读过《左传》的人都会对其中的预言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梦境预言尤有特点,描写十分精彩,在全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左传》梦境预言的基本作用
据张高评先生统计,《左传》中的梦境预言约有26条[1],历代很多人对此现象提出批评,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中的观点:“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也。”[2]这一观点其实只看到了它的表象,而没有认识到这些梦境预言在行文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将这些梦境预言从《左传》文本中抽去,那么《左传》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就会大打折扣。这些梦境预言或对国家的存亡做出预测,或对战争的成败做出预测,或对氏族的兴衰做出预测,或对个人的祸福做出预测,成为《左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下面即对梦境预言的基本作用作逐一分析。
(一)预测国家存亡与战争成败
春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纵观此段历史,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周天子名存实亡,国与国之间纷争不断,大国彼此进行争霸战争,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而很多小的诸侯国,或为大国吞并,或国运不振;在一国之内也出现了各种内乱和政权更迭现象,如在鲁国,以季氏为代表三桓势力掌握国家政权;在齐国,则是由陈氏代姜氏成为国君;原先强盛的晋国,则被韩、赵、魏三家一分为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国家的兴衰可谓朝夕变化,以往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左传》的梦境预言中有很多就是预测国家存亡的,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所记述的赵简子之梦: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赢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3]1513
这个梦境预言是对楚国国运进行了预测。而到了鲁定公四年的时候,吴师败楚师于柏牛,攻入楚国的都城郢,几乎面临亡国的命运,后因申包胥哭于秦廷,求得援军,才得以保住楚国。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史墨占梦所言,所列种种皆一一应验。而其间相差五年之久,可见其预言的准确性。从上文可以看出,春秋时代各国都设有专门占梦的官员,足见其对于梦境预言的重视以及占梦现象的普遍。对于如何占梦,古代有一些详尽的步骤,并且有专门的占梦之吏,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据统计,《左传》中各国之间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约为480次,可见当时战争是何等的频繁。战争成败关系国家存亡,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直以来,《左传》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都备受推崇。而梦境预言将对战争成败的预测与战争进程的描述很好地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发生的城濮之战:
……楚师背酅而舍,晋候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美美,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河山,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候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3]451
城濮之战的前夕,晋楚两军的最高统帅都做了一个与战事相关的梦。晋文公梦到“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乃胜;楚子玉梦见河神“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而没有采纳河神的建议,遂败。看似这个梦非常的奇异,细细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晋军之所以能胜,是因为他们的战略战术采用得当,战前联合齐、秦两个大国,并用计谋将楚的盟友曹、卫两国离间,此其一;战中采取先攻弱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加之子犯退避三舍,胥臣蒙马以虎皮,这些谋略运用得当,此其二。而楚国的子玉恰恰相反,战前不听辅臣的劝谏,一意孤行,不得人心,战中毫无战略战术可言。所以晋楚的城濮之战,未战而胜负已分,这里的梦境预言既是神异的又是合情合理的,梦境预言很好地起到了预叙的作用,与战争的描写巧妙地融为一体。
在这两个梦境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梦的过程之中,加入了很多人为的主观因素。晋文公梦到“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他自己感觉到似乎是不详之兆,我们从这个梦中也丝毫找不到吉祥的端倪。而子犯却说:“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在这里,子犯对梦的解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仅仅是在解梦,而且是在圆梦,让梦的内容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时做什么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不论什么样的梦都为他的观点服务。子犯对于这个梦的解释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心理战术,让晋文公反忧为喜,增强了他对此次战役的必胜的信心。楚国的大臣荣季在战败之后,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时,说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其失败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梦的昭示,而是失去民心,所以致败。从本质上说,这是人的意志与鬼神意志的较量,从中可以看出,虽然还有很多的鬼神因素,但是“人为”的重要性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预测氏族兴衰与个人祸福
在梦境预言中,氏族兴衰与个人的祸福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周朝社会之中,宗族体系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这实际体现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各级政权。春秋时期,社会结构与体制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氏族内部斗争此起彼伏,宗族体系遭到创击,梦境预言对此有很好的反映。如《左传·昭公七年》中卫国立嫡一事: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锄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絷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故孔成子立灵公[3]1297。
这个梦的解梦过程是同《周易》的卜筮结合在一起的,很有代表性。而这个梦的实质是争夺卫国国君之位,孔成子立元为灵公,从梦境和卜筮两个方面为其提供合理的依据,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所特有的争嫡手段,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汉高祖斩白蛇乃赤帝之子,或梦日入怀,都为他们自己的身份增加了一份神秘色彩。这个梦境的预言成为增加政治资本的一种手段,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算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智慧,为立灵公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左传·宣公三年》的“燕姞梦兰”,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不是凭借这个梦的话,公子兰的夺嫡之争是不会那么顺利地取得胜利的。
对于个人祸福的预测,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左传·宣公十五年》的“魏颗梦结草”,它体现的是一种善恶报应的思想,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而有些梦境预言对个人祸福、生死的预测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神秘性。我们且看《左传·成公十年》中晋候梦大厉的例子: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3]849。
这个梦境预言很有意思。接连有三梦,梦后有梦。先梦大厉报仇,奠定晋候之死的源起,接着梦见疾为二竖子的对话,最后以小臣之梦结尾,三梦皆应验,且非常神奇。本段文字将梦境预言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语言生动有趣,可谓一波三折,笔笔涉趣,堪称奇文。
这则预言充满了神秘色彩,晋候有意来挑衅鬼神的意志,“召桑田巫,示而杀之”,而一切都已经有所安排,不能逃脱,“不食新矣”的预言最终还是得以实现,梦境预言主宰着未来的祸福,丝毫不差。再如《左传·成公十七年》中的声伯梦魂魄被取,最终应验而死等等。人的祸福自有上天安排,这体现出梦境预言神秘性的特征。
二、《左传》梦境预言的文化基础
《左传》中这么多的梦境预言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当时的文化背景为基础产生的。春秋时代,一方面受到巫筮遗风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百家争鸣,各种学说放射出思想的光辉,人文理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梦境预言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神秘性与和合理性相互交融。而这个特征正是巫筮遗风与人文理性相互交融的结果。
(一)巫筮遗风的承续
梦境预言很多都带有神秘性,如上文提到的《左传·成公十年》中的晋候之死,《左传·宣公三年》中的因兰而生,刈兰而卒,《左传·成公十七年》中的声伯之死等等,这些预言都表明鬼神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周族原来即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虽以礼乐为主,但承袭商的文化也有很多,和商文化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据《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4]可以看出商文化是一种巫祝文化,对鬼神非常的迷信,他们运用各种巫筮占卜来预测未来,包括国家的政事都由卜筮决定。运用巫史结合的手段,使民众相信鬼神支配着生活中的一切。这种传统在春秋时期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也有一些承续。而梦的神秘性正好同这种思维相契合。这种梦境预言与原始宗教与传统的巫祝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当时巫祝文化的一种直接体现。在当时原始宗教还未完全消退和“万物有灵”的时代大背景下,梦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操纵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左传》作为当时重要的文史典籍,自然而然地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二)人文理性的发展
春秋时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继续发展周朝以来的人文理性的精神,如郑子产提出的“天道远,人道迩”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始宗教和鬼神观念对人的束缚。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儒、墨、法、道为代表的百家学说,思想和文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和进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这时的“天”具有极强的人文色彩,鬼神的作用依然存在,但遭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削弱。所以出现了大量具有合理性特征的梦境预言。这些预言的内容都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披上了梦境的外衣而已。此外,天文历法和医学都有一定的发展,使人们对于生死有了清晰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一时期人们对天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虽然“神”的权威还依然存在,但是“人”的地位有大幅度的上升。《左传·成公五年》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反梦预言,即梦境之事与现实之事相违背,没有应验,“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而婴进行了祭祀,却“明日而亡”,在这里,梦中之神的灵验性消失了,这些反梦预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于“鬼神”怀疑,这正是人文理性发展的结果。再如《左传·昭公四年》中叔孙穆子梦天压己,也是一个反梦。对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不可信,不足恃;微晤鬼神聪明正直而一,冯依在德,已敬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知心知斯意矣。”[5]更多地体现出了因果、善恶的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巫筮遗风中的“鬼神”与人文理性中的“人为”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构成了《左传》梦境预言的神秘性与合理性相互并存的特征。
三、《左传》梦境预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左传》是先秦典籍中对梦境记述最多的一部,其梦境预言对后世的文学叙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文学作品与之有关。刘文英在《梦与中国文化》中论及“就文学艺术本身来说,梦象,梦境和梦体验,是一项用之不竭、永远写不完的题材”[6]。在《诗经·齐风·鸡鸣》中有“虫飞薨薨,甘与子梦”[7]265,《小雅·斯干》中有“乃寝乃兴,乃占我梦”[7]546,出现了关于梦的内容,但只是只言片语。而到了《左传》中则是大篇幅地记述梦境预言。《左传》的梦境预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甲骨占梦卜辞的干瘪乏味,到《诗经》的零星表述,至《左传》之时,无论是梦境的完整性,还是数量的丰富性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司马迁的《史记》承袭了这种手法,其中的梦也多以预测功能出现在文本之中,最得《左传》的精髓。其后的文学作品中以梦来预测未来,取得成就最高的莫过于《红楼梦》了。作为代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曹雪芹将梦境预言运用得炉火纯青。如“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普幻仙姑曲演红楼梦”,在这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梦境中,昭示了《红楼梦》中主要女性人物形象的命运结局,可以说将梦境预言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虽不是以梦来进行预测,但其虚幻的叙事色彩却是与《左传》一脉相承的:庄子梦中成为一只翩翩之蝶,物我合一,逍遥自由;李白也有大量关于梦的诗,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气势磅礴,奇特无比;白居易的《长恨歌》,梦里相会,情动至今;苏轼的一句“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情至深处,泪洒满襟;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以《牡丹亭》为最,缠绵千古;关汉卿的《窦娥冤》托梦鸣冤;《三国演义》中虽只是偶然涉及,如第七十八回曹操梦三马同槽,前后呼应,增添趣味;再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狐妖鬼梦,看似荒唐,最显真切。
从上面我们可以大体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中与“梦”这一母题相关的篇章都大放异彩。而这一传统正是由《左传》所奠定的,其记梦的现实主义动机与其外在形式上的浪漫主义色彩相得益彰,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梦境预言在《左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到预测国家存亡与战争成败,小到预测氏族兴衰与个人祸福,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趣味性,也起到了预叙的作用;梦境预言不是凭空而来或是作者主观想象的,而是有着深厚文化基础的。巫祝遗风与人文理性相互碰撞,使其梦境预言具有神秘性与合理性相交融的特征。作为《左传》文本中重要的叙事手段,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历代关于“梦”这一母题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多有佳作,都离不开《左传》的开源启流之功。
[1]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3.
[2]马宗霍.《论衡》校读笺识[M].北京:中华书局,2010:369.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79.
[5]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09.
[6]刘文英.梦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46.
[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