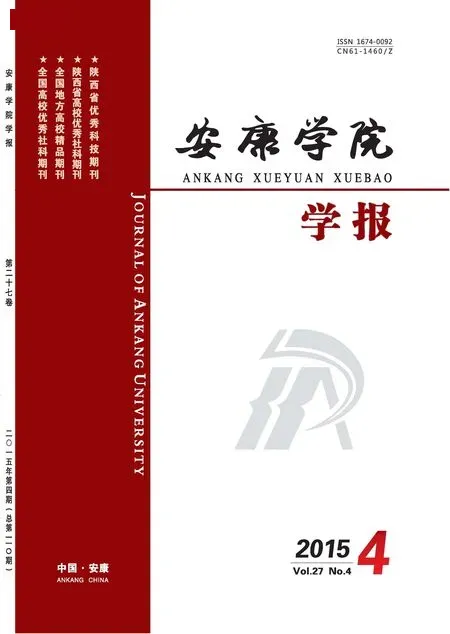曹文轩文学批评思想梳议
古超强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高州 525200)
曹文轩,以其成长小说,如《根鸟》《细米》《感动》《野风车》《红瓦黑瓦》《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①此八部作品,最初于2005年4月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成版,取总名《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近年,曹文轩又先后完成了《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作品。等在文坛上放异彩,又以其文学研究,如《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等在学界逞才情。其创作与批评的并重互动,既使文学批评理论具有指导现实的意味,又使文学创作获得一种理论的指引。曹文轩在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文学批评必须坚持审美特质;文学批评理论必须中国化;文学批评理论必须和创作互动互用。
一、文学必须坚持审美特质
在曹文轩那里,世界被他一分为三:上帝创造的物质世界是“第一世界”;人类面对物质世界创造出的哲学艺术等是“第二世界”;在哲学、艺术中创造出来的“乌有之乡”则被称为第三世界。曹文轩认为,文艺和哲学等能满足人的精神欲望,就是因为它们存在着一个“乌有之乡”。哲学创造的世界由抽象的观念、判断、推理等组成,文学世界则由直观形象的画面形成。因为文艺不仅仅是认识,还是审美的,在这个基础上,曹文轩阐述了文艺的审美化理想:存在是文学的根本出发点,所以美感第一,思想第二;审美功能的核心表现是悲悯情怀;文学的表现要提升至形而上的大美境界。
(一)强调美感,兼顾思想
曹文轩认为,存在是文艺之根本,所以作家对存在的不同理解,就导致了对文艺的不同理解。存在的事物美丑共存,所以从存在中来的文艺就不能只追求认识功能而抛弃审美功能,而应美感与思想并重,进而关注美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美感比思想更富有道德感染力量,所以文艺如果注重美感的抒写,就能使人变得良善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感具有永恒性,思想则具有相对性,因此“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1]。这个思想体现在写作上,文学就应追求美和美感,且追求美的写作永恒化。
因为美感具有比思想巨大的力量,所以曹文轩批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小说,逐渐放弃了小说的审美价值,而一味委身于认识价值”[2],思想上追求深刻冷峻,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深度”,表现上却“自然地带来了对粗鄙物象的癖好”[2]。曹文轩认为:没有先验的判断证明终极关怀是文艺的根本使命;也没有任何证明古典非终极关怀,仅就其价值而言,就一定要比现代的终极关怀来得低下;“当人类需要最起码的实际关怀时,如此终极而玄虚的关怀又有什么意义呢?”[3]现代形态的文艺贬低和反对古典形态的文艺,认为古典形态的小说唯美是求,而美就是不深刻的,不深刻相对于深刻而言,是不成熟低级的形态,所以古典形态的小说是小说的低级初级形态。实质上是以现代形态的文艺的认识价值来衡量古典形态的文艺的审美价值,无疑这是很荒谬的。曹文轩认为,文学的关怀是审美的现实关怀,所以文艺不能够也不应该“在被强制性地承担着过量的思想重压”[2],失去优雅气度和飞翔高度。
在具体的文学表现形态上,曹文轩认为划分现代和古典,只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文艺是表达存在的,所以文艺的古典与现代是由存在的状况所决定的[4],但究竟该使用哪种表现方式,则应该根据表达存在的需要来选择。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就能够用古典形态的文艺形式表达出现代性的主题[5]。这说明两种形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共存并用的[6]444。在具体的创作,比如《草房子》《红瓦》等一系列成长小说中,曹文轩比较喜欢运用童年视角,因为这个视角能够传达出他的纯净美感。成人眼中的世界肮脏污秽,而在儿童眼中,却是充满“纯净”“诗性”“幻想”“忧郁”的色彩[7]。曹文轩不仅仅从理论上阐述美感,而且在写作中实践了理论。
(二)悲悯情怀是文学审美功能的核心表现
曹文轩认为悲悯情怀(或者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核心属性[8]215。所谓悲悯情怀,是指“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8]219。悲悯精神是古典小说的核心精神,到了现代,悲悯情怀却逐渐被废弃掉[8]215。尤其是在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现代化生存境况下,悲悯精神显得不合时宜,但又是人生之必需。为什么古典悲悯情怀会与现代社会相融?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系列异化危机,而古典的悲悯精神正是拯救现代人情感饥渴危机之良方。
在这个意义上,曹文轩批评当下的文艺过分追求认识功能,牺牲了审美功能。以批评现代派的“零度写作”①“零度写作”既指作者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写作,又指作者塑造情感冷漠价值缺失的人物形象,实质是极端强调小说的认识功能。为例,曹文轩认为“只是一种姿态”,支撑“零度写作”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说明[8]213-214,因而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派文艺家以“零度”作为幌子,在叙述中诗化、美化暴力和丑恶,蕴涵着叙述者“暗藏不住的快意与美学情趣”,回避人际间的正常情感,使得“零度写作”既虚伪又可恶[8]215。其实,曹文轩批评极端化的追求认识价值的倾向,就是因为这已经伤及美感的实现和悲悯情怀的感化力量。
曹文轩重新提出并注重“悲悯精神”,试图重新发挥文艺的审美作用,慰藉丰盈现代化生存中人的心灵和情感。古典的精神宝藏在现代化语境中被重新挖掘出来,高高扬起,试图使现代文艺既能认识存在的危机和悲剧,又能通过文艺的审美超脱异化生存,形而上地解脱人的精神危机,达到审美的自由境界。这是一个试图以审美性精神世界拯救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理想。
(三)形而上大美境界的文学表现
形而上问题,是“企图探找揭示世界万物之本原,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世界”[9]。形而上问题超越一切时代、国家、阶级、民族而具有永恒性。文艺的本质是审美性直觉和情感,而哲学的本质是理性,两者本是对立的,可是,理性以蕴藏于形象的形式存在于文艺中,这样,理性与情感对立的双方以文学的形象为中介,达到对立之统一。所以文学是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结合体。从这个基点出发,曹文轩以形而上精神解构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建构中国当代具有古典意味的形而上的文学表现理论。
中国的思维传统是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崇尚直觉与和谐,缺乏悲剧精神,易堕入实用主义和非逻辑非理性的陷阱[10]263-305。中国文艺长期浸润于实用主义的思维传统,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实用化、庸俗化。比如“文革”时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被看作是与起重机、汽车等一样具有实际用途的工具,把“现实主义”庸俗化。另外,把平等的存在变成有优劣之分的生活[8]49,作家面对存在的平等态度,有了高下之分、优劣之别。这种观念体现在写作上,就是只能关注“有价值”的和“主流”的生活,其他的统统被抛弃。如果“有价值”和“主流”代表政治、国家、民族之时,文学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那么它就被剥夺了审美性,其认识功能被突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文学的美感只能是缘木求鱼。
曹文轩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批判的或者说是建设性的人文精神”[6]439。所以现实没有时间之区分,无轻重厚薄之分,都可以成为文学的题材[6]438。因此,存在的时间性在形而上文学写作里失去了界限,形而上的界限就是文学的界限;而形而上的界限是无限的,所以文学也是无限的。这为文学的无限想象和虚构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
曹文轩认为,文艺的形而上精神主要表现为“忧郁和忧郁情调”“游戏精神”“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贵族化趣味”“共同人性基础上的文学经典价值追求”。
忧郁是指形而下的生活痛苦升华为形而上的精神痛苦,超越存在的悲惨而内化为主体的一种品格,所以,忧郁具有指向自我的悲剧色彩,是一种自我表现超越的精神境界。忧郁所体现出来的美,是一种形而上悲剧体认的人格美,外化为文学作品就是忧郁情调,哀伤而不绝望,体认悲剧而不失进取心。曹文轩的作品如《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等,就弥漫着忧郁情调。
如果说忧郁情调是指向内在的形而上精神,那么游戏精神就是指向外在的形而上精神,是主体对存在悲剧性体验的外在投射。游戏不但体现为文学作品中的嬉笑、幽默和智慧[8]44,而且文艺中的“游戏”体现的恰是人的存在的悲剧性[8]48。存在着的人是能动主体,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可是人在上帝之前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必然地服从上帝,人的所有努力就带有徒劳无功的味道,所以人的存在就必然地蕴涵着悲剧性。人类可以选择不存在,不存在就可以不被上帝调笑,可是如果不存在,人就失去了生存的立足点,所以人必须存在;而存在就必须被上帝调笑,所以人的存在是一种尴尬。行为的悲剧性与存在的尴尬状态,就是存在本身,只要人存在,就必然受到上帝的制约。上帝,已不仅仅是指不可测的命运,也指现代化的秩序和机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精神”表面是嬉笑好玩,实质是指一种对人类悲剧性和尴尬存在的反讽和超越。文艺作为“游戏精神”的载体,获得了与人类同在的永恒魅力和不断攀升的可能性。人虽然不能在现实中超越存在,但可以在文艺中超越存在、超越一切,并产生审美的快意[8]174。“游戏精神”的具体实现就是通过创作和阅读体验到对存在的审美性超越和认识性超越[8]176。
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贵族化趣味,是文化教养培养出来的形而上精神的体现。曹文轩批评中国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倾向,反对新写实派关注庸常的写作理念,因为这与国家民族的文学的前进方向矛盾。曹文轩把“贵族”与“平民”提升至美学范畴,认为在适合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要求文学表现宏大和巨大的事物,内在精神具有悲剧性,表达的结果达到崇高的境界。因此,贵族趣味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美的体现[11]。
与所有古典主义者一样,曹文轩认为文学应表现形而上的共同人性,追求文学永恒性的经典价值[12]。所以他要求文学应该写形而上性质的事物,如微妙的人性、古典的美感、游戏精神等等,也即写作了形而上境界的作品是经典的作品。判断文学作品的经典与否的方法是“放水法”或者叫“可译法”[4],作品不因为语境的转换如翻译等而依然保持其价值的就是经得起“放水”的,就是写作了永恒主题的作品,就是经典,所以这样的作品是值得写作和推崇的。
二、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必须中国化
曹文轩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必须中国化,即所有文艺理论的阐释和译介,都以中国为本位、为中国所用。中国的存在,决定中国的文艺创作及研究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和接受,因为中国人没有办法摆脱中国这个先天存在。所以,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为本位,去接受西方的思想,就必须先破除对西方思想的迷信,这样才可以立足中国本位上合理地吸收西方思想的营养。
曹文轩批驳了文艺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因为我们在一切问题上,“将西方作为论述一切问题的前提,将西方作为衡量一切价值体系的尺度,将西方作为我们进行一切话语活动的中轴”,从而“背对自己的历史而眺望西方”[8]23。原因是中国经过文革这个思想贫困期,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引介西方理论资源,从而养成一种依赖西方理论资源、唯西方资源马首是瞻的思维惯性。
曹文轩认为,引进西方理论资源的历史功绩与“五四”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的历史功绩可以相提并论[6]448。我们饥不择食地接纳西方理论资源,后果之一是西方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6]457,中国本土传统的理论资源完全“失语”。后果之二在于对西方思想不加批判地使用。在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把产生于西方文学实践和文化氛围的西方理论,未经批判地运用到与西方文学实践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危险的“玩火的游戏”[6]463。其三,对西方理论的膜拜崇拜,实质是“西方中心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渗透,所以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也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西方学术批评的规范。中国现行的学术规范是借鉴西方的“逻辑的、体系的、理性的批评模式”的产物[6]457。过于理性化、技术化、格式化的文学批评模式,会破坏“一个人的文学感悟能力”[6]462。所以,曹文轩极为推崇日本“讲究感悟与材料考证”的理性与悟性结合的文学批评[6]463,试图倡导“中国古典的学术表达方式加上西方的学术规范与推理方式这样一种结合”的批评模式[5]。其《小说门》,将艺术灵性和知识经验深深地融入严密的思辨理性和逻辑推理之中,达到了两者的结合与交融。这是其在具体学术写作中追求审美与认识两者融通的结果。
如果说质疑反驳西方中心论是“破”的话,那么曹文轩提出以本土化为核心的文艺理论观点就是“立”。以小说为例,曹文轩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小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小说史”[8]23。比如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的《源氏物语》是在完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中国的《红楼梦》则完全是中国化的作品,西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在文化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写作出来的[8]19-20,所以小说是自发的形式,与文化交流无关[8]18。曹文轩认为西方小说形式统治地位的形成,缘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一切做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解释”[8]23。中国小说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未能深入挖掘古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并加以理论阐释,不能将古代的小说理论有效地换为现代小说写作和研究的资源,是“解释意识和结实能力的双重缺乏”[8]23。比如曹文轩所举例的西方小说形式“小说套小说”,而中国古代小说中早已存在“纹章工艺”,指“在一个纹章中再放置一个完全相同但却是被缩小的纹章的技艺”[8]21。两者地位不同,正是西方的理论阐释充分而被定为首创的结果,其实中国古代早已存在类似的技法,只是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而被淹没在历史的地平线之下。
中国古典诗化写作资源是个巨大的资源库,曹文轩认为知识是一个历史绵延系统[5],过去中蕴涵着现在,现在延续着将来,所以古典资源的现代转化是有可能的。曹文轩认为要依靠西方的理性演绎归纳思维工具,来梳理总结中国本土的诗化零碎感悟式的写作资源,要靠西方的文艺理论对比,凸显中国文艺理论的特色,这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西方化,而且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两者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5]。
曹文轩认为,“造物主所设置的这个世界,绝对是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6]450,所以,理论资源贫困的中国有着自己的后路。既然世界有无限解释的可能性,西方人能够创造无限多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面对存在进行创造。曹文轩认为哲学有两种,一种是“如何认识已有的世界”,一种是“如何构建未有的世界”[10]137,所以,文学批评理论可分为两种,一种描写“已有”的,一种诱发“未有”的[10]138,前者是负责解释文学文本等现实存在的理论,后者则是引导引发创作和批评的理论。诱发“未有”的理论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10]137,不是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的。因为人不仅有理性的需要,还有情感的需要,所以这种空泛空灵的理论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曹文轩认为可以把虚构想象引入文学理论中,创作出具有精神审美作用和引导创作至新方向的理论。
总而言之,曹文轩认为,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小说理论、文学批评理论,既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的理论资源,也要对传统的古典诗化写作资源进行西方化的转换,更加要面对存在进行虚构想象,才可以创造出与世界对话的文学批评理论。
三、倡导审美化批评,理论和创作互动互用
曹文轩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大文化批评”的天下。所谓“大文化批评”,是指从文学作品中阐释、剖析其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其注意力在“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学文本与文化环境的外部联系上”[8]4。曹文轩认为其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的大气的思维形式”和“思想高度”[8]2,是在文化废墟之上必然出现的批评形式。但是,“大文化批评”一统天下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的豪富感”[8]3和批评的霸道、专横、无赖之气,并随之引起文坛秩序的混乱——作品良莠不分。因为判定作品高下的不是文学的审美原则,而是认识原则,即作品的文化意蕴和哲理性。另外,“大文化批评”往往不是从文学文本阅读出发进行批评,不是用理论去解剖作品,而是用作品去论证理论。“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知识拿来解释文学的文本”[13]13,并且“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那些思想做阐释和重复说明”[6]447,这样必然导致“文学判断力的瘫痪”[8]4、“纯粹的文学批评的自惭形秽”[8]9和对作品文化价值的“过度阐释”[8]6。实际上,“大文化批评”是过分追求形而上深刻哲理的文学思潮在文学批评中的一种极端化表现,是西方理论资源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曹文轩将“大文化批评”定位为“从文化角度介入的文学批评”[8]9,将其归属于“文学批评”这个大范畴之下,为纯文学的创作和纯文学批评的回归和重新兴起,奠定了合理性、合法性基础。
曹文轩提出向“纯文学批评”的回归,其实质是呼唤文学的美感超越与关怀现实之精神,也即文学的美感等审美性(文学性)的强调和回归。所以,曹文轩认为文学批评应该首先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不让文学文本成为理论的注解。曹文轩自己的文学研究,就是让文学批评回返到文学自身中来,比如所研究当代文学所列举的文学现象有“悲剧精神”“回归故事”“堕入庸常”“神秘主义”“流浪意识”“感觉崇尚”等[13]1-2,都是从文学这个基本点出发的。所有的现象都首先是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哲学现象;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在文学、美学的基础上来解读的,实质是将游离于文学以外的文学研究扭转回归到文学内部来,重新提倡文学的审美性和审美的文学性。这是对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清醒而有力的反驳,也是对文学审美性的坚持。
在坚持文学审美性的回归的同时,曹文轩认为,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创作应该实现互动互用[8]297-323。从创作实践中总结提升的经验感悟,必须经过理论化系统化构建成审美化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后应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进行修正和“证伪”,从而真正实现文学创作与理论的相互作用。这样,理论就不是空谈空泛的理论,而是具有针对性灵活性的理论,而且理论与文学现象结合起来,得到了及时的更新,理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超前的指引作用。创作的经验也得到发扬和提升,这样有助于创作和批评的深入深化。曹文轩强调文学理论的实用性,这与许多大而无当的理论著作,流连和满足于空洞的理论述说和逻辑推理,自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类为研究而研究的著作,不但对研究没有帮助,而且破坏人的认识和审美能力,凝固人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大堆的学术垃圾。曹文轩自己在具体的学术著作中,试图一改这些流弊,他在《小说门》中大量地述说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阅读经验,由于从实际中来,所以就有足够的实用性。比如系统化地探讨时间空间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功能等;专章论述风景在小说中的类型、地位意义和相关的写作经验;提出中国小说有自发的形式等。这都是开拓性质的论述。曹文轩不仅对经验进行了提升,而且有所创新和发展。如他将风景写作的作用分为七种:“引入与过度”“调节节奏”“营造氛围”“烘托与反衬”“静呈奥义”“盈育美感”“风格与气派的生成”[8]13-16。如果没有深刻的体会和经验,决计写不出这样细致入微、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些经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具有巨大的指引作用;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也是窥透小说艺术奥秘的一把钥匙。从理论上的提倡到实际上的学术写作,曹文轩都坚持文学理论具有创作论的色彩,在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界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曹文轩的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之下,自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意味。曹文轩的文学批评理论追求,以文学的审美性价值为核心,据此来决定文学形式的古典与现代并用,决定文学批评的资源必须有助于文学审美性情感的表现,并且规定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形而上的永恒价值,其实就是审美性价值的重新确立。不可否认的是,曹文轩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局限性还是存在的。首先,曹文轩认为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是对立统一体,但这只是理论设想。因为曹文轩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比如《草房子》《细米》等中,都倾向于温馨温暖的美感,相应地削减了思想的深刻力量。这样显出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文学的审美批评的地位颇尴尬,因为就文学批评的学科要求来说,其科学性是追求,而文学审美批评因为有美感与直觉的存在,显得科学性不够,所以不值得信任。如果就批评文本而言,感悟直觉式的批评能够切合文学本身,所以文学审美批评因为理性的概念和判断,显得与文学本身格格不入,不能像文学那样讨人喜欢。人们更加愿意接受文学文本本身,而不愿意接受所谓审美性的批评。曹文轩提出在西方的框架里改造中国审美直觉式的设想,其实是取了个中庸做法。再次,曹文轩追求文学的经典价值,认为文学的价值能够超越时空、阶级、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从而可以不朽;这与其文学批评理论追求民族化、中国化是一个矛盾,没有认识到文学必然是把时代性与超越时代性结合在一起的对立统一体。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强烈地渲染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色彩,可是它仍然超越历史的时空界限而为我们所欢迎、所理解,是增值的杰作。
即使如此,曹文轩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学性研究、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创作与批评互动的思想,对中国文学创造和批评的良性发展,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走向与世界对话的开端。
[1]曹文轩,胡少卿.美的力量>思想的力量[N].科学时报,2003-03-17.
[2]曹文轩.论短篇小说的现代形态[J].北京文学,1998(4):103-108.
[3]曹文轩.《红瓦》代后记[M]//曹文轩.曹文轩文集:红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585.
[4]曹文轩.曹文轩:文学为人生最高尚的嗜好[N].北京青年报,2003-01-09.
[5]曹文轩,徐妍.与一位古典风格的现代主义者对话——曹文轩专访[EB/OL].[2015-03-21].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2793.
[6]曹文轩.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7]曹文轩.美比思想更震撼[N].中国文化报,2003-03-13.
[8]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9]曹文轩.沉沦与飞飏——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1):18-25.
[10]曹文轩.第二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11]曹文轩.文学不能转向审丑[N].光明日报,2003-01-24.
[12]曹文轩.关于根鸟[M]//曹文轩.曹文轩文集:根鸟 山羊不吃天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
[13]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