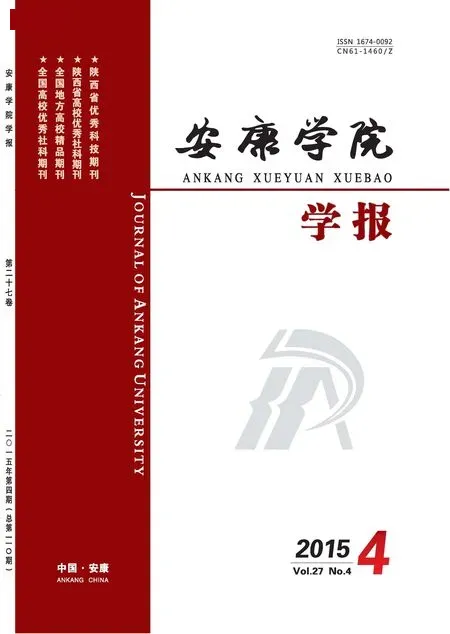盛可以短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和女性意识
刘丁榕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大都将女性禁锢在自己的房间当中,自恋式地抚摸小小的自我,轻声细语地诉说自己的闺房秘事,将女性低矮的天空捆绑成了一个树木横截面般大小的椭圆。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原本应该对父权制度下女性身份的缺席进行斗争与反抗,对男权话语霸权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大厦进行颠覆与消解,可是肆无忌惮、不顾尊严的女性身体描述反倒掉进了男性窥视者的隐秘欲望当中,于无形中迎合了商业化潮流下消费者的心理,成为反抗男权的初衷的极大反讽。盛可以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对于女性个体经验的表达上,她对男性身体的大胆暴露,对男权文化下男性话语地位的解构,真实呈现出男女两性在现实社会的性别地位与性别景观。透过她笔下的这些男性形象,可以清晰触摸到盛可以女性意识的脉搏,而她对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个体经验的书写与现实境遇的叙述则寄托着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语写作的局限,转向了理性批判的现实道路。如老诗人郑敏所言:“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也就是说,女性写作如果只是自说自话,幽闭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去关注更为宽广的人生和世界,是不可能对男权社会构成任何威胁的,只有站在人类的角度体现出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女性写作才能显示出自己独有的价值,才具有现实存在的意义,才能在充分保持女性尊严的同时展现出女性美与艺术美的极致。
本文结合盛可以童年生活经历与个人底层生活经验,探寻她笔下男性懦弱胆小、虚伪自私的原因,认为在对这些病态男的叙述中蕴含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以男性视角进行自嘲自讽,一边塑造男性形象一边解构男性形象,这一方面是在颠覆、瓦解男权社会和谐公正的表象,达到一种宣泄的快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借男性之口自嘲自讽是为缓解自身的焦虑,舒缓压抑的心灵,可毕竟受伤害的还是女性,那些胆小懦弱、虚伪自私、缺乏爱的能力的男性带给她们的心灵创伤是绝不可能只靠反抗与报复就能抚平的。而男性又借助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耀武扬威,将女性审判在道德秩序的断头台上,这样女性就陷入了痛苦的挣扎当中,而男性却拿着免死金牌毫发无伤地继续耀武扬威在历史的舞台。这不禁使作者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盛可以站在人类的角度对男女两性的整体命运进行思索与叩问,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2]。在男女两性关系的对照中,关注女性的个体经验与艰难的生存境遇,寄托了作者的人文理想,这是一种建立在人道主义之上的女性意识表达,更具有理性意义与现实批判价值。
一、作家女性意识的萌芽与发展
盛可以的短篇小说风格变化多端,手法灵活多样,但与其长篇小说一样都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在短篇小说《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中,她塑造了众多男性形象,他们都是缺乏爱的能力的弱者,或是同性恋,或是胆小懦弱的伪君子,或是灵肉分离的享乐主义者,这与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童年时期脾气暴躁、重男轻女的父亲带给盛可以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家里四兄妹,盛可以最小,常常因为顶撞父亲而遭到毒打,甚至是同学母亲看不下去了将她藏在自己的家中。她和姐姐的成长都是忧郁的,为了逃离家庭,盛可以的姐姐仓促嫁人,而盛可以则选择了独立。盛可以一度仇恨父亲多年,并易父姓为母姓,多年后仍会梦见自己被父亲追砍。成年之后,盛可以开始到处一个人打拼,她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多年徘徊在城市底层,看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凭借自己对文字的敏感与深入准确的感受力与洞察力,她辞去工作开始了写作。所以,盛可以笔下那些懦弱胆小、自私虚伪的缺乏爱的能力的男性的出现其实是她内心世界的外化。她出于一种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憎恶,女性意识清醒而且强烈。而她笔下的女性虽然性格冷硬、言语刻薄,但是心地善良,男性则胆小怕事、虚伪自私,以“性”为诱饵,打着爱情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
《人面狮身》中的骆驼虽然外表光鲜亮丽,是个鉴宝节目的主持人,但实际却是作为一个性能力缺失的同性恋者虚伪地活着,在同性与异性的感情之中摇摆不定,与异性的交往只不过是对于其同性恋身份的遮蔽,实际上欺骗了爱情也负担不起爱情的责任。《德懋堂》里的马墙是一个高富帅,他在与“我”这个美术学院的英语老师陷入爱河之后,却只留下200万的存款失踪了,留下了怀有三胞胎的“我”,而“我”竟然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多次跳楼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马墙在自己的妻子与“我”之间徘徊不定,一面给“我”希望以及承诺,一面又难以兑现,本质上说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手术》里的李喊为寻身体的愉悦和唐晓南在一起,当李喊发现她左乳异常需要做手术时,他秘密推荐自己的父亲做主刀医生。手术过程中,唐晓楠经历了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与痛苦。当唐晓南听到李喊父亲说李喊两个月后将要出国时,她的婚姻梦破碎了,他们的地下恋像她的肿瘤一样被切割掉了。李喊根本就没有想过结婚,面对自己的父亲显得很懦弱,手术结束后就离开了。他面对感情没有任何责任感,只是一个灵肉分离的享乐主义者。《白草地》里的武仲冬是个公司的小销售员,当他自以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自己的老婆蓝图与情人玛雅之间的时候,却没想到被自己的老婆和情人联合起来实施了报复,导致性能力衰退。武仲冬泛滥的爱其实体现了他爱的能力的问题,泛滥的爱不是爱,欺骗的爱更是可耻的爱,他没有能力负担起自己承诺的爱。
灰暗的童年生活记忆带给盛可以心灵的创伤,她女性意识逐渐萌芽,成年之后多年底层生活经验使她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写作素材。女性意识的成长壮大,激发了她创作的欲望,她几乎是粗暴地扑向了男权社会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一种原始的粗犷凌厉撕开了男性同胞黑暗灵魂下伪善的面具。男性的温柔与承诺是一剂毒药,他们总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做出各种保障与承诺,在以“性”为诱饵取得女性信任后却很难担负起婚姻的重任,或者选择逃离或者再次陷入新的引诱之中。
二、以男性视角对男权意识的批判
在盛可以的部分短篇小说中,她采用了男性叙述者的视角进行叙述,通过对男性的自我解构与自我嘲讽来达到表现女性意识与女性立场的目的。作家在进行一场温柔的阴谋布局,在貌似为男性代言的男性叙述者的声音中哼着不和谐的调子,把男性隐秘而丑陋的欲望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极度生活化的真实、透明的描写呈现了人性深处黑暗的灵魂。盛可以采用这种叙述方式不是想要获得“雌雄同体”、两性和谐的目的,她直指的是男权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它的瓦解与颠覆丝毫不留情面。盛可以说:“我喜欢用男士的语气来叙事。使我的作品中充满理智、机智,透彻的作品与个人气质结合起来更重要。”[3]盛可以的这部分作品是最能体现其女性意识的作品,她的男性叙述者的声音很刺耳、很凌厉,男性同胞们似乎不能装作听不见,当他们丑陋不堪的心理被强行送上刑场时,他们是那么焦躁与羞愧。
短篇小说《快感》采用的就是男性叙述视角,男主人公是一个无业游民,整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靠着女友在娱乐场所坐台、跑场来养活自己,可是他却拿着女友的血汗钱在外面找女人,还恶言恶语地猜忌误解女友,自私自利、无羞耻地通过损害别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对于男性毫无廉耻的自尊发出一声冷笑。《白草地》中以“我”的面目出现的是一名男性武仲冬,他是外企的一名小职员,尽管工作辛苦,可是业绩却并不突出,他靠巴结多丽这样的采购员获得一点儿销售业绩,与妻子蓝图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婚姻关系,而且还与玛雅玩儿起了婚外情,玛雅不但没有向武仲冬索要任何回报反倒给了武仲冬不少好处。正当武仲冬得意地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以为自己对女人了如指掌、得心应手之时,没想到却被自己的妻子和情人联合报复得丧失了性能力,妻子在每天一杯的盐水里下了药——雌性激素,原来他的婚外情从来都没有逃出妻子的视线,情人所赠的礼物也是自己妻子在网络上拍卖的礼物。盛可以借武仲冬之口讽刺了男性沦为女性猎物的过程,可怕的不是妻子与情人的斗争,而是女人与女人联合起来形成的坚固城墙。在这部小说中,正是通过男性叙述者之口在极大程度上呈现了男性由猎人沦为猎物的荒诞,其中对男权的批判立场异常鲜明,演绎了酣畅淋漓的“弑夫”行为。《惟愿中年丧妻》中的老齐道出了中年男人们共同的暗黑心理:“升官发财死老婆”,人到中年,青春不再,爱情不再,婚姻摇摇欲坠,婚外情似乎成了有权有势的中年男人必不可少的一项,没有婚外情会被别人笑话。一方面男人们团结作案,滴水不漏享受着婚外情的刺激,另一方面却又不想离婚,因为离婚成本太高。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大半生的财富,十几年的习惯与经历也不可能说断就断。于是老齐自骂:“人,真他妈的荒唐透顶!”最后,只能在男同胞中间含混不清地说:“愿……中年……丧……那个……喝!”[4]
盛可以的男性叙述角度叙事充满了自嘲、荒诞与讽刺,女性作家以男性口吻对男性进行自我嘲讽、自我暴露、自我解构本身就是对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同时,作家采用男性视角也可以避免女性立场过于鲜明所带来的偏见,这样站在天平中央发出来的女性声音即便是带有女权主义的色彩也更带有客观性。她在呼吁男同胞们进行自省,提醒他们女性是弱者,但当她们集体联合起来反抗报复男性的时候,她们的天空就不再是低矮的,她们的话语犹如“坚硬的稀粥”!
三、女性作家之困惑的女性意识
盛可以以男性视角叙述的方式反抗、报复男权社会,一方面是在颠覆、瓦解男权社会,达到一种宣泄的快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借男性之口自嘲自讽是为了缓解自身的焦虑、舒缓压抑的心灵,可毕竟受伤害的还是女性,那些胆小懦弱、虚伪自私、缺乏爱的能力的男性带给她们的心灵创伤是绝对不可能只靠反抗与报复就能抚平的。而男性又借助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耀武扬威,将女性审判在道德秩序的断头台上,这样女性就陷入了痛苦的挣扎当中,而男性却拿着免死金牌毫发无伤地继续耀武扬威在历史的舞台。在盛可以眼中,男性的世界是一个“道德世界”;她的小说世界,则是一个“情感世界”,这两个世界对撞,没有产生新的物质,而是化为虚无[5]。当“情感世界”遇到“道德世界”,相当于以卵击石,终会通向破碎与毁灭。盛可以在与庞大的男权社会相对抗的过程中,在灵肉分离的苦苦挣扎与探索里被道德这块口香糖黏住,她困惑了、失望了,她发展起来的女性意识因受到攻击而毁坏。但困惑与迷茫之后,盛可以的这份女性意识并没有消失,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里获得了建立在人道主义意义之上的女性意识的更为丰富的含义。“情感世界”的意义永远要大于“道德世界”,“情感世界”的终极关怀目标永远是人类,是需要社会关注的弱者,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个体经验的复杂性与现实境遇的艰难感触及了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理想。
当女性以决绝的姿态宣告自己只需要肉体的“取暖”而非灵魂的“注视”时,她们发现灵肉分离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将欲望从一个有情有欲的人身上剥离开来是多么天真。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永远无法被简化,女性在灵肉探索的过程中通常会放弃原先的肉体“取暖”理想而最终选择灵魂的长久陪伴,而她们矛盾困惑自我斗争的结果却通向了悲观与虚无。所以,盛可以笔下的女子为情伤得很专注。盛可以对这些矛盾困惑、自我挣扎的女性投去深切的一瞥,那一瞥里满是辛酸泪。《德懋堂》里的“我”与马墙虽然都是婚外情,但是“我”在一次次地等待马墙兑现承诺;面对只留下200万离开自己的马墙,“我”守着一个三胞胎孤独承受,曾经两次为马墙选择跳楼,最后一次跳楼将自己彻底毁灭了。作家在批判无力承担爱的责任的马墙的同时,对“我”因马墙跳楼的个体遭遇与艰难的生活处境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表现了女性面对社会遭遇深深地无力与失望,带有作家深刻的人文关怀。《手术》里的唐晓南本来只是因为李喊长得帅和他交往,而后来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灵肉分离,只为肉体的欢愉而不顾灵魂的深陷,爱了就是爱了,无法无力抽身而去。李喊虽然不能否认自己不爱唐晓南,但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可以放弃一切,包括唐晓南。唐晓南手术时冰冷而痛苦,盛可以叙述得冷静而残酷,漫长的手术过程带给女性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层面的巨大伤害。盛可以暴露着女性的痛苦,实际上也关怀着女性的痛苦,关注着女性的生命体验。《取暖运动》里的刘夜和巫小倩本来就是因为“取暖运动”在一起的,当寒冷的冬天结束了,两人都不再需要“取暖运动”,刘夜最后对巫小倩说:“你活得很自私,你只爱你自己。你走了也好,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不可否认的是,巫小倩在这段感情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物质与精神,而两人的感情终以刘夜的抱怨宣告结束。盛可以在对女性内心的纠结与困惑中对女性的生存境遇进行叩问,叙述女性的身体经验与情感体验,在暴露男性弱点、直指男权文化的同时,关注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的个体经验与现实生活境遇。
盛可以说:“我的写作,源自于困惑。因为困惑,我必须分析,要分析,必须解剖。我只有通过叙述来解剖心灵,解剖肉体,解剖生活。”[6]盛可以挥舞着一把手术刀,精细完美地进行切割,手起刀落,呈现出清晰的血丝纹理,以逼近残酷的写真,呈现了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的个体经验与艰难的生存境遇,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更重要的是,其女性意识中寄托着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理想,从而更具有理性价值。
[1]郑敏.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J].诗探索,1995(3):60-61.
[2]洪治纲.文坛关注·盛可以专辑——主持人语[J].当代文坛,2007(2):29.
[3]盛可以.盛可以小说创作对谈录[J].河池学院学报,2005(6):72-75.
[4]盛可以.留一个房间给你用[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209.
[5]王琦.情欲化社会的话语分裂——盛可以小说论[J].南方文坛,2014(4):99-103.
[6]李力平.逼近·还原·突围——解读盛可以《Turnon》及其他[J].名作欣赏,2004(5):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