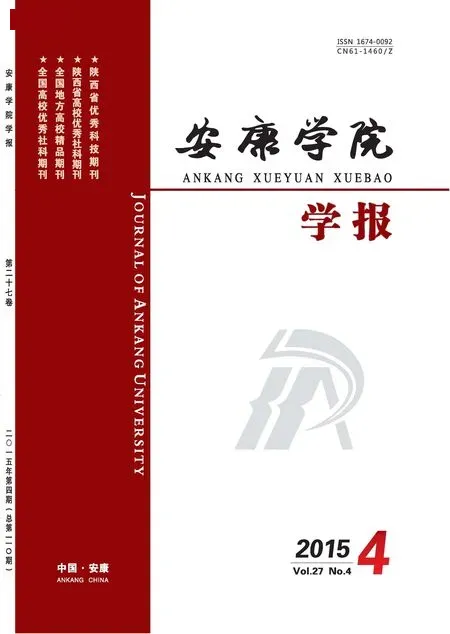论《不真空论》的“真”与“不真”
张彤磊
(湖南文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湖南 常德 415000)
僧肇深解大乘空宗中观学要旨,被鸠摩罗什誉为“秦人解空第一”,同时又精察玄学理辞,故能会通玄佛,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不真空论》是僧肇最为接近罗什中观思想的一篇论文。本文以“真”与“不真”为中心讨论僧肇对中观学派思维方式的理解和运用,同时阐明僧肇受玄学的影响而将中观学彻底否定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肯定式的思维方式。
一、“真”与“不真”的含义
(一)“真实”与“真假”
《不真空论》一文中“真”字共出现37次,根据文义,“真”与“不真”的辩证关系可分为二层:
1.第一层“真”是从缘起事物的现象立义,“真”指真实存在,事物真实存在故有自性;“不真”即缘起之物无自性故非真实存在,本质是“空”,所以不真即空。
事物是否真实存在,即事物是否有自性?《不真空论》反复阐明事物并非真实的存在。若用“有自性”替换“真”,或“无自性”替换“不真”(“非真”),《不真空论》中的如下表述,文意不变:
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1]144。
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如此,则非无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于何而可物[1]145?
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1]144。
“象非真象”“物非真物”“有者非真有”,都在说明事物的存在是非真实的存在。但事物何以非真实存在?
《不真空论》开篇即言:“夫至虚无生者,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有物之宗极者也。”[1]144万物的本性是“至虚”“无生”,是“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非谓绝对的虚空、虚无,而是指事物因缘和合,本质无自性,故“空”(“至虚”“无生”“无”)、“非真”。对缘起之物无自性故“自虚”“非真”,《不真空论》三次重复了这一命题:
是以至人通神心于无穷,穷所不能滞,极耳目于视听,声色所不能制者,岂不以其即万物之自虚,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1]144。
夫圣人之于物也,即万物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通哉[1]145?
是以圣人乘千万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1]146。
“即万物之自虚”立足于缘起论,说明万物生非真生,有非真有,本质是无自性、毕竟空。而且,万物本性之空,非小乘“析色明空”,乃不待分析,当体即空,缘起即性空。所以,汤用彤指出:“此义为通篇主旨,而用之以自别于从来之异执也。”[2]263
2.第二层“真”依“即万物之自虚”立义,从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同时来说明缘起事物。此“真”之义是以缘起事物无自性为命题对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有自性)所作的真假判断。以缘起事物为真实其实是“不真”或说是“假”的“真”(真实之真)、“伪”的“真”(真实之真);以缘起事物为“空”(“至虚”“至无”)才是真正的“真”(真假之真)。换言之,从现象看,缘起事物虽然存在但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不真”;从本质看,缘起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本质是“空”,这才是真正的“真”。此“真”之义也是《不真空论》重点阐述的内容。
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之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1]145-146。
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1]144?
上文立足缘起论,表达的基本含义是,缘起事物虽然存在,但非真实存在,故非有,非有即指非真有而并非否定有;缘起事物无自性本质是空,但现象存在,并非绝对的虚空、真实的虚空,故非无,非无即指非真无而并非否定无。
在《不真空论》中,僧肇明确地表达出不真空的含义:
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形象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1]146。
如果说缘起事物是有,这个有不是真的真实的存在;如果说缘起事物是无,缘起事物已经存在。缘起事物已经存在不能说是无,只是缘起事物的存在是不真实、非实有、无自性、毕竟空而已。不真空的道理也就在于此。
(二)“真假”与“有无”
在鸠摩罗什尚未系统将龙树中观学传入汉地之前,受魏晋玄学本体论思维影响,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中国般若学者还是在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框架下讨论般若空义,以无解空,偏而不即。《不真空论》把有无问题转换为有与真有,无与真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缘起事物无自性本质是空作为判定是否为真的标准,运用双遮双遣的中道思维,对“六家七宗”的代表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
《不真空论》评价本无宗: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即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1]144-145?
僧肇认为,本无宗“非有,有即无”是对的,因为“非有”之非是否定“有”,所有“有”的否定就是“无”,故“非有即无”;但本无宗“非无,无即无”,把“无”的否定也作为“无”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把无作为真正的无,这个无就成为了有,也就是有了自性。僧肇认为正确看待有无关系应该是“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非有”的意思是否定“有”的“真”,即自性之有、本体之有、“真有”;“非无”的意思是否定无的真,即自性之无、实体之无、本体之无、“真无”。所以,僧肇进一步指出本无宗“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即“非有的批判对象是(非)这个有吗?非无是(非)这个无吗?”其实是否定有无的真。可见,僧肇所批判的正是本无宗把有无关系归于“无”而否定了假有、假无,把“无”实体化、本体化的思维方式。
《不真空论》评价心无宗:
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1]144。
僧肇认为,心无宗的理论缺陷是“物虚”,没有认识到万物本质为空,而是把万物作为真实的存在,以心空物。
僧肇评价即色宗: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1]144。
僧肇认为,即色宗虽然论证物质现象不是不真实的存在,但只是看到了色之假有、非真,而没有领悟到物质现象的本质即空,当色即空,当体明空。
显然,在《不真空论》中,僧肇是以“即万物之自虚”为真命题,直接对有无进行判断。“即万物之自虚”也即缘起事物无自性本质是空,与“缘起性空”之义等同。但“缘起性空”这个命题并非形式逻辑包含两项“S是P”结构的命题,而是指依靠般若智慧、不加分析直接体认缘起即性空,当体空、毕竟空。但是,僧肇“真有”与“真无”概念的引入对于破斥“六家七宗”乃至魏晋玄学或以有为真有,或以无为真无的观念,是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因为当有非真有,无非真无时,偏执于有无任何一边自然都失去了理论依托。
二、如何认识“真”与“不真”
“缘起性空”指的是当体明空,而并非执空以真,如果执空以真,则又是对真的偏而不即因而陷入恶趣空。《不真空论》运用中观学派中道思想,以二谛相即来认识“真”与“不真”的关系。
(一)二谛相即
真谛以缘起事物的本质性空为真,俗谛以缘起事物的现象实有为真,是为二谛。真俗二谛构成认识论上的“真”与“不真”的辩证关系。二谛理论非中观学派独有,但中观学派以二谛相即来认识中道实相,也即相对于真俗二谛而言,二谛相即才是真正的真谛,第一真谛。《中论》云:“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3]897依据中观学派中道思想,俗谛虽然只是一种假设的真理,但反映出缘起事物的虚幻假有,从真谛的立场才能看到缘起事物无自性的本质。但真俗二谛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执著于俗谛则为假象所惑,执著于真谛则陷入恶趣空,真谛亦转为俗谛。二谛相即则是既看到缘起事物的现象虚幻不真,同时又看到缘起事物本质无自性,这样才能辨明“真”与“不真”,洞鉴诸法最高真实。《不真空论》中直引经文说明如下:
《中论》云,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也。寻夫不有不无者,岂谓涤除万物,杜塞视听,寂廖虚豁,然后为真谛乎[1]145?
故《放光》云,第一真谛,无成无得;世俗谛故,便有成有得[1]145。
故经云,真谛俗谛,谓有异耶?答曰,无异也。此经直辨真谛以明非有,俗谛以明非无。岂以谛二而二于物哉[1]145?
然则非有非无者,信真谛之谈也[1]145。
僧肇认为,真俗二谛没有差别,岂能说有真俗二谛的观点便有二种真理呢?——“岂以谛二而二于物哉?”真谛从本质认识缘起事物,缘起事物无自性本质是空,缘起事物的存在只是假象,所以“真谛以明非有”;俗谛从现象认识缘起事物,以缘起事物为真实的存在,虽然不见缘起事物的本质是无自性之空,但是肯定了缘起事物的存在(虽然是不真实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俗谛否定了绝对的空,所以“俗谛以明非无”。
二谛相即则同时从本质和现象来认识缘起事物,也是对真、俗二谛在否定中的超越。从本质上看,缘起事物本质无自性是空,所以非有,但缘起事物存在,但缘起事物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故非真有;从现象上看,缘起事物存在所以非无,但是这个无并非绝对的虚空、真实的虚空,什么都没有的无,而是包含有的无,所以非真无。从本质和现象同时认识缘起事物可表述为:有非真有,故非有非真有;无非真无,故非无非真无。也就是说,从现象看,现象之有非真实之有,故现象之有不是真正的有;从本质看,事物的本质不是绝对之无,真实之无,所以不是真正的无;从本质和现象同时来看,事物既是有又是无,既非有又非无,所以非有非非有,非无非非无。
对于魏晋玄学以及深受魏晋玄学本体论思维影响的般若学“六家七宗”而言,有无关系指向的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而魏晋玄学及般若学“六家七宗”对待有无关系上或执有为真有,或执无为真无,造成在对待本体与现象关系上偏执一边。当《不真空论》以有非真有,无非真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观点看待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也即转换为:现象非现象,本体非本体,亦现象亦本体,非现象非本体。僧肇一方面对现象与本体同时否定,表明僧肇是在继承罗什所传中观学拒斥为世界寻求一个本体论意义的基础上来阐述空义的;一方面在否定现象与本体的同时又肯定现象与本体,指出认识诸法实相要从本质与现象两个方面同时考察,最终以般若智慧直观本质即现象、现象即本质,而直觉缘起即性空,当体空,毕竟空。
(二)超言绝象
二谛相即是依般若智慧直观有无,现象与本质,而非语言概念所能表述。《不真空论》说:
故《放光》云,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实。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当名之实,非物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不当实,实不当名。名实无当,万物安在?故《中观》云:物无彼此,而人以此为此,以彼为彼。彼亦以此为彼,以彼为此。此彼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怀必然之志。然则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无。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1]146。
缘起事物无自性本质是空,其形象虚幻只是假名,并无与之对应的实在。譬如幻化人只是概念的存在,并非有真实的幻化人。所以《不真空论》指出,若从事物的概念(名)去认识事物,事物没有和其概念相当的实在;从事物要求概念与之相符合,但概念无法体现事物的功能。没有和事物概念相符合的事物,所以事物不是概念的事物,概念不能体现事物的功用,所以概念不是事物的概念。因此,名不当实,实不当名。既然名实不当,何有所谓万物。所以《中论》指出,事物没有彼此的分别,但是人们以此为此,以彼为彼。同样,人们也可以以此为彼,以彼为此。此和彼不能由一个固定的概念来定义,而惑者执分彼与此。彼和此本来不能说是有,惑者分别彼与此的观念也不能说是无。彼与此既然不存在,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存在的呢?所以,万物不是真实存在的,万物的概念只是假名而已。
名不当实,实不当名,无法用语言概念来认识最高真实。《不真空论》说:
夫以物物于物,则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虽物而非物。物不即名而就实,名不即物而履真。然则真谛独静于名教之外,岂曰文言之能辨哉[1]145?
事物不是因为它有事物的概念,这个概念就符合于它的实在;事物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它加之于事物,这个概念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真谛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述的。在《注维摩诘经·弟子品》中,僧肇说:
夫文字之作,生于惑取,法无可取,则文相自离,虚妄假名,智者不著[4]352。
名言概念皆是主观分别而惑取假象,诸法缘起性空本无所取,所以名言概念和缘起性空事物本不对应。智者明了假象的虚妄性,不会认为名言概念能反映诸法实相。既然名言概念不可能表达诸法实相,所以对诸法实相的理解就不应受名言概念的局限。
三、“真”与“不真”关系立意
《不真空论》立足缘起论,以双遮双遣的方法揭示“真”与“不真”的关系,说明事物因缘起而虚幻假有,本质是无自性、自虚、是空;事物本质虽空,但又因缘起事物假有而非绝对空无,只有二谛相即,真假并观,既看到事物的有又看到事物的无,才能正确认识诸法实相,而要认识诸法实相必须依靠超越语言名相的特殊的般若智慧。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真空论》契合大乘中观学说中道思想。鸠摩罗什所传中观学是以对经验和超验的双重否定来拒斥理性对经验知识及形而上的任何追求而导向以般若智慧体证诸法实相,《不真空论》虽然也认为只有以般若智慧才能体证诸法实相,但更为强调通过特殊的精神修养来提升主体精神境界,使主体在经验世界中体证真俗不二、由俗转真。这一思维转换虽然以诸法本质性空为前提,却暗含了对经验世界的肯定,这也就意味着罗什所传的彻底否定式的思维方式被一定程度地转换为肯定式的思维①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指出:“《不真空论》在于阐述客体自身的‘不真’而‘空’,这同郭象以来,玄学强调在主观认识上的无心而‘顺物’,同汉魏以来般若学的否定一切的倾向,都有不同”(详见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这表明僧肇的思维方式已经和般若学彻底否定的思维方式有了差异。。而这一点,在《不真空论》辨别“真”与“不真”关系的归趣中得到明确的体现。
自非圣明特达,何能契神于有无之间哉!是以至人通神心于无穷,穷所不能滞;极耳目于视听,声色所不能制者,岂不以其即万物之自虚,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1]144。
所谓“神明”“神心”“真心”是指般若智慧,圣人能以般若智慧契合于有无之间,洞察诸法非有非无之相,故能穷尽万有而不为事物变化所累。在《注维摩诘经》中,僧肇也说:
若能空虚其怀,冥心真境,妙存环中,有无一观者,虽复智周万物,未始为有,幽涂无照,未始为无。故能齐天地为一旨,而不乖其实,镜群有以玄通,而物我俱一。物我俱一,故智无照功,不乖其实,故物物自同[4]372。
僧肇所指的般若智慧是以无分别观念将物我、主客之差别彻底泯灭,即所谓“物我同根,是非一气”[1]144,从而朗鉴最高真实,贯通有无、真俗。显然,这与玄学以主观精神来消解主客对立,物我玄同的思路旨趣相似。唐君毅指出:“他(僧肇)将玄学的物我冥然一如,提揭为主体观物之自虚之佛家式智照意趣,但空虚心神,妙鉴物性的鉴照,就形态而论,基本上与玄学言物我相冥,没有异致”[5]。二者虽都主张以主体的精神体验消除主客之别,但玄学是以无心观物有以顺有,实现物我玄同,而僧肇是以虚心观物无以体真,以达心物两冥。僧肇所指的般若智慧是依靠主体特殊的修养才能获得,获得方法和途径是空虚心神,妙鉴万物自虚本性。这样一来,“通过僧肇的阐释,佛家即物自虚的万法皆空原理,跟玄学言主观的玄鉴理趣味,相同为一,使前者沾上浓烈的主观主义色彩”[6]。这种浓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又体现在僧肇对主体和经验世界的肯定,所以对于《不真空论》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辨别“真”与“不真”的归趣最终落实到在现实世界当下社会人生。《不真空论》结束语说:
是以圣人乘千化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故经云:甚奇,世尊!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1]146。
圣人具有般若智慧故能体察诸法实相而不为事物的千变万化而迷惑,洞鉴诸法“自虚”的本性。通过“真”与“不真”关系的论述,僧肇以真俗不二的中道思想把世俗世界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诸法实相并非外在于事物,而就在事物本身中体现,“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任何一事物都显现诸法性空本质,“触事而真”。主体以般若智慧随时当下体证诸法实相,在体悟真谛的理境中,心灵清净纯明与事物混然如一,此即“体之即神”。
[1]石峻,楼宇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G].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
[3]龙树菩萨.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M].鸠摩罗什,译//《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835-906.
[4]僧肇.注维摩诘经·卷3[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5]唐君毅.僧肇三论与玄学[M]//三论典籍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6]唐秀连.僧肇的佛学理解与格义佛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185.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