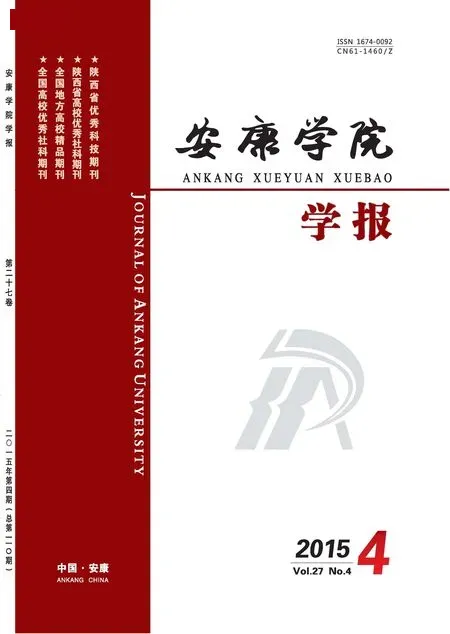论路遥小说乡土叙事的文化内涵
爨玲玲,崔有第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安康 725000)
最近,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数家电视台热播,好评如潮,时隔二十多年又一次再现了当年小说问世并获得茅盾文学奖时的盛况,这足以说明优秀的文艺作品确实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路遥是当代乡土作家的典型代表,他的《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则是“文革”结束后乡土小说的经典之作。乡土叙事是以乡土生活为叙事基础的,不论是作家对乡土生活的回忆,还是对乡土生活的解析与建构,其间往往蕴含着一种深厚而温馨的乡情,这种乡情对于那些具有丰富情感和敏锐洞察力的作家更是意义非凡。路遥作为黄土地孕育的陕北后生,对这片养育了他的黄土高原有着一种深沉的爱恋,一种咏赞不尽的激情,一种深厚的乡土情结。正如他自己所说:“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1]由此可见,他对这块贫瘠、厚重的黄土地爱得如此深沉,而这种对乡土地域环境和乡土文化痴迷的爱恋与崇拜对路遥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纵观路遥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浓郁的乡土情结贯穿于他的多部小说中。他的作品扎根于黄土地,散发着浓重的乡土气息,使读者在阅读时,除了透过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去领悟作品所表达的深刻主题外,还能从那些绚丽多彩的乡风民俗、乡土自然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感受陕北文化的独特魅力。路遥的乡土叙事包含了对道德的认识、对婚姻的看法、对女性的认识、对民俗的认知、对黄土的态度等等,而本文仅着眼于路遥乡土叙事中的陕北民俗、乡土自然、农民式的乡土观念三个重要方面,分析论述它们的作用,挖掘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陕北民俗及其文化内涵
(一)质朴厚实的陕北方言
陕北方言是陕北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它表达感情亲切、准确、有力,散发着最原始的光辉,在某种情况下普通话是无法产生这种效果的。在路遥的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地道的陕北农民形象,如德顺爷爷、刘立本、孙玉厚、高加林的妈妈等等,他们的话语中方言的味道特别浓厚。《人生》中加林妈看见高加林光着身子,便说“二杆子,操心凉了”。在陕北方言中“操心”即担心的意思,“二杆子”是指无知、傻子、做事过火的人,一般带有责备、骂人的意味。但在不同语境中,其感情色彩也不同。在这里,作为母亲,加林的妈妈表面上是责备儿子,实际上话语中却隐藏着一种爱子心切的感情。当高加林、刘巧珍给水里撒了漂白粉净化水,村里立刻为这事轰动起来。“没出山的婆姨女子、老人娃娃,都纷纷出来看他们”。这里运用了人称方言,“女子”是指没出嫁的女孩,婆姨是指已婚妇女,“娃娃”则指小孩子。另外,在《平凡的世界》中写到由于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平时溜溜达达不好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仔细思考一下“烂包”,会发现它是个无比生动的词语:一个包子的皮烂掉了,里面的馅料都撒了出来,不美观,而且没有办法再吃了。如果要把它“翻译”成普通话,应该是“糟糕、混乱、坏”的意思。在这里作家没有用“糟糕”,而用“烂包”,将抽象的描述形象生动化,来形容贫困之极的窘迫生活,既表达了王满银家生活糟糕到极点的状况,同时方言的运用也使表达形象生动,给人一种亲切感,起到了感染读者的作用。当孙少平被选为煤矿工人时,他欣喜若狂,以为自己的生活环境会好一些,于是便把自己的被褥送给别人。可是,等他来到住宿地看到一幅惨象时,他后悔了,觉得自己很“恓惶”。在陕北方言中,“恓惶”即可怜兮兮的意思,形容人境遇落魄、饱受折磨后的状态。除此之外,其他例子还有很多。
陕北方言对路遥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它表达感情亲切有力,而且使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真实,为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陕北方言有专属自己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给小说增添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使其散发着鲜活的民间气息。
(二)生动激情的陕北民歌
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貌、凛冽的狂风、闭塞的交通造就了陕北人豪放直率、淳朴憨厚的性格,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喜欢用民歌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而信天游是陕北民歌的精华,它真实而朴素地记录了陕北人的生活、命运与追求,表达了陕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纯洁爱情的执着追求。路遥在作品中巧妙运用民歌,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陕北的一种民俗习惯,而且能够准确传达人物的感情,还能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
《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从陷入爱河到分道扬镳,都是以一些民歌为媒介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首先,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甜蜜爱情是以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快回来》拉开序幕的。当高加林在河里洗完澡,两手交叉舒服地躺在地上时,从右侧的玉米地突然传出女孩子悠扬的信天游歌声:
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2]10
这首民歌表达的是一位痴情的少女对自己心上人的爱慕之情,其中“毛眼眼”,指的就是少女美丽明亮的眼睛,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女子的花容月貌。歌声虽缺乏训练,有点野味,但依然甜美嘹亮。这引起了高加林的注意,他猜到是本村的刘巧珍。巧珍一直深爱着加林,但由于自己没文化,内心感到十分自卑,没勇气向自己的心上人袒露心声,因此她在爱河中苦苦挣扎。于是,作者巧妙运用这首爱情民歌为两人搭建了交往的桥梁。看似阴差阳错,实则是作家的刻意安排。这样既可避免巧珍当面表白的鲁莽,符合她本身的性格特征,同时又使故事情节表达委婉,过渡自然,一举两得。
加林与巧珍的爱情可谓一波三折,最后还是以悲剧收场。当高加林走后门被告发后不得不回到黄土地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的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
哥哥你不成才
卖了良心才回来……[2]87
虽然这古老的歌谣是从小孩子的嘴里唱出来的,但它那深沉的谴责力量,却使高加林惊心动魄。这种独特的表达技巧是强有力的,是用普通议论无法表达的。
陕北民歌不仅增强了文学语言的地方特色,而且与人物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丰富了人物性格。由此可见,陕北民歌深刻地凸显了陕北的地域特色,提升了文学语言的韵味,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生动性、民间性和地域性,在小说的整体构建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这种带有浓厚地域性的原生态民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陕北人自编自唱的歌曲,是他们心灵感悟的真实写照。它不受音乐知识的约束,不受歌唱方法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歌唱来抒发内心情感。这些民歌表达了陕北人民对未来的憧憬、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感悟,反映了陕北人民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和朴素勤劳的创新精神。
(三)独具特色的陕北婚俗
陕北人讲究面子,无论自己经济实力好坏,都要尽己所能将子女的婚礼办得热闹红火,应有的婚礼仪式绝对不能省略。这种观念是人们在与陕北艰难环境作斗争中形成的,表现了陕北人坚强、好胜的性格特征。如《人生》中对巧珍和马栓结婚礼仪的描写:“吹鼓手一行走在前面,后面是迎新媳妇的高头大马,鞍前马后,披红挂彩”,陕北人结婚讲究骑马、吹号,以表喜气,这是陕北的传统习俗。“迎亲的人被接下后不久,第一顿饭就开始了;按习俗是吃饸饹。”荞面饸饹是陕北人最喜爱的主食之一。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陕北人吃荞面饸饹一定要配上羊腥汤,饸饹和羊腥汤二者缺一不可。同时,作品中这样描写:“席面是传统的‘八碗’四荤四素、四冷四热;一壶烧酒居中,八个白瓷酒杯红油漆八仙桌上摆开。第一席是双方的舅家;接下来是其他嫡亲;然后是门中人、帮忙的人和刘立本的朋友。”[2]77陕北婚宴极其讲究,巧珍婚礼的描写就是一个情景再现,有了八碗就显得吉祥体面,同时吃饭次序也不是同时进行,而是有一定的次序讲究,第一席是双方舅家或娘家人,也是最重要的客人,其他客人同样按照习俗规定,依次入席。陕北人结婚吃羊肉饸饹,一方面是受陕北冬季气候寒冷的影响,人们喜欢吃这样的食物驱寒,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歌中以饸饹和羊腥汤来比喻男女青年“死死活活相跟上”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四)粗犷豪迈的陕北秧歌
陕北人豪放直率的性格还造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娱乐方式,即陕北大秧歌,也叫“阳歌”或“闹红火”。该舞蹈动作丰富、豪迈粗犷、潇洒大方,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憨厚、开朗乐观的性格和“黄土地式”的热情豪迈。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到:“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3]269这充分体现了陕北秧歌场面之壮大、气势之恢宏、气氛之热烈。
秧歌到了,要放鞭炮迎接,完了之后主人得给行赏。在这之间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程序,即唱秧歌曲。唱词是用陕北方言来表现的,有祖辈相传的也有现场即兴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中也有这样的场面描写。
一个伞头唱:
万有亲朋你细听
转九曲你来到双水村,
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另一个伞头对道:
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
你问我栽下些什么灯?
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3]80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唱秧歌曲的是举着伞的伞头,人们之所以手中拿伞而非其他道具,这就牵涉到了陕北秧歌的文化内涵。陕北人生于黄土地,靠天吃饭,对太阳有一种崇拜之情,所以秧歌在历史上曾叫做“阳歌”。而唱秧歌曲的之所以是伞头,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手中擎“日”,表达陕北人对太阳的赞美、敬畏及对来年好收成的一种祈祷。
由于陕北秧歌的独特魅力,即使是在现在这样的快节奏生活状态下,人们依然传承着这一传统民俗文化。一方面,它是陕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陕北人对这片黄土地的无限热爱之情,反映了陕北人淳朴、热情的民风;另一方面,当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使各方面竞争异常激烈,人们精神压力甚大,而这豪放的陕北秧歌就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因此,陕北民众对秧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热爱之情。
二、乡土自然及其文化内涵
一个作家的生活阅历、思想观念、个性气质不仅制约着他对题材的选择和开掘,而且影响到他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基调。刘建军、蒙万夫先生分析柳青的艺术观时曾精辟地指出:“现实主义以现实生活为自己直接描写反映的对象,以按生活的本来样子忠实地反映现实为自己的任务,这就使它在认识和反映现实上,符合人们唯物主义地认识现实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就具有客观法则的性质。一切勇于正视现实、要把文学艺术当作为人生、为社会的工具,用它来展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启迪人们去干预、改造现实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就容易接受和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4]执著地以文学干预生活、影响社会,为实现美好人生理想而奋斗的路遥,自然而然地像他的前辈一样,自觉选择了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
路遥是一位情感丰富细腻、极富激情的作家,他对故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有着一种深切的尊敬和热爱之情,对养育他成长的这片黄土地上的山山水水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留恋之情。他在小说中用充满感情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故乡陕北黄土高原上独特的景物、风情、民俗世态,饱含着一种泥土的气息。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黄土高原的地貌景物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皱脸——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就达十六亿吨。就在这大自然无数黄色的自然中无数的皱褶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哪条褶皱走进去都能碰到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如同瓜藤一般串联着一个接一个的村庄[3]80。
这段描写,不仅揭示出陕北黄土高原的那种古老、神奇、厚重、博大的特征,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这片热土的无限热爱、崇敬之情。
在《人生》中,高加林被下掉民办教师后,心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一直处于闷闷不乐、失落怅惘的状态,当他突然想起给远在新疆的叔父写信可助他离开黄土地时,他的心情一下由阴转晴,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这时他望见田野的景色原来如此美丽:
远方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大川道里,玉米已经一人多高,每一株都怀了一个到两个可爱的小绿棒;绿棒的顶端,都吐出了粉红的缨丝。山坡上,蔓豆、小豆、黄豆、土豆都在开花,红、白、黄、蓝,点缀在无边无涯的绿色之间。庄稼大部分刚锄过二遍,又因为下了饱晌雨,因此地里没有显出旱象,湿滴滴的、绿油油的,看了真叫人舒坦[2]9。
这段对八月田野景色的描写,仿佛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作者让这样的美景在高加林心情变好时出现,更能衬托出高加林当时那种轻松、快乐、如释重负的心情。由此可见,路遥的这种乡土叙事,不仅描绘了美丽的八月田野,充满了浓郁的乡土色彩,渗透着作者对故乡自然景象的热爱,对生活的敬畏和热爱之情,而且形成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给人一种诗意的氛围和美的享受,从而使人物和自然景物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也是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因此,路遥的乡土叙事不仅给读者一种亲切的乡土气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感受这份惬意的同时,认识到大自然的美好,认识到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宇宙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从而时刻提醒人们保护自然、爱护自然,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农民式的乡土观念及其文化内涵
路遥的乡土情结使他始终对黄土地、对农民充满深情。这种深情,既表达了他对农民最真实的爱,同时也使他将自己那种农民式的乡土观念渗透于作品之中。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在这片黄土地上长大的,所以他的思想情感始终停留在这片土地上,这种对乡土的崇拜使他不能容忍任何有悖于乡土的行为,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弃儿,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在《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生浮沉与他乡土观的转变,正是路遥这种思想的表现。高加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这片黄土地哺育他长大成人,给了他美妙的童年时光。而当他进城上学,身上的泥土味渐渐地淡了,他不想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一辈子,不满足农村生活的宁静闭塞,想展翅高飞,去繁华的大城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他忽略了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自己能读高中并成为有文化的人,也是父辈们在这片黄土地上耕耘的结果,他与黄土地有着不可磨灭的亲情关系。当他被别人下掉民办教师的职位,重新回到黄土地时,他因成为真正的农民,心里无比失落、怅惘、苦闷时,是生活在黄土地上的朴实农民德顺爷爷和刘巧珍给了他安慰和温暖;当走后门事件被揭发,心灰意冷的他再次回归黄土地时,也是黄土地上的乡亲们给了他真诚的安慰:“天下农民一茬子人哩!”“慢慢看吧,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哩。”尤其是小说中的德顺爷爷对乡土的热爱,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农民式乡土观。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乡土智慧,去教导高加林:无论干什么,都不能离开乡土这个“根”。这样的人生启迪,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走多远、飞多高,都不能脱离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和这些可亲可敬的乡亲们。由此可见,高加林与黄土地分分合合,在人生的道路上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路遥通过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现实,肯定了乡土对一个人不可隔断的牵引力。而且小说的最后通过高加林的忏悔来显示乡土的神圣和尊严,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这片黄土地深深的爱恋之情。除此之外,《平凡的世界》中的农民企业家孙少安,通过自己艰难的探索和不懈努力,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砖厂,走上了小康道路。但他深知自己是农民的后代,双水村就是他的生存世界,无论是以前的贫穷屈辱还是现在的风光荣耀,都是这块黄土地给予他的。因此,他不忘自己的故乡,不忘家乡的人民,依然扎根农村,带领家乡父老乡亲一起致富奔小康,这也是农民式乡土观的一种表现。
可见,在路遥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家乡自然景色的描绘,还是对家乡人情美的赞颂,或是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安排,都反映了这种农民式的乡土观——“只有扎根乡土才能活人”。它不仅仅是一种典型的农民式乡土观念,更是一种农民式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哲学概括。生于黄土地,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生活的“根”,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像作品中德顺爷爷的那种近乎非理智的乡土观,让我们对父辈的生存观念感到一点悲哀。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农民式的乡土观念更显得有点落后、愚昧。所以说这种农民式的乡土观念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个人的成长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它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领域的东西,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既然物质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这种意识必然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就会阻碍人的发展。
总之,路遥以他娴熟的乡土叙事,为我们重现了陕北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农民式的乡土观念。通过对路遥作品中乡土文化的解剖分析,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更全面地了解了陕北的风土人情,更透彻地认识到路遥及他的农民式乡土观念。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乡土文化正在消亡。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有义务以各种合法方式拯救我们的文化,使其万古长青。而路遥自己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他的乡土叙事,一方面使其作品真实、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多种乡土文化正在走向消亡的今天,路遥的乡土叙事也起到了发扬陕北文化、提醒人们勿忘根本的作用。
[1]路遥.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438.
[2]路遥.路遥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3]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4]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论柳青的艺术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