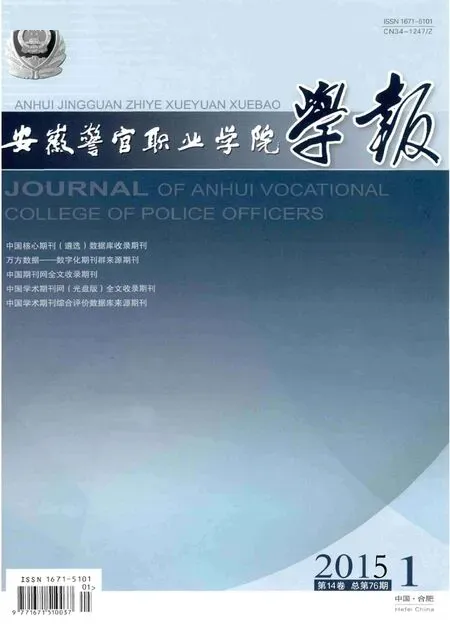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意义、现状与展望
吴志红,高德华
(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8)
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意义、现状与展望
吴志红,高德华
(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8)
建设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既是新时期我国反腐斗争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公立高校健康发展的需要。现阶段,各公立高校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部分公立高校的教职人员对高校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对风险点的查找缺乏权威监督、防控措施存在不足等。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今后应以制度建设为基本路径,以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和配套为依托,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根本保证。
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意义;现状;展望
2011年,中央纪委印发了《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中纪发 〔2011〕42号)(下文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廉政风险防控是将风险管理理论和现代质量管理方法引入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岗位风险防控为基础,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其目标是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有力、制度管用、预警及时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高预防腐败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构建科学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规范权力运行、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要求,是促进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现实需要,是推进预防腐败工作的有力抓手。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公立高校也开展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一、公立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意义
首先,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我国反腐斗争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权力驻足的地方就有腐败滋生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一直被定位为事业单位,不属于国家机关,但是目前我国公立高校的行政化却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高校的行政化是指“高校的办学理念、职能配置、组织建构、运转机制、决策管理等方面呈现与行政机构相似的特征”[1]。公立高校的行政化在内部组织管理体制上体现为效仿行政机关的科层制建立管理体制,行政机构组织不仅庞大,而且成为学校的主导部门,行政权力在学校的教育问题、学术问题和各项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和教代会的民主管理权力被虚化或被弱化;在外部,我国公立高校依附于国家对高校的行政管理权,公立高校不仅被划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不同行政级别,高校的校级领导也由上级党委(党组)调配任免,其中,省属高校由省委组织部(或省委高教工委、科教工委)掌控,部属高校由教育部(或其他主管部门)掌控。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权通过全面掌控公立高校的各种资源,严重干预了公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仅高校的人、财、物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掌控,而且高校办学的一些具体事务及相关资源也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如高校办学经费由教育行政机关下拨(专项费、科研项目经费等);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博士点、硕士点、新专业设置、教师编制、高级职称比例,以及高校升格、更名,都要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拥有对公立高校的考核、评估权。
公立高校行政化的实质是学校内部行政权独大,学校外部行政权对其的过度干涉,而无论是内部行政权的运行还是应对外部国家行政权的过程中,都有腐败滋生的条件和生长的空间,公立高校因而成为教育系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建设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就是基于当前反腐倡廉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所进行的,立足预防、强化监督的工作创新,是我国廉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该项工作也被列为2013年“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之一。
其次,公立高校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有利于保护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公立高校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法》赋予了我国公立高校广泛的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教学、科学研究、交流合作、财物管理、确定调整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及待遇等各个方面,此外公立高校还可以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如校办工厂,物资采购等。随着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改革,公立高校在上述领域的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大。但是,高校的内部治理机制并没有随着其办学自主权的扩大而发生重大变革,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对公立高校各项办学自主权的监督明显不足,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和条件,近年来,公立高校基建、招生、学术腐败案件呈多发态势,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威望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必然危害到公立高校的健康发展。
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制度机制建设,有利于规范公立高校内部管理者的权力,预防和减少腐败的发生,为公立高校正当行使办学自主权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将公立高校自主办学权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沦为公立高校内部一部分领导干部及部分岗位教职人员牟取个人私利的借口和工具。
二、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现状
(一)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取得的进展
近年来,根据中纪委的《指导意见》,教育系统积极开展了全国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健全高效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积极推进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截至2012年6月21日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2409所高校已逐步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75所直属高校全部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各公立高校所开展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成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领导班子。各公立高校通常成立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在学校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工作。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要或分管党政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纪检监察、党委组织部、人事处、财务处、审计处、规划、法规处多个部门组成。领导小组设有办公室,设在校纪检监察部门。
第二,确定重点部门和重点风险防控人员。各公立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重点工作是先确定廉政风险相对较高的重点部门,作为第一批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单位。如北京大学确定的重点部门有:组织部、人事部、财务部、学工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校产办、教务部(招生办)、研究生院、继续教育部、科研部、社会科学部、科技开发部;北京林业大学确定的重点部门有: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事处、科技处、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工会、校医院、信息中心、期刊编辑部、继续教育学院、体育教学部、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林场、林大附小;各学院;河海大学确定的重点部门有:组织部、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院、人事处、财务处、学生处、基建处、后勤管理处、校产办、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图书馆、后勤集团、各学院。可见,校级人事、财物、资产、招生、科研、基建、后勤等职能部门和单位、各二级学院是各公立高校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首选的重点单位。各公立高校的重点风险防控人员普遍包括校领导、处级领导和重点岗位人员。
第三,确定廉政风险防控的工作部署。各高校对廉政风险防控的工作部署大致都分为五个步骤:(1)动员部署阶段 (宣传动员阶段);(2)查找风险点阶段;(3)制定防控措施阶段;(4)考核防范效果阶段;(5)完善操作规程阶段(整改落实阶段)。在以上几个共同的步骤之外,有的高校还在最后部署了总结表彰阶段,如北京大学;有的高校则将工作部署得更加细致,在动员部署阶段之后,安排了梳理管理职权阶段,如河海大学;有的高校则在具体步骤中进一步布置了更加具体工作安排,如北京联合大学将“查找风险点”阶段进一步区分为:查找岗位风险、查找部门风险、评定风险等级三个内容。
(二)公立高校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目前存在的问题
1.部分公立高校的教职人员对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认识存在偏差
首先,部分教职人员并没有从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内在机理及其功能层面来认识相关工作。廉政风险防控将风险管理理论和现代质量管理方法引入反腐倡廉建设,是我国构建反腐体系的重要创新举措。高校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工作体系的必然要求,这一机制建设也必然成为我国反腐倡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反腐倡廉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决定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的长期性,需要各高校有计划、有决心地稳步逐渐推进。但是,部分高校的在职人员却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性质认识不足,没有从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机制建设层面来认识高校的相关工作,而是倾向于认为高校开展的有关工作是一阵风的运动式的,是短期内的和非持续性的,从而在应对学校的有关要求时存在应付、敷衍的心理,影响了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进度和质量。
其次,部分高校的教职员工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所针对的对象存在错误认识。许多高校的教职员工认为廉政风险防控的对象仅限于高校的领导干部,与自己无关,因此对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相关工作漠不关心。其实,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作为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是促进我国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重要手段,这也是目前各高校将学校领导、处级以上干部作为重点风险防控人员的原因。但是,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还具有进一步规范高校校办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预防学术不端和科研腐败行为的功能。因此,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所针对的对象不仅包括学校的领导干部,也包括重点岗位的人员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普通教职员工。
2.对所查找的风险点缺乏权威监督
找准风险点是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前提。查找风险点,就是围绕各项权力运行情况和岗位职责,系统查找在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并引入风险评估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划分风险等级,再据此分类制定防控措施。根据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各高校可以通过自己查找、群众评议、专家建议、案例分析和组织审定等方式,重点查找权力行使、制度机制和思想道德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但是在实践中,各高校对各单位呈报上来的风险点却缺乏专业的、权威的监督,无法确定各单位查找的风险点是否全面、准确,从而影响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后续环节。这主要是因为,高校内部单位数量众多,性质各异,职能不同,风险点的排查不仅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工作量也非常大,这使得编制相关事项的流程图和排查风险点的工作还主要依靠各单位自己来完成。以河海大学为例,根据该校所编制的“廉政风险防控相关重要事项目录”,该校风险点排查工作涉及人事处、学生处、基建处、图书馆等十四个部门和十九个二级学院,共六十四项重要事项。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虽由纪检监察、党委组织部、人事处、财务处、审计处、规划法规处多个部门组成,但是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人员对各单位和学院的大部分内部工作流程仍然是门外汉,而高校纪检监察部门也缺少足够的办案经验和案例积累,从而无法对各单位风险点的排查起到应有的把关作用。
3.针对风险点所提出的防控措施不足
目前各公立高校针对所排查出的风险点都提出了相应的防控措施,这也是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各高校所提出的防控措施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由于作为防控措施基础的风险点排查在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各单位针对风险点所提出的防控措施也就难免存在先天不足,尤其全面性方面存在不足;(2)在微观上,高校内部各单位所提出的防控措施的针对性不足,往往仅限于原则性的描述,如“避免……的随意性”;或者简单将防控措施定位为落实某项已经存在的制度,使防控措施变为对现有制度、上级文件的简单照搬;(3)防控措施的科学性存在问题。有的单位所提出防控措施存在随意性,缺少科学性论证,不仅在能否有效防控风险点方面存在疑问,而且防控措施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风险点;(4)在宏观层面上,高校内部各单位所提出的防控措施之间往往缺乏协调性、系统性。由于防控措施主要是由高校内部各单位针对自己的风险点所提出,所以难免具有差异性和分散性,加上各单位所提出的防控措施通常具有应急性、临时性,所以进一步增加了各单位防控措施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各项防控措施之间缺乏协调性,增加了系统化、制度化的难度;(5)防控措施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依赖于各项防控措施的切实落实,而这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工作,也是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能否发挥长期功效的重要支撑。目前,各高校排查风险点和提出防控措施的工作刚刚取得初步成果,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防控措施能否得到有效落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展望
(一)制度建设是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基本路径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一个综合体系,而制度建设显然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共中央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注重治本,注重预防,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不仅可以为高校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提供合法性基础,而且可以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及时加以确认、固定,从而有效防止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流于形式化、运动化或出现反复,真正使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成为长期的、持续的工作。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制度建设,应当围绕廉政风险预防、监控和处置三大部分来进行。
第一,廉政风险预防机制中的制度建设。廉政风险预防机制包括宣传教育机制和预测分析机制,其中预测分析机制需要建立多种制度加以支撑:(1)廉政风险信息收集制度,包括:廉政监督员制度、廉政信息月报年报制度、信访举报制度;(2)廉政风险信息分析制度,主要包括:风险等级评定指标体系、风险等级信息分级管理制度。
第二,廉政风险监控机制中的制度建设。(1)建立健全决策管理制度和监督审查机制。其中既包括实体性的制度,如筛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用权行为、“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权力运行的“关节点”、内部管理的“薄弱点”、问题易发多发的“风险点”的查找和确定;也包括程序性的制度,如完善、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各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制定有关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建立校务公开制度、相关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2)完善现有监督体制内的各项制度,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过程监督、审计监督、责任监督和纪律监督。
第三,廉政风险处置机制中的制度建设。(1)建立健全激励惩处机制。如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考评办法,强化问责;(2)恢复修正制度。针对防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廉政风险转变为腐败行为的情况,回溯风险管理链条各个环节,修正问题,恢复权力正常运行程序,实现廉政风险动态管理,为不断丰富和完善防控体系提供支撑,促进预防腐败长效机制建设。
(二)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需要以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和配套为支撑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国家反腐倡廉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预防腐败体系的一个分支。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需要以国家廉政风险防控体系作为平台和支持,而不是任何制度都重起炉灶;另一方面,高校在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过程中,相关制度的构建和落实也需要依靠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为其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基础。
校务公开制度是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中的重要制度,校务公开至少包括学校信息公开和校务程序公开两种制度。学校信息公开的法律基础是政府信息公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但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10月1日实施后,其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中当然有立法层面的问题,如该条例与《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等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规定缺乏操作性等,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适用的问题主要“是政策性的而非规范性的”[2],行政机关在实施该条例时对信息公开的态度往往较为保守,更倾向于不公开,使得政府公开的信息并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的需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运行不畅的现实情形无法为高校校务信息公开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运行社会环境,必然会给高校校务信息公开带来消极影响。校务公开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是高校行政管理程序公开,该制度的法律基础是国家行政程序法律的相关制度。虽然我国通过《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中的程序规定,在现代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我国至今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因此不能在国家法律层面为公立高校的行政管理程序提供可兹参照的制度支撑,使得目前公立高校行政管理程序主要还处于内部流程的自我梳理和自我规范阶段。
预防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工作人员的腐败是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重要内容,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财产申报制度与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密切相关。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一直被视为国家预防腐败的利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目前涉及到财产申报内容的主要有三个规定:(1)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3)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是这些规定仍是政策层面的,至今尚未上升成为国家法律层面的规范,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在实施中也“摆脱不了形同虚设的走过场尴尬境地”[3]。国家层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使得公立高校内部相关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缺少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不仅在制度构建过程中会面临无法可依的状况,在实施中也难以避免会遭遇到与国家有关财产申报政策实施相同的状况,从而使得高校廉政风险预防机制建设的成效大打折扣。
(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现代大学制度是指“与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大学外部关系、内部组织结构及大学成员行为规范的体系。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宏观调控、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民主管理、社会评估监督;举办者、行政管理者、办学者、学习者责、权、利分明”[4]。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一章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等,据此,有关方面将“现代大学制度”概括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对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取得成效具有根本性的保证作用,因为现代大学制度能够从根本上减少行政权力在公立高校的寻租空间,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现代大学制度能够科学诠释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公立高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重要背景是目前我国公立高校较为严重的行政化现状,该现象的实质其实就是内部行政权独大,外部国家行政权的干涉过度。正是公立高校行政化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使得公立高校构建廉政风险风控机制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理顺公立高校与作为举办者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基础条件。有学者提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以“大学本位论”代替“国家或地方本位论”[5],“国家或地方本位论”是指“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代替学校,承担全部的办学职能”;“大学本位论”是“让每一个高等教育的基本单位都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性,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做到既有大学的自身利益,又服从国家的统一利益,形成能够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机制”[6]。“大学本位论”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特征,其核心是以政府转变职能为前提,落实《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可见,现代大学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国家行政权对公立高校的不必要干涉,并且在公立高校内部形成以办学自主权为核心的科学运行体制,大大限缩了行政权力存在的空间,规范了行政权力运行的方式,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了行政权力腐败的可能性。
其次,现代大学制度能够建立与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并行的腐败预防机制,从而大大减轻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所承担的任务。“民主管理”、“学术自由”等内容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所对应的公立高校内部权力就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权力”,有学者将这两种权力描述我国公立高校内部的第三、第四种权力,与“执政党的权力”、“行政权力”(所谓的第一、第二种权力)并列。现代大学制度就是使这四种权力各司其职的制度安排,其中,执政党的权力成为超脱性的先进文化方面的领导权;行政权成为为第三、第四种权力服务的事务性、附属性的权力;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权力是公立高校内部最核心的权力,成为公立高校运行的主导性权力[7]。落实公立高校的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权力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可以使公立高校摆脱对国家行政权的过度依附。公立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机制本身就包含校务公开、校务参与等具有预防腐败功能的内容,而学术自治机制还可以通过建立自律性的权威机制大大减少普通教职科研人员的学术腐败。【参 考 文 献】
[1]冉亚辉.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实质及其控制[J].现代教育管理, 2010(10):31.
[2]程洁.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适用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9 (1):28-36.
[3]孙国祥.财产申报制度建构中的相关问题刍议[J].江海学刊, 2010(2):143.
[4]赵文华,高磊,马玲.论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校长职业化[J].复旦教育论坛,2004(3):35.
[5][6]张祖英,许积年.对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73.
[7]汤正翔.构建中国式现代大学制度:四项权力的重新定位问题[J].高教高职研究,2009(9-上):174-177.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Control Mechanism in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Significance,the Status Quo and the Prospects
Wu Zhihong,Gao Dehua,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98)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control mechanism in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rruption risk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demand of the new situation as China’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enters a new stage,but also is a protection of the universities’autonomy and the ne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At present,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control mechanisms in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made some progress,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misconcep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control mechanism,lack of supervision in risk detection,and deficiency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In the future,the system construction should be the basic path,taking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national laws and supporting system as its basis and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public universities;risk control mechanism;significance;status Quo;prospects
G649.21
A
1671-5101(2015)01-0110-06
(责任编辑:孙雯)
2014-11-20
本文系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3B13614)的阶段性成果。
吴志红(1974-),女,辽宁抚顺人,河海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高德华(1961-),女,山东蒲台人,河海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