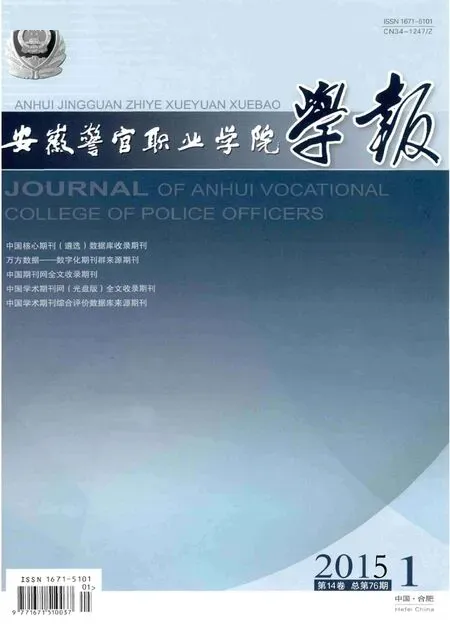论行政允诺范式的阿基米德支点
——以“黄银友案”为分析对象
黄琳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8)
论行政允诺范式的阿基米德支点
——以“黄银友案”为分析对象
黄琳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8)
行政允诺虽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增列为新型行政行为之一,但行政法学及法律规范中均缺少对其内涵的进一步解释。以“黄银友案”裁判文书为观察切入点,发现行政相对人从不特定转变为特定并引起法律关系端点发生变动,进而从中抽象出行政允诺二阶段论之范式。通过剖析其他涉及行政允诺的司法实例以检视这一初步范式。对比分析显示,行政允诺之相对人既包括特定相对人,也包括不特定相对人;涉及行政允诺的司法实践易与他类案由发生复合。
行政允诺;法律关系;行政相对人;行政合同;行政奖励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行政目的及机能日益复杂、行政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等认知已成为当代行政法学界的共识。随着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等观念的确立,传统“命令服从式”的行政行为已显出滞后性,行政主体尝试运用诸多非权力行政方式以回应时代变迁。“现代行政不单纯是权力行政活动,从质到量都显著地增加了包括私方式和私规范在内的非权力活动。”[1]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参与、行政允诺①就“行政允诺”的称谓而言,有学者主张继承民法体系的称谓,以“行政承诺”称之;也有学者主张以“行政允诺”称之,以彰显行政法体系之特色。参见杨卿:《行政允诺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笔者遵循后一种做法,但在引述文献时为尊重原文,仍使用原作者选择的方式。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虽学界前辈已对这些新兴事物作了诸多理论探索,但讨论范围多集中于前三者,除部分专题论文外,各类专著、文集中鲜见行政允诺之身影。
然而,行政允诺虽游离于主流学者研究视域之外,但在行政实践中却颇受青睐,各类行政允诺层出不穷。“我们必须承认,行政承诺发展到今天,无论范围、数量还是内容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行政承诺在行政措施中的频繁适用,行政承诺对行政效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似是为回应这一现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法发[2004]2号《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与法发[2009]54《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将行政允诺与行政奖励、行政合同等一同增列为行政行为种类之一、要求各级法院依法积极受理这些新类型案件。然而,更为细致的解释却付之阙如。迄今,学者们对行政允诺的定义仍各执一词、难定一尊。综合而言,有以下几种观点:“行政承诺是指行政主体依其职权所作出的待其条件成就时履行相关义务的信守型允诺”;[3]“行政承诺就是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依其行政职权,对特定的事项或者特定的人员,做出的答应照办某项事务的行为”;[4]“行政承诺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通过公开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许诺,相对人完成了其在承诺中制定的行为后给予一定奖励的行政行为”。[5]其余观点虽略有区别,但均大同小异。笔者认为,与其斟酌文字上的细微差别、试图作出一个封闭性的精准定义,莫不如从行政允诺的动态演变着手,以司法实例为对象,通过厘清司法实践的论证逻辑,从中发现并提炼行政允诺的本质属性。为此,本文以“黄银友、张希明诉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政府、大冶市保安镇人民政府行政允诺案”(以下简称“黄银友案”)①《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第22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作初步剖释,以期对这一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型行政行为形成规范化的判断框架。
二、个案聚焦:“黄银友案”的重新审视
(一)事实概要
2000年9月18日,大冶市委、大冶市政府颁发的冶发[2000]38号《大冶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办法》(以下简称“《优惠办法》”)规定:“凡从市外引进合作、合资、独资项目者,引进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经验资确认后按实际到位资金的千分之八由受益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上述中介奖,如无我方收益单位,由大冶市财政支付。”同月31日,保安镇政府向黄银友出具“承诺书”。2003年8月上旬黄银友与相关负责人一同到浙江联系投资项目。同年10月15日,浙江省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黄银友出具中介证明。10月16日,浙江尖峰集团与大冶市政府在大冶市正式签订投资协议,黄银友获邀出席仪式。2004年8月3日至2007年12月14日,黄银友多次向大冶市政府请求给予中介奖,但大冶市政府均未予答复。2008年10月6日,黄银友、张希明以大冶市政府、保安镇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认为双方之间已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行政允诺法律关系,请求两被告给予中介奖励款。一审法院判决两被告依据《优惠办法》给予原告奖励。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二)裁判理由解读
本案中原被告的主要争点在于双方之间的行政允诺关系是否成立。原告认为已成立,被告则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大冶市政府制定的《优惠办法》是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招商引资积极性,以实现政府职能和公共利益为目的向不特定相对人发出承诺,在相对人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后由自己或由自己所属的职能部门给予该相对人物质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上述事实说明黄银友、张希明在浙江尖锋集团500万吨水泥项目落户大冶市保安镇的过程中,实施了招商引资中介行为。大冶市政府、保安镇政府辩称黄银友、张希明不是大冶尖峰水泥项目的引进人、其与黄银友、张希明之间无合法有效的行政允诺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处,一审法院否定了两被告主张的行政允诺关系不成立的论点,间接对原被告双方间的行政允诺关系予以肯定。细观之,笔者认为,对一审法院的论证思路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一审法院肯定了大冶市政府颁发的《优惠办法》是单方承诺,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实现政府职能和公共利益。其次,法院指出该承诺属于附条件承诺,惟有相对人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后,大冶市政府方才予以兑现。结合《优惠办法》之具体内容,前述“某一特定行为”无疑限定为“从市外引进合作、合资、独资项目者,引进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一招商引资中介行为。再次,该承诺之内容为相对人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后、由大冶市政府给予该相对人物质利益或其他利益。此外,由前述事实概要可知,原告黄银友、张希明确已实施了招商引资中介行为,一力促成浙江尖峰集团水泥项目落户大冶市。故此,原告之行为满足被告提出的单方承诺,双方之间成立行政允诺法律关系。
至此,一审法院的审理思路已跃然纸上。然而,若仅止于此,我们仍无法探知行政允诺的规范化判断架构。行政允诺异于他类行政行为之处为何?如何对行政允诺进行类型化解读?为了对行政允诺范式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需要真正找到剖析这一谜题的阿基米德支点。由于“法律形式理论着眼于点式观察,一个法律关系将会遭到撕裂”[6],笔者认为,莫不如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切入点、探究“黄银友案”中行政法律关系的演变脉络,进而发现行政允诺的规范化表述。
三、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论拷问
“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活动之法律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组织理论(法主体)、行政过程理论 (法主体自身之行为可能性)、以及行政上权利义务关系(法主体间行为可能性之相互关系)。”[7]而所谓“法主体”,依据凯尔森之理论,是指“将某一利益或行为可能性归属某一资格主体后,所形成之特定法秩序本身之拟人化载体”。[8]于此,前述“黄银友案”中的法主体即可解释为行政主体(大冶市政府、保安镇政府)与行政相对人(黄银友、张希明)。而结合前述案件事实及此处的法律关系三要素说,我们不难推断,惟有厘清法主体及法主体自身之行为可能性,方能清晰解读本案行政允诺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上权利义务关系”。鉴于“现代行政法体系中行政相对人构成了行政权的目的,行政机关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在于满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9],结合行政允诺自身之特殊性,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行政相对人”这一特定法秩序之解读。
(一)阿基米德支点:行政相对人之转变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黄银友案”。从前述案件事实可知,被告大冶市政府发布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办法》后,原告黄银友、张希明为获得奖励积极联系浙江尖峰集团并成功完成招商引资的任务。随后,两原告依据《优惠办法》中“引进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经验资确认后按实际到位资金的千分之八由受益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之规定,以实际完成引资任务为由向大冶市政府请求支付奖励款项。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本案的行政相对人即为两原告黄银友、张希明。
这一结论并无不妥之处。然而,若仔细观察本案的具体发展脉络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原告黄银友、张希明提出奖励申请之前,《优惠办法》中已对大冶市政府这一行政允诺行为的相对人作了暗示。《优惠办法》称:“凡从市外引进合作、合资、独资项目者,引进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经验资确认后按实际到位资金的千分之八由受益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上述中介奖,如无我方收益单位,由大冶市财政支付。”由此可知,大冶市政府允诺给予中介奖的相对人需预先满足两个要件:从市外引进项目;引进额超过1000万元。除此以外并无其他特殊规定。易言之,《优惠办法》的目标群体为所有不特定相对人,凡是引进外资达1000万元以上者皆可获得奖励;意即,大冶市政府给予中介奖励的行政允诺最初并未限定相对人范围,而是指向不特定相对人。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本案中的行政相对人从最初的不特定相对人转变为诉讼伊始的特定相对人。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便是:这一转变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转变对于本案的行政允诺会造成何种影响?笔者认为,解答疑惑的关键点还在于行政允诺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
(二)行政允诺法律关系端点之转移
法律关系之端点是“法律关系论”的代表性人物阿特贝格受纯粹法学派法理论之影响提出的法律关系三种本质要素之一,“通常指权利主体”①阿特贝格(N.Achterberg)建构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他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要素可归纳为三种:法律关系之端点;法主体之相对性;各种法规范所决定之法律关系之不同强度。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7页。。而阿特贝格法律关系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以法律关系端点之不同所架构的六类法律关系。②六类法律关系分别为:(1)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关系(如国家与私人);(2)组织和组织的关系(如联邦与州);(3)组织和机关的关系(如州政府与州警察局);(4)组织和机关担当者的关系(如国家与公务员);(5)机关与机关担当者的关系(如联邦环境保护局与所属职员);(6)机关与机关的关系。参见同①书,第128页。有鉴于此,则前文所提及的行政相对人转变问题,其根源是否在于本案中的法律关系端点发生转移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前文已经提及,《优惠办法》是大冶市政府为己方设定的单方行政允诺,其允诺内容可归纳为:不特定相对人引进外资项目+引进额超过1000万元+经验资确认=大冶市政府支付中介奖。无疑,此时的行政允诺法律关系之端点为大冶市政府及不特定相对人。另一方面,由案件事实可知,黄银友、张希明确已满足前述招商引资条件,并向大冶市政府申领中介奖。故此时的法律关系端点归属于黄银友、张希明及大冶市政府。显然,因中介行为的出现,原本指向不特定相对人的端点滑向特定相对人。然而,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这一转移对本案的法律关系会造成何种影响?以法律关系四层结构③山本隆司教授主张行政法律关系有四种类型,分别为:第一层,行为之自由;第二层,实体法关系;第三层,程序法关系;第四层,组织法关系。参见同①书,第133页以下。而言,笔者认为,此时端点的转移使得本案的实体法关系发生了质变。④笔者认为,以案件事实论,“黄银友案”的核心问题为大冶市政府的行政允诺是否成立,此为实体争议问题。除此以外,本案并未涉及法律关系的其他层次。
由前文可知,法主体间行为可能性之相互关系,抑或“利益结构”,是行政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各类主体间之利益结构纷繁复杂,大体而言可分为“反对利害关系”与“互换利害关系”两类。“反对利害关系”意指对某一主体课予一定行为义务之方式,以保护其他主体之行为可能性,此时被课予义务主体与被保护主体间的利益结构呈现一种相反方向的对立结构,且私人一方通常隐藏不见。与之相对,若行政介入后私人一方显现于垂直冲突之利益结构者,则为“互换利害关系”。[10]基于此,若重新审视“黄银友案”之各类利益冲突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行政法律关系端点之转移对本案之利益结构存在实质影响。
如前所述,原告黄银友、张希明实施的招商引资中介行为影响了本案中法律关系端点之指向,昭显了行政相对人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一中介行为亦为本案利益结构之划分奠定了基础。正如前文之论述,中介行为实施之前,《优惠办法》向不特定相对人作出了单方允诺。此时,若任何不特定相对人从事了《优惠办法》所规定的招商引资中介行为,皆有可能获得奖励。易言之,《优惠办法》对大冶市政府课予了给予中介奖励的义务,而该任意相对人则有获得奖励之权利,此时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属反向对立结构。但因该中介行为尚未实施,故该“任意相对人”隐藏于不特定相对人之大范围中。另一方面,中介行为实施之后,黄银友、张希明作为特定相对人向大冶市政府申领奖励款项,此时利益结构冲突双方得以确定。概言之,前者属反对利害关系,后者则为互换利害关系。
行文至此,“黄银友案”所牵涉的行政法律关系已清晰可辨。然而,尚有一个关键问题游离于我们的研究视域之外,能否以“黄银友案”为依托、从中剖析行政允诺范式化框架?笔者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审法院的判决中找到答案。
(三)行政允诺范式之二阶段论
前文已论及中介行为在“黄银友案”中发挥着分界点的作用:中介行为实施之前,大冶市政府为己方设定单方允诺;中介行为实施之后,大冶市政府需向两原告支付奖励款项。笔者认为,此时我们不妨借用“二阶段论”①德国学者将先行之行政行为从私法上债权之债务关系切离以构成“独立之行政处分”,提出所谓“二阶段论”。二阶段说之理论构成,并非定型,因应不同法律关系类型而有差异。参见刘宗德:《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3页。来对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作进一步剖析。循此逻辑,我们可以将中介行为之前的阶段作为第一阶段,此时大冶市政府需依据《优惠办法》决定对于谁给予奖励、准否奖励等事宜;而中介行为之后,大冶市政府对黄银友、张希明负有奖励义务的阶段则视为第二阶段。而单以第二阶段而言,此时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皆属特定,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负有给付义务,究其形式,与行政合同颇具相似之处。
事实上,关于上述二阶段论,学者间存有颇多争议。有学者主张“行政允诺具有双重性:一个行政允诺实质上包含两个行为,即作出允诺行为本身以及是否履行允诺义务的行为。前者主要指行政主体发布带有允诺内容的规范性文件或通告行为,而后者在行政允诺纠纷案件中通常表现为行政主体的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允诺义务的行为。”[11]又如“行政允诺行为也只有在推进到有了特定对象之后才会有真正的法律意义。”[12]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行政允诺仅包含第一阶段,若推进至第二阶段,则其法律关系已发生质变。如“一旦社会公众中的个体接受行政主体的承诺并实施承诺所指定的相应行为时,即表明该个体接受了承诺所确定的内容并愿意与行政主体缔结合同。行政主体与该个体之间形成行政合同法律关系时,行政承诺就转化为行政合同,行政承诺的具体事项同时转化为行政合同的具体条款。”[13]还有学者提出“行政承诺系一种自我义务的设定与约束,从利益取向上来考察则大多可以归入单务契约。”[14]诸多论点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鉴于“黄银友案”自身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15],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一案例中发现司法部门推崇的观点。
让我们再次将视线回到“黄银友案”。判决主文伊始,一审法院便指出,“大冶市政府制定的《优惠办法》是……向不特定相对人发出承诺,在相对人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后由自己或由自己所属的职能部门给予该相对人物质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另一方面,“黄银友、张希明实施了招商引资中介行为。”故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间已成立合法有效的行政允诺关系,“大冶市政府、保安镇政府辩称其与黄银友、张希明之间无合法有效的行政允诺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随后,法院就具体奖励款进行了深入审查,指出“大冶市政府及保安镇政府应根据《优惠办法》的规定对黄银友、张希明给予兑现奖励。”至此,法院的观点已不言自明,其认为行政允诺的核心为前述第一阶段,至于第二阶段的奖励给付则不属于行政允诺之范围,如图1。
然而,更为迫切的问题随之产生:从“黄银友案”中抽离出的这一行政允诺范式是否具有普适性?若行政允诺仅限第一阶段,则第二阶段应作何解释?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对更多司法实例作进一步的分析。
四、诉诸司法实践的行政允诺
上述分析毕竟只是沙盘推演,为回应真实世界之需要,我们仍需以司法实践为标尺对图1中的范式作进一步的校验。
(一)典型司法案例比对
笔者尝试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进行检索,共搜集到7个涉及行政允诺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梳理检读,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部分案例虽以“行政允诺”为案由命名,但案件发展脉络与前述范式相差甚远;而另一些案例虽与“黄银友案”相似,但并未将“行政允诺”作为案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或许研读法院判决理由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概言之,这些案例可作如下简约分类:
1.与“黄银友案”相似
案例1:辽宁省本溪市民族贸易公司清算小组与荣成市人民政府经济行政允诺纠纷上诉案。法院认为:荣成市政府的《投资指南》和开发区管委的《奖励办法》是行政主体为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对引进国内外资金及项目的奖励措施,符合本地区的公共利益,是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的行政管理目标,向相对人作出的为自己设定义务的行政允诺具体行政行为。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鲁行终字第1号。
案例2:陈增月诉东台市富安镇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允诺义务纠纷案。法院认为:被告东台市富安镇人民政府作出富发[2002]04号《关于开展“百日招商竞赛”活动的意见》,允诺包括全社会不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期限内招商引资成功给予奖励,属于被告自由裁量的范围,不违反政策、法律,是被告为自己设定一定义务的行政允诺。②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东行初字第00047号。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案例1与案例2的基本脉络与“黄银友案”相似度较高,其内在逻辑符合图1之设定,均为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相对人作出单方允诺、承诺在相对人为一定行为后对其给予奖励。
2.允诺针对特定相对人
案例3:谷西村委会诉洛阳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许可案。法院认为:洛阳市政府承诺谷西村委会对涉诉国有土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受让权,该承诺是洛阳市政府对谷西村委会单方面作出的承诺,属于行政允诺;并且该承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③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洛行终字第119号判决。
案例4:上海浦东新区高海汽车测试设备厂诉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府允诺纠纷案。法院认为:经高海厂的中介引荐,引进上海爱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到织里镇投资住宅开发项目,织里镇政府允诺对中介人高海厂给予招商引资奖励,这是行政主体针对特定对象的行政允诺,具备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④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浙湖行受终字第1号。
案例5:迟同太等诉乳山市海阳所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海阳所镇政府在作出准予上诉人迟同太退休并发放退休待遇的行政允诺后,应当按照其允诺的内容履行义务,其无正当理由停止发放迟同太的退休待遇,侵犯了迟同太的合法权益,该行为违法。⑤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威行终字第10号。
这3个案例虽均在判决主文中提及 “行政允诺”,但细观之,其内在特征与图1不尽相同,究其本质,在于这3个案例中的允诺均指向特定相对人,如案例3中,洛阳市政府向谷西村委会承诺给予其优先受让权;案例4中,织里镇向高海厂允诺给予招商奖励;案例5中,海阳所镇政府向迟同太承诺发放退休待遇。如此一来,也就不存在第二阶段中相对人的转变。显然,单以图1所设的行政允诺范式而言,这3个案例均不属于行政允诺之范畴。
3.允诺指向不特定相对人但非以“行政允诺”为案由
案例6:张炽脉、裘爱玲诉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招商引资奖励行政职责案。法院认为:绍兴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绍政发 [2002]6号文件系关于招商引资的规范性文件,是其对符合招商引资条件的单位、个人进行奖励所设定的义务,在与上位法没有抵触的情况下,应属有效。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行终字第65号。
案例7:郭伟明诉广东省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不予行政奖励案。法院认为:《深圳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三条及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是举报人,并未限定举报人的身份。本案原告是署名举报,原告要求对举报行为给予奖励,被告以原告参与违法行为为由,作出不给予举报奖励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①以下简称“黄银友案”:《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第22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乍一看,这两个案例都没有明确提及行政允诺,但究其本质,案例具体事实与发展脉络均与图1相近。然而,法院却避开行政允诺、均以“行政奖励”为切入点进行审理。
结合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图1所示之行政允诺范式在案例1、2均可得到印证。另一方面,案例3、4、5突破了图1的限制,将针对特定相对人的单方允诺也涵盖其中。与此同时,案例6、7另辟蹊径,放弃行政允诺、转而以行政奖励为突破口。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有何深意呢?若单纯以审理时间检视,案例1、2、3早于“黄银友案”,其余案件则在该案之后。这是否说明自2000年起法院不断尝试对招商引资类行政允诺案件作规范化审理、并在“黄银友案”中形成较为体系化的论证框架,而后因各类新案件不断涌现、这一框架也随之修正?但如此一来,又无法解释案例6、7的存在。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辨析各类与行政允诺相似的概念。
(二)相似概念辨析
1.行政允诺与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其具有如下特征:(1)当事人一方是行政主体;(2)目的是为了行使行政职能;(3)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4)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5)纠纷通常通过行政法的救济途径解决。[16]显然,行政允诺并不具备这些特征。一方面,第一阶段只存在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并未与相对人达成合意;另一方面,第二阶段给付奖励款项时,行政优益权无从谈起,若行政机关拒绝兑现允诺,不仅与行政允诺初衷相悖、也不符合依法行政之诚实信用原则。依此观点检视前述案例3-5,尽管允诺从最初开始即针对特定相对人,但明显欠缺构成行政合同之必备要件,无法归入行政合同之列。笔者认为,不妨将其理解为法院应因实践变化对图1范例作了拓展。
2.行政允诺与行政奖励。
行政奖励,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予奖励权的组织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与个人,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的行政行为。其特征有:(1)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目的在于表彰和激励先进;(3)对象广泛;(4)内容是给予受奖者某些精神或物质利益;(5)是使受奖人获得奖励性权利的一种法定奖励行为。[17]由是观之,行政奖励区别于行政允诺之特殊性就在于其法定性,即须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奖励是在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的规定另行制定奖励条件和随意确立奖励标准。”[18]依次逻辑检视前述案例6、7,《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区外(内)商投资项目引荐者实行奖励的规定通知》为绍兴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深圳市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是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与深圳市卫生局共同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二者均不属于法律、法规之范畴。显然依此二者作出的奖励行为不宜认定为行政奖励。那么,法院在审理中为何回避“行政允诺”而以“行政奖励”为切入点呢?事实上,行政允诺制度的兴起是行政法治实践努力回应公共行政和积极行政体现。但因发展时间较短,法院对于行政奖励和行政允诺并未完全明确其中差异,二者产生的具体纠纷易相混淆而导致案由复合。笔者认为,就案件核心而言,案例6、7均为行政允诺,只是该允诺以奖励之外貌出现。
(三)行政允诺范式之进阶分析
层层推进至此,我们可得出结论:行政允诺通常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允诺成立阶段,第二阶段为给付允诺内容阶段;行政机关为己方设定的附条件单方允诺可面向特定相对人,亦可指向不特定相对人;当所附条件成熟时,面向不特定相对人的允诺即转化为特定主体之间的给付关系。见图2。
五、结语
回归“黄银友案”,案件事实仅就外形以观似乎并未涉及行政允诺的深层内涵,遑论行政允诺之构成要件与成立要件。若仅从法律形式论观之,囿于行政允诺之新兴性,难免陷入论证混乱。莫若转换视角,以相对人转变这一阿基米德支点切入,考察案例中各权利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因“法律关系将目光从形式理论所重视的行政决定移转到其所产生或应该发生影响的关系。其并不注重于决定的程序,而是将重心放在形式与实质的当事人及其分配的利益的观察”,[19]循此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行政允诺二阶段论之特征。“黄银友案”给我们的启示即是,在观察新类型行政行为时不能单从概念盲目出发,还应关注法律关系与利益结构之变动。
[1]张弘,周瑞军.私法化下行政法的发展[C]//胡建淼.公法研究》(第六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80.
[2][4]王伦,耿志武.行政承诺及其可诉性[J].人民司法,2002(8): 58.
[3]高鸿.行政承诺及其司法审查[J].人民司法,2002(4):61.
[5]李玉敏,陈志立,蔡靖.行政承诺案件的性质及审理对象[J].法律适用,2003(12):47.
[6]张锟盛.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体系革新的动力[C]//当代公法新论(中),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35.
[7][8][10]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M].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162,161,194.
[9]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12.
[11]戴俊英.行政允诺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J].湖北社会科学, 2010(12):158.
[12]王喜珍.行政允诺行为的行政法理透视[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67.
[13]高鸿.行政承诺及其司法审查[J].人民司法,2002(4):62.
[14]杨解君,崔小峰.行政法上的单务契约与双务契约[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43.
[15]《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编辑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
[16]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8-280.
[17]杨解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59-360.
[18]阎尔宝.政府的单方允诺——行政向私法的逃避[J].人民司法,1999(1):49.
[19]张锟盛.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体系革新的动力[C]//当代公法新论》(中),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57.
On Archimedes's Fulcrum of Administrative Promise——TakingHuang Yinyou Caseas Example
Huang Li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08)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taken the administrative promise as one of new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which still has less further connot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law regulations.The article, takingHuang Yinyou Caseas example,found that certain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have changed the legal relationship,and concludes a new mode of administrative promise.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include both specified counterparts and unspecified counterparts,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 concerned the administrative promise tends to reach the composite with other similar cases.
administrative promise;legal relationship;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administrative contract; administrative reward
DF312
A
1671-5101(2015)01-0023-07
(责任编辑:陶政)
2014-10-20
黄琳(1990-),女,浙江象山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2013级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一大冶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