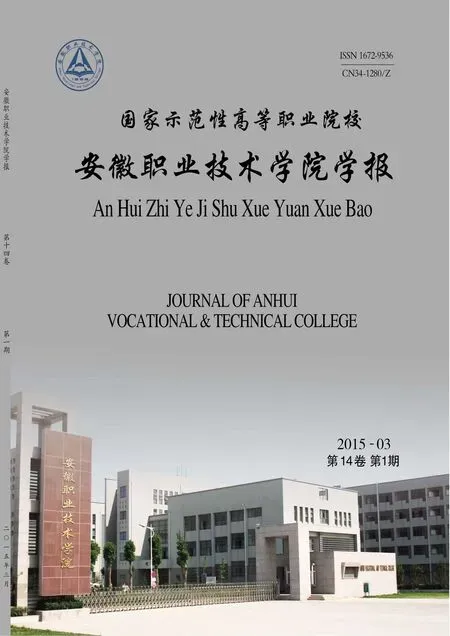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研究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研究
符号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的要素,是一定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作为物质形式来表达意义的符号,因此它具有符号的一切特征,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1]。“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表现,索绪尔称之为能指或施指,“义”是语言符号的内容,索绪尔称之为所指或受指。只有义与音的结合才能指称现实现象构成语言的符号,语音和意义在具体的语言中统一于一体,密不可分。
索绪尔将任意性作为语言学理论的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学。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首先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种意义为什么用这种声音形式而不用另一种声音形式,这中间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汉语中为什么把“用两条腿走路、会说话、会干活的动物”这样的意义和rén这个语音形式结合起来,这是没有道理可说的,完全由社会的习惯所决定。所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对于语言符号的意义而言完全是任意的,是人为规定的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2]。
1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
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就语言符号能指和语言符号所指之间的联系而言,只有任意性的存在。最初的符号能指一经产生便经久不衰,保持了永远的不可论证性。
人们可以从不同语言中数字概念的表达来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之所以选择数字,是因为数字的意义最不容易发生偏离,因此也更具有实证的可靠性,如:
汉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英语: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法语:un/une, deux, trios, quatre, cinq, six, sept, huit, neuf, dix;
德语:eins, zwei, drei, vier, funf, sechs, sieben, acht, neun, zehn;
日语:hito-, futa-, mi-, yon-, itsu-, mu-, nana-, ya-, kokono-, too;
荷兰语:een, twee, drie, vier, vijf, zes, zeven, acht, negen, tien。
2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双向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双向的。换句话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还不仅存在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它同时存在于符号能指的一方或所指的一方。
相同的声音在同一种语言里可以用来指不同的概念。例如:日语中的kami可以指“神”、“纸”、“头发”等意义。在英语中,man一词具有泛指“人类”的一般意义,同时又指“男人”,它在日常语言使用中的歧义足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符号能指的任意性:假如一个女人从船上落水,人们偏偏喊道:“Man overboard!”(有人落水啦!);假如她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死,那司机却被判“manslaughter”(谋杀罪);假如她负工伤,获得的却是“workmen’s compensation”(工伤补偿);可是假如她到标有“Men Only”(男人入内)的门口,她立即意识到,这个告示不是针对动物、植物或无生命的生物,而是针对她的。
不同的声音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比如,汉语和日语中都出现同一“年龄”对应两种符号所指。除了直接的数字发音外,还有另外的语音形式。例如:huajia(花甲),kanreki对应“60岁”;guxi(古稀),koki对应“70岁”;xishou(喜寿),kiju对应“77岁”;mishou(米寿),beiju对应“88岁”。
3空符号现象的存在
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空符号和语言规律的例外,这正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一种必然表现和根本基础[3]。韦世林[4]从内涵和外延分别定义了空符号。他把空符号的性质定义为“停顿”、“空位”、“距离”、“间隔”,或者作为表现形式的代码,对那些实符号进行衬托、提示或分隔的一类特殊符号。语言活动中有分隔需要时,符号系统、符号活动则为空符号的出现创造条件。空符号的操作方式主要是人为设置的。世界和物之间的亲密性在“之间”就形成一种“缺失”,这种“缺失”可以是空白、距离、虚无、停顿等。实符号存在的前提是空符号的存在,就像老子所言“有无相生”。
以汉语复合词“管家”为例,“管家”表达的是施事,指“管理家的人”,“人”在组合形式中省去,是一个人为的积极的空符号。再以语言中频频出现的缩略语为例。缩略语所指明确,而能指形式萎缩,这样形成了局部的空符号。这些空符号具有单一性、公共性的特点,如“湖人”、“交大”、“NBA”等。
众所周知,事物先于语言符号而存在,语言符号则先于规则而存在,所谓语法规则、语言规律、可论证性等都是人们对语言事实发生概率之后的总结与归纳,所以我们才遭遇语言零符号现象和语言规律的例外,也就是说,因为语言符号能指和语言符号所指之间不存在任何天然或必然的联系,语言空符号才有可能合法地存在。而又因为语言零符号事实在先,语言规律事实在后,这才有了例外存在的合理性。反过来说,倘若没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根本性的命题,语言零符号和语言规律的例外就不可能合法地存在。
4语言符号所指的张力
语言符号任意性具有可证实的广延度,即在符号能指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认语言符号所指的张力。语言符号能指一方永远是分级的、范畴化的,而语言符号所指的一方却总是错综复杂的统一体,因此语言符号所指往往具有边界不明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允许了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存在。
关于色彩,语言符号提供了诸如红、橙、黄、绿、青、紫等颜色,但是“红”的能指在色谱上的起迄点在哪里,和“橙”如何分界,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而已。再以人生为例,人生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过程,语言符号里关于人生的分级包括婴儿、幼儿、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等等,这些人生阶段之间的分界本来就是模糊的,加上不同的语境又增添了不确定性,如青年科学家和青年运动员,前者年龄可能大于后者。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仅在于声音形式与概念之间,而且单方面延伸到语言符号所指,又反过来影响到语言符号能指与语言符号所指结合体的横向组合或线性语符列,如:小奶牛——大白兔(谁更大?),高鼻梁——高塔(一样高?)等等。
5拟声词和合成词的非完全任意性
语言符号并不是完全任意的,比如拟声词和合成词。小孩模仿大人的言行,人们模仿大自然之中的各种现象,模仿是人类的本能。在人类社会之初人们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来表达某种意义或表示某种事物,于是就出现了拟声词。语言系统中的拟声词往往是对极常见的并且有着极强特征的客观事物进行模仿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代表着客观事物和现象,必须是让人们一听到拟声词的音就马上可以联想起来的事物。如一听到“汪汪汪汪”这个音,马上就让人想起狗这种动物;一听到“哗哗哗哗哗”的声音人们就会想起流水。这样拟声词就并不是完全的任意了。可是拟声词,也不是纯粹的拟声,而是被音响形象和理念解构了的操作对象,是被范畴化了的概念或心理再现。所以,拟声词恰恰是一种心理上的任意,从更为极端的语言现象中体现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更进一步地分析,人们习惯性地都以为自己听到的是自然物的声音,而其实听到的都是反映到脑子里的理论性,即概念或心理再现。例如,听到泉水声,人们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是泉水?人们对语言最早的接触就是概念,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实践纯粹的拟声行为。而事实上,只要人们去实践所谓的拟声行为,它便已经被概念和音响形象解构了。正因为语言符号是心理实体,所以才出现了同一符号所指对应不同语言符号的能指的现象。无论是拟声词还是普通名词,统一语言符号所指在各种语言中对应不同的语言符号能指,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另外一些合成词也不是完全的任意,在声音和意义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在英语中教授们将可用来板书的板叫做“blackboard”而不是“bluebird”或是其他的词语。索绪尔认为“black”和“board”的合成过程跟词形成了词组的过程很相似,新词组的意思与组成词组的词的意义有关联。这两方面并不是否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恰恰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且是人们不能不考虑的两个方面。
6语言符号的约定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否意味着使用语言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任何能指来表示任何所指呢?不是这样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是就语言起源时的情况来说的,指最初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代表客观事物或现象这个意义内容是任意的,不是说人们可以对语义内容作随意解释。符号的音义关系一经社会约定而进入交际之后,它对人们就有强制性,每一个人都只能乖乖地接受它,个人绝不能随意更改,也无权更改。使用语言的人必须遵守该语言共同体公认的规约即约定性。假如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使用语言,比如把“死”说成“活”,把“高”说成“矮”等等,如果这种任意性没有任何规定性,没有强制性,各人可以自说自话,乱说一套,那么结果是谁也听不懂谁的话,语言交际就无法进行,语言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了。索绪尔认为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起来虽然是自由选择的,但对使用它的语言共同体来说,却是固定的、不自由的[5]。例如:交通灯中红色表示停止、绿色表示通行,这些经过历史的无数次演变已经变成一种人们都熟悉的规则了,不用任何人提醒或告知的常理,如果不理解任意性的真正内涵随意更改的话,那么世界就会处于混乱之中。所以在努力研究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的约定性,这样才能使人们的研究更有意义,更符合已存在的这个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Simpson, J.M.Y. A First Course in Linguistic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9:209—212.
[2]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7—69.
[3]刘润清. 语言学理论与流派[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9—132.
[4]裴文. 普通语言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179—181.
[5]王铭玉,宋尧. 符号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27—129.
(责任编辑:杨阳)
徐珊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湖北十堰442000)
摘要: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包括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任意性的双向性、空符号现象的存在、语言符号所指的张力、拟声词和合成词的非完全任意性,提出人们要真正理解任意性的内涵,要在努力研究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同时重视它的约定性,使研究更符合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约定性
Abstract:With an analysis of the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from five aspects: the arbitrariness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bidirectional nature of arbitrariness, the existence of empty signs, the flexibility of signified and non-complete arbitrariness of onomatopoeic words and compound word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to realize the conventionality of linguistic signs and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arbitrarines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linguistic signs; arbitrariness; conventionality
作者简介:徐珊(1981—),女,湖北黄冈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及翻译。
基金项目:2014年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科研项目“释意理论下的商务英语口译研究”阶段性成果(2014C17)
收稿日期:2015—01—07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36(2015)01—00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