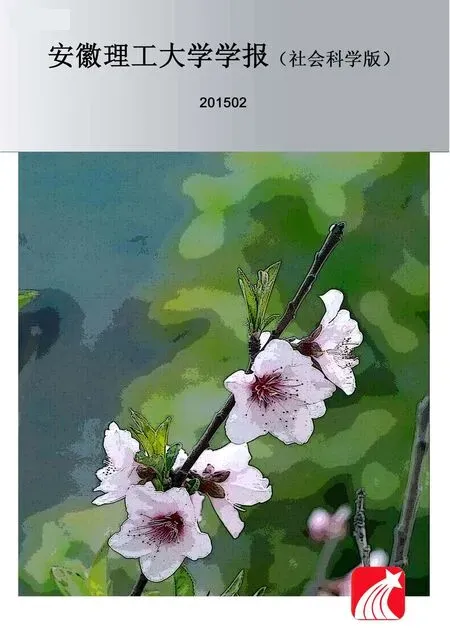论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孙大军
(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淮南 232038)
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消费和现代高科技媒体的猛烈冲击,花鼓灯艺术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淹没于滔滔的现代艺术洪流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虽成学界共识,但其现实境遇却依然面临尴尬;继承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更是谈不到。只有真正认识到花鼓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才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
一、花鼓灯艺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3 700 多年农耕历史的文明国度,地理辽阔,地貌不同,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也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兼具南北方过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灯艺术的美学精神集中展现出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人生观与文化观,体现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花鼓灯艺术的播布区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
自然环境往往会决定人的生存形式,影响人的生活形态,从而也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自古以来,河流区域几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 000 多公里。在安徽境内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淮河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这里季风显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常常造成水旱灾害。历史上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疆域归属不稳定,既受南下的齐鲁礼乐文明之风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吴文化也曾在这里积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构成对安徽花鼓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鼓灯是人们在单调枯燥的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来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人们通过沿途卖唱、广场演艺、半路拦歌、对歌抒怀、小戏压场、抵灯竞技等形式,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通过优美的动作和民歌小调,缓解疲劳,自娱自乐。“玩灯的共有千千万,都是淮河两岸人”这一花鼓灯灯歌唱词,进一步表明了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性特征。
(二)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地域过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线的南北交融与过渡。淮河地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秦岭一起,是我国划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长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筛选、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长;二是历史上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头桐柏地区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区乃是蔡楚文化的发祥地。据记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从河南上蔡迁都州来国(今凤台县)。加之吴楚大战的反复争夺,淮河流域就有了长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从江南移民14 万,以充实中都府(今凤阳以及淮河一带)。这实际上也把江南的经济——文化成分带至淮河两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东瓯、闽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吴越文化之影响,淮河下游的北部又与齐鲁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过贸易、战争等途径对淮河沿岸有所影响;北方历朝历代的战争与征伐,都让人民生灵涂炭。为求生存,人们只能四处逃避以躲战乱,纷纷迁移于淮河两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两岸杂居共存,进行商贸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区也得以集结交融,终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无论是“北歌南灯”,还是“东伞西鼓”,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灯,则是“扇绢”并用、“伞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刚劲爽朗的特点,又有南方灵巧柔美的风韵,兼容南北风韵,并蓄东西优长,具有独特创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灯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热情奔放的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舞蹈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安徽花鼓灯舞蹈成为汉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1]。
(三)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朴道家思想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内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他别的社会所没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灯文化亦是如此。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单位中成长,通过他们使得花鼓灯文化世代流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运行形态和现象。安徽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主要是在水灾频患的淮河中游,高频率、无规律的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淮河两岸具有明显特点的自然现象,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一直面临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却又无法摆脱荒年过后的不同寻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贫瘠,带给人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凝结了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皆诞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则成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资源和食粮。这种精神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态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淮南子》一书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灯播布区,道家这种的逍遥、洒脱与昂扬、欢腾的花鼓灯的即兴性、娱乐性等艺术风貌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农耕文化下汉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灯艺人敬神拜神的传统和灯歌叙事抒情、劝诫说理的价值取向,花鼓灯音乐望风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贴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现手法,都是花鼓灯艺术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体现[3]。正是在这种结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里反复孕育,催生出花鼓灯艺术悲中涵喜、苦中取乐的美学精神气质。淮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长期的求生存斗争中,既直面严酷现实又以坚韧不拔品格不断实现着精神的超越,最终创造出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激情迸发的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遥,是悲剧人生中的憧憬;艺术地展现出苦难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这样说,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铿锵的节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犷中的细腻、坚毅里的豪迈,已经悄然融进了淮河人的血液,成为这里民众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铸为淮河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对花鼓灯艺术的文化认同
花鼓灯艺术是安徽沿淮地区民间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始终是围绕着这条河流,一直传递着沿淮人民的喜怒哀乐,蕴涵着淮河两岸普通百姓的内心精神诉求,花鼓灯原始朴素的灯歌、灵活洒脱的舞蹈、遒劲豪迈的锣鼓,体现出淮河流域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化属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钟爱,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基础。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花鼓灯是在淮河流域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地方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淮河中游的河湾乡村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草根艺术。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两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艺术形式表现着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信念。虽然花鼓灯的流传遍及苏鲁豫皖四省,但却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内的凤台、怀远、颖上等淮河中游地区,并产生过红极一时的影响人物,如凤台陈敬芝,艺名人称“一条线”,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畅淋漓;怀远冯国佩,艺名人称“小金莲”,他的舞蹈花团锦簇,舒展大方;颍上郑九如,艺名人称“小白鞋”,他的舞蹈潇洒飘逸、优美动人。他们从小就在淮河岸边长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响,痴迷并喜欢上了花鼓灯,发展并呈现出来自身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相同的文化“次生态系统”,才使得花鼓灯艺术,能够在淮河流域得到流传,赢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爱,造就了安徽花鼓灯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化生态景观。
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出对象是农民,主要表现农民的耕种收作、婚丧嫁娶、情感及娱乐形式、审美理想等人生内涵,蕴含着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灯常将艺术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如插秧、拾棉花、摇船,端针匾、单挎篮、割麦花、踏车步、推车步等,都纳入表演的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这些大量取材于民间的体裁,让人们在欣赏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唤起亲切的历史记忆,找到精神的归宿。
从接受心理层面来看,花鼓灯的“花”,是女性的象征,过去却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灯的“鼓”,是最核心的乐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灯的“灯”,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儿女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之光。这是获得收成的民众向上苍感恩和礼拜的象征物,更是民众的审美心理的外化形式。这种心理的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说,安徽花鼓灯舞体审美意识的选择乃是花鼓灯艺术传衍的根基,是农民朋友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对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对新时代精神与花鼓灯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互动与联系在安徽花鼓灯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发生学上说,花鼓灯的起源或许与早期民间驱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祷天地的巫术和民俗宗教有关[4]。
三、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又开始实施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须正视的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对村庄集体文化的解构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严重冲击,导致农村现有的传统历史文化民间特色文化日渐消亡,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花鼓灯作为一种农民自娱自乐、存活在农村的原生态地方民间艺术,它艺术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们的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两岸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凝聚着淮河流域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更加有力地显示了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6]。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可以增强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7]。
第一,历史民俗的价值。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花鼓灯始终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繁衍而传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灯的艺术形式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劳动、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风情的记忆,承载着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花鼓灯艺术里面包孕着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性格,是淮河儿女用艺术来呈现认识世界畅想未来的一种灵活的继承方式,这种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人文价值[8]。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方民间艺术,很接地气,深得农民朋友的喜爱,千百年来,他们通过自我结社的形式,在田间地头、宗庙村庄演出,通过灯歌的演唱,对内具有疏导思想、缓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对外具有鞭挞假恶丑社会现象,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花鼓灯艺术通过特定歌舞语汇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古老中国土地上纯朴民众的诗意人生观与旷达人生哲学,体现着乡村社区以仁义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识及其伦理道德风尚,以及这两者完美结合所呈现出来的纯朴而潇洒、自尊而爱人的文化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正与当前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民间文化艺术复兴的背景下,许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花鼓灯艺术作品正悄然实现着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灯歌唱词中依据地方风俗习惯选材,很多内容宣扬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针对社会出现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导着农村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判断。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决定了淮河流域人们对花鼓灯的热爱与迷恋,深受百姓的喜欢,成为农村文明的一种风尚,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别从人类文化学理论建构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各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民间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风民俗为基石的。由此可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在当前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安徽花鼓灯艺术是汉民族地方民间艺术,已经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农民所传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花鼓灯艺术中舞蹈、灯歌、锣鼓等多种艺术的完美结合,已经把生活变得艺术化起来,让江淮儿女诗意生活。花鼓灯艺术中对情感的细致描绘,对人物性格外貌的动作呈示,泼辣中有细腻、粗犷中有妩媚、嬉笑中含真情,体现出淮河南北文化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安徽花鼓灯在艺术领域沉淀的审美观念也日益鲜明独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艺术符号。花鼓灯艺术要求必须扎根于广漠的农村,接触土地上纯粹的农民,才能延续和继承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这些传统文化形式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它淳朴、优美、热情、欢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的就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原汁原味、接地气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四百多个舞蹈语汇,五十多种基本形态步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标志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高度。节奏鲜明自成体系的花鼓灯“锣鼓”,抒情优美、幽默俏皮、即兴演唱的花鼓灯“灯歌”,拧倾的舞姿形态、溜刹的步伐动律的花鼓灯“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灯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时尚文化的强力冲击,安徽花鼓灯这一本土民间原生态艺术瑰宝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一样,正在快速消亡,这一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门口的民间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新思维交织碰撞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态实现“现代性转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已经成为安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只有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指导和改造,在花鼓灯艺术的表演套路、服装道具等进行改造,提高其品质型、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我们更要重视民间传统艺术人才的发掘,他们是淮河流域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作为活态传承人,保护和传承大量地方民间文化,让灿烂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地方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社会发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灯艺术需要创新传承,它不仅能够使安徽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农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实质性的丰富和提升。尤其是,作为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水准的汉族民间艺术,花鼓灯是淮河流域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基石。离开了传统,特别是脱离了民间文化传统,任何新文化建设都难以避免走向“底气不足”乃至呈现“空中楼阁”态势。
[1]赵士军.花鼓灯活态传承中的三维构建[A].谢克林.中国花鼓灯学术论文集[C].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4.
[2]露丝. 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3]喻林.花鼓灯音乐的道家文化阐释[J].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3(1):11 -16.
[4]潘丽.花鼓灯的现实调查与保护的思考[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院,2007:17.
[5]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新农村文化[J].建设文化遗产,2010(2):1 -5.
[6]马智敏. 对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建议——基于安徽R 村的实证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3):39 -42.
[7]周楠.花鼓灯文化生态村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改革与开放,2012(11):182.
[8]黄永林.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现代与传统[J]. 民俗研究,2008(4):14 -23.
[9]王强,朱惠斌.以民间传统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可行性分析[J].天府新论,2010(6):102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