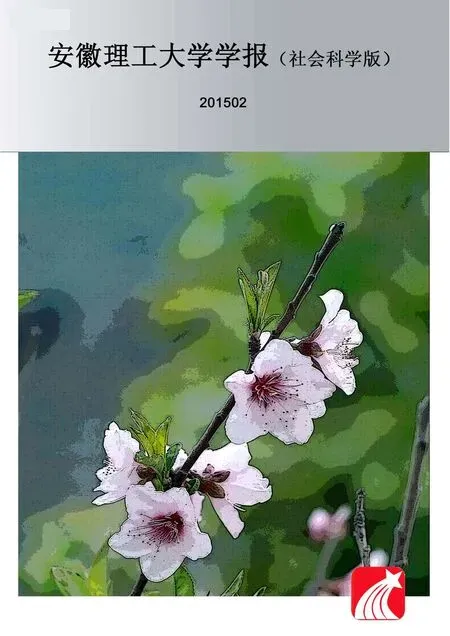论《淮南子》性命哲学的和观念
王硕民
(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 基础部,安徽 蚌埠 233011)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性命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原为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易·乾》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天寿之属也。”朱熹本义云:“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易传》又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见之“性”显然指人的情志,“命”即天命。其后道家养生学说则以性命合为人的生命,十分重视“性”“命”这两个人类固有的本质元素,将性视为精神的生命,命作为肉体的生命。《淮南子》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以道为统揽,将先秦的“和”观念用于修身养性中,论者亟言性命精神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具有对立统一规律价值的性命哲学观念。其中性出现175 次,命150 次,性命连用16 次,和149次。淮南子的性命之和,就是要以“和”求得修身养性的自觉,从而臻于养生的最高境界。今天系统研究《淮南子》性命哲学的“和”观念对于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必须调适阴阳之和
经过长期战乱后的汉代前期,处于相对和平状态,一些贵族逐渐贪图安逸,纵情声色犬马,既戕害身体,又误政事。为此,有思想家借鉴前人的修身养性主张,要求既要强身体,又要修德行,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1]1。在淮南子看来,要利于性命的修养一切就要达到“和”。“和”为产生于先秦的古老哲学命题,淮南子将其继承发扬,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将和视为应遵循的客观规律,人类从事一切活动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既可以用在认识自然万物的生长,也可以用于认知、指导人类社会的和谐动作。
首先将“和”用在对自然万物生长规律的认识上。淮南子认为万物和辑是“达道”的关键步骤,自然万物生长都需要“和”。《俶真训》认为,从“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的初始之时,就需要“被德含和”。《天文训》提出了“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的命题。假如,“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而将风调雨顺,收成好称为“岁和”。阴阳变化,四季往来如此,五行相治,也得相互融和,才能成为器用。《览冥训》云:“故至阴飂飂,至阳赫赫,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而至阴寒冷,至阳酷暑,只有阴阳接触交融合成中和之气,才有万物的产生[2]91。《泰族训》云:“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氾论训》则强调指出:“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万物生长成熟都离不开精纯的中和之气。这即是阴阳二气交和合便产生万物的生命繁衍规律。
人类生长当然也要“和”。《氾论训》辩证地指出:“积阴则沉,积阳则飞”,只有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人生的十月怀胎则是阴阳二气合和所致,《精神训》引老子云:“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证此理。《本经训》证实:“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本篇还说:“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和”贯穿一切。早期《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就提出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个符合朴素辩证法的生命哲学观念。
推而广之,其他社会活动也离不开“和”。淮南子认为“和”可以指导办一切事情,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治家理国也要“和”,且要实现“太和”。《主术训》认为君主的举动要慎重,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就会达到“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兵略训》指出治军打仗也要“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如此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览冥训》还深刻指出:“故以智力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治理国家仅靠耍小聪明或武力打压是难以长治久安的,“通于太和者,惛若纯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为此《说山训》断言:“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
修身养性同样需要“和”。“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沈浮俯仰”;如果能够把握“和”的规律,就能“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2]18。如此,《原道训》有“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与“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之说。《俶真训》说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而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以此告诫人们不能让外界事物来扰乱自己的性命,而应“以顺于天”。性与命,一者是精神的,一者是物质的,二者相辅相成,这就犹如乌号之弓、谿子之弩,不能无弦而射,越舲蜀艇,不能无水而浮[2]33。
要保持健康的天然本性,就应“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就能够达到“其为欢不忻忻,其为悲不惙惙”。如此,喜怒哀乐就不会伤身[2]13。《俶真训》云:“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如此“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祸福弗能挠滑,非誉弗能尘垢,故能致其极”,则可“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论者以道始,数言“和”对持养性命精神之重要,强调正确处理好天人的关系,行为符合道的运行,注重以“和”修身养性,近可修身齐其家,远可治国平天下。
二、法天顺情,欲不过节:必须导引情礼之和
而要修身必先正心诚意,规导情礼之和。为此,先应寻找影响性命不和的根源,《本经训》认为“情欲”则是一个主要因素,指出:“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人之情,即“思虑聪明喜怒”,情是人的思想、心理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客观存在的。高诱注:“情,性也。”《论衡·本性》以为,“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礼记·礼运》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此七情弗学而能。东汉许慎说“情”是人之阴气有欲者。淮南子则认为情是人的本性。《俶真训》提出“古之治天下也,必达乎性命之情。”“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精神训》批评道德衰败、趋附舍本逐末学说的人,是“内总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悲人。”《淮南子》中情与性命成为密切关联的因素,且“性命之情”的提法多次出现。
关于这方面淮南子作了较为深刻而系统的论述。淮南子认为“情”对正心有极大的干扰,是影响性命修养之本原,在开篇就分析了性命与情之间的关系:“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2]16《诠言训》要求“适情性,则欲不过节”,如此“养性知足”,这就赋予情关乎性命修养的谐和理念。本篇从朴素唯物辩证法角度将维系人生命的因素归结为“正”与“邪”两个对立方面,指出邪与正相伤。由此,引入“欲”与“性”相害的理论,且二者不可两立,必须以正压邪,这样邪气才不会浸入肌体,从而远离百病。反之,以邪压正的人,必然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而自伤其身。因此指出:“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强调以“和”处理好性情的关系,得出“益无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的结论。
且在干扰性命之情中两性关系之“情”为害最为突出。早在淮南子之前,古人就承认两性之“情”的合理性。《周易》就有“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3]67之说。这就是用天地运行与阴阳和合产生宇宙万物规律来比附男女交媾孕育新生,承认男女之间“情”的客观性。基于此,淮南子认为必须处理好男女之情,明此理可葆身修性养。《精神训》给予情欲的肯定,提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提出了“法天顺情”和顺的性命观念,以求达到身体的和谐。淮南子还指责当时的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这就好比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同样,治理百姓,修养性命如同畜养禽兽,不堵塞好苑囿围墙的缺口,使其产生逃走的野心,而系绊其足,以禁其动,然后“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并说孔子之“通学”弟子颜渊夭死,季路菹于卫,子夏失明等,皆因“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虽有些偏执,但却揭示了人伦正常之情不能遏制无疑是正确的,今天看来这也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命哲学。
而淮南子在肯定保持男女常情的同时,又提出对情欲必须加以正确疏导,提醒人们应该有所节制。《谬称训》深刻揭示“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的道理。《精神训》指出:“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皆人累也”。所以说,嗜欲使人之气越,好憎使人之心劳;如果“弗疾去,则志气日耗”。这一理论旨在以内在的理性抵制外来的诱惑。汉代的性命哲学也试图从这方面来寻找根据,认为节欲是养性的重要途径之一。枚乘《七发》则以文学手法揭示此理:“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从生理上来说,人一旦过于动情,则易耗损精气,影响健康。《韩非子·扬权》早就有“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之说。《易林·家人之临》直接提出“节情省欲”。此可为《淮南子》逸豫害身理论的佐证。由此,《本经训》云:“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也赞同用礼乐节制情欲,调适血气之和。
三、形神气志,各居其宜:必须保持形神之和
淮南子主张调节好精、气、神与志之间的关系,也是达到以“和”修养性命的重要环节。在他看来,只有保持精气神,才能使气血充盈、形神调和,体安志明。《原道训》开篇就揭示:“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泰族训》指出:“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而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俶真训》云:“神清者,嗜欲弗能乱。”人有五脏六腑,七情六欲,而精、气是维系性命的重要元素,精气神与性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看精、神与气的内在联系。淮南子在《精神训》中则解说:“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指出精神、形体都源于大自然。《主术训》又说:“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足见人之精气与天地的密切联系与极为难得而可宝贵。古人认为人的精气神是上天赋予的,与天地相通的媒介是气。《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这就是说气是无孔不入的。《礼记·祭义》指出气与神也是密切关联的,云:“气也者,神之盛也。”《论衡·无形篇》云:“形、气,天性也。”认为形与气都是人的本性。《灵枢·岁露论》说“腠理开则邪气入”,当然影响身体健康。西汉经学家韩婴则肯定了“气”在人体中的物理作用,认为人的身体“莫贵于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在吾身也,不可不慎也”[7]769。王充深刻认识到人的性命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提出人寿命的长短取决于气之强弱的观点:“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荀子·修身》早就提出“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白虎通》云:“精者,静也,太阴施化之气也,象水之化,须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阳之气也,出入无间,总云肢体万化之本也。”[5]390以为精、神都与气有关,是人身体变化的根本。先前的《吕氏春秋》就认识到精气的重要作用。《尽数篇》指出:“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强调精气不但赋予了万物的功能特性,而且还赐予人类的智慧,“集于圣人,与为敻明。”因而,《淮南子·原道训》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这就形象地体会出了性命与形、气、神之间的关系。高诱注《精神训》云:“精者人之气,神者人之守也。”《俶真训》深刻指出:“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复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这就叫做“失道”。因此《原道训》开篇就要求:“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
再看气与志的涵养关系。《精神训》认为:“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如此,“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犹未足为也,岂直祸福之间哉!”这里从道家守静的观念看待精神,阐释了深刻的精气神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持精神之重要,有哲学的也有医学的。古人早就从精神意识的角度探讨气与志的关系,认为保持身体的元素就是“气”,而前者属于物质的,后者属于精神的,二者互相联系,共同维系人的生命。《孟子·公孙丑》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既曰: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认为人的“气”要受到思想意识“志”的支配。东汉赵岐注:“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志帅气而行之,度其可否也。”气本来是由志来导引、支配的。孟子还认为“气”可以养而得,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汉初陆贾《新语·怀虑》所说的“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流于外”与此也是一致的。《本经训》进而分析,如果迷恋“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这就“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这种思想似受到《易·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的启示。
因而,形神气志要各得其所。精气神相互贯通,形成了情损精,而精生气,气凝神,志帅气,气保志的逻辑关系。《原道训》说:“夫形者,生之所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因此,形体如果处于不适的环境就会伤残,气血如果运行不当就会泄失,精神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昏昧。对此三者,不可不慎守。“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俶真训》进而指出:“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如此,就能“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虽显夸饰,但说明保持精神之和,对于修养性命有着无所不通的作用。
四、调理情性,端正心术:必须臻于执中之和
淮南子认为调和精气神以修养性命还要“执中”,提出“执中含和”的命题。《缪称训》指出:“情系于中,行形于外。”《齐俗训》又说:“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因而“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2]115,如果关乎性命之情相互胁迫而不止,就产生体内的不和。《原道训》又指出:“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鉴此,《泰族训》认为有大气慨的人应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季协调。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能够坚执中庸之道,秉持和合之气,不但利于个体的修养,而且有利于治国理政,且能够达到“神化”的境地。《道应训》引老子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是达到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淮南子这里所说的“中”不是方位词,而是哲学概念。《说文》云:“中,内也。”内,即内心。《淮南子·原道训》云:“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高诱注:“藏之于胸臆之内。”又“是故内不得于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这里的“中”都同“心”。《史记·乐书》论:“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张守杰正义:“中,心也。”曹操《短歌行》有“忧从中来”诗句。“中”还有“正”的意思。《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贾公彦疏:“使得中正也。”《晏子春秋·内篇》说:“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张纯一注:“中,正也。”因此,《荀子·天论》要求:“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作为“和”的相关哲学概念,“中”较早见于《论语·尧曰》“允执其中”。刘宝楠《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之用。”《礼记·中庸》引孔子言:“舜其大知也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而用中,舜所用尧之道也。”此“中”是不偏不倚之意。《中庸》还将“中”与“诚”相联系,说:“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也是《中庸》提出的人格追求,就是端正心意,无自欺。“中”还被荀子赋予具体内容,云:“曷谓中?曰:礼义是也。”[8]82中,就是规范人们心性与行为的法度。
有时将“中”与“和”合二为一。《管子·正》有“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荀子·劝学》认为乐乃“中和之纪”。《淮南子·泰族训》进而深刻理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论。但是,中与和二者是有区别的,又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用于修性养命哲学,中则处于和的本原位置。郑玄注:“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朱熹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由此可见,“中”即位置,不偏不倚,也是内心,是情所能控制的持正稳定最恰当的地步;“和”即协和,是状态,也是结果,则为性情不相互抵牾的平和融洽的最佳境界。
淮南子进一步阐释了由中致和的奥妙。《原道训》云:“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中之得则五藏宁,思虑平;精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鞼”,详细地破解了“中”对于精神的规范作用。《精神训》要按照“至道”要求,“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就能“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如果“性有不欲,心有不乐”,即可“无乐而不为”。《缪称训》称:“诚中之人,乐而不忣,如鸮好声,熊之好经”,同样能够达到“养以和,持以适”的境地。淮南子在这里将由“中”到“和”的严密逻辑关系细致地表达出来。所以,淮南子认为修身重要的是心一专诚,如果“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悦亲有道,修身不诚,则不能事亲;诚身有道,心不专一,则不能专诚[2]152。“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2]155,心诚则灵。圣明君主应“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2]349。因此,《诠言训》强调:“圣人胜心,众人胜欲。”这一观念虽然有些偏见,但说明只要通达圣明就能抓住治心去欲修养性命的要诀。《泰族训》说:“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没有得己而失人的,也没有失己而得人的道理。
因此,修身养性要回归素朴淳真状态,就要从治心开始,即从思想源头上加以修治。鉴于“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逸矣”,《原道训》倡言:“彻于心术之论,则嗜欲好憎外矣!”首先要以治心术倡导乐道安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淮南子的“治心术”,就是以整治思想,净化心灵,导引人们安分乐道。《诠言训》强调“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人们能够懂得天命,则不惑于祸福,动静循理;端治心术,则不妄喜怒,赏罚不阿;理顺好憎,则不贪无用,不以欲用害性;调适情性,则欲不过节,养性知足。《本经训》还要引导人们“心反其初”,回到和顺而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的“太清之始”,民心即可向善。这就要从思想根源上获得认识的超越,用心诚悫,益于修身养性。
五、综论
《淮南子》继承发展了先秦思想家的“和”观念,是集大成者。在道的统揽下,淮南子赋予性命之学以广泛而特别的内涵,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倾向。《要略》论述了作《泰族》的主旨足以明确:“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以达到“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此为治国之大本。这一高论在今天对于人们修身养性,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朱熹.四书五经(上).大学章句集注[M].北京:中国书店,1985.
[2]刘安.淮南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朱熹. 四书五经(上):周易本义[M]. 北京:中国书店,1985.
[4]班固.汉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5]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彭铎.潜夫论笺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韩婴.韩诗外传[M].上海:上海书店,1982.
[8]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