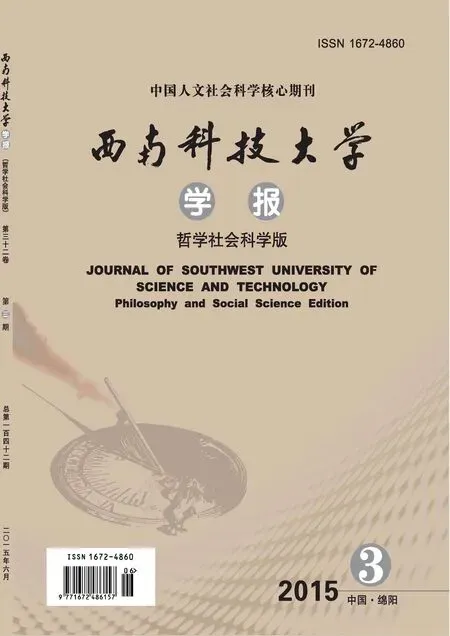形式美的移植和古诗英译的审美再现
周建华
(巢湖学院外语系 安徽巢湖 238000)
形式美的移植和古诗英译的审美再现
周建华
(巢湖学院外语系安徽巢湖238000)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古诗的内涵和意蕴无法脱离古诗的形式而存在。古诗英译时,只有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特征移植到英语文本中,才能在译文中再现中国古典诗歌所独有的形式之美,才能在译文中真正体现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因此,在古诗的译介中,译者应该充分关注古诗的形式,尽力移植古诗形式特征,并传达这些形式特征所蕴含的美学意义,从而实现古诗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诗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美;文化移植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翻译家们孜孜以求,致力于斟词酌句,试图完美地传达诗歌的意蕴和风格。然而,译者们上下求索的翻译实践却被评论家们断言为“诗歌不可译”,故而英国诗人雪莱叹息译诗无用[1]58;鲁迅先生也认为译诗是出力不讨好的事[2]72-76。著名翻译家纽马克认为译诗是翻译中损失最大的[3]15;翻译家杨绛也认为“愈是好诗,经过翻译损失愈大”[4]347。如此一来,似乎诗歌变得不可译,中国古典诗歌更不可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部分,古典诗歌的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古典诗歌有其独特的形式风格特征,这些形式风格承载了独一无二的东方美学诉求。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古典诗歌形式风格及其审美意义的译介理应受到译者的格外关注。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古诗英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有着独特美学价值和审美意义的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特征,并让这些形式特征的审美意义即古诗的形式美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和传播。
一、翻译与诗歌形式的译介
翻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完成翻译的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地纠结于如何处理文本的形式、文本的意义、文本的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庞德以意象为重;苏珊·巴斯内特以文化为根;功能派强调效果;阐释学着重吸收和补偿。然而不论哪一派那一家,文本的形式是最不受关注的,也似乎是翻译中最先舍弃的那个部分。
然而“文学翻译所要表达的绝不限于原作的基本意义”,文学翻译还要考虑原作的语言风格。作品风格往往体现在作者的遣词造句之中,即与原作的语言形式密切相关,因此译者需全面细致地理解“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并使读者也能获得同样全面而细致的理解和感受[5] 8。“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义,也只附在字句上”[4]347。刘宓庆所提出翻译审美再现的4点基本要求就包含形式特征,他认为在双语可译性限度内,应充分保留原语的行文形式体式[6]218-219。可见文学翻译必须考虑和关注原文本的形式特征,而不能仅仅重述原文的主要内容,应该在译文中着力体现原文这种语言形式上的风格特征,即使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语言形式,也要尽量寻求替代性的语言形式,让原文的风格和审美价值得以再现。这是文学翻译的独特性所要求的,也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是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而著称的,因此诗歌翻译更要注意其形式特征,以及这种形式风格在译文中的审美再现。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格律都是古典诗歌重要的特征。即使是近体诗或自由诗也有一定的音韵形式特征[7]174。 译诗应尽量保留原文特点,并让译文能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相似的语用效果。苏珊·巴斯内特也认为:“诗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的”[1]69。诗歌的形式意义决定“诗歌翻译的原则应该是更要忠实于原作, 所谓为了‘神似’而不必苛求‘形似’,至少在诗歌翻译方面是必须抛弃的”[8]50-53。翻译诗歌的“首要问题就是形式与意义(内容) 的统一”,可以通过“形美”更好地为“意美”服务[9]83-88。就诗歌翻译而言,“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形式不同,意义和所传递的信息就不同,”形式对等“是衡量译文合适性的一个标准。[10]21-23可见,诗歌的形式与其他文本的形式不同。如果说翻译语言学派认为语言形式决定语言的意义过于极端,那么在诗歌这种文体中是基本适应的。由于诗歌是形式和意义的综合体。无形不成诗体,不但诗歌的”传形“和达意本为一体,且诗歌的形式也是其作品风格的集中体现。甚至可以说诗歌形式本身就是诗歌部分甚至大部分意义所在,诗歌的形式如果在译文中找不到替代的语言形式,那么在翻译中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以其句式工整对仗,音韵朗朗上口而著称。此外中国古诗形式简洁,意蕴含而不露,是东方含蓄美学的极致体现。古诗往往”意寓于形“,”意“与”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的语言形式对于意义的表达与传递有着重要作用[11] 246-249。许渊冲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要关注3美的原则,即”意美、形美和音美“。翻译古诗时“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这是形美”;译诗要使得译作“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这是音美”[12]85。然而,许渊冲的形美主要是指古诗的视觉上的形式,其实古诗的音美也是由其形式上的特征所产生的。而古诗的意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诗歌独特的形式特征。
由以上论述可知,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时要注重形式特征的译介,尽量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特征,即尽量寻求形式上的对等。中英语言的巨大差异使得翻译时很难找到与原文形式一一对等的语言表述结构,我们就需要在译文中体现原诗形式特征所自涵的意义(这里指与诗歌阐释的意义相对形式本身所体现的历史、文化、文学等意义),尤其要关注和体现原诗形式所体现的独特中国诗歌风格和审美意义,即使不能找到对等的语言结构,也要在译文中再现出原诗的这些形式特征所体现的风格和审美意义。
二、古诗形式特征的审美再现
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独特形式,是意义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体。诗歌的意义无法脱离形式而存在,诗歌发生任何形式上的改变都将导致其意义的变化。因此翻译古典诗歌时,对于意义和形式的任何比较和权衡,都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与众不同的形式特征,它的遣词造句、意象、音韵等形式特征都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一)古诗形式对称美的再现
中国古诗以其形式的工整对称而著称。对形式工整对称的讲究也是东方美学中对于平衡和谐的一种追求。朱光潜认为对仗和排偶是古典律诗的基本特点,是源于对事物成双成对规律的追求,这种形式特征在他看来是诗人的一种“审美游戏”[13]81。对仗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常见的诗歌对称的形式,学习做诗往往都是从对句开始的。通过相邻句的对应字词相对或对比,给读者一种对称的美感和效果。这种对称的形式如果无法在译文中得到体现,那原诗的美就损失了大半。比较下面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两种译文。
译文1:I raise my head,-/
The Splendid moon I see:
Then droops my head
And sink to dreams of thee-
My fatherland, of thee! (克莱默·宾译)[14] 82
译文2: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away home. (Tr. S. Obata译)[15]418
两种译文都传达了原诗的主要意义,表达了诗人在旅途中对月思乡、孤独寂寥的哀伤之情。S. Obata的译文极力保留原诗的形式,尤其是4个动词raised,bowed ,looked out, thought of与原诗一样两两对应,体现了原诗的对称之美。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前两句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诗中“白日”与“黄河”相对,“山”与“海”相和,“依”和“尽”分别对应“入”和“流”。诗句对仗工整。
译文1:The pale sun is sinking behind the mountain.
And the Yellow river is running toward the sea.(王守义,约翰·诺弗尔译)[16]6
译文2:The mountain is eating away the setting sun;
Going seawards the yellow river is on the run.(吴钧陶译)[15]421
译文2诗句的末尾“sun”和“run”押韵,采用了英文诗歌尾韵的形式,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但是没有译文1对原诗形式上的关注,失去了原诗工整对称,简洁直白的文风。
下面两篇译文通过运用形式对等的原则,通过模拟原诗诗句,即用词和句式一一对应的形式特点,体现了原诗的形式对称之美。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前两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被许渊冲译为“Crimson rain swirls in waves under our will./Green mountains turn to bridges at our wish”[15]166。
译文完全采用原诗的形式,体现了中国古诗形式对仗的特点。其中“Crimson rain(红雨)”对应 “Green mountains(青山)”,“swirls in waves(翻作浪)”和“turn to bridges(化为桥)”结构相同,而“under our will(随心)”和 “at our wish(着意)”完全对等。可以说许渊冲的这两句译文是英文写就的中国古诗。而许渊冲的另一篇译诗也是如此。“The pathways red with cherry blossoms/ The lakeside green with willow leaves.”[15]166是翻译周恩来《春日偶成》中的两句诗“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译文与原诗形式几乎完全一致,用词未做任何增减。译文对仗也异常工整,更难能可贵的是“红”“绿”不但相互对应,而且与原诗一样都活用为动词,生动活泼,春意盎然,堪称一首中国古体诗的佳作。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提出的横向裂缝评价模型,采用江苏京沪高速公路和沿江高速公路路面横向裂缝实测数据进行分析,这两条路均为半刚性基层沥青混凝土面层,其中京沪高速公路基层为38cm的二灰稳定碎石基层,沿江高速公路基层为38cm的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分析结果汇总于表1所示。
除了对句,古典诗歌中还有其他一些手法能体现诗歌的对称美,如回文诗就是对称美的典型代表。回文诗不但诗句之间对应工整,而且順读倒看皆可,因此翻译回文诗作应该对其形式着重关注。如王安石的回文诗《碧芜》“碧芜平野旷,黄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饮,身闲累苦吟。”,正读反读皆成诗,译文中如果忽视了这种形式上的回文特点,原诗的妙趣就荡然无存了。
中国古典诗歌对形式的对称非常讲究,许多经典古诗不仅意蕴深远,而且对仗工整。形式对称工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风格特征,只有关注了古典诗歌形式上的这种对称,并将这种对称的语言形式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中国古典诗歌独有的对称美才能通过译文得以传播。
(二)古诗形式音韵美的再现
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适合吟诵,诗的美不仅在于它娱目宜心,更在于它悦耳动听,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如此。诗经中多篇均为古代劳动人民劳作所唱的号子,乐府诗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词是根据歌者乐者所奏所唱的词牌创作的,而诗人做诗一般称为吟诗。“吟”即“诵读”,也是边“作” 边“诵”之意,其中含有声音上、文字上的艺术加工之意,即通过“吟”使声音发生抑扬顿挫的变化,因此“吟”包含有形式感的考虑[17] 19-27。由此可见,诗歌如同音乐一样,有其独特的韵律特征和音韵之美。故此,翻译时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尽可能地再现古典诗歌的音韵上的形式特征,让其审美意义得到再现。
中国古典诗歌除了采用平仄押韵等音韵手法来体现诗的音乐性,还有一些独特的形式特征,如采用叠字和重复来表达诗的音韵之美,用叠字和反复来模拟歌曲回环往复的音韵特点。提到叠字运用就不能忽略李清照的《声声慢》。李清照在这首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叠字手法,诗的开端一连用了7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7个叠字将诗人的清冷生活和凄苦的心境渲染到了极致。叠字正是这首诗的独特之处,而翻译这首诗就无法回避叠字这种形式。比较下面两种译文:
译文1:I’ve a sense of something missing I must seek
Everything about me looks dismal and bleak.
Nothing that gives me pleasure, I can find. (徐忠杰译)[15]425
徐的译文忽视了原诗的音韵特征,不但损失了诗歌朗朗上口的音韵之美,更无法体现原诗通过叠字重复体现的伤感的主调。林的译文虽不能完全模拟原文的形式,但通过运用英文的重复和头韵的修辞手法,再现了原文的音韵美。表面上看来,林的译文的选词和意义好像与原文相差甚远,但通过dim, dark, dense, dull, damp, dank, dead这一系列阴郁、伤感词汇的叠加,完美地展示了原诗所表达的情感。
下面3首诗译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处理原诗的叠字,既保留了诗歌的音韵美,也体现了叠字在意义和情绪上的渲染和强调。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译文“Deep, deep the courtyard where he is, so deep”[19]67通过3个“deep”的重复体现了原文音韵上回环的效果,并通过句式的强调将最后一个“deep”独立出来并用修饰语“so”进一步加以强调,表达了欧阳修《蝶恋花》原诗所表达的幽深寂寥的意境。而将温庭筠《梦江南》“斜晖脉脉水悠悠”一句译为“The slanting sun sheds a sympathetic ray, The carefree river carries it way.”[19] 21则运用了头韵的手法体现原文的绵长悠远的音韵美。而用“You wave your hand and go your way; Your steed still neighs, ’Adieu! Adieu!’”[20]58来译李白《送友人》的诗句“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采用了拟声词Adieu的重复来体现原文“萧萧”两字的音韵特点和叠字所表达的友人远去马鸣萦绕不散的惜别之情。
除了叠字,中国古典诗歌也运用词句的反复来产生一种音韵上的回环反复的美感。与叠字翻译不同,英文创作中也有“重复”这种修辞手法。因此,可以用重复的修辞格来翻译古典诗歌反复的形式特征,尽量体现原诗的音韵美,从而真正地传达原诗的意蕴。如许渊冲所译的《丑奴儿》,就用了重复的修辞格来翻译原诗重点词句反复的形式特征。原诗“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用了两个重复结构,而译文“While young, I knew no grief I could not bear./I’d like to go upstair,/ I’d like to go upstair./ To write new verses, with a false despair./I know what grief is now that I am old,/I would not have it told,/I would not have it told./But only say I’m glad that autumn’s cold./”[19]167直接用了两个相应的重复结构直译原文。译文通过移植辛弃疾原诗的重复结构及其音韵特征,突出体现了诗人欲说还休的愁绪,将诗的形式和含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古诗反复手法运用的极致表现是顶针诗。如《乐府古词》中收录的一首《青青河畔草》,就是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写就的。“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句与句之间,首尾相连,绵延不断,仿佛一女子反复地吟唱着对离别爱人的绵绵情思。如果在翻译中忽略了诗的形式特点,就失去了原诗音韵之美,而在表达诗人缠绵不绝的思恋之情时,便会有所欠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英语言的巨大差异,古诗英译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和原诗一一对应的音韵形式。但是音韵美恰恰是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在翻译中应该受到足够重视。译者即使找不到完全一样的语言形式,也可以寻求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原诗形式上的韵律美感,让古诗的音韵之美在译文中得以保留。
(三)古诗形式简洁美的再现
中国古典诗歌以其形式简练含蓄而著称。古诗和中国写意画一样,往往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画面,表达出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思想情感。这种形式简约的特征突出体现了东方文化简约含蓄的美学特征。与此同时,这种形式的简约往往得益于中文表意文字和意合的语言形式特征,而英文是拼音文字,其句法是形合的特征。更何况西方文化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注重形式规范,因此英文表达中往往注重衔接和指示,宁可繁琐也不能失之规范。因此译者往往通过添加各种连接成分来翻译诗文的意义,古诗的简约之美也因此在翻译中遗失。
中国古诗在创作中使其形式简约的方法有很多种,如多用单音节词;省略人称和连词;多用典故等等。其中“列锦”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简洁的极致体现,往往通过将多个物象直接排列在一起,简约地勾勒出诗人所要描写的情景,用白描的手法凸显隽永的意蕴和深沉的情绪。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就运用了列锦的手法,将明月、树枝、惊飞的乌鸦和午夜、清风、蝉鸣的多个意象直接并列在一起,不添加任何的联系词汇,也不作任何的评述,简约而意蕴深远,符合东方美学的含蓄隽永的特性。而许渊冲的译文“Startled by magpies leaving the branch in moonlight,/I hear cicadas shrill in the breeze at midnight。”[19] 173增加了“by,in,in,at”等4个介词,和“leave, hear”这两个动词形式,并增添主语“I(我)”。原文中的鸣、惊虽是动词,但目的是为了衬托夜的寂静。而“鹊飞”隐在意象之后,并未在文中突显出来。译文中10个实词就有4个动词,与诗意所要体现的寂静不符。而人称代词“我”的添加也破坏了原文的含蓄之美。原诗对叙述者故意不提,可以将所绘之景和所述之感与作者脱离开来,形成一种距离之美。这种脱离作者主观的情景意境,方便了读者的移情。更重要的是原诗通过意象直接叠加所形成的简约之美受到极大地损伤。
再比较一下陆游《钗头凤》前两句的两个译本。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译文1:What soft, ruddy hands with a beauty of line,
As they pour for me exquisite vintage wine,
All over town are signs and colours of spring:
Willows along the walls form a festooned string. (徐忠杰译)[21] 98-99
译文2:Pink hands so fine,
Gold-branched wine,
Spring paints the willows green,
Palace walls can’t define. (许渊冲译)[19]144
陆游运用了列锦的手法,寥寥数语勾画出红袖添香,把酒言欢,春意浓浓,情谊深深的旧日幸福生活,删繁就简,形式简约。而这种简约恰恰突出了旧日生活在作者脑海中所留下的最深刻印记,最突出的意象——那把盏的芊芊玉手;隐去了一切背景和装饰,作者的眷恋之情也由此得到突出和渲染。在译文1中,短短12个汉字扩展成了32个英文词汇,原诗的意思虽得到了准确地传达,但简约的风格荡然无存。许渊冲的译文虽没有将意象直接放置在一起,但可以看出译者极力删繁就简,保持原文简约的风格。
许的译文虽未完全体现列锦的简洁之美,但体现了译者对应这种独特的古诗形式文化的自觉性。当然,也有译者试图直译列锦手法,如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译为“Where is sobering place? /Willow trees, river bank, morning breeze, waning moon”[22]125-128,其中第二句译文诗直接移植了原文中列锦这种形式特征。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前3句每句直接由3个物象并置而成,是列锦手法的集中表现。多位译者都曾较完美地体现了原诗简洁的表现风格。如Schlepp的译文“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k,/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s.”[23]331。周芳珠的译文“Withered vine, old tree, a raven at dusk crows,/Tiny bridge, thatched cottages, the stream flows,/Ancient road, bleak wind, a bony steed slows.”[24] 97也与之类似。两位译者的译文虽然选词和韵律各不相同,但都注意到了原文采用列锦手法的形式特征,并极力保持原文的形式特色和简约的风格。
中国古诗形式简洁而意蕴深远,由于中、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古诗英译中,译者为了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并较完整地传达原诗的意义,往往需要增添许多词语和句子成分,因此古诗英译中,中国古诗的形式简洁的风格和美学意义往往难以传达。然而如果无法在译文中体现出中国古诗的形式简约之美,就不能体现原诗所要表达的含蓄而深远的意境,也谈不上传达东方诗歌美学的意蕴了。
诚然,中国古典诗歌具有美学价值的形式方面的特征远不止本文分析的这几种,古典诗歌的形式美更不局限于对称、音韵和简约这几个方面。因此,在古诗英译中,要深入分析诗歌的形式特征及其蕴含的审美意义,然后在译文中找到相应的语言形式,再现原诗形式特征所体现的审美意义,把古诗的形式美移植到目的语文本中。著名诗人、翻译家庞德曾极力移植中国古诗独特的形式特征,尽量保留中国古诗的语言形式风格的原貌,采用直译法来翻译中国古诗诗句。尽管译文对目的语受众而言非常陌生,但《泰晤士报》评价他的这种译法是最恰当的,认为这种“奇异而优美的原文直译,能使我们的语言受到震动而获得新的美”[25]229。可见在古诗英译中,如果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宁可采用陌生化的直译,也要传达原诗的形式风格特征及其美学意义。
结语
中国古典诗歌有着独特的形式风格,这种形式风格往往承载了一定的美学价值和意义。译者想要将这朵东方文学的奇葩分享给西方读者,就必须承担起完整地将其意义和形式综合进行译介的责任。如果仅仅将视觉停留在讨论究竟内容重于形式抑或形式高于内容,这对于古诗英译而言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译者只有在译文中体现出中国古诗的形式特征,才能体现原诗所要表达的含蓄而深远的意境,真正传达东方诗歌美学的意蕴。因此古诗英译时,要尽可能完美地移植中国古诗的形式特征,即尽可能寻求形式上的对等,尤其蕴含着独特东方文学和美学价值的形式特征。即使无法找到对应的语言形式,也要利用多种方法,甚至不惜采用陌生化的直译来传达原诗的形式风格特征,让原诗的形式美在译文中得到再现。
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不仅仅是承载意义和思想感情的容器,它本身就体现了更为重要的文学和美学意义,这也是进行这种跨文化翻译的目的所在。因此就翻译的目的论而言,古诗形式特征的译介和形式美的移植,也是古诗英译的关键所在。译者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诗的目的是将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和美学价值从源语言介绍到目的语,从而丰富这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中,通过对诗歌形式特征及其审美和文化价值的传达,可以促进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从而达到苏珊·巴斯内特对诗歌翻译的期望[1]66:诗歌并没有在翻译中损失,而恰恰通过翻译而有所得。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san, Andre Lefebvre.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58,69,66.
[2]斯宝祖. 从译诗难谈起[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1):74-76.
[3]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15.
[4]杨绛. 翻译的技巧[A].//杨绛文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347.
[5]金隄. 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8.
[6]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修订本)[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218-219.
[7]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74.
[8]金文宁. 从《荒原》的几种译文谈诗歌翻译的特殊性[J].中国翻译, 2002(3): 50-53.
[9]崔德军. 日本俳句的翻译形式和意蕴——以许渊冲“三美”思想作指导[J].宜宾学院学报, 2013(10):83-88.
[10]黄国文. 从《天净沙秋思》的音译看“形式对等”的重要性[J].中国翻译, 2003(2): 21-23.
[11]曾祥宏. “三美对等”视角下的古诗翻译——以许渊冲的古诗英译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 2012(11): 246-249.
[12]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85.
[13]朱光潜. 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81.
[14]韩巍. 平行原则下的唐诗英译研究[D].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82.
[15]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418, 421, 166, 425.
[16]王守义,等. 唐诗三百首英译[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6.
[17]童庆炳. 《文心雕龙》“感物吟志” 说[J].文艺研究, 1998(5): 19-27
[18]潘家云. 《声声慢》翻译赏析与试译[J].外国语言文学, 2003(3):53-55
[19]许渊冲. 最爱唐宋词[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6: 67, 21, 167, 173.
[20]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M].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1:58.
[21]徐忠杰. 词百首英译[M].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98-99.
[22]朝晖. 古典诗词里道家哲学在英译中的传达——以柳永长调《雨霖铃》中两句的英译为例[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2010(3): 125-128.
[23]文殊. 诗词英译选[C].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331.
[24]周方珠. 英译元曲200首[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97.
[25]赵毅衡. 远游的诗神[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229.
胡红霞(1977-)女,江西婺源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教学与研究。
Transplanting Form Beauty: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
ZHOU Jian-hu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Chaohu College,
Chaohu 238000, Anhui, China)
Abstract: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s the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content; and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a poem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its form. Thus the special formal constituents of classical poetry needed to be transplanted into target language, so that the form beauty of the original poetry can be recreated into target language, and its special style and aesthetic value can be truly achieved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Form, therefore, should be given proper attention in the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convey its aesthetic meaning. Through the transplanting of form and representation of its aesthetic meaning, the cultural value of poetry translation is achieved.
Key words:Poetry translatio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eauty in form;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通讯作者:王俊程(1979-),男,云南禄劝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三农”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05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3-006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4XMZ098);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社科类重点项目(2014C001Z);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14YJ030)资助。 (项目编号:10YJCZH243)
作者简介:周建华(1976-),女,安徽巢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跨文化传播 李达(1990-),男,湖北洪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和“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