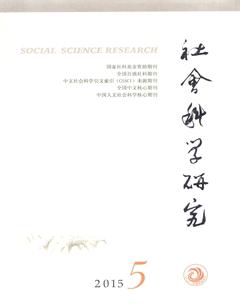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与对策
刘岩
〔摘要〕 此文拟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可能采用的对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经由不同路径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尤其是极大鼓舞了以身体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书写,同时也激发了在文学批评中广泛使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开始陆续做出反思,并期待这些反思能够激发女性主义的中国学术话语,从而增强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关键词〕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0-06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进程是一个早已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的课题。同许多其他西方哲学思潮和批评理论一样,女性主义也是全球化背景之下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带有鲜明的理论旅行印迹和知识生产的全球化特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西学中各种“主义”的译介和接受一直抱有热情,在众多带有“主义”后缀的哲学思潮中,女性主义是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界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西学资源,这从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译介和广泛应用的学术成果中可见一斑。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历程,已有数位学者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其中杨莉馨在综合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把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历程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小荷才露尖尖角:投石探路的初期引介(1981—1985年);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次浪潮的开始涌动(1986—1989年);苏醒后的狂欢:第二次浪潮的丰硕收获(1990—1995年)以及高潮后的总结与反思:女性主义诗学的纵深发展(1996—2000年)。〔1〕也有学者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历程划分为女性意识觉醒的1980年代、走向成熟和繁盛的1990年代以及多元化的新世纪等三个主要阶段。〔2〕虽然这种依照每五年或每十年划分为一个阶段的方式有人为切割历史进程的弊端,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划分为学界把握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大致的线索。在几乎所有研究此课题的学者中,都会提及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们很难忽视或低估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女性研究的促进作用,因为它由政府出面,以体制化的方式唤醒了国人的性别意识,把中国的性别研究推向了“高潮”和“繁盛”。今年是这次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后的第20个年头,人类社会也已经迈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世纪之交以及之后女性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新趋势、新关注,总结目前达成的一些共识并据此思考其未来的发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讨论将以中国文学文化批评领域为主要观察点。
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本土经验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规模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就是这一浪潮中的重要一支。在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已经从对于西方文论的盲目崇拜和单向引进发展到冷静的反思阶段,其中重要的内容集中在西方文论的中国本土化问题。仅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而言,有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课题共立项12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2012年),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3项,青年项目3项,后期资助项目3项。可以说,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思考中国在相关论域的推进方式,成为近年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除了上述宏观背景之外,女性研究的学者尤为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西方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而且它源于女性对于自身的存在以及对于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是因为性别的问题总是同人的存在根本相关,讨论性别问题时无法不与自己身处的社会现实相联系,所以,国内女性研究学者对于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解释或指导中国现实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警觉的。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外在冲击力,远远大于我们内在自发的省悟力”〔3〕,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者已经开始陆续反思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译介和传播之后产生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思考如何才能让西方文论更为有效地应用于我国的学术研究,解决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
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跨学科特质,也由于性别问题的社会属性,我国学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研究首先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展开,然后蔓延到教育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金铃主编的《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2002年)、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的文集《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2002年)以及余宁平、杜芳琴主编的《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2003年)都是这一领域早期的探索,其中后者试图审视妇女学的跨学科特质,并通过分析一些个案呈现女性研究在全球不同区域关注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差异。200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华人学者王政发表文章《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①,分析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以及科学研究中妇女学全球化的内涵,并期待其经验能够对中国学界有所启发。她以斯皮瓦克(G. C. Spivak)的女性主义理论为例,说明斯皮瓦克对于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精英地位时刻保持警醒,并深刻关注到了以跨国资本运作为主要特征的后殖民社会中性别关系的特征以及出现的新问题,作者因此提醒国内学者不能盲目认同西方理念和价值观念,而应该正视中国在实施市场经济之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从而以大多数妇女的经历建构知识体系。针对如何建构中国女性批评话语的问题,北京大学贺桂梅通过考察中国女性文学的兴起所借助的三种西方理论资源——新启蒙主义话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指出后者是中国女性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中被遗忘的重要资源,她因此主张只有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诸如阶级、民族、世代等——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4〕,才是走出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困境的有效方式。那么,中国的研究者如何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言说自己的女性经验结合起来,亦即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到底有怎样的内涵,自然成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上海大学董丽敏主张,“在理想的层面上,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应该意味着对本土女性生存经验特殊性的尊重与挖掘,意味着寻找女性本土言说方式的尝试,也意味着在对抗传统的菲勒斯文化基础上,又试图摆脱西方女性主义‘母亲的双重叛逆的开始。”〔5〕作者主张,中国学界在利用西方女性主义为参照系逐渐开始观照自身之后,必须检视中国特有的文化空间和经济地域,从而为女性主义的后续发展提供本土的思想资源。上述主张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继而,寻找并言说女性书写的特质就自然成为学界另一关注点。南京师范大学杨莉馨着重研究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之下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指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较为欠缺对‘女性美学,女性思维与想象的独特性,女性对题材、主题、意象、语言、文体等的处理与女性生理、社会性别之间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6〕,她因此主张在利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时应该注意挖掘中国本土的性别研究资源。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周乐诗同样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中国女性文学,她认为,无论是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文学批评中应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都具有可行性,但是,“我们既应该避免把本土性别理论当作西方理论的附属部分,把本土当成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也应避免以本土理论去对抗西方理论,以自己的经验去否定他人的结论”。〔7〕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学者对于单向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做法已经有所反思,对于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或从事文学文化批评可能产生的问题已有所认识,于是,建构女性主义的中国话语成为学界新的关注点。虽然截至目前,有所建树并切实可行的方法仍然有限,但是,上述研究充分显示出中国学者已经形成了某种学术自觉,并试图避免对于西方理论的盲目认同。综合现有研究来看,西方女性主义同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错位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的第一、二次浪潮)是以女性解放运动的形式首先出现并继而伴随理性思考而形成的,它源于女性对于性别平等的诉求及相应的社会实践;而在中国,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一直受到法律保护,虽然作为个体的女性在社会现实中仍然会遭遇性别歧视现象,但从社会整体上看,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因此,有学者主张,“中国女性主义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没有往独立运动的方向发展,这既是一种生存策略设计的需要,也体现了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特点。”〔8〕中国女性主义是否拥有有意识的生存策略,这一点尚有待讨论,不过,中国女性主义的缘起和根本诉求同西方女性主义有所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源于女权运动的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以在大学开设的女性研究课程以及为此撰写和编写的各类著作和教材为主要成果,其最初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最显著而直接的作用之一)就是用理论指导女性解放运动以及女性的社会实践参见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2nd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300.,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则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反观中国女性的生存现实,其最直接而显著的书写式呈现就是女性文学的繁荣。
第二,西方女性主义享有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同中国女性主义的有所不同。西方文明有着悠久的哲学传统,对于人的存在形成了特殊的自识与反思的思辨模式;而中国哲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发展轨迹、思维模式和知识体系均有别于西方,汉语语言的文化特质不仅造成哲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39-41页。,而且也导致文学批评方法的差异。参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3-13页。西方女性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发展背景是西方后结构主义的大氛围,在“反思西方知识体系”以及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思维的背景之下,“女权主义学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同西方学术思潮主流没有逻辑上的矛盾”〔9〕,这些是构成女性主义在西方知识界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很难获得突破,“最大的难点不仅在于女性学者缺少学科建设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想在身处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学术界异军突起,对女性学者来说是对自身的学术和精神力量的巨大挑战”。〔10〕
有鉴于此,在文学文化批评中简单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必然会出现吊诡之处。审视西方女性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时常会看到大量借用西方理论术语对于文学文本的阐释,一些研究者不顾这些术语产生的西方语境,把针对某一西方文化现象和文学传统而提出的观察视角当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阐释,动辄就是要挑战、反叛或颠覆性别秩序,滥用“父权制”“性别政治”“厌女”“他者”“边缘化”“沉默”“缺席”“镜像”“恋母情结”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术语,对于文学作品中女性身体的呈现也沿用西方文化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文化隐喻,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对于文本单一维度的、高度政治化的解读,也必然会忽视作品的美学价值。有学者已经认识到,如果运用西方的性别批评理论讨论中国古代的性属问题,“很有可能要面对‘以西格中、‘以今律古的质疑和拷问”。〔11〕更何况,“性别并不是文学的结构性因素”〔12〕,强行运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并不能增加对于文学文化作品的阐释力度,也难以还原文本的文学性,因此需要我们着意警惕和避免。
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对策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进中国学术界已经30余年,在最初单一引介的阶段中,“我们很容易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简单化为一种现实解决方案。……女性主义无形中便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参照系的存在来取代自己的思考,以现成话语的消费来消解自己的话语创造,其知识生产的力不从心可见一斑”。〔13〕那么,如何才能发展出自己的女性主义学术话语,提高知识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在性别研究领域做出中国学界的独特贡献,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认真讨论和研究。要有效建构女性主义的中国话语,需要对中国的性别问题本身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并能够据此展开理论层面的言说。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本土经验的特殊性,因为这会遮蔽女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也会割裂女性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由于女性主义理论同女性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其研究的问题针对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而女性生活的主要内容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似性,所以,某一地域或文化中产生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以为其他地域或文化的女性提供经验。应该看到,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的女性主义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的女性理论建构阶段,而在某些欠发达地区和文化中,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中提出的某些政治诉求还尚未实现。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理论才具有更为突出的借鉴性、参照性、互补性。在19世纪末,梁启超曾对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多有洞察,主张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并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其社会地位才能得到提升。他坚信“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于1897年协助经元善创办上海经正女学堂,并亲自撰写了学堂章程。这样的观察和举措同西方女性主义早期的理论和实践不谋而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早在18世纪末就曾专门讨论过女性同男性一样接受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参见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105-113.;而比梁启超晚30年之后,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曾设想如果女人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并且每年有500英镑的收入可以支配,那么,女性就可以如男性一样自由地写作。参见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1928),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97. 然而,女性接受教育这一诉求在一些国家至今仍未能实现,巴基斯坦的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还在为上学而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于2014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说明在当今世界,女童接受学校教育仍然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地域的特殊性,要看到女性主义在全球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虽然每个‘本土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使得非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14〕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源观察并指导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实践,与此同时,也通过审视世界不同地域和文化女性面临的不同问题而进一步完善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不同流派,虽然这些流派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关注点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仍然分享共同的理论前提和某些共同的研究问题有学者分析指出,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这个区分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实际上,二者均把“女性美学”置于分析的首位,均同时冒着“生理决定论”的风险。参见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130.,这恰恰增强了女性主义理论在异质土壤的适应性。
第二,海外华人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关于更多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女性所做的研究,参见王政《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现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47-51页;Gail Hershatter:《20世纪90年代欧美的中国妇女研究》,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2006年春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7-89页;刘霓、黄育馥:《国外中国女性研究:文献与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学者在海外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培养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学术话语更容易被西方学界接受,加上他们往往占有研究资料上的便利,因此,他们的研究较容易被西方学界所接受,这为国内学者向世界分享中国女性的生活经验、梳理中国女性文化的特质、介绍我国女性研究成果方面提供了经验。近年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用英语撰写的研究成果被译成汉语,继而在国内出版,为国内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其中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各子系列以及季进、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的译作为突出代表。此处仅举数例加以说明: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韩敏中、盛宁译,2003年)在西方批评理论(尤其是斯皮瓦克的“下属群体”概念)的视野下,研读大量史料(报章公开报道的新闻、妓院的管理条例、警察审讯记录、医生撰写的性病调查报告等),以期对上海妓女这一群体做出较为客观、真实的呈现;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1995; 李志生译,2005年)结合明末清初的坊刻、名妓文化、家居伦理等考察了明末清初中国江南较为宽松的性别秩序,修正了把中国性别秩序刻板化的思维定势。高彦颐的另一部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2005;苗延威译,2009年)则以三寸金莲为着眼点,考察了缠足的源头与流变,分析了女性身体在中国文化中承载的文化隐喻和伦理价值。可以看出,上述研究成果的着眼点都很小,研究者并未被现有观点所束缚,而是在研究过程中借助第一手资料,做了扎实的实证考据,论述过程很有说服力,因此常能做出有创见的发现。这样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学术理路对我国的性别研究当有所启示,成为除西方批评理论本身之外的另一种镜像,促使我们反观自己的研究理路,思考如何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第三,在文学文化批评中,我们应强化阅读体验在批评中的重要性,而非首先挥舞各种“主义”的大棒,应以问题为出发点,而非批评概念为先导,应以增强对于文本的理解为目标,而非视追求学术热点为时尚,这样就能避免文学文化批评中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现象。既然学界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中国现实与社会实践之间有不同方面的差距和错位,那么,盲目套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文学文本势必导致平面化的阐释,甚至是对于原作的曲解。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以及作用,也涉及到文学理论的社会意义,在各种批评流派纷争的20世纪后半叶一直持续引发理论家思考。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15〕,常常已经对于某一现象、某一关系、某一情景做出了解释,套用理论解读文本因此就预设了结论,接受了理论原有的前提,研究本身充其量只是为原有的理论增加了另一个例证。“批评是一条要走的路,而不是一个要被命名的目的地。”〔16〕如果从阅读体验出发,从文本中发现问题,然后借助不同的理论分析问题,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对于原有的问题做出新的洞察。周小仪认为,中国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的理论概念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的倾向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看作是“一种解读文学的普遍有效的手段,对其意识形态特征视而不见,更不要说对其地域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分析和认识”。〔17〕但实际上,“普遍性的文学概念不过是一种理论幻想”〔18〕,研究者必须在具体情境中综合分析文学作品的各种元素,才能发现其意义和价值。《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2012年)的三位编者季家珍(Joan Judge)、胡缨和游鉴明在著作序言中回顾了她们研究女性传记文学的初衷①:中国最早关于女子生平的传记是公元前32年刘向的《列女传》,那么,这是否是中国古代关于女性行为的唯一规范?中国女性自己书写的传记可以追溯到何时?又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女性自己书写的传记同男性为女人所做的传记对于女性生活的呈现有何不同?体现了怎样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性别秩序?她们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寻找史料,确定阅读方法,并逐渐梳理出中国女性传记的发展脉络和承载形式,她们据此做出的研究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不妨在文学文化批评中更多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开始研究,对文学作品做出真正有洞察的理解,胡适当年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至今仍然有警示作用。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谈到跨国资本时代的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时,曾敏锐地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融通。虽然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概念从根本上形成对立和互补的双方,它们相对于对方而定义,但是,一些文化现象兼具全球与本土的特质,成为“全球本土”(glocal)的不同构型。〔19〕他进一步如下阐明了本土与全球的关系:
在本土叙事意义上的本土保持了一种空间上的具体联系,但是作为批评性概念的本土,其边界应该是开放型的(或松懈型的)。当代本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发明与建构的场所,因此只有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即建构“构成”叙事的过程中对它进行定义——最简单的理由便是现在的本土最终会被全球代替。〔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