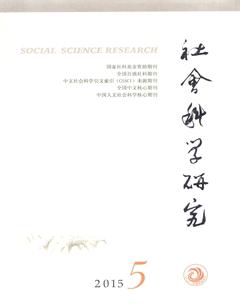遵守纪律: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
张一兵
〔摘要〕 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新的统治形式,正是与之前的外部强制(高悬的皮鞭)截然不同,即通过控制人们的内在思想中的自主的构境式认同使其自我奴役!权力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压迫,不再是被具象主体拥有的外部强制,甚至成为了人们自觉追逐的他性镜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它的实现正是通过自拘的纪律,它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全新的社会控制论核心,它的缘起是资本力量让劳动者通过对工厂中与生产运转机制相一致的纪律(技术规范要求)的自我认同,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和操作,使外部的纪律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以实现对肉体的根本操纵和支配。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社会中普遍发生的自我奴役的自拘性的真实基础。
〔关键词〕 福柯;《规训与惩罚》;纪律;自拘性;自我驯服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145-07
福柯①认为,不同于专制权力的外部强制,资产阶级将现代社会控制方式演化成为一种支配的艺术,这种隐性奴役的本质就是规训,即形成以一种自觉被遵守的纪律为生存原则的自拘性。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走向光明的“‘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权利,也发明了纪律”。〔1〕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第三部分第一章中重点讨论了这种规训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新的肉体控制方式中,人成为一尊自动运转的装置,这种自动运转的核心机制竟是某种自我驯服。自我驯服的基础在于对纪律的自我认同——在持续不断的训练和操作中,外部的纪律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社会对肉体从根本上的塑形操纵和根本支配由此实现。本文将讨论福柯这一重要的政治哲学观念。
一、匿名的惩罚艺术
福柯深刻地看到,相比之封建专制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中“出现了新的资本积累方式(nouvelles formes daccumulation du capital),新的生产关系(rapports de production)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这都是在肯定性地复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质性描述的观点。这种做法与他《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中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福柯开始成为没有“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者。当然,这会是一种双重姿态:一方面福柯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思考构境支撑点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突破马克思原有研究构式的边界。因而,在社会控制的层面上 “越来越有必要确定一种惩罚策略(stratégie)及其方法,用一种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la continuité et de la permanence)机制取代临时应付和毫无节制的机制”。〔2〕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福柯这里所说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统治新策略的无面孔和微观布展机制。他是在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对世界的深刻改变,在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社会构序、控制的对象和范围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专制社会里没有节制的暴力处罚方式对新的社会生活已不再适用,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反专制的结果是从外部塑形上根本祛除直接暴力,所以,不可见的软性支配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场的出发点。福柯宣称,这种新的策略必须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或者说,这就是新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支配艺术构境。
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控制形式的这种改变依循了主观层面上的“人道化”和物性操控层面的“精于计算”的两个原则,在具体运演中已逐渐生成了“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économie calculée du pouvoir de punir)”。不难发现,福柯反复在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话语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中来。
第一个层面,人道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标榜的光亮面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要控制和奴役人们,但支配的方式可以变得更加温和和富有人情味。并且,新型权力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谋算出来的,在呈现方式上它甚至可以表现为某种不是统治的艺术和非人为的工具性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韦伯奠定了资产阶级官僚制的可计算、可操作性的逻辑。
以福柯之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政治权力的作用点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作为新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esprit),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de représentations et de signes)游戏。〔3〕这个所谓表象和符号的游戏也就是福柯已经指认过的,新的权力不再直接作用于肉身,而将作用于政治灵魂。何以实现?福柯的回答是:资产阶级所籍以控制人的灵魂的东西,正是“‘启蒙思想家(Idéologues)已经建构的话语”,即民主与科学的话语。这是令我们震撼的断言!福柯指认道:
这种话语实际上借助关于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借助该理论所重构的系列(séries)和发生过程,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sémiologie)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表面(surface dinscription);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politique des corps)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4〕
我们约略能回忆得起来,所谓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看起来都十分接近于福柯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有关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古典时期中认识型构架的描述。在那里,表象与符号同时被视为词对物的烙印,用以表征一种暴力性构序和支配关系。然而到了此处,福柯却将表象指认为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的工具,表象成了肉体政治学的原则,也由此,福柯才会断言“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这期间,话语与存在关系的构境层显然已经发生了一次不小的话语内涵重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福柯援引了法国政治家塞尔万①的一段表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5〕这是极深刻的隐喻。在福柯眼中,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新的统治形式,正是与之前的外部强制(高悬的皮鞭)截然不同,“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即通过控制人们的内在思想中的自主的构境式认同使其自我奴役!接着,福柯进一步将之深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中独特的自我规训下的自拘性。并且,福柯将这种新型的“符号技术(sémiotechnique)”统治术界定为“意识形态权力(pouvoir idéologique)”。〔6〕这倒是意识形态理论中一个新的发明。在福柯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权力与传统的外部专制权力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所具备的某种场境式的无形性和匿名性(anonymes)。他指认道:这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不是在人群的上方,而是在其结构之中恰当地与这些人群的其他功能衔接,而且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方式起作用。与之相适应的是匿名的权力工具(instruments de pouvoir anonymes)。这些手段涵盖整个人群。它们作为等级监视手段,严密地进行不断的登记、评估和分类。总之,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客体化(objective)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认知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signes fastueux)。〔7〕
与传统社会中君王那种高高在上的表演性显赫威严以及直接强诸于人们肉体上的可见暴力相区别,资产阶级制造的社会控制方式恰恰不是国家总统或首相那种有面孔的权威(在这里,虽然他们占有了原来“天子”的空位,但这些有面孔的权威只是一幅表演性的摆设),在此,权力已不被占有,而转化为渗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无脸的匿名权力。权力,就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场境中,以看不见的、温和的身体化方式,自动地像机器一般运转其隐性塑形机制。
这种以表象和符号控制为核心的权力技术学是一种表面上更加温和的惩罚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让人感到温馨的惩罚艺术(Lart de punir)。艺术是美和享受,在美和享乐中开心地被支配和奴役,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构境层。所以,现代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建构的重要表象属性之一。“这是一种操纵相互冲突的能量(énergies qui se combattent)的艺术,一种用联想把意像组合(associent)起来的艺术,是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的艺术。这就需要确立对立价值的表象,确立对立力量之间的数量差异,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符号(signes-obstacles)体系”。〔8〕
在今天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权力控制和社会支配都已经不再表现为暴力强制,反而呈现为仿佛是艺术享受般的自主拥戴,这是资本主义新型社会控制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表述,叫“镇压通过后退的迂回在生效(La répression opère par le détour de la régression.)”。①这种被鼓励去认同的控制的艺术,通过资产阶级鼓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意象的组合,建构起一幅现代“人”的外部更加文明的呈现形象,以操纵实质中存在着的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能量冲突,使其屈从于某种看不见的权力关系网。于是,权力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压迫,不再是被具象主体拥有的外部强制,甚至成为了人们自觉追逐的他性镜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福柯犀利地说道,资产阶级的“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 〔9〕用日下时兴的话来讲,这就叫自觉的法制观念。如今,“它作为景观、符号和话语而无处不在。它像一本打开的书,随时可以阅读。它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而运作”。〔10〕公民意识镜像,即是将臣服性身体化的教化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将福柯这里的无主体的“惩罚艺术”解读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基于理性主体目光的新的“监管理性”〔11〕——是完全错误的。
二、人是自动驯服机器
第二个层面,精于计算中的“人是机器”,人成为资产阶级权力摆布下自动驯服的政治玩偶。福柯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古典时期”(17-18世纪)开始,人的肉体就被发现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objet et cible de pouvoir)”。当然,这一次,肉体已不再是专制暴力下被酷刑折磨和杀戮的对象,而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模式中的“被操纵(quon manipule)、被加工(quon faonne)、被训练的(quon dresse)对象。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12〕;被统治者不再是皮鞭和屠刀下“会说话的工具”,而是训练有素的独立法人主体,被启蒙和发动为一台台新型的法理型的政治装置和自动运行的劳作机器。后来,斯洛特戴克曾经将这种资产阶级的新型奴隶式主体性建构描述为:“让发号施令者似乎进入了听从命令者的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听从命令者的服从和让步看起来就听从了某种内心声音一样。”〔13〕这个观点是深刻的。
福柯声称,拉美特利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为:《人是机器》(1747)等。的《人是机器》(Homme-machine)正是有关这种“精于计算”的社会控制方式转变的深刻写照。他说:
这本书既是对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Réduction matérialiste),又是一般的训练理论(théorie générale du dressage)。其中心观念是“驯服性”(docilité)。该书将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驯服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装置(automates)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poupées politiques),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modèles réduits)。〔14〕
福柯的解读是否切中拉美特利的原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过度诠释的文字的确揭示出今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本质。在福柯看来,“人是机器”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人已在新的肉体控制方式中成为某种自动运转的装置,实现其自动运转的核心机制就是作为政治玩偶本质的自我驯服。在此书中,福柯13次使用docilité一词。然而,这种自我驯服如何生成的呢?这正是福柯此书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福柯告诉我们,在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体成为如此专横干预的对象,史无前例”。这个“史无前例”指的并不是通过外部暴力方式加诸于肉体的强制,而是指权力施加于肉体的内部深层控制。 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福柯实际讨论的控制对象再一次成为真实的肉体,而非他前面强调的政治肉体(“灵魂”)。福柯提醒我们关注这一新的精于计算的人体控制方式中存在的诸多“新颖之处”:
首先是控制的范围(abord)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控制方式中,人体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精确到细部的捏揉(le travailler dans le détail),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无穷细小的微分权力(pouvoir infinitésimal)”。〔15〕
真是太精辟了,福柯这里的“精确到细部的捏揉”和“支配活动人体的无穷细小的微分权力”,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控制范围和层面的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对肉体的压迫形式已不再是先前封建专制时将之关进地牢或施加酷刑那样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加诸于每一个肉体细部的看不见的控制和奴役之中。我觉得,这恰恰是韦伯、法约尔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法国现代科学管理学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在泰勒制流水线生产机制下生成的肯定性科学管理的一种批判政治学翻转。
其次,是控制对象(objet)的不同。新的社会控制对象“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éléments signifiants)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e)。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16〕在这里,控制的对象不再是指向肉体存在状态的看得见、听得见的直接命令(圣旨、宣判书和禁令),而是看不见的具体存在机制构序和做事情的内在行为塑形结构。控制,不再发生于人们可察觉的意识层面,它转入了无意识的肉体存在内部运转机制,在这里,权力已经悄然转化成了肉体本身生存的支配性力量线。福柯还说,令上述内在机制得以日常运转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exercice)”。操练(或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控制的微细权力运转机制成为一种身体化的存在。福柯随后还会专门讨论这个训练。
其三是控制模式(méthodes)的改变。与传统刑罚那种在瞬间抽打上皮肤的鞭子不同,而今的控制方式是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隐性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17〕新的控制模式是在对时间、空间和活动本身的某种构序和重新编码中,实现对生命过程的总体控制。
三、纪律:身体化规训的自拘性生成
福柯指认,这种由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服-功利关系(rapport de docilité-utilité)”的方法,就是资产阶级所谓法理型的“纪律”(disciplines)。〔18〕Discipline在法文中也有惩戒的意思,它是本书的重要关键词,福柯在此书中共计130次使用此词。在我看来,这个法理型的纪律应该是福柯在此书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发现!
我们知道,纪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说法,它出现在现代工厂生产、军事管理和学校教育中。通常,纪律是一个被正面肯定的有效管理和教化措施。而在福柯这里,纪律则被指认为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全新的社会控制论核心,它的缘起是资本力量让劳动者通过对工厂中与生产运转机制相一致的纪律(技术规范要求)的自觉认同,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和操作,使外部的纪律(法规)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以实现对肉体的根本操纵和支配。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社会中普遍发生的自我奴役的自拘性(法治人)的真实基础。还应该指出,福柯自己从来没有提及的马克斯·韦伯和青年卢卡奇,正是他政治哲学中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史渊源。韦伯在界划现代性法理社会的过程中,悬置了实质合理性的社会本质,通过形式合理性(即工具理性)将社会生活锚定在看得见的事实层面,并且由认知-技术建构生产(流水线)和社会存在的标准化、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过程。而青年卢卡奇则将韦伯的合理化结构颠倒过来,直接引出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流水线生产程序中工艺技术对劳动者肉体和观念的新型物化现象的批判,由此进入马克思并未关注的控制-支配层面:生产有罪论。福柯此间的讨论,显然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思考线索,只是将后者进一步引申到社会政治控制的构境域中罢了。
福柯认为,17-18世纪,由现代工业生产发明的“纪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formules générales de domination)”,这是一种与传统社会控制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不再是可以被明确抗拒的外部强制。纪律控制的第一个构境层级,不是传统强权之下的认命和臣服,而是从内心里对法规的自觉认同和遵守。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发明纪律控制(法治),开创了支配艺术的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控制的外部压迫质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宣告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规训。对福柯的这个说法,布朗肖提出了异议,后者认为福柯夸大其词,因为“规训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比如说,通过某种成功的训练方法,一头熊被驯化,变成看门狗,或勇敢的警察”。〔19〕在这一点上,我愿意为福柯辩护,因为在工业生产中生成和突现的纪律式的自拘性与基于肉体生理反应的反复驯化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的分歧只能说明布朗肖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笔下资产阶级工业化中规训的本质。
也是为了进一步厘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纪律与传统社会中的外部压迫之间的异质性,福柯还细致地界划出四种差异性边界:
首先,这种新型的统治方式与过去的奴隶制(esclavage)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rapport dappropriation)上”,与之相比,纪律仿佛更“高雅”,因为它无需通过粗暴的直接奴役关系就能获得显著的实际效果。纪律不是那种基于占有关系之上的野蛮奴役,反之,它与支配对象的关系恰恰是非暴力和非强制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进入纪律(遵纪守法的自律)甚至会表现为具有某种文明化和有教养的特征。所以,人们并不排斥纪律的自律构序,反而积极努力地入序和臣服其中。其次,纪律也不同于通常的仆役(domesticité)关系。仆人的存在是在主人的个人意志“为所欲为”情境中确立的,而纪律则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纪律不是主仆关系中的单向性主人意志,而恰恰呈现为执行的自主性特征,无悔和自愿地遵守纪律是长久有效的支配。其三,纪律也不同于附庸(vassalité)关系。“后者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依附关系,更多地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地涉及人体的运作”,而纪律性支配则是建立在内在臣服基础上人体本身的自动驯服和自动运转。在这种认同性臣服构境中,被支配者反倒自以为是自主性的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其四,纪律也不同于禁欲主义(ascétisme)以及修行式“戒律”。宗教式的禁欲是看破红尘的出世主义,它的目的是“弃绝功利”,而纪律的“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的控制”,恰恰意在增加入世的功利性。〔20〕如果,发财成了神性的天职,那么,规训和自制则是走向成功的通道。在一定的意义上,韦伯对新教的形而上学解读也内嵌了这一层构境意蕴。
也是基于上述意义,福柯指认资产阶级发明的“纪律”代表着在新的社会控制中“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1〕有用的支配,这是规训支配构序结构的第二个构境层级。传统奴役形式中皮鞭下的顺从未必就能实现最好的利用,反而是资产阶级通过“纪律”支配的肉体将达及更加有用中的顺从,因为,新的顺从是从肉体存在的内部有效功能中发生的。此即为福柯笔下这个规训(surveiller)的本质。在福柯看来,正是这种规训——对纪律的认同和训练,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manipulation calculée)。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anatomie politique),也是一种“权力力学”(mécanique du pouvoir)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服的”肉体(des corps dociles)。〔22〕
这是说,不同于皮鞭的纪律制造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的特殊肉体,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所谓正常人的“才能”“能力”和“创造性”,令其能自主性地发展,不断增强它,使之有用(成功),从而进入主动入序和自动驯服的状态。以怀特的概括:资产阶级主张“驯服、努力工作、能够创造经济价值、自制、恪守良心,总之一句话,就是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正常人”。〔23〕这是对的,正常人正是康吉莱姆和福柯批判性构境的起点。福柯辨识道,“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的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24〕前一句显然是马克思的话语——福柯在这里想要强调,与马克思关注的经济剥削的层面不同——他自己认为,资产阶级的纪律规训正是在生产劳作训练中,通过让人变得具有能力而使其无意识被支配。巴里巴尔意识到了福柯对马克思话语的自觉运用。他说,“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吸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中劳动力的划分方法,来说明规训手段是如何通过抵消工人的对抗性来增加工人身体的效用的”。 〔25〕但他却没有留意到福柯语中夹带的恶意的差异性标注。
福柯追溯道,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并不是一个简单突现的东西,它实际上“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processus souvent mineurs)汇合而成的”。〔26〕在此书中,福柯9次使用这个他挪用自配的anatomie politique(政治解剖学)。必须强调,此处这个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很关键,资产阶级的规训政治通常都不呈现为激烈的显性政治变化,而恰恰是通过不显著的发散性的微细质点偏移来逐渐实现的。这些不起眼的“小过程”可能起源各异、领域分散,但却深刻在生成支配构序层面上的“相互重叠、重复或模拟,相互支持”,最终“它们逐渐汇聚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一般方法的蓝图”。这种貌似平静的表面特征,也是福柯所认定的资产阶级政治运作的重要隐性机制,政治运转恰恰发生于传统政治学讨论语境下不是政治活动的巨大灰色盲区构境中。在福柯这里,不是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最大的政治!
福柯判断,这种规训最初是在西方的中学里萌生的,随后进入初等教育。谢里登注意到,在英国最古老的“初级”学校中的班级就被称为“标准”(standards),而福柯所读的法国著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规训学校”(ecoles normales)。〔27〕很快,规训就蔓延到医院领域,再经过几十年功夫,它们就彻底改造了军队组织;并且,“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 〔28〕从而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控制的基本模式。其实,规训生成的真正基始之处是现代工厂,或者说,它就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工艺结构中对主体的要求。福柯在下面这一段描述中正确地提及了这一历史质点。福柯发现,它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传播有时很快(如在军队和技术学校或中学之间),有时则很慢、很谨慎(如大工厂的隐秘的军事化,militarisation insidieuse)。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采纳它们都是为了适应特殊的需要,如工业革新,某种传染病的再度流行,来复枪的发明或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完全被铭刻(inscrivent)在一般的和本质的社会转变(transformations générales et essentielles)中。〔29〕
我以为,此间最关键的是在大工厂中发生的“隐秘的军事化”规训,恰恰是因这种生产构序中的机制铭刻在人的劳作存在中,继而才在其他社会活动中次生为一种全面的塑形和构序场境。这也就是说,对社会转变的铭刻,是从最根本的劳动生产构序中开始的。全社会的自我规训是客观存在在工业生产中被构序(组织化)的顺应结果。哈维直接指认说,马克思在福柯之前最先说明了资本主义规训中“特殊的监视空间的建构”,并且还专门从《资本论》第一卷中援引了两段长长的表述,即18世纪工厂“习艺所”和按照军队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工厂的自然规律”。〔30〕然而,福柯的看法似乎不是这样。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2〕〔14〕〔15〕〔16〕〔17〕〔18〕〔20〕〔21〕〔22〕〔24〕〔26〕〔28〕〔29〕〔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49,96-97,111,113,113,113,246-247,117,125,145,154,154,155,155,155,155,155-156,156,156,156,156,157,157.
〔1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89.
〔13〕〔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M〕.常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7-88.
〔19〕〔法〕布朗肖.我想像中的米歇尔·福柯〔M〕//肖莎,译.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34.
〔23〕〔美〕怀特.福柯〔M〕//〔英〕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7.
〔25〕〔法〕巴里巴尔.福柯与马克思:唯名论的问题〔M〕//李增,译.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457.
〔27〕〔英〕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M〕.尚志英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9.
〔30〕〔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6-257.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