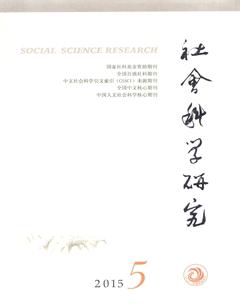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王献华
〔摘要〕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关键词〕 林志纯;日知文集;“中西古典学”;“古典学”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179-07
要了解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了解中国学者对古代世界的历史认识,林志纯(日知)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林先生并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一个狭义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从业者,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研究工作的认识超越了狭义的学科门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关怀。他以理论创新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定位,并且根据这种新的构想做出了系统的努力。这就是林先生自己命名的“中西古典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
上世纪90年代是林先生集中提出并实践“中西古典学”研究的时期。③这一时期林先生提出“中西古典学”构想的理论性文章最重要的有《论中西古典学》(1993),《再论中西古典学》(1996)等,后来基本收入1999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西古典学引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则是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研究的实践,具有范例价值,系统地展现出“中西古典学”的概念框架、研究路径和问题意识。特别是201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林先生的弟子张强教授主持编辑的五卷本《日知文集》,将林先生的重要作品集中起来,包括《中西古典学引论》和《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为后学学习和研究林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本文便依据《日知文集》收入的文献,尝试对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做一次初步的整理和理解。①
一、 “中西古典学”的学术构想
《论中西古典学》一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曰“中西邦学与中西古典学”(卷四:459-460)。《说文》“邦”“国”互训,林先生以为即英文city-state所译之polis,表达“城”“邑”“国家”“公社”“公民集团”等含义。“邦由全权公民(邦人、国人)组成。邦人之于邦,是自由民,同时又依附于邦,古希腊人所谓‘邦之动物,古中国人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皆表示邦人的本质”。“邦人国人在五伦中居最高地位,这是古典文明的普遍原则,中国西方都无例外”,此之谓“古典时代的民主”。“邦是文明出现时期,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时产生的组织形式,古代世界各民族(至少是定居民族)都曾有过”。“荷马、赫西奥德的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政治学,西塞罗的辞令,在中国三经三礼,诸子百家,自黄帝至共和,自孔子至司马迁”,莫不“兴于邦学之日,以古典不朽传至今朝。”因为邦是古典时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邦学”乃是古典学之始基,“其内容则邦人(国人)的民主政治也”。
第二部分曰“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卷四:461-465)。林先生认为,从公元前一千年代初的古希腊文化开始,经过罗马古代共和国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西方或者欧洲的古典时代,“或延长至东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时代” 。这样理解的西方或者欧洲的古典时代,先后均有大规模的蛮族入侵,第一次是在迈锡尼文化衰亡和古希腊文化出现之间,第二次则是西欧古典文化结束到文艺复兴(约相当于公元5-15世纪,即欧洲的中世纪),这两次大规模蛮族入侵让古代欧洲进入“黑暗时代”,可依先后分别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时代”。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凭着古典文明文化的再生,由中世纪走进近代”。林先生强调,在西方近代史的初期,来自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和古典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孔子的哲学思想,都起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黑暗时代,所以古典文化得以持续发展,但总的来说,其社会和科学技术成就与西方古典文化相当。这一点乃是“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可以说,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问题,中国古典时代与西方古典时代是基本不相上下的;中国古典时代的继续发展,比之欧洲黑暗时代,是高潮低潮问题,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比之西方黑暗时代是胜过的;中国科技的发展,到了近代现代,在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则被欧洲超过了”。
《论中西古典学》一文的第三部分曰“天上人间,科学与民主,中西古典学的历史任务”(卷四:465-472),规范“中西古典学”的研究目标。古希腊人在公元前776年创办奥林匹克赛会,在中国古代史上,这一年是周幽王六年,也正好是《诗经》中的《十月之交》保存下来第一次可靠的日食记录所在的一年。此时在位的周幽王是周宣王之子,周厉王之孙,而在此不久前的厉宣之间(公元前841-前828年)曾有过14年的“共和”时代。林先生认为,这14年的“共和”见证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标记着中国古典时代的君主制在“汤武革命”后向公卿执政制的转变。林先生说,“公卿执政制是古典文明的政治制度的本质,即古代民主政治,如雅典之‘雅康制度那样”。正如公元前776年是“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时期,此后希腊进入真正的古典民主政治时期(卷四:462),古中国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古典文明全盛时期。这是《十月之交》在科学史和天文学史意义之外,对中国古典“民主政治”的意义(卷四:467;另见卷三:300-301)。
《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是对上文所提“中西古典学必须重新研究”的任务进行的“再一次尝试”,林先生在其中试图对中西古典学的构想给出更明确的说明。文章的第一节“中国和欧洲古典史发展的形势不同”开宗明义,指出欧洲古典史有黑暗时代(中世纪),而中国古典史没有这样的过程和结果。林先生在这里注意到“欧洲古典史”和“西方古典史”两个概念在严格意义上有所差别,因为广义的西方古典史从范围上可以涵括近东之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等,只有在狭义上作为“欧洲古典史”的“西方古典史”才不包括这些地区在内,虽然可以在研究中联系比较这些地区。狭义上的“西方古典史”也就是“欧洲古典史”,林先生取其狭义。“‘西指古希腊、罗马,为方便计,有时亦称欧洲古典史”(卷四:474;对比卷三:1)。除了传统所说的中世纪,欧洲的古典史上还有一个“黑暗时代”,就是迈锡尼到后来的希腊文化之间的时期。
“中国古无‘黑暗时代,亦无‘中世纪”。和欧洲不同,“中国在古典时代之后接入古典帝国时代”。结合对《史记》前四表的解读,林先生在文章的第二节中将中国古典时代的时空范围和内容核心勾勒出来(卷四:477-487)。从时间和发展阶段上说,“共和之前,古典之五帝三代;共和之后,古典之春秋时代,前者属王政时代,后者属霸政时代,以及公卿执政时代,执政之公卿发展为当权在位之国君,乃至称‘王,即战国之形势。然后由战国发展为帝国,汉帝国是矣。六国或战国,为向古帝国之过渡,皆属古典时代”(卷四:478)。就中国古代史上的这个时期,《太史公自序》曾总结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林先生对司马迁的说法做出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里提到的“汤武”“春秋”“陈涉”,“其历史地位、作用,一也。”而这里司马迁所谓的“道”指的是王道,所谓的“政”指的是“王政”,“皆古典时代之内容也”(卷四:478)。中国古典时代后是古典帝国,自秦汉至南北朝为第一古典帝国,自唐至清为第二古典帝国,之后直接进入近现代。
文章第三节“欧洲古典时代之转入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古典帝国中绝”。希腊古典世界之兴,若不计宫廷文化时代和黑暗时代,实略晚于中国古典的创始。而欧洲古典时代之结束,在东罗马查士丁尼时代,“欧洲的古典帝国中绝”,“此中西古典学之一根本区别!”(卷四:482)根据林先生的看法,固然中间西南亚及印度的一部分,在希腊化帝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这样的时期连属于附近地方,因此进入古典世界,从整体上说旧世界的古典时代“不外中国古典和西方(欧洲)古典两大片而已。”(卷四:418)就这古典时代的两大片而言,其根本差别在于中国古典时代长期延续,由古典时代而古典帝国,之后直接进入近代而没有经历中世纪。欧洲古典只发展至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因为古典已经断绝,只好“来一个巧妙阶段,回顾古典,把从古典所得益者,用之于近代,历史上这叫做‘文艺复兴。”(卷四:482)
第四节专门谈“文艺复兴与中西古典学”。林先生再次强调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进入近代史的时期,包括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和古典中国的哲学思想,如孔子的哲学思想,在西方“都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林先生重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所说,“同是古典时代,时代相近似,社会的成就亦相当。此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卷四:484-485)
二、“中西古典学”的主体内容
林先生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的“前言”说,这本书“只着重论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道出了“中西古典学”的主要内容。全书第一篇《绪论》分作七章,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划定古典文明史所关心的范围,然后以公卿执政制为关键概念,试图澄清东西方古典民主政治和东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研究问题。第二、三篇各章则大体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论述“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创始时期”和“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全盛时代”。第四篇介绍西方古典民主政治时代的历史背景,内容是公元前二千年代末至公元前一千年代初的古代中东帝国。第五篇合论中西古典文明,回到“黑暗时代”问题解说中西古典发展道路的差异。
之所以将“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写成了事实上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主要关怀的古典民主政治史,是因为林先生认为民主政治是城邦时代的一般现象,中国的城邦时代更是如此。古典民主政治是“邦学”的根本所在,而邦学是古典学的始基和核心内容。“民主政治,只属于城邦阶段,帝国时代是专制政治时代,民主政治看不见了”,尽管“不是所有古代城邦都出现过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就没有”,在古代中国,“民主政治不仅有,而且出现比较早,比较典型”(卷三:1;另见同书:300-301)。对西方古典政治的研究已经不止一个世纪,而中国“近来才在排除传统见解,研究讨论之中,许多材料尚待搜集和解剖”(卷三:162)。
具体而言,“在东半球或旧大陆,古典文明或古代文明集中出现于亚欧非三洲相连接的地带,西起地中海周围,东至中国海沿岸”(卷三:7)。这片地方是人类史上最早产生文明和国家的地带,“此即古典文明世界,亦称古代文明世界”(卷三:7)。林先生认为,堪称古代文明世界或古典文明世界者,只有旧大陆的这个地带而已,在此之外的旧大陆其他地区,或者新大陆的美洲和澳洲,并不直接纳入古典文明世界或者古代文明世界的研究范围。这个“南北东西成片存在于旧大陆的古代文明世界,依其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中间部分是古代近东(北非、西亚)、南亚和中亚,其西方是古代欧洲,东方则是古代中国”(卷三:8)。近现代欧洲学者强调北非、西亚、南亚、中亚、伊朗部分同欧洲之间的关联,林先生据此说,“中间近东至中亚、南亚部分,同西方欧洲部分,构成了古代文明世界的西方古典文明系统”,这个西方系统“与中国古典文明系统形成中西两大古典文明并立的局面”(卷三:14-15)。
“古典时代的国家,由城邦到帝国;古典时代的文明也由城邦阶段进入帝国阶段。城邦—帝国,城邦阶段文明—帝国阶段文明,这基本上是古代文明世界普遍存在于三大地区的历史现象,为中西古典文明所共有”(卷三:29-30)。根据中国古典文献游牧文明可称为“行国”,林先生认为它遵循类似的发展规律:“其始期近似于邦,与城郭之国相等,而其后期,行国就是帝国,如匈奴帝国”(卷三:53)。“行国帝国”将欧洲带入中世纪,中国的古典帝国则抵挡住了“行国帝国”的入侵而得以保存。就城邦而言,“有城邦就有城邦联盟”。所谓“雅典帝国”或“雅典同盟”实质上仍然是雅典为首的城邦联盟,所谓“周天下”也是以周邦为首的周人城邦联盟(卷三:42-50、78-85、208-209)。雅典和中国的城邦都经历了从“原始君主制时代”到“公卿执政制时代”的发展历程(参见卷三:155引《古代城邦史研究》的分期)。公卿执政制指主政当权者而言。古中国的公卿制,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公卿执政便是由公卿而非天子或者诸侯来执掌政权。“正如雅典实行雅康制后,巴西勒斯(邦君、王)还有宗教权一样,中国当春秋时代,邦君也仍有宗教权。”如此理解的话也就能看到,公卿执政制时代是古典时代城邦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古希腊史上,还是在古代中国史上都是一样的(卷三:62-63及表格)。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公卿执政制时代都在大约自公元前9—8世纪至公元前4—3世纪总共大约5个世纪之久。
古典文明史关心的历史发展进程集中在这段时间之内,关注对象则是这段时间内的古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学的内容,这就是所谓“中西古典学”的基本内容。林先生强调民主政治是城邦时代古典世界的普遍现象,而不是希腊城邦独有的现象。“把一人统治的君主制或君主政治(μοναχεα)混入邦君政治(βασιλεα),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错误(邦君政治就不一定是一人统治,如斯巴达有两君);他的另一个重要错误在于不知道亚洲或东方先前也有过城邦阶段,把亚洲当时波斯帝国时代的专制统治看成永远如此,因而断定亚洲人比之欧洲人更富奴性,‘忍受专制统治”(卷三:153)。
古代中国的“民主”指的是“民之主”。林先生说,这个概念产生于西周之前,始见于周初作品《多方》。这时候的“民主”指的是邦君或邦的联盟的盟主之邦的邦君,也就是“王”或者“天子”,其中逻辑如孟子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卷三:206-210)。“禹汤文武是这些邦君或王、天子的典型”。到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公卿执政制时代,“民主”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指的不限于(或不是)邦君,而是执政的公卿,邦君的君逐渐退到后位,专管(或主要管)宗教了”(卷三:157)。“公卿掌管政治,掌管民事,当然是民之主”(卷三:159)。“邦君失国与公卿得国,是古中国民主(民之主)形式的重要发展。”(卷三:162)问题在于,西方希腊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民为主”,与古典中国的“民之主”可不可以对比?林先生指出,所谓“民”在两个语境中都指全权公民、自由民,奴隶和无权者除外,“这一点双方一致,无可非难”,而这一点提供了将二者并论的基础。例如“民为主”的“由民投票”,如“陶片放逐法”所体现的公民投票,林先生根据《左传》所记郑国子产当政前后故事,指出当时郑国的“国人”“诸大夫”都有分别如民众会和长老会议这样的组织,还有“乡校”,子产当政正是依赖这样的民主政治力量(卷三:417-422)。
三、 “中西古典学”的核心关怀
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有鲜明的现实关怀,首先是对现代价值的认同和对未来的信念。《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以《学习恩格斯1884年的一篇遗稿》开篇。“遗稿最后说,未来社会要把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清醒,同古代城邦对社会福利的关心,彼此的长处,结合起来。这,我们想想看,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时代吗?”林先生解释说,“近代科学进步,人们才有清醒的思想,不受皇天命运的愚弄;古代社会关心同邦同族人的福利,定期取消债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卷三:2-3)。《再论中西古典学》“余论”从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而成《清代学术概论》说起,但林先生不同意梁氏对文艺复兴“以复古为解放”的理解。“应注意的,是走向近代,而不是‘复古!”(卷四:486)
与此相结合的是一种对古老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的关注,例如在谈及古代“共和”时,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溢于言表的赞颂(卷三:312-313)。这种爱国主义体现在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珍惜中国古典传统在思想和实践上的价值。林先生认为孔子是古典文明时代东、西方的第一个政治学作者,“《论语》是世界第一部政治学著作”(卷三:76-77)。而且“古代中国先秦的政治学,由于城邦制度发展比较单纯,讨论邦与天下(邦的联盟)的关系,王与霸的关系(均为盟主之邦),比之西方古典政治学似乎高明多了”。林先生感叹道,“世之论古典政治学者,但知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不知孔墨孟荀之书皆政治学著作也!”(卷三:124)
林先生将管仲、梭伦、赵盾、克里斯提尼、子产、太米斯托克利、范蠡、伯里克利、商鞅、德谟斯梯尼列为雅典和中国公卿执政制时代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卷三:63-64),将孔子、希罗多德、苏格拉底、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列为公卿执政制时代政治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卷三:68;同书77页另加上后来的西塞禄)。王失去政治之权,公卿以执政地位专国,以民众利益为依归,如郑之子产,可称“民主政治”。孔子称“忠”,但作为邦学或城邦学的《论语》需要在忠于邦人、国人的语境内解读,这样一来便能够看到,“在古中国,在古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思想,在政治学上都是主导的。”(卷三:69;另见同书:85-88、113-114)
但林先生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特别是古典帝国的传统,并非没有严重的问题。他试图对此给出解释。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近代国家,文艺复兴后因为能够珍惜古典、利用古典而得其利好,不曾发生黑暗时代,亦不知类似西欧之中世文化的中国,反而备受古典精神沦丧的伤害,其中原因便与古典帝国有关。先秦的古典政治制度和古典哲学思想,林先生说,“一变于统一专制帝国之秦汉时代,再变于分裂时日的魏晋南北朝及当时盛行的玄学(佛学)思想”,之后则进入佛道教盛行的隋唐盛世,古典中国儒学墨学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到宋明理学时期,古典学说“在专制统治下,不得不走入抽象的糊涂意识之中,古典真实精神破产矣”(卷四:468)。明清之际虽然也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思潮”出现,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但经过剃发留辫的清代专制荼毒,“古典学破产,斯文扫地矣!”结果,恰恰由于没有中世纪,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典帝国,不断改变古典政治文化以为己用,古典民主早已变成‘古典专制”(卷四:486)。《大学》纲领原本在于“亲民”,宋儒改为“新民”。林先生说,“程氏乱改,朱注误用,多少学子误读!”(卷四:487)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古典帝国史。“秦汉帝国本亦古典时代史的一部分,犹之罗马帝国亦欧洲古典文明之组成部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固然古典文化在古典帝国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古典民主变成了“古典”专制,古典文化还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得以继续发展。秦汉以降两千年,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内在发展脉络观察,其发展不大受政权更迭的影响,仍然能够按照历史发展方向有所前进(卷四:487)。至于中国没有因为蛮族入侵而形成黑暗时代的原因,林先生认为首先在于中国文明在之前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各族基本生活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已经日趋同化。如匈奴至冒顿以下,已成游牧帝国,不再是早期氏族部落组织形式的蛮族,而古代中国有可变之礼俗,却没有排他的宗教(卷三:477-482)。
和欧洲的发展路径相比,古代中国从古典时代以降发展的连续性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林先生认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思想文化方面都找不到合适的解说。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一种人民革命的传统,是这样的人民革命的传统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一次又一次地返老还童。汤武革命、国人运动,以及思想家、哲人号召或实际领导下的民众起义,例如“以孔子家族为首的历史上有知识分子参加或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前“是中国(古典)历史上历来革命运动的主流”。这样的革命传统只见于中国而不见于欧洲 (卷三:206;另见卷四:471-472、483-484)。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陈涉首事。林先生说,“这是什么系统,古典民主的系统”(卷三:94)。
基于这样的认识,固然“古典中国,由古典时代到古典帝国,历时长而且复杂,古典时代的政治、文化,到后来变而又变了”,要继承古典民主的传统,林先生说,“恐怕应走的道路,要达到民主,是‘革命而不是‘文艺复兴吧?”(卷四:487)这样的“革命”,是汤武陈王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延续,也是回归中国古典民主政治的手段。古典民主政治,在林先生这里既是回归的目的,也是回归的手段,虽然这样的回归并非“复古”,而是走向“近代”,走向未来。
四、“中西古典学”的基本方法
阅读林先生的作品,往往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的写作自成一格,和冷静自制的史学写作并不相类。他思考问题和处理资料的方式也极有特点。这些给我们总结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的方法论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但用心体会的话,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自身比较一致的方法论特点。在对具体研究问题的处理上,林先生强调通过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复原古代文明世界,将论证的基础建立在对史实和概念的澄清上,如关于勒夫坎狄考古发掘的讨论(卷三:34-42),对“共和”和“共伯和”的文字考订和辨析(卷三:316-327)。在理论层面上,则或可将林先生的方法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整体史观和中国通史传统的某种结合,尤其重视史学阐释。①对复原历史的强调和对史学阐释的重视之间有很大的张力,但这也让林先生的作品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上文已经提到,林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明自成系统,而西亚、北非、南亚、中亚文明都因为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而共同形成西方文明系统,成为“中西古典学”要面对的“古典文明世界(一个整体)”(卷三:15,图示)。为了说明这种整体性,特别是中国古典文明和此处定义的西方古典文明之间的整体性,林先生专门提起丝绸之路,并将丝绸之路称为强调整体性的古代文明世界的象征。他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不必东起长安、洛阳,也不必止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在这些大城市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卷三:20)。林先生并罗列考古和文献证据,说明中国和西方“自新石器文化至古典时代文明”,一直在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的礼俗习尚方面不断地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卷三:27)。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林先生受传统史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甚深。在史学概念的使用上,林先生非常注意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概念,例如对“公卿执政制度”的创造性发挥(卷三:154),以及在历史分期上采用《史记》以“共和”为界,将“黄帝以来迄共和”和“自共和迄孔子”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认为其“符合历史实际”(卷三:305-308)。《太史公自序》云:“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林先生将汤武陈王革命这种“吊民伐罪”,“民欲天从”的革命传统当做中国古典精神的宝贵传统来对待,特别是儒家与陈王革命的历史关联,强调“孔甲为陈王博士”(卷三:93-99)。
在具体研究上,强调根据原始材料的实证研究之外,林先生较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需要说明的是,比较研究对于林先生,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案和解决手段,是为他的整体框架服务的。只在后者的意义上,林先生对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做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例如林先生在讲到中国和西欧中世纪的时候,固然 “有许多方面,许多问题,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补充,彼此启发的”,但紧接着他说,“无论是古典,还是中世,中国和西方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问题的。”(卷三:145)是“行国帝国”在中国和欧洲造成的不同结果,让欧洲和中国的中世纪有了颇为不同的形态。而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上来说,中世纪的差异只是历史的变形,而二者进入近代的时间相差并不很长(卷三:146)。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和基本立场,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论中西古典学》和《再论中西古典学》是《中西古典学引论》的最后两篇,应该说也是林先生系统地阐述“中西古典学”最重要的理论作品,比较充分地展示出先生对“中西古典学”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林先生对“中西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定位相当明确。对林先生来说,“中西古典学”固然首先是个研究规划,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学科规划,应该作为一种学科规划纳入后来者的视野加以探讨。
小结
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了解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的理论和实践,成书于1981年的《世界上古史纲》以及初版于1989年由林先生主编的《世界城邦史研究》,是尤其不能忽略的两部作品。和这两部作品有关的史实和理论方面的具体问题留待来日讨论,这里只依据《日知文集》版《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和《中西古典学引论》,对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学术构想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林先生的字里行间感受他学术上的勇猛精进和思想上的雄才大略。在“古典学”概念受到重视的今天,回顾林先生穷毕生之力提出的“中西古典学”构想,更有着特别的意义,尽管这样的回顾也带来必要的反思和批评。
就本文所及,首先《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虽号称“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但其中内容的选择性很强。全书第二篇以下主体内容,除第十九章简单介绍中东地区古代帝国之外,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古代的论述。考虑到上述提及的林先生对中国城邦时代研究的有意强调,这种篇幅上的侧重可以理解。只是林先生将古代文明和国家最早的发祥地,最早进入“古代(或古典)帝国阶段”的“中东”地区简单地看做“古代文明世界的居间部分”,用一章的篇幅介绍完毕,主要依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描述了一下从亚述帝国到波斯帝国的发展梗概。尽管其中也有属于先生自己的思考,如关于两河流域亚述帝国之前所谓帝国和周王朝的类比,并列其于“盟主之邦”的概念框架之内(卷三:455),这样的处理还是让人难以接受。将整个希腊之前的近东历史当做背景处理的做法,和林先生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偏见实在是同样的来源(卷三:122-125)。“东方专制主义”确实是欧洲史学的一大误解,但这样的误解并不仅仅针对中国。
更容易引起争议的仍然是林先生关于民主政治的表述。批评意见这里不必要一一陈述,而且林先生的看法初看起来确实有荒唐不经之处,需要仔细辨析明白方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林先生所说的“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面来理解,也就是将重点放在“非专制”的特点上,其观点却显现出深刻的洞见。这样的谨慎理解应该是在对待林先生作品中瑕瑜互见之处时特别需要的。其余如城邦时代和帝国时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差别,林先生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和有必要的。另如林先生对“公卿执政制”理论的发挥,值得深入思考。林先生对孔子的分析,特别是强调《论语》“是纯粹的邦学或城邦学”,也值得研究者深思(卷三:78-93)。此处相关的“天下”问题,可参见刘家和《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收入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