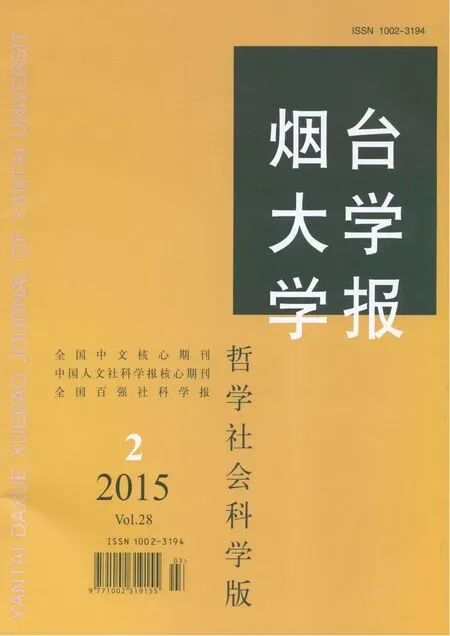论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基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
彭启福,钟 俊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基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
彭启福,钟 俊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学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人民法院对各种解释方法的选择不是智识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定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特别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作用。为确保法律解释方法得到正确运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作为办案指导,另一方面要拓展生效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开的广度与深度。而从长远来看,则需要改革完善法官制度,建设一支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高素质法官队伍。
自由裁量权;法律解释方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裁判文书;法官队伍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2.009
自由裁量权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秉持正确司法理念,运用科学方法,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最终作出依法有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裁判的权力。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助于消除“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防止司法恣意和司法腐败,从而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法发[2012]7号文),曾从法律解释方法等十六个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做出过明确规范。为此,笔者就法律解释方法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问题略陈己见。
一、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与位阶
“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①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而所谓“法律解释方法”,即是指为了获得裁判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作业所使用之方法。②黄涌:《建立“二元化”法律解释方法适用模式的研究》,见柳经纬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四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和数目归纳不一,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但综合起来看,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划分为四类: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利益衡量。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又包括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而论理解释则具体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本文探讨的“法律解释方法”,指的就是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它分为十个种类:(1)文义解释,即根据法律条文中文字所表示的真实含义进行解释。(2)体系解释,即把某个法律条文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根据它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确定该条文的含义。(3)法意解释,又称为立法解释,即以探求立法者的原意是什么来进行解释。(4)扩张解释,即当法律条文所表现的文义过于狭窄,不足以体现立法的真实意思,无法包容案件事实时,可扩张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解释。(5)限缩解释,即当法律条文含义过宽,把本不应该适用的事实包括进去时,就要将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缩小解释。(6)当然解释,即某个法律条文虽未明文规定适用于某案件事实,但从立法本意来看,该案件事实更应该适用该法律条文。(7)目的解释,即以立法目的作为根据来解释法律规定。(8)合宪解释,即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及基本法规定的原则。(9)比较法解释,即用国外的规定和判例来解释本国的法律条文。(10)社会学解释,即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解释法律规定。*王仲云:《法律方法及其运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由于运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将导致不同的解释结果,故而需要在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确定一个位阶顺序,来解决方法运用中的冲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倘若我们能够为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确定一个稳定的排序,那么就可以为法律意义的生成确定一个不变的路径,如此就可以有效地约束司法者的恣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学术界对法律解释方法排序问题(即解释规则)的探讨达成了一定共识,梁慧星先生将其总结如下:(1)文义解释应首先采用,用文义解释若有复数解释结果时,方能继之以论理解释。(2)在为论理解释时,应先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方法,以探求法律规范意旨;在确定法律意旨的前提下,可以继之以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或当然解释,以判明法律之意义内容;若仍不能完全澄清法律文义之疑义,应进一步作目的解释以探求立法目的;或在以上述方法已初步确定法律意义内容后,再作目的解释,以立法目的检查、确定之;最后以合宪性解释进行审核。(3)倘若经采用论理解释仍不能确定解释结论,可进一步用比较法解释或社会学解释。(4)所作解释,不得完全无视法条之文义。(5)经解释存在相互抵触之解释结果,且各种解释结果均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时,则应进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从中选出具有社会妥当性的解释结果,作为解释结论。*梁慧星:《民法解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
二、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
不难发现,上述解释规则对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其背后隐含着一种逻辑:尽量在法律文本的范围内完成解释活动,或者说,“法律形式主义的解释”优先于“法律现实主义的解释”。这种逻辑仍然体现着形式主义法学对法律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追求,以及对司法能动性和自由裁量权的戒备。毕竟,如果司法过程被搀杂太多法律之外的因素,法院的判决乃至法律自身就会变得相当不确定,这极有可能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的泛滥,恣意擅断和徇私舞弊也极有可能乘虚而入,法律自身以及法治的权威和尊严都将面临严重挑战。事实上,只是由于司法三段论所依据的形式理性思维解决不了司法裁判中的前提问题,法律解释方法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才获得了正当性的依据。
对于上述解释规则,一种乐观的评价是,解释方法的排序已经为案件的裁判提供了一个初始的操作框架并因此降低了疑难案件的司法难度。国内绝大多数研究法律解释的学者赞同这种观点,美国的罗纳德·德沃金、德国的卡尔·拉伦兹也持这种观点。*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另一种悲观的评价是,对各种解释方法的排序,虽然确认了某种解释方法相对于另一种解释方法具有优先性,却不能明确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后位的解释方法可以取代前位的解释方法,因此不能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提供一套可以作为方法的程序性指令。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美国批判法学的倡导者,其中对解释规则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卡尔·卢埃林和理查德·波斯纳。*参见Karl N. “Llewellyn,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Appellate Decision”,50 Vanderbilt Law Review,pp. 401-406.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为了对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有全面认识,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这两种评价孰是孰非。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提到的埃尔默案,是在法律解释方法排序问题研究中经常提及的案件*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4-19页。。其案情为:1882年埃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的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埃尔默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随时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埃尔默的罪行被发现后,被定罪,判处监禁。其祖父的两个女儿巩纳丽尔和里根,向遗产管理人提出要求说,现在应由他们代替埃尔默继承遗产。而埃尔默能否成为祖父遗产的继承人,则引起了当时法官们的争论。法官格雷按照文义解释方法,认为埃尔默仍然享有继承权,因为当时纽约州的法律没有规定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丧失继承权。但是另一位法官厄尔则按照立法意图解释法,认为应剥夺埃尔默的继承权。厄尔法官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埃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
从埃尔默案的判决以及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解释方法排序的影子,但却看不到排序被期待的那种作为操作规则的方法论意义。诚如梁治平先生所言:“有一点很清楚,在面对不止一种可以采用的方法时,我们无法由方法本身了解到,究竟应当选择这种方法或排序还是另一方法或排序”。*梁治平:《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见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92页。的确,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无法从方法自身得到解决,方法间的冲突必须靠原则来解决,是原则统驭方法。不过,原则统驭方法的结论虽然使我们可以把目光越过方法间的争论,却又使我们陷入了各种原则的冲突之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主张都必然有相应的法律原则支持。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已成立的法律应得到普遍遵守”原则和“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原则间的冲突。因此,要彻底解决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就必须寻找为原则冲突定纷止争的元规则。*雷绍玲:《论法律解释元规则》,《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只有发展出一套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解释方法的元规则,法律解释学才能功德圆满,并真正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圆满解决。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唯一涉及法律解释方法排序问题的官方文件——《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也仅仅是强调了文义解释的优先性: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涵义的,该涵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以及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不是一种程序性的操作规则,它至多被看作是一个程序性的操作指南——仅仅是指南,而非指令。
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甚至不具有操作指南的意义,因为人民法院对各种解释方法的选择不是智识性的,而是策略性的。法官处理案件,一般是先根据自己的司法经验,综合性地对案件作出初步的判断,然后再去寻找法律依据。若是能够找到明确、唯一的法律规定,则会依该法律规定裁判;若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存在两个以上彼此冲突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与自己的判断相矛盾,法官就会根据法律原则,借助各种解释方法来论证自己裁判的合法性。这种先有结论后寻找理由的思维过程,就像普通人不是先考虑语法规则再开口说话一样,对语法规则的考虑只是在检验所说话语是否正确时才会出现。*侯学勇:《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吗》,《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7期。诚如法国法学家萨勒利斯所言:“一开始就有了结果,然后它找到法律原则,所有的法律解释都是如此。”*转引自Benjamin N.Cardozo,The Nature ofJudicial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170.拉德布鲁赫也指出,是解释追随着解释结果,而不是相反。*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第107页。在这种“结论先导”或“结论主导”型的思维模式下,法律依据的寻找、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都是为了“证明”最初结论的正确。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苏力先生才断言:“法律解释的问题不在于发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而在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做法提出有根据的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显而易见,由于法律解释元规则的缺位,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已经陷入困境。其原因在于它企图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意识来追求法律的客观性,天真地认为只要按照程序性规则选取解释方法,就能发现法律的客观本义并由此推演出对案件“唯一正确”的裁判。而归根结底,又在于它遵从了形式主义法学的思维:法律相对于所适用的对象总是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个机械的、纯客观的反映过程。然而,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揭示的那样,“法律并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有效。”*Cadamer,Georg H. Truth and Method,New York: Cross Roads, 1984,p275.法律不只是作为条文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而存在。解释者对法律的解释映射在法律之中,直接构成法律的一部分。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解释注定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单纯的复制。*梁迎修:《超越解释——对疑难案件法律解释方法功能之反思》,《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因此,将法律解释视为一种纯粹的智识性追求,也注定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不过,尽管法律解释学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法律解释方法在司法中的作用。首先,法律解释方法不仅为法官在裁判中进行法律发现提供了大致的路向,同时也为检验裁判的正确性提供了批判性标准。*王彬:《超越基础主义的法律解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2期。其次,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使裁判的获得成为一种公开民主、分析说理的过程,为案件结论提供了一种符合“逻辑理性”的根据,从而极大提高了裁判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最重要的是,法律解释方法固然不能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但却有能力否决一个和法律“不沾边”的裁判,从而有效地限制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
在法律解释方法运用问题上,形式主义法学主张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排除解释者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的主观价值判断。但如此一来,法官的司法审判无疑将成为法条指挥下的机械操作,法律也就成了僵死的教条。例如,有一农民自己出资几十万元为村里建桥通路,并协议补偿了工程占用的他人自留地。大桥竣工后,后者反悔,以自留地被侵占为由诉至法院,法院以农民自留地不准买卖为由判决建桥农民侵权,拆桥还地恢复原状。对照法条似乎判得有据,然自古以来修桥铺路都被视为功德无量的大善事,怎么到了社会主义法治时代反成了侵权违法之事?*张雪樵:《科学执法的法律思维》,《法治研究》2010年第6期。很明显,法院在本案中没能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失范的。
事实上,法律解释不是单纯地查找和发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而是以特定的法律价值为指南的合目的性的实践理性活动,同时法官也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所以法律解释过程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沈仲衡:《疑难案件的法律解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众所周知的或者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或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行所持有的偏见,在法官决定人们都应一体遵守的法律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三段论所起的作用。”*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1页。以此而论,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的司法处理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实践理性问题,它需要综合权衡法律内外的各种因素,在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均衡点,从而彰显司法的终极智慧。例如,在2001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二奶”受遗赠案中,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面对一份形式合法且经过公证的遗嘱,法院完全可以按照“三段论”做出支持原告“二奶”的裁判。但是如果这样裁判,表面上看是“忠实服从了法律”,实际则使法律和法院沦为了某些人通过不道德行为达到其不正当目的的工具,同时也将招致社会公众的强烈非议,这显然与司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理念背道而驰。于是,一条公序良俗原则——“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被不失时机地派上了用场,法院在进行价值判断后权衡利弊,最终否定了遗嘱的法律效力。*何海波:《认真对待道德》,《法制日报》2002年10月24日,第2版。
由此可见,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当然来自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推演,预测不同裁判方案的社会效果并对相互冲突的权利或利益进行权衡与取舍,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决定了案件应当如何裁判、法律应当如何解释。这恰如波斯纳所言:“在通盘考虑之后,后果比较好的解释因为其后果比较好这一点,也许就是‘正确的’解释。”*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而在预测社会效果中进行的利益衡量,其本质是价值判断。因此,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需要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对各类案件中的利益冲突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指导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实现个案公正、协调个体利益、化解局部矛盾,贯彻法治精神、追求实质正义,以达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张军:《在司法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方法论》,《求是》2011年第4期。
由于裁判文书是司法权行使的最终体现,所以强化对裁判文书的规范,让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文书公开自由裁量过程,并对自由裁量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充分论述,就能对法律解释方法的正确运用进行有效监督,这也是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有效方式。而要强化对裁判文书的规范,就必须拓展生效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开的广度与深度。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要“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为此,笔者建议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四条,删除“(二)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和“(四)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两项,从而使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外,绝大多数生效裁判文书都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等不宜公开的内容依然要做技术处理)。同时,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及其亲属均可申请从中国法学会或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法律专家库,随机选取数名德高望重且无利害关系的法律专家对该裁判文书进行评论,评论内容可与裁判文书同时公布或在限期内公布,评论内容及其社会反响作为法官年终考核的参考依据。通过这一改革,司法审判的任何瑕疵和疏漏都有可能被公众所关注,由此形成的强大社会舆论,将有助于督促人民法院审慎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让司法恣意和司法腐败无处遁形,也有助于平息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不满,做到辨法析理、胜败皆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改革设想虽然美好,但从中国现阶段法官的司法环境、司法能力和司法心理等因素整体考察,无疑会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故只能在试点中逐步推进。从长远来看,各级人民法院要想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来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过硬、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高素质法官队伍。这是因为,哲学诠释学告诉我们:解释是一种对文本的理解活动,在理解的过程中,无法排除解释主体的“前见”;拥有不同“前见”的法官面对同样的法律条文,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只有建设一支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高素质法官队伍,才能确保人民法院在利益衡量中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实现案件裁判“两个效果”的统一。
首先,就职业法官队伍建设而言,应采取以下举措:
(一)科学考核,建立法官的淘汰机制。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因此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法官少而精、辅助人员专而足”的人员配备模式,法官按单独序列管理,以便提高准入门槛,增强职业保障,配足辅助人员,提升公正司法能力。通俗的讲,就是对法官队伍重新洗牌。按照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上海法院拟在3至5年内逐步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员额比例控制在33%、52%和15%。尽管上海只是试点,但这个改革方案还是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何帆:《做好法官员额制的“加减法”》,《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17日,第2版。为此,今后各地应在合理确定法官员额的基础上,通过公平公开的竞聘上岗,将最优秀的法官留在现有体制内,在法官岗位上更好地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下的法官淘汰机制:年度考核时,将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对法官的评价作为重要依据,当事人以输入密码进行网络投票或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投票的方式,自愿参与对办案法官的评价,凡满意率低于投票总人数20%的法官,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连续两年不称职便可依《法官法》第40条的规定予以辞退,空缺的法官岗位重新竞聘。与此同时,在省一级高级人民法院成立有学者、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人员参加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并于省级高级人民法院网站设置“法官惩戒委员会”链接网页,在强调实事求是、理性反映问题的前提下,公开所有群众的举报、投诉及其处理结果;实名举报人如对惩戒委员会处理结果不服,可申请从省级法学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数名法律专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开展调查,调查报告上网公示,调查小组成员对报告真实性负法律责任。这样一来,就可确保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淘汰出一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法官。
(二)重视品行,完善法官的选任程序。法官的个人道德及人格魅力对于成功化解社会纠纷,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是至关重要的。而只有品行良好、正直善良的人,才能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正如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所言:“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史尚宽:《宪法论丛》,台湾:荣泰印书馆,1973年,第336页。但与政治素质或业务素质不同,要使法官具备良好的品行,主要途径不能是职业道德建设或道德教育,而是必须把住“入口关”,注重对“好人”的选拔任用。2001年修改的《法官法》第九条仅原则性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而缺乏具体可操作性方案,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鉴于对道德品行的评判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程序解决的问题,故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和研究成果,尽早出台《法官遴选办法》(试行),完善法官的遴选制度。例如在省一级成立由法官代表、律师和法学学者代表、两会代表等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提出法官人选并对提名负连带责任,若该法官今后被确认违法违纪,赞成提名的委员需要引咎辞去委员职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再如,在对初任法官进行职前培训期间,通过官网、电视、报纸等媒体对其任职信息进行一周以上的公示,并以重奖方式鼓励人们举报其不良行为。
(三)深化改革,健全法官的保障体系。在淘汰不合格法官、完善遴选制度的同时,要注意健全法官的职业保障体系,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确保优秀人才流向法官队伍。为此,第一,要完善法官的职业身份保障制度,保障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例如前述“法官惩戒委员会”既要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要保障法官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法官如对惩戒委员会处理结果不服,也可以申请从省法学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数名法律专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开展调查。第二,要健全法官的职业收入保障制度。除了尽快建立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的配套薪酬制度,建立以专业等级为基础的法官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外(即法官工资、津贴等不再与行政级别挂钩),还应推行相应的法官奖励计划,每年确定一定比例的法官予以奖励,以保障其年度总收入处于当地法律从业者中的上游水准。这样一来,既可以吸引优秀的律师、法学专家及其他优秀法律工作者加入法官队伍,又可激励其他法官廉洁自律、公正司法,强化人们对法官职业神圣感、荣誉感的认同。第三,要建立法官的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多年来,频发的法官遇袭事件,让法官成为“高危职业”:被拘禁、被枪击、被泼硫酸……此外,纠缠、侮辱、诽谤法官的事件亦不在少数,法官群体履职面临着严峻的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鉴于此,应采取为法官购买意外身故、残疾保险等措施,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
在加强职业法官队伍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
(一)重视人民陪审员的行业背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提出了扩大人民陪审员总量的“倍增计划”,即2至3年内将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翻一番,从目前的8.7万名增至20万名左右,并将确保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社区居民等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的三分之二。为充分体现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笔者建议在推进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时,要重视人民陪审员的行业背景,确保社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代表被任命为人民陪审员,以便“把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法律意识、道德观念带到法院里来运用”,*《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539-540页。帮助职业法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这方面,可借鉴人民政协按界别分配委员名额的办法,根据各地法院受案类型的统计分析,合理决定各行业人民陪审员名额分配。
(二)改革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机制。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优良传统,是在审判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也是确保法院的人民性、防止法院官僚化的重要举措。为了实现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对目前陪审员人选由基层法院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确定、并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官僚化模式,要进行必要的民主化改革。笔者建议参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第三章的规定,在基层法院提名候选人后,由该法院司法辖区内的居民以自愿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人民陪审员,以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司法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听取民意的功能。同时,建议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条件,明确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即可,而把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作为推荐候选人的主要标准。这样做也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思路——“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的保障机制。《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行[2005]72号)印发以来,基层人民法院陪审工作经费保障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仍有很多基层法院没有对人民陪审员的交通、误工等费用建立统一的补助标准,更没有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建立相关经费的正常增长机制。这极大地压抑了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参与陪审工作的热情。为增强人民陪审员岗位的吸引力,各地人大今后要加大对人民陪审员工作经费保障的监督检查力度,积极推动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严格按照单独列项、统一管理的要求,全面落实人民陪审员工作经费保障的有关规定,足额发放人民陪审员的交通、误工等补助费用,并探索建立经费保障标准及定期调整机制;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认真落实对优秀人民陪审员进行表彰奖励的规定,以此吸引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积极加入到人民陪审员的队伍中来。
[责任编辑:赵守江]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urt Discretionary Power——Based on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PENG Qi-fu, ZHONG-Jun
(InstituteofPolitics,AnhuiNormalUniversity,AnhuiWuhu241000,China)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is not methodologically meaningful, the choice of methods to interpret by the people court is not intellectual, but strategical. Even so, we still can not completely negate the method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the regulation of discre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t present, the people courts at all levels should take Marxism philosophy of law as the guidance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judgment documents to the public. In the long run, we need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judges, and build a team of judges that combines the high-quality judges of occupation and democracy.
discretionary power;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Marxism philosophy of law; judgment; judges
2014-12-18
彭启福(1963- ),男,福建长汀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诠释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14YJC710058)
D
A
1002-3194(2015)02-006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