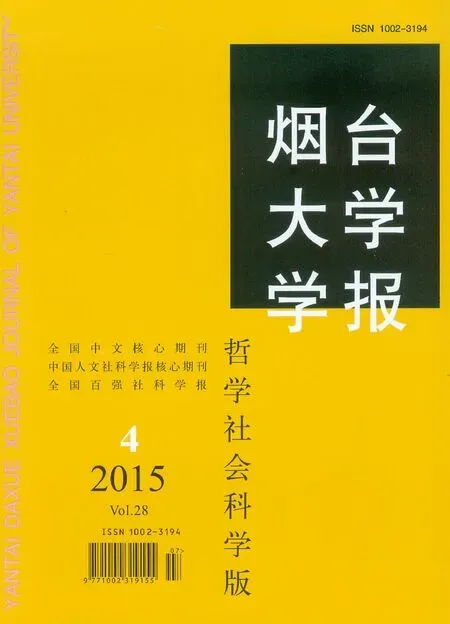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
——圣经《创世记》前三章底本的融合
黄 峰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
——圣经《创世记》前三章底本的融合
黄 峰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由于兼有P、J两个底本的创世内容,《创世记》前三章在叙事逻辑上具有显性冲突。但犹太教祭司们在坚持宗教信仰准则的同时,巧妙地通过表层文本的细节叙事暗示出亚当在吃禁果中的隐性犯罪,并进而建构起“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潜文本叙事结构。《创世记》前三章利用这种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叙事共谋关系,不仅有效地化解了P、J两底本之间的显性冲突,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完善了创世故事,这对增强整个圣经文本的内在凝聚力有着重要作用。
《创世记》;圣经文本;表层文本;潜文本;叙事共谋;底本融合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4.011
作为宗教经典,圣经自诞生伊始就伴随着崇敬与诋毁、坚信与质疑的释经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圣经自身由于不同底本(documentary materials)的“糅合”所导致的部分叙事逻辑混乱,确实为后世千百年来的意义纷争留下了释经困难的窗口。以《创世记》前三章为例,因为存在J本(亚卫本)、P本(祭司本)两个底本的缘故,文本叙事表层就存在着明显的叙事冲突:两种不同形式的创世模式,两种不同的男女诞生模式,以及两种不同的对耶和华神的称呼,而夏娃吃禁果一事则只是J底本独有的内容。因此,针对圣经的任何释经行为都无法忽视这种文本表层的叙事冲突现象及其由此带来的诠释困难。
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为从文学角度诠释圣经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通过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特点认识文本整体。还以《创世记》前三章为例,仅从表层文本叙事看,P底本的七日创世与J底本的吃禁果都只是单一的叙事片段,无法共同串联起两个有矛盾的底本。但犹太祭司们把两者编撰在一起的事实情况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暗示:七日创世与吃禁果绝不仅仅是P、J底本各自独有的叙事片段。比如,吃禁果片段不仅是伊甸园故事的转折点,更是在整个创世故事(两个底本的共同主题)的大背景中给予叙述。因此,对吃禁果一事的分析,不仅要聚焦于伊甸园单一语境(J底本)下的细节叙事,还应站在统一的创世环境(J、P底本)中予以关注,也即透过表层文本的叙事,寻找潜文本叙事结构存在的可能,寻找其在更大范围(JP统一体)内的叙事意义。
一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米开朗琪罗在创作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场景时,把夏娃画得极其丑陋,甚至猥琐得像个野兽。①叶丰编:《圣经图录》,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8页。神学家坚信是夏娃的贪念导致了“原罪”的出现,而“原罪”就是导致后世子孙背负枷锁而倍感无望的“犯罪学”根源。就连文艺批评家奥尔巴赫也认为夏娃“只有幼稚的、孩童般大胆而又轻率有罪的好奇心”。②Erich Auerbach,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47.因此,从宗教信仰、传统释经学甚至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来看,夏娃都必须为“原罪”接受惩罚。但吃善恶树果子的罪过难道就“全”是夏娃的错吗?亚当在这一过程中的“沉默”或“不在场”是否可以为其作无罪的解脱呢?答案只能从文本的细节叙事中寻找。
从《创世记》(2:16-17)可以看出,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③圣经版本:NIV.(THE HOLY BIBLE,NEW INTERNATIONAL WERSION,本文引用的圣经英文均出自此版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神只对亚当说了这段话,因为此时女人(犯罪之后被亚当取名为夏娃)作为a helper(suitable for him)还未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女人本人并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告诫。但下文中女人确实和蛇有过对话,并“大致”说出了神的意思,唯一的可能就是亚当转述了神的告诫。但按照英伽登关于作品只是“图式化”的构造,包含许多“未定点”的观点来看,在神对亚当进行告诫之后,在女人与蛇进行说话之前,确实存在叙事上的“未定点”,即:亚当是如何转述神的告诫的。
我们需要对女人与蛇的对话进行文本细读。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3:2-3)。把这句话与神和亚当交谈的那句话(创2: 16-17)相比,女人在表述上明显有三处发生了变化。变化就意味着有潜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能为读者提供窥视文本叙事意义的窗口。
变化之一是亚当在传话时的语焉不详。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创2:9,用的是复数),但神在对亚当叮嘱时,用的是单数的名词“树”(创2:17),明确指出是园子“当中”之一的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另一棵在园子“当中”的生命树与其他树的果子一样都可以吃。但女人在和蛇对话时,只提到园子“当中”有一棵树(创3:3,用的是单数)的果子不能吃,而且没有明确指出是哪棵树。换句话说,就算不计较“当中”一词意指是一个面还是一个点,反正女人此时并没有分清同为园子“当中”的生命树与善恶树,也没有分清到底哪棵树的果子该吃,哪棵树的果子不该吃。因此,上帝最重要的告诫在女人这里出现了误读,被遗漏了最关键的信息。这一细微叙述的前后差异为女人最后被蛇诱骗,埋下了伏笔。因为,蛇明确告诉她,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不会死,你反而会如神一般知道善恶。这时很自然的逻辑推理就是,女人会以为那一定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会让人“死”。由于神只对亚当而没有对女人直接告诫,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亚当在转述神的告诫时,有意无意地疏漏了关键信息的传达。如果这一推测无法摆脱主观臆测的嫌疑的话,我们还可以从神的原话(创2:17)与(创3:3)相比的另外两处细微变化直接窥视到亚当的个人意图及行为。
变化之二是亚当在传话时的添油加醋。女人在和蛇对话时,说的是“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创3:3)。这与神的原话(创2:17)相比,多了句“不可‘摸’”的意思。神没有和亚当说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摸”、“碰”或“拿”之类的意思,只是强调万万不可吃。摸了、碰了果子会不会死,这点神没有明确告诫,这正是亚当为之好奇、困惑的地方。但女人与蛇对话时,却有了这句表述。那么,这层意思由何而来,是女人自己揣测的,还是亚当告诉她的?答案还是在文本的细微之处显现出来。《创世记》(3:6)写到“she took some and ate it”,女人先是拿了果子(而且是some),然后才吃了一个果子。作为用词简约但绝不简单的圣经文本,在这一文本细微之处特意突出与“不可摸”之间的叙述对应:女人动手“摸了”一些果子。按照女人的逻辑,如果真如上帝所言,摸了不该摸的果子就一定会死。但当她“连续”摸了一些果子时,却没有任何情况发生。这就让女人更深信蛇的话,吃善恶树的果子不应有事,所以女人干净利落地吃了其中一个果子。就这样,单纯的女人在误解神的旨意的路上进一步走远了。而在整个摸、吃的过程中,亚当没有任何劝阻,在看到没有什么事发生时,他也不客气地吃了,因为神的告诫已经被验证为不可信了(哪知神的旨意岂是人所能猜透的)。因此,亚当对女人的暗中误导,加之女人的轻信,使其成为亚当试验神的旨意的最佳试验品。
变化之三是亚当在传话时的避重就轻。在《创》(2:17)中,神对亚当叮嘱时,口气十分严厉,如果吃了果子,就“一定”会死①关于“死”的具体含义有不同诠释结果,较著名的是犹太思想家斐洛关于两种类型“死”的寓意释经法。本文因关注吃禁果前后的文本叙述细节,故而不对“死”做过多延伸阐释。此处仅理解为会有严重的后果。,表述为“will surely die”,也就是“立即”会死,表述十分明确。但女人与蛇交谈时,也提到吃了果子会死,但表述却只剩下“will die”,也即“将”会死。语气词的省略使得严厉的惩罚立马显得轻缓许多了。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女人在拿了又吃了果子之后,确实没有立竿见影的“死”(或任何形式的被惩罚)。而此时亚当就在那女人身边(创3:6,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who was with her,and he ate it.)。圣经作为意识形态强烈的宗教文本,在用词上一向简洁干练。但在这里,圣经文本特意用同位语的方式,强调女人把果子给了“就在其身边”的亚当,然后后者才吃了果子。因此,表层叙述在这里看似很随意的一句同位语,却反讽地透露了表层文本叙事真正要说的话:亚当没有阻拦女人。亚当把严厉的即时式惩罚转换成较为轻缓的将来式惩罚,导致女人再次轻信,哪怕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结果也不会很严重。因此,当那女人把善恶树的果子拿了又吃了,并且又没有特殊情况发生时,一直在其身边的亚当也就接下果子并吃了。换句话说,亚当并不清楚吃善恶树果子后的具体惩罚效果是怎样,而那个女人连续做了两件亚当自己想做但又不敢尝试的事情:摸与吃。这样看来,当上帝开始调查原因时,亚当张口就来的说辞(创3:12),更像是精心准备的辩解,完全推脱自己应负的罪责。
《创世记》在叙述伊甸园故事时,并没有浪费过多笔墨去塑造亚当、夏娃的性格特征。但经过上述分析可见,表层文本叙事的简洁并不代表叙事内涵的简洁。通过叙事细节的突显,表层文本含蓄地展示了亚当在整个吃禁果过程中的“不在场的在场”,他那好奇、谨慎、诱骗、甚至有点无赖等特点在字里行间不断闪现。犹太思想家斐洛为后世解读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他认为伊甸园中蛇是代表“快乐”的存在物,象征无休止的个体欲望。②斐洛:《论〈创世记〉》,王晓朝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7页。蛇是最狡猾的动物(创3:1),它的奇特不仅仅在于其“‘狡猾’原文['ārûm]和亚当‘赤身露体’的原文字根['ārôm]十分接近,”③邝炳钊:《创世记注释》(卷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35页。暗示了它与亚当在形态上的相似性,还在于它居然知道神与亚当的谈话,并用诱惑的语气反问那个女子。因此,蛇“能说话、会思考,就好像是人的另一个自我,人的一种意识形态”①南宫梅芳:《圣经中的女性——〈创世记〉的文本与潜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4页。,不仅与亚当具有异型同构的联系,更是亚当欲望的载体,并最终误导那个女人。传统释经所认为的夏娃被蛇诱惑,亚当与其一起承担罪责,现在看来更应是亚当诱惑夏娃,夏娃被亚当利用,夏娃才是整个事件的被动受害者,而非单纯的犯罪者。
二
表层文本叙事的细节解读为读者展示了亚当不易被察觉的另一面,同时透露出蛇与亚当具有某种形式的异型同构特点。但考虑到伊甸园故事只是整个创世故事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圣经研究学者罗伯特·阿尔特在分析类型场景的意义时,认为应“将此时此刻在历史与神学意义的更大的框架上进行理解”。②罗伯特·阿尔特:《圣经叙事的艺术》,章智源译,北京:商务印术馆,2010年,第83页。因此,读者有必要把诠释视野放在更大的叙事框架上,以便更好地理解创世故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原罪”的单一宗教解读。反对扩大诠释视野的来源批评学者也许会认为,只能对来源不同的底本进行独立研究,不能忽视彼此之间的叙述矛盾。但这种研究对于后世读者而言,其弊端之一是将已成定本的圣经人为地分割成若干历史断片,看似更深入了解圣经之来源,但对整体掌握并没有帮助。故而,罗伯特·阿尔特、利兰·莱肯等圣经研究学者主张,应把圣经文本作为一个既成定本进行整体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体观察看似杂乱矛盾的表象。本文无疑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看待《创世记》前三章的叙述矛盾。
从这个角度分析,“从神创造万物,到伊甸园故事,再到人类始祖被驱逐”组成一个更为完整、更大范围的叙事单元——创世阶段,包含P、J两个底本的全部创世内容,吃禁果仅仅是这一整体的关键转折点。围绕这一转折点,该单元建构起潜在的叙事结构——三次祝福与三次诅咒的对应叙述模式。其结构特征表现为:神连续三次“祝福”,继而发出三次“诅咒”,这是一个完整、对称的潜文本叙事。因此,从叙事学角度看,两个底本创世故事的表层叙事矛盾并不妨碍将两者在潜文本层面上重新进行更广阔的叙事建构。
三次祝福全部发生在创世第一阶段,也即P底本的创世中。神在第五日把圣经中的“第一次祝福”给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有生命的动物(不包括植物),在第六日把“第二次祝福”赐给了按照自己形象造出来的男男女女(整个人类),“第三次祝福”则赐给了第七日本身,称其为圣日。按照叙述顺序,动物享有神的恩宠而高于植物、光体等无生命物体,人类因分享神的形象而高于动物,但第七日本身则是神休息的日子,因神而荣耀,比人类距离神更进一步。因此,后来在西奈山上,耶和华面授摩西十诫时还不忘要子民们纪念安息日,并守为圣日。三次祝福与具体的创世过程巧妙结合,形成逐渐走高的施恩趋势。
在创世第二阶段,也即J底本的创世中,由于亚当与女人背弃神的告诫而选择吃禁果,所以耶和华神连续三次发出诅咒的威声,在力度上也是呈现逐渐加强的趋势。首先,耶和华神把“第一次诅咒”给了最狡猾的动物:蛇,罚它终日爬行、吃土;把“第二次诅咒”给了女人,增加其怀胎之苦,受蛇的困扰,并受丈夫管辖;最后把“第三次诅咒”给了亚当,罚他终日劳苦,复归于土。神当然应诅咒人类,因为圣经是一部推崇上帝话语权威的宗教文本,而人类违反的恰恰就是神的话语。但在叙事结构层面,这种先“祝福”,后“诅咒”的叙事策略就建构起三次祝福与三次诅咒对应的框架,这也是《创世记》前三章所包含的潜文本叙事结构。
通过表层文本细读与潜文本叙事结构可见,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叙述结构中存在着巧妙的叙述对应关系。这种对应不仅体现在次数上的相同,都是三次(“3”本身在圣经中就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更体现在内容上的呼应,具有彼此逐一对应的叙述逻辑。较为明显的对应是第一轮祝福与诅咒。第一次被祝福的各类“动物”对应的正是第一次被诅咒的“蛇”,双方都是有生命的动物,只不过是群体缩减为个体的差异,较为宽泛的名词对应具体所指的名词。由上文分析可见,这个最狡猾的蛇其实是亚当本人的欲望镜像,一个隐喻符号。因此,表层文本虽没直接言明但暗中把犯罪的矛头指向了亚当,到了潜文本叙事层面时,耶和华神同样把亚当的欲望显形“蛇”当作受罚的第一对象,并与被祝福的动物们对应。此处我们已可以见到表层文本与潜文本在叙事方面的共谋行为,并起到了消解P、J底本冲突的叙事作用。
第二轮祝福与诅咒的对象,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但较第一轮祝福与诅咒的对象要更高一级。被祝福的是全体人类(“男男女女”),而被诅咒的是那个女子(即事后被亚当称为“夏娃”的那个女子),依然是群体对应个体,较为宽泛的名词对应具体所指的名词。全体人类比全体动物在属性上高级,而被惩罚要负责生养后代的夏娃则比单个的亚当更重要。但需要注意的叙述细节是:第二轮被诅咒的那个女人本是无性别的个体,她是在被诅咒之后才拥有了生理上的女性特征(创3:16)。换句话说,在被诅咒之前,亚当与那个女人是服侍神的同工伴侣,而不是夫妻式的伴侣,女人仅仅是亚当的帮手,两者的地位在神看来是一致的(均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创1:27))。一直到被诅咒时,神才明确说出她要承担生儿育女的痛苦,这时两性的生理区别才开始出现。因此,从《创》前三节潜文本对应结构的叙述看,神在创世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性别,更不仅仅是对女人的惩罚。第二轮对应叙述形式从叙事学上看,与第一轮叙事策略基本一致,不仅在更高层次上突出了祝福与诅咒的呼应,而且进一步弥合了P、J底本的缝隙。
如果被诅咒的亚当(蛇)与被祝福的动物对应,被诅咒的女人与被祝福的人类对应,那就必须解释第三轮中被诅咒的亚当怎么会与被祝福的圣日有对应关系?又是否比第二轮的对象更高级呢?在表层文本(创2:7)的叙述中可以找到答案。亚当是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所造,将生气(灵)吹在他鼻孔里。从希伯来语上看,“亚当”与“土地”有词源上的关联。①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66页。而从希腊语上看,“亚当”(Adam)是由东(anatole)、西(dysis)、北(arktos)、南(mesembria)四个词的首字母链接而来的,②冯象:《〈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6页。亦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三轮诅咒时,耶和华神没有先指责亚当,而是先诅咒大地,然后再诅咒亚当重归于尘土的原因了。而第三轮耶和华神诅咒亚当要终日在土地上劳作,与第一轮诅咒蛇(亚当)终日吃土,都指向了亚当与土地的关联。因此,在潜文本叙事层面,与圣日被祝福对应的不是作为单个的亚当,而是其所出之处的土地。“土地思想在作者的思考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创世记》全卷几乎无一处情节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及土地……显而易见,人地关系成为作者的主要兴趣所在。”③T.Desmond Alexander:《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刘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因此,与前两层对应一样,圣日可算作较为宽泛的名词,而土地是具体所指的名词,由空到实,由不朽到可朽,与由群体到个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本轮祝福与诅咒的呼应比第二轮的呼应对象更为宏大,一个至圣,一个至俗。当然,P、J底本在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中进一步融合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P与J两个底本在表层内容叙述上存在逻辑矛盾,甚至对神的称谓也不一致,但圣经的编撰者(们)却依然把两者编排在一起,用潜在的叙事结构来化解表面内容的冲突。这种匠心独具的叙事结构安排绝不是来源批评学派的学者们所能解释的。
三
从表层文本细节叙事中凸显出本真面目的亚当,在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潜文本叙事结构中起到了关键的串联作用。因为,正是亚当既“狡猾”又“来源于土”的独特个性真正从文本细节中浮现时,潜文本的对应叙事结构才得以成立。但潜文本叙事结构的建构不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学意义上的自圆其说行为,它无疑化解了由不同底本冲突带来的表层叙事矛盾,凸显了圣经叙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因此,至少针对《创世记》前三章而言,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之间具有明显的叙事共谋关系:共同建构了统一的创世故事。
“共谋”(collusion)在20世纪俄国叙事学家普洛普看来,指受害人被骗但无意中又帮助了坏人的行为,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行动功能之一。这些功能性行为只是单纯的人物行动,只是情节中一系列的行动环节,有时具有转折意义,有时则为了增加情节的曲折性。但从对《创世记》前三章的分析看来,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关系不是指某个具体动作行为,而是指叙事结构上表层文本与潜层文本的呼应特征/关系。它超越了两个底本的矛盾沟壑,“共谋”地建构起一个更大也更完整的叙事单元,从内容上包括神创自然界、创万物及伊甸园的全部情节。但考虑到J、P两底本的诞生年代相距几百年的历史,而且早诞生的J底本又放在晚出现的P底本之后等因素,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关系就不应是简单的拿捏在一起的文学性技巧。实际上,这种叙事共谋关系/特征的出现是了解P底本时代历史气息的“可视性”证据。
首先,叙事共谋关系体现了坚守犹太教信仰的目的性。公元前5世纪处于寄人篱下的犹太祭司们(如以斯拉、尼希米),历经千辛万苦编纂出摩西五经并进行专门的释经活动,其旨归无疑是宗教性目的,而不是文学性目的。但先期诞生的J底本具有明显的生活气息与世俗格调,虽然流传久远,但犹太教祭司们却对其不甚满意,更是无法接受人性化的神。因此,如何利用成熟的犹太教思想对其进行消解或整改,以达到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目的就是祭司们编撰的重点。这一时期编撰而来的P底本正是秉承了祭司们的宗教立场,重构一个充满神圣性的、严谨有序的创世阶段,并树立起神的无限权能与崇高。因此,根据底本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的观点,“梅瑟五书(即摩西五经)最后的编者,是以祭典(P本)作骨干编辑这些资料。”①宗座圣经委员会:《教会内的圣经诠释》,冼嘉仪译,香港:思高圣经学会,1995年,第9页。
但J本毕竟是最原始的底本资料,“仍然那么具有原创性,……我们仍旧陷身于无法同化其原创性的那个传统中”②哈罗德·布鲁姆,《神圣真理的毁灭》,刘佳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因此既然无法完全抛弃掉,祭司们有意或无意地采用文学的手法,利用表层文本(J底本之伊甸园部分)中亚当的本真面目,建构起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潜文本叙事结构,达到整合了P、J两底本创世叙事的目的。同时,出于坚守犹太教信仰的目的,把P底本安放在《创世记》的首章位置。这样一来,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关系体现出的首要特点应是流亡时代的护教行为,而不只是纯文学的创作因素。在这三章中,宗教意识形态占据绝对的统治位置,对所有独立化、片段化的叙事细节进行深层的整合。这样一来,祭司们就把犹太教的思维模式与信仰体系内在化为一种超叙事、超文本的意义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圣经文本已决然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生产,而成为犹太教思想的载体。
其次,叙事共谋关系体现了由多神论向一神论进化的时代性。从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对应结构中呈现出的对立模式,无论是整体叙述从祝福转变为诅咒,还是每一轮叙述对象的“冲突”式对应,都具有同一性的叙事特征:和谐与被逐、获得与失去、有序与混乱、遵守与背弃……因此,该潜文本结构展示的是“二元对立”——一种普遍存在的叙事模式。究其原因,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是由两个底本叙事冲突所带来的必然特征:第一,P底本展示的是祝福,J底本强调的是诅咒;第二,P底本与J底本具有明显时代差,是两段历史时期的交错;第三,P底本是祭司们的严谨创作,而J底本是长时期流传于民间的集体创作,从风格到体裁都不一致。考虑到底本说理论包括四个不同底本,所以二/多元对立项的普遍存在反映的是圣经实际编撰过程中的困难,即底本叙事之间的矛盾冲突。
但叙事共谋所融合的J、P底本毕竟来自两段不同的时代背景,J底本虽早至亚伯拉罕时代就已出现,但那时希伯来人一直受到异族多神信仰的影响,多次背离耶和华神而改为崇拜其他异族神或偶像(如出32:4,拜金牛犊为神;士2:11,侍奉异族神“巴力”),结果导致集体创作的J本世俗性较重。因此,及至公元前5世纪的犹太教祭司们开始编撰摩西五经时,一神论成为编撰的首要原则。P本虽然此时才编撰而成,但因其表述更为严谨、规范,神的威严与权能更加突出,用它统领世俗性较浓的J本,无疑会把纷乱的世俗信仰统摄在一神论的观念之下,既涵括了多神并存的历时的短暂纷争,又展示了一神信仰的共时的永恒价值。这种多神论向一神论宗教观的进化,也是P、J等底本最终能够融合在一起,从而超越表层矛盾的宗教学根源。因此,P、J被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关系整合为关于创世的完整叙事单元(PJ)后,后者才真正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连贯性:体现了神对人类的态度由恩宠到惩罚的历时性变化,也凸显了人类对神要坚定其权威的共时性信仰。
而对那个女人(夏娃)而言,被诅咒、被驱逐都是必然的。正如基督教强调的“幸运的堕落”(The Happy Fall)一样,如果没有夏娃的犯罪,也就没有原罪一说,也就不可能有耶稣基督的降临①刘意青:《〈圣经〉文学阐释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也就更不可能有迎接末世的新天新地的机会了。而从本文的叙事学立场看,没有夏娃单纯而好奇的吃果子,就不能暴露出亚当潜在的个人欲望与犯罪事实,也就无法解释在诅咒亚当的时候耶和华神为什么把矛头指向土地,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潜文本结构也就无法构成,届时P、J底本之间的叙事缝隙必将成为诠释过程中的真正障碍。因此,只能由表层文本的吃禁果被罚一事作为关键转折点,才能建构起独特的潜文本叙事结构,并借助叙事共谋的文学策略弥补底本之间的叙事缝隙,并达到坚定宗教信仰之最终目的。
弗洛伊德认为“犹太祭司们在他们所作的记述中,力图在自己的时代和摩西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连续性。”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5页。无疑,这种意图容易导致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J底本作为最早的凝聚民族意识的叙事单元,具有后来者无法超越的原创性。犹太教祭司们无法忽视,只能选择继承。另一方面时代背景的风云变幻,需要祭司们在更成熟的犹太教高度上统摄圣经文本整体,超越早先的单一叙事单元以适应坚定信仰的时代需要。于是就出现不同时代多个底本(J、E、D、P)的交叉糅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叙事冲突。但以《创世记》前三章为例,通过对其文本细读,读者可以透过内容上的宗教劝诫,窥视到祭司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文学手法破解上述两难局面,即利用吃禁果这一事件作为三次祝福——三次诅咒叙事结构的关键转折点,并构造起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关系。也正因这种叙事共谋关系的存在,《创世记》前三章得以超越不同底本的叙事冲突,并组成完整的创世故事。因此,至少在摩西五经的范围内,不同底本之间应是通过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从中后世读者不仅可以获得宗教信仰上的崇敬感,也可以寻觅到了解古希伯来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可视性”证据。毕竟,任何民族创世神话的价值之一即奠基于体现出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的生存境地与精神体验。
The Narrative Collu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Text and Subtext——On the Fusion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i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Genesis
HUANG 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Genesis contains different creation contents from both P and J documentary materials,so it has dominant conflict o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But Judaism priests,on the one hand,persisted in the rule of religious belief,and on the other hand,suggested that Adam hidden crime in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subtly through the narrative details of the text surface,and then constructed a subtext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three times blessing-three times cursing”.By using the narrative collu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text and subtext,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Genesis not only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dominant conflict between P and J,but also improves the creation story on a deeper level.This relationship is of great effect on enhancing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the wholly Biblical text
Genesis;Biblical text;Surface text;subtext;the narrative collusion;the fusion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I 106.99
A
1002-3194(2015)04-0094-08
[责任编辑:诚 钧]
2015-02-12
黄峰(1982-),男,安徽阜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圣经文学。
———山西教育信息化工作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