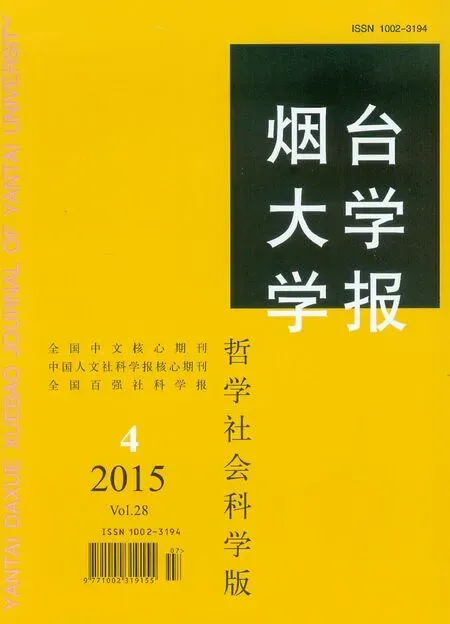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高 飞
(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高 飞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高度重视,将涉农政策的精神转化为法律制度,以法律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今后承包地流转制度完善的重要任务。其中,理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进一步彰显承包地流转自由,既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健全的基本前提,也是新一轮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制度目标。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权;承包地调整;流转自由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4.003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外出务工农民人数越来越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日益频繁。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面积达3.4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6%。①参见叶兴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6期。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助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也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业现代化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故为了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一轮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目标,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指导思想。为将上述政策精神落到实处,2014年中央1号文件(即《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2015年中央1号文件(即《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然而,要将这些政策精神转化为法律制度,并以法律制度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则需要进一步对相关政策进行梳理。本文拟以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和政策规定为对象,探讨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诸因素,期望对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一、理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
尽管早在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就已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直至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才对包产到户正式予以肯定,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承包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党和国家开始以积极手段推行包产到户。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日益迫切。1986年4月颁布的《民法通则》在第80条和第81条将农民经营承包地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命名为“承包经营权”。虽然在《民法通则》中立法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为一种物权,①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但却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从而引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与债权性之争。2002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专门法律规范,该法未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不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却强调“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从而间接明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更是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类型予以规定,在法律制度上终结了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的分歧。
然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不少政策起草和执行部门的专家认为该决定在农村土地变革方面提出了“三权分离”的制度框架。所谓“三权分离”,就是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而农户流转的客体就是经营权。根据“三权分离”的观点,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身份性,从而成为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力推广的阻碍。这种观点误读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明显违背了物权规范的制度逻辑。
首先,承包权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不能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从我国当前法律规定来看,所谓的承包权在法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后,有立法部门的专家在解读该法时,指出第5条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权,并认为对于承包权的理解应该注意三个方面,即:(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承包的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及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2)有权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3)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成员。③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通俗读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2页。可见,该条内容与主张“三权分离”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的专家对承包权的理解正相吻合。如张红宇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取得,需要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条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权的取得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挂钩的”,实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后,“承包权主要体现为给承包农户带来财产收益,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价值;经营权则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并由此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多元化土地经营方式。”④张红宇:《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人民日报》2014年1月14日,第7版。再如陈锡文认为,承包权不能流转,这样在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进行抵押时,承包权就没有被抵押,从而既能缓解农民的贷款难,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便到期还不上贷款,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的经营收益,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承包权。①参见冯华、陈仁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不能突破——专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第2版。叶兴庆更是明确提出,“承包权属于成员权,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资格拥有,具有明显的社区封闭性和不可交易性”,化断农户承包权,“就是要界定集体成员资格、锁定集体成员范围,在起点公平的基础上落实‘长久不变’,并对承包权的权能边界进行清晰界定”。②叶兴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6期。根据这些推动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从“两权分离”变革为“三权分离”的专家的观点,之所以需要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设承包权和经营权,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包含承包权且该权利专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构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障碍。这种看法明显是由对承包权的误读造成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的规定和主张“三权分离”的专家的观点来看,所谓的承包权尽管只能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成员权(社员权),成员是团体的一分子,而不是财产的一部分,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其应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组成部分,该权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初始取得的一种资格。③严格来说,此处所谓的承包权是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初始取得的一种资格,在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中,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的规定,该承包权是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的一种资格。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承包农民集体之土地的权利从不曾被包含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之中,因而也就不存在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问题,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归因于其内容包含承包权,实无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难题的解决。
其次,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的所谓的经营权在法律性质上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区别。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一种土地使用权。主张“三权分离”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的专家强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目的是为了加强承包地流转。这些专家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混合体,在人口不流动、土地不流转的情形下,这样两种差异较大的权利可以浑然一体、相安无事,但在承包农户外出务工增多、土地流转加快、土地融资需求扩张的新形势下,承包权与经营权继续混为一体会带来法理上的困惑和政策上的混乱;④参见叶兴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6期。经营权独立出来,则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多元化土地经营方式。⑤参见张红宇:《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人民日报》2014年1月14日,第7版。另参见冯海发:《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夯实基础——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农村改革几个重大问题的理解》,《农民日报》2013年11月18日,第1版。可是,正如上文所述,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含有承包权这一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是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误读,与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并不相符。而且,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具有流转性”,⑥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通俗读本》,第76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用11个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作出了规定,《物权法》也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础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进行了规范。在实践中,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承包地流转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全国平均来看,1996年有2.6%的耕地发生了流转,截至2008年,耕地流转面积增加到17.1%。⑦参见黄季焜等:《中国的农地制度、农地流转和农地投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不仅在法律上得到确认,而且在流转实践中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因此,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归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含有承包权,并由此创设分离出承包权的经营权,无疑曲解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和内容,也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病症”开错了“药方”。
总之,为了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与经营权,并以分离出的经营权作为流转的客体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农民集体成员初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须基于农民集体的成员资格(即所谓的承包权),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其权利内容并不含有农民集体的成员资格,即使从理论上分离出所谓可以流转的经营权也只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换名称的替代物,两者在法律性质和权利内涵上完全等同。因此,应当在观念上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权利人的私人财产,从而为权利人依法自由流转奠定制度理念基础。
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承包期限一般只有两三年。①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不过,1984年中央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自此保持承包期限长期稳定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追求的目标。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更是明确规定:“在原定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决不能动摇。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同时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种政策精神直到今天仍是党和政府涉农政策的重要内容。
为了使保持承包期长期稳定的政策具有更高的权威,并强化其执行力度,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时第14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2003年3月开始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仍然遵循“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宗旨,在第20条针对不同类型的农地对承包期分别进行了规定,即“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为了“有利于保证广大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更好地鼓励承包人在承包期即将届满时,继续向承包地进行资金、劳力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物权法》第126条完全继受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限的规范,并增加一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规定继续承包。”这些规范都是我国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政策的法律表现。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稳定是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使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不变的规定得到严格贯彻,就必须确保在承包期限内承包地不调整或不应调整,故《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均对承包地调整作出了限制。可见,我国关于承包地调整与土地承包期限的法律规范是相配套的。然而,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运行并没有完全遵循制度逻辑,随意调整承包地的做法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还为多数农户所支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000年8月对全国11省134县267村291家农户调查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26.8%的农户认为30年承包期限内不调整土地好,而高达36.8%的农户认为30年承包期限内应当调整土地,另有19.2%的农户认为30年承包期限内应当调整土地但要严格限制。①参见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2002年9月下旬至11月初在湖北、山西、江苏、山东、广东5省、近20个县(市、区)、40余个乡(镇)、60余个村近500农户的一份实地调查结果也显示,70%的受访农户表示其承包的土地被调整过。②参见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有学者对6省的调查也发现,2000年、2009年分别有45%、52%的农户对土地调整持赞同的态度,且2009年这一比例高于2000年。③参见黄季焜等:《中国的农地制度、农地流转和农地投资》,第39页。可见,在农村社会,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承包地的调整还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的理想的制度设计与现实中农民对承包地调整的普通认同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具有独立的财产性。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地进行调整,实际上是对农民权利的剥夺。而且,因用益物权是以对物的利用为目的而设立的物权,标的物的存在与否对用益物权的目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常情形下是标的物灭失,则用益物权消灭。④参见房绍坤:《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基于用益物权的特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即使承包地因自然灾害而严重毁损,也不应当调整承包地。然而,这种从法律上看来承包地不得调整的制度逻辑在实践中却土崩瓦解了。在承包地调整问题上,现实生活与理想制度之冲突的根源在于,农民具有作为农民集体的成员与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双重角色。在我国,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是对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分割,承包期越长,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⑤参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第59页。200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同时也取消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其中村提留在性质上是“农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享有利益的体现,村提留的取消使得农民集体不能够再获取任何地租,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享有的合法土地权益彻底虚化。⑥参见高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24-125页。然而,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益本应由全体农民集体成员分享,在村提留取消后该利益被体现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从而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名义上享有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既获得了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收益,同时还获取了基于农民集体的成员角色应当分享的土地所有权的收益。没有承包土地的农民集体成员,则不仅不能享有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收益,同样也不能分享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收益。
由于集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也就是解决吃饭问题,⑦参见陈莹、张安录:《农地转用过程中农民的认知与福利变化分析——基于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农户与村级问卷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5期。同时,土地又是一种提供失业保障、病残保障、养老保障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无地人口,也就连带丧失了土地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权。作为不拥有承包地的农民集体的成员,往往希望能够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因为这种收益目前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他们产生了调整承包地的强烈愿望。有学者在江苏省姜堰市和甘肃省渭源县对四村1000农户进行调查后,通过对两省四村农户土地承包差异情况的分析发现,自1998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实行“一包30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以来,各地农户间的人均土地承包面积,已经发生了较大分化。从总体上看,家有无地人口的农户,已经占到被调查农户总数的47%,无地人口已经占到被调查农户人口总数的19%。其中,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13%,完全无地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0.7%。①参见杜吟棠:《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分析——以江苏、甘肃两地四村的农户调查为例》,2008年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http://rdi.cass.cn/show-News.asp?id=20634&key=杜吟棠,2015年3月24日。该次调查结果表明,未能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利益的农民数额很大,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群体。
因此,集体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必须在遵循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制度逻辑的情况下,考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在农民集体成员之间公平分配的措施,否则,这种理想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就不会平息,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必将最终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顺畅运行。将农民集体进行股份合作社改造,并适当恢复地租(承包金)制度,是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的重要举措。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支付地租后,地租作为农民集体的收益,在农民集体成员中按照股份进行分配,从而使无地人口也能够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之收益。同时,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拒绝在承包期内调整土地则有了更有力的理由,此时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制度也就能够得以顺利实现,从而为流转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三、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由性
基于私法自治,物权人原则上得自由行使其物权,包括物权的让与和抛弃。②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行使其权利的方式,当然应遵循自由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即为对流转自由原则的规范。但就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观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受到制度上的较多限制,有必要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对相关制度予以修改。
第一,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设计理念,给予权利人更大的自主空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权利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的法律上的处分,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上的处分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对权利的处分,即将权利转移给他人;其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即以权利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③参见房绍坤:《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第193页。具体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采用不违背物权属性的各种方式进行流转。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可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物权法》第128条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在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表述上存在差异:一是《物权法》没有列举出租的流转方式;二是《物权法》没有规定“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物权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规范看似有别,但两者并无实质差异:其一,转包和出租的法律性质相同,将二者区别规定不具科学性,应将它们归并为一种流转方式;④参见陈小君等:《田野、实证与法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71页。其二,《物权法》规定的是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而“等”具有表示列举未尽之义,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7页。此可被理解为“其他方式”的另一种表达。可见,我国法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采用了开放式模式。不过,我国《担保法》第37条第2款和《物权法》第184条又明确禁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法律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的情形下,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法理上欠缺正当性。①参见高圣平:《中国土地法制的现代化——以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中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36-137页。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之禁止的制度设计反映出我国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选择没有真正体现方式多元的理念。其实,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可以成为处分行为的客体,法律不应当限制其采用何种流转方式,只要符合关于对物权的法律上的处分的原理,均应予以认可。
第二,取消发包人的干预,以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运转更为便捷。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物权法》第128条明确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流转,可见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须经发包方同意也为《物权法》所确认。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的理由有二: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发包方要与受让方确定新的承包关系,发包方需要确认受让方是否有履行承包义务的能力;二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承包方将因失去承包地而丧失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将来可能要求农民集体为其提供生活保障。②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通俗读本》,第87页。然而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来看,上述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该规定违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之定位有名无实,因为只有普通债务的转让才须征得债权人(即原对方当事人)的同意。③参见陈小君等:《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须征得发包方同意,其实质是明确村级层面对承包地流转予以管制,从理论上来看,此种流转管制增加了流转交易的链条,增加了交易成本或启动成本,对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④参见黄季焜等:《中国的农地制度、农地流转和农地投资》,第129-142页。再次,承包方的生活保障问题应该通过积极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其中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将农民集体进行股份合作社改造,并适当恢复地租(承包金)制度后,也可以将该地租的分配作为提供给无地农户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最后,受让方是否有履行承包义务的能力,的确影响到发包方权利的实现,但如以流转受让方具有履行能力作为发包方同意的前提,则无异于为发包方武断干预提供了借口,其实,只要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履行义务的责任,就可以促使受让人履行相应的义务。此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这也是不妥当的。所谓备案,是指向主管机关报告事由存案以备查考。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59页。发包方不是承包方的主管机关,发包方与承包方是平等主体,其行使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而不是行政管理权(力),要求承包方流转承包地须报发包方备案,明显是对发包方的法律地位作出了错误的定位。总之,为减少发包方干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隐患,并使发包方知悉承包方因承包地流转而发生变动的情形,仅需要明确规定承包方在流转承包地时通知发包方即可。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应当相信承包方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能够基于自己的利益作出合理的决策,从而赋予承包方在流转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在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对该权利流转加以限制的主要根源,但是现行法律制度对社会保障功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特影响关注不够且欠缺针对性,往往是一禁了之,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由难以实现的关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何在,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流转自由原则的地位。
四、结 语
为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凸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价值,使农民成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受益者,党和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予以法律化的过程中,应该全面剖析相关政策的制度内涵,并将含糊甚至可能不太规范的政策话语以法律逻辑明晰化,以使法律规范充分反映政策精神。探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运行的制约因素,尤其是理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进一步彰显承包地流转自由,既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健全的基本前提,也是新一轮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制度目标。
On the Pligh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GAO Fei1,2
(1.Institute of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2.Law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re highly valued by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l policy.It is a task to make the spirit of agriculture policy into law institution.Clarification of the real right attribute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assurance of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further highlight of the freedom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not only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and also the aim of a new round of the reform of the law system of rural land.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membership right;adjustment of the contracted land;the freedom of transfer
D 912.3
A
1002-3194(2015)04-0021-08
[责任编辑:赵守江]
2015-03-19
高飞(1972-),男,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产法。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2011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法律问题研究”(2013M53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