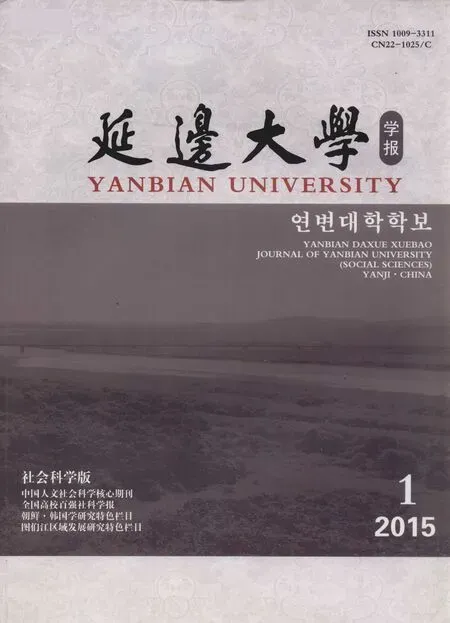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前提性问题探索
张艳秋,吴 鹏
(1.延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2.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作为一门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学问,政治哲学始终伴随着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重大转向,从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洛克、卢梭,再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黑格尔,直至当代西方的罗尔斯、诺齐克、桑德尔,政治哲学始终活跃在历代思想家的理论视野之中,虽然因其形而上的特性也曾短暂黯淡,但是由于现实的政治生活无法完全被科学所掌握,政治哲学又再一次踏上了学术的前台。20世纪8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汉译本的发行,迅速掀起了我国学术界研究政治哲学的热潮,政治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心话语。进入21世纪,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生,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更重要的是理论本身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遗产。
一、马克思与政治哲学的相遇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首先要从“政治哲学”这一前提性的理论概念入手,理解政治哲学内涵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看待“政治”与“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哲学”这一表达式是“政治”与“哲学”两者关联的体现,对两者关联的理解向我们敞开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一种是以政治为核心,认为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进行哲学的分析,利用哲学严格的逻辑要求来澄清政治语言的逻辑混乱;另一种是以哲学为核心,认为政治哲学是通过哲学追求形而上学的本性来揭示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定。通过对两种理论视角的思考和分析,笔者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与哲学两个学科之间交叉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理论空间,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学的制度设计层面,也不能完全地倾向于哲学的纯粹思辨层面;它体现着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路径,同时也确定了以政治生活为对象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政治生活进行哲学式的追问和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始终面临着必然与自由的矛盾问题,因而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建立在“必然”基础之上的、以事实认知为目的而进行的经验描述和理性分析的路径,可称之为科学分析的考察方式;另一种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以价值评价为目的而进行的理想诉求与规范建构的路径,可称之为规范理论的考察方式。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通过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审视,指向一种更加美好的、理想性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的批判和超越维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学科。那么这种规范性的考察方式是否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呢,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基础所在。
无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探索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会灭亡的革命性预言。但是对于马克思是否建立了一种规范性理论,我们往往持质疑态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始终反对“关于正义的空话”,认为在政治或道德的地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关于自由、平等、正义的谴责,仅仅停留在关于道德的错误和虚幻的观念之中,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一针见血地揭露问题的症结;进而,马克思、恩格斯将“正义”的根源归结于物质生产,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性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的虚幻性与欺骗性。那么,作为科学认知的唯物史观和作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真的就是格格不入的吗?如果单纯地从两种考察路径本身来看,诉诸道义立场的规范性考察方式与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分析路径确实是各行其道的,但是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二者却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起点,“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能动性要求人们在物质生活实践中具有价值判断功能,对客观现实保持一种否定和超越意识;受动性则规定人的价值判断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必须以物质世界为客观基础。这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映射在考察方式上,就是价值评价与科学分析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本质蕴含在唯物史观之中。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总结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揭示了阶级、国家产生的原因,揭露了在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形式下的工人的异化生存状态,进而在规范性层面上提出了超越政治正义的社会正义即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对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人文关怀。可以确定,历史唯物主义既囊括了历史哲学的内容,也蕴含了政治哲学的维度,因为马克思始终为“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而奋斗。
二、马克思与传统政治哲学的论战
纵观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并没有在任何一本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而是散落在他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论战过程中。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首先要明确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而理论前提的确立则需要从他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入手。
(一)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毋庸置疑,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前提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莱茵报》被查封以后,马克思在小城克罗茨纳赫阅读了大量关于国家和法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并撰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此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渐行渐远。
此后,马克思下决心从理论上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划清界线,开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强调,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1]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原则和基础,国家的意志规定着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法律和利益。然而,马克思却对这一颠倒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2]“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2]通过批判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产生并决定政治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可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宣告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决裂,同时也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
说到黑格尔政治哲学,不得不提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虽然他用“自我意识”替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理性主义。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布鲁诺论述了犹太人要求的解放是使政治摆脱宗教的解放,只要犹太人摆脱了犹太教,就能获得“人权”。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的解放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政治解放作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它实现的人们对封建专制的摆脱,并未真正促成人的解放,而是把人们又带入了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泥潭;政治解放使人们获得政治层面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却无法获得实质上的经济层面的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全新价值追求。
(二)对蒲鲁东政治哲学的批判
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已广为人知,但是对于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或许并不是特别熟悉。在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核心就是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而且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主张都是围绕着他心目中的公平和正义而展开的。
蒲鲁东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中,把“正义”作为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正义的前提和表现“就是在劳动的平等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就是像社会成员那样从事活动”。[3]蒲鲁东强调,正义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是规范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定律,“正义是位居于中央的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围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3]纵观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每个人获得一份相等的财产并在此条件下进行活动,是正义的首要原则和具体表现;正义是决定现实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正义是超历史的永恒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看似把正义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他颠倒了两者的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4]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们从某一原则出发的主观臆想。通过对蒲鲁东政治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正义、平等这一系列的政治哲学的原则和追求,是人们物质生产的产物,不是正义决定现实社会,而是现实社会的发展决定正义内涵的改变,没有永恒的平等和正义。
(三)对拉萨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拉萨尔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他的分配正义论,其“劳动”观点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拉萨尔的思考路径可以总结如下:一切社会财富都来源于劳动的生产与创造——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应该占有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劳动不是劳动者个体孤立进行的活动,而是劳动者在社会合作中共同完成的,因而劳动产品应该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就是正义的实质所在。乍一看,拉萨尔的思维逻辑非常清晰,并且也抓住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劳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5]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劳动的重要地位,而是要全面揭示劳动所蕴含的丰富内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生产劳动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抛开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劳动范畴的抽象化,劳动的本质就不可能全面地呈现。接着,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分配正义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是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6]这里就明确地阐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社会的分配方式是物质生产的产物,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了政治哲学的物质生产根源,实现了对拉萨尔政治哲学的超越。
(四)对杜林政治哲学的批判
杜林的政治哲学思想看似深奥完备,但事实上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设计出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实质上是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自然状态学说的再现,这种研究进路早在17、18世纪的霍布斯、卢梭、洛克等人的思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杜林看来,复杂的现实社会可以彻底地简化为“两个人”的存在,社会存在可能的最为简单的要素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两个人”,通过对这“两个人”的研究,杜林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7]按照杜林的论述,这两个人不能互相伤害,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意愿,双方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义务关系。随后,杜林将这两个人的平等推广开来,认为只要人们对正义有充分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平等就能够得以实现。
对于杜林的政治哲学主张,马克思并未直接进行批判,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直接完成的,但是恩格斯在批判的过程中是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的平等正义主张只是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想象和虚构,一旦涉足现实问题,杜林所谓的道义上的准则就显得无能为力。恩格斯说:“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5]杜林根据平等正义原则构建的未来经济公社的设想,也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翻版。他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环境,得到的就只能是抽象的政治哲学理想。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揭示
在批判传统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场,确立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前提,只有通过深刻地总结和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其政治哲学的思考路径和理论创新。
首先,马克思肃清了政治哲学的唯心主义根源,把公平、正义与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联系起来,为政治哲学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众所周知,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法、国家等政治哲学层面的论述也是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下进行的。受黑格尔的影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采用一种价值悬设的逻辑,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此后,由于物质利益问题与理性主义国家观之间的矛盾,动摇了马克思关于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幻想,他逐渐认识到国家不是一种凌驾于私人的、等级的利益之上的普遍的东西,进而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随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马克思发布了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政治哲学断裂的宣言,他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马克思确立了“物质的生活关系”对“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的基础性地位,让政治哲学走上了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
其次,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人性论推衍出的普遍的政治哲学原则,要求把“现实的人”作为政治哲学的价值主体。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把抽象的人性论作为政治哲学思想基础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众多思想家通过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设想,设立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并以此为基础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原则。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杜林也走上了同样的研究道路,他通过对构成社会“最简单的要素”即“两个人”的设定,推演出了一条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公理”——“两个人”的意志彼此完全平等。对此,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自然状态”下抽象的人出发去寻找实现人类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研究路径,确立了政治哲学的价值主体——“现实的个人”。
再次,马克思反对把抽象的政治概念作为超历史的永恒规范,揭示了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在蒲鲁东、拉萨尔和杜林的观念中,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非正义的,因此要依据抽象的正义原则的内在规定去改变社会现实,在分配领域实现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平分配和交换,这样就能够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则指出,诸如公平、正义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只不过是关于物质利益关系的道德评价,是根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思想观念,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依据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的内容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阶级根据阶级利益的需要,对这些政治价值的理解也大相径庭,进而提出不同的价值诉求。
最后,马克思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对政治生活领域的排斥,相反,他不仅肯定了正义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探索超越政治正义、通向社会正义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们对平等、正义等政治价值的批判,并没有直接看到二者对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呼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只关注经济生活而排斥政治生活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9]作为人类永恒的政治价值追求,正义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专利,它也是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运动协会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就肯定了正义的价值。马克思是关注政治生活的,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设立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和目标,而是更加深入地透视政治生活领域背后的经济因素,因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政治图景才能够真正实现。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现实的个人”促成了马克思与政治哲学的相遇,并且帮助马克思克服了传统先验建构的政治哲学的理论瓶颈。马克思不仅没有忽视对政治生活领域的关注,而且在与传统政治哲学的论战中,深入到政治生活背后的物质利益问题,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超越,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美好愿景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实现路径。
[1][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0页。
[3][法]蒲鲁东著:《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9、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444、4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7][德]杜林著:《哲学教程》,郭官义、李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