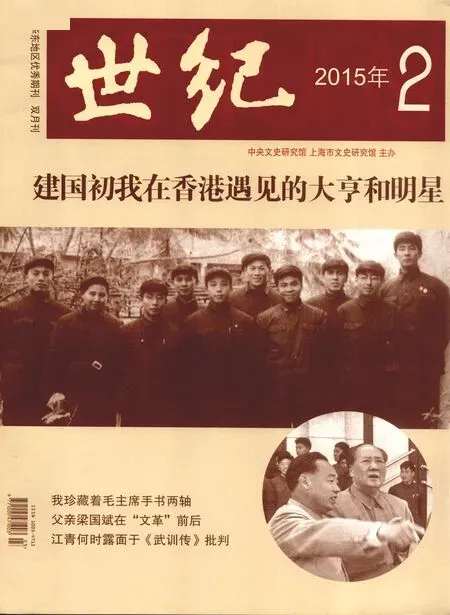陈伯达组织“《红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
穆 欣
陈伯达曾在所写《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中说:“‘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的)对我提出担任文革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周总理说:‘那你开个小组的名单。’”
陈伯达说这些话,似乎他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很乐意,是勉强接受的。实际上,他是抢着当的。1966年4月9日到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陈伯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彭真为首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拟发的《二月提纲》。这个会还没有开完,他就抢着“组阁”了。
4月12日下午,我在光明日报社刚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起来,顿即感到厌烦。为什么?因为连续多日,总受姚溱电话的骚扰。姚溱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和另一位副部长吴冷西一起代表中宣部分管北京各报的宣传报道工作。过去每次召集各报负责人开会,例由中宣部办公室通知,他们本人从未直接给报社打过电话,也从没有管过报纸的版面安排。但自《二月提纲》下达后成立彭真的五人小组特设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姚溱是这个办公室的一员)以后,姚溱突然直接关注我们报纸的版面安排,一再告诉我说:这次批判要“特别慎重”,要随时向他请示报告,要求把报纸涉及学术批判的文章清样和批判吴晗文章的版样送审。他还提出“注意质量”,限定有关学术批判的文章每周最多出两块版(我们这个报纸是以学术报道为重点的),而且指定每一块版上必须同时发表正、反两个方面的文章,“以利于‘放’”。有几次送去的版样上没有“反面文章”(按:指支持吴晗的文章),他都退回来要求重新组版。
前文讲过,过去姚溱本人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这时他却每天都来电话,多时一天打过七次。这些电话常从报社办公室追到宿舍,不在宿舍就向家人追问到哪里去了,又把电话追到我所去的别处。看起来像有紧急的事,实际上还是“没事找事”,又是几句空话,无非是要监视我的行踪。如此反常,令人恼火。他为什么这样,至今不解。当时自己还不了解中央高层领导间的矛盾、斗争真相,我们报纸编辑部是“守规矩”的,编辑工作一直是按中央宣传部的安排办事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不放心?
因为以前曾有这些情况,这次以为又是姚溱的电话。接听后方知是红旗杂志总编室的电话,要我第二天到《红旗》编辑部开会,通知者只说会议是陈伯达召开的,没讲研究什么问题。那时还不知道中央书记处开会的事,过去自己与陈伯达从无来往,接电话后不免有点纳闷。
红旗杂志社在沙滩中央宣传部大楼上办公。13日上午来到《红旗》会议室的时候,陈伯达已先到了。他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加强对学术批判的领导,决定成立《红旗》杂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共计八人:陈伯达、尹达、王力、范若愚、关锋、戚本禹、穆欣、杜敬。这八个人除了我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外,其余都在《红旗》杂志工作。那天陈伯达兴致颇高,宣布了名单后,曾肉麻地拍着坐在身旁的尹达肩膀套近乎:“咱们两个‘达’终于在一起了。”
这天会上,就是陈伯达一个人讲话。他引经据典大谈学术批判问题,情绪相当激动,讲话的火药味很浓。他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苏联已从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回资产阶级专政。原来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什么都被打倒了。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进攻时起时落,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在这时读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面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的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险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
陈伯达说:资产阶级钱很多,送给很多人钱,就跟过去了。很容易,请一顿饭就拉过去了。它用各种办法来进行腐蚀,把金箍咒套在你的脑袋上。所以主席说,阶级斗争还要搞几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只要看封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就可以了解。那时是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现在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性质完全不同。
又说,两个阶级、两种宇宙观的斗争是长期的。主席经常警告我们,搞不好要出修正主义。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
这个有名的“书呆子”,书是背得很熟,就是未能联系实际,也没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个“理论家”一辈子的悲剧就在这里。
接着,陈伯达就谈到《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事情,竭力攻击没有在场的原《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前一年已经被陈伯达排挤走了),讲到他在有关编辑工作以及理论问题上和邓作过的某些“斗争”。当时虽然不知道那些事情的真相,但看他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邓力群全面否定的武断态度,感到他这些话都很难以令人相信。乱七八糟地扯了一些事情后,他又激动而且非常夸张、无限上纲地说:“《红旗》杂志的专政也有无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同时还说什么“我同邓力群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问题”,让人听得发笑。他还激动地攻击田家英和中央宣传部一些同志,看来他已决心要“报仇”了。
陈伯达说,《红旗》应当加强学术批判,做到合乎中央对《红旗》的要求,“要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成为真正的红旗”。又说,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大家容易接受。《红旗》杂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做得还不够)。但是讲到批判国内修正主义,有些人就不行了。因为国际修正主义在十万八千里外,离得远远的;国内就不同了。为了加强《红旗》的学术批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这个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关于学术批判问题,请大家到这里讨论。每周讨论一次,研究刊登什么文章,和《光明日报》互相支持。希望大家严肃地、开朗地,以无产阶级风格对待学术批判问题,互相提醒。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问题是不要犯严重错误,犯了错误就改。严格的科学态度,就是文章要反复地改。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改的就改。还说,我没有心思整人,但我不惯于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和平共处。对资产阶级意识要无情地批判,可以讥讽嘲笑。资产阶级意识如不狠狠地批判,它是不会倒的。
这个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就开过这一次会,只陈伯达一个人放了一阵空炮,没作任何具体安排,没做任何事情。所谓“每周讨论一次”也是一句空话。这天是开过的唯一的一次会议,是“成立会”,也是“散伙会”。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即批准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名单,4月26日到上海开会,5月16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前后均由陈伯达担任组长,风光一时。
陈伯达这个组长被江青架空以后,小组主要权力实际掌握在江青手里。但他仍然抓住那个“组长”的名分不放,江青一伙干下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得由他承担。
毛泽东素知陈伯达窝囊,曾说过“给陈伯达很多位子,他都没有掌住”,晓得他斗不过“刀子嘴,是非窝”的江青。陈伯达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上批评我:‘不干,也不辞职。’这证明了我不能割舍一个虚伪的名位。”又说:“我当时挂了这样的名义,没有解职,又没有辞职,不能制止这些事的发生,当然也有责任,谨听党和国家的裁决。”
(本文为已故的《光明日报》原总编辑穆欣先生的遗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