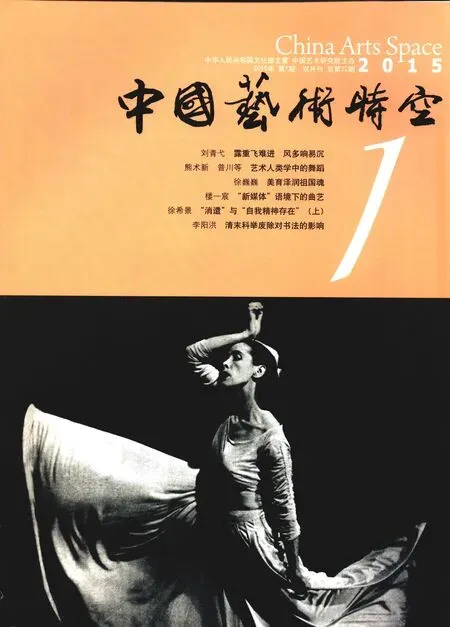大地阶梯上的音乐圣徒
——藏族音乐学者嘉雍群培
刘晓伟
大地阶梯上的音乐圣徒
——藏族音乐学者嘉雍群培
刘晓伟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犹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
从此以后,我在群山中国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极目远望时,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详细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
——阿来《大地的阶梯》

2014年第二期的《中国音乐》刊登了中央民族大学嘉雍群培教授的论文《藏传佛教因明中的音乐学方法论》,这是他近几年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又一篇重要论述,却成了他生前最后的表达。我国少数民族音乐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位专家,尚未花甲,匆匆离去,骨灰洒在故土,灵魂新生。
每一个藏族学者都像藏族作家阿来文字描述的一样,在大地的阶梯在朝圣的路途行走着。音乐学者嘉雍群培也一样,进入到藏族音乐研究这个领域如果从发表第一篇文章算起,已经20年了,从一个热情的藏族青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藏族音乐研究学者,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他将音乐研究视为自己的朝圣之旅。
嘉雍群培,藏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藏族文化艺术”、“艺术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近年来出版的主要论著有:《雪域乐学新论》、《藏族文化艺术》、《藏族宗教与文化》(合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合著)、《中华民族史》(撰写西藏部分)、《中国民间舞蹈集成·青海卷》(藏族部分)、《玉树民间故事集》(合著)、《玉树民间谚语》 (合著)等。并多次参加在日本、韩国、中国北京和香港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些碎片化的符号表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在朝圣阶梯上叩行的脚步。
嘉雍群培教授的学术研究可以以攻读博士学位作为分水岭,从研究的特点来看,前期是“广博”,之后是“精深”。
在2007年以前,嘉雍群培老师公开发表的论文已经有23篇,涉猎范围有藏族民间歌舞与宗教音乐,但首先还是关于自己家乡玉树的艺术形式。
在论文《通天河的诱惑》、《多彩的帐篷》、《玉树草原的煨桑祭祀和赛马》、《玉树民间文化艺术“三绝”》、 《玉树的游侠歌》、《玉树武士舞研究》、《玉树藏区民间歌舞“伊”的风格》中,他更像一个诗人。

在《通天河的诱惑》中他这样开始感人的玛尼调的表达:转经的人们也开始唱起玛尼调,凄凉的歌声在空旷的山野河谷回响,像是在乞求、哭诉,又像是在忏悔,这是信徒们对今生“此岸”一切的诉说,也是对“彼岸”“乐园”的呼喊。①嘉雍群培《通天河的诱惑》,载《中国西藏》(汉文版)1998年第1期,第40—42页。
用诗歌一样美丽的语言,饱含情感追寻那片属于他的土地上的艺术精灵。
在研究玉树的同时,他也将目光开始投向整个康巴藏区,写出了论文《论藏族康巴山歌中的“昂叠”》、《 康巴藏族歌舞“卓”的风采》、《康巴藏族山歌的韵味》、《富有特色的康巴藏区“侠盗歌”》、 《藏族“国哇”研究》、《结古寺第一世嘉南活佛的音乐创作和他的音乐思想》、《结古寺第一世嘉南活佛编创的“曲卓”及其旋律手法》等。

之后更是开始了对整个藏区的关注:《藏族的“昌鲁”(游侠歌)》、《藏族强盗游侠歌的产生及艺术特色》、《藏族傩舞艺术的形成及发展》、《藏族宗教乐舞的形成及发展》、《多仁·丹增班觉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影响》、《论藏族弦子(谐)艺术的形成与类别》。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了他的学术视野的拓展、研究的深入,在他的研究中更多去探讨作为符号层面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涉及到了宗教、哲学、政治、社会与文化。
如果说前期的研究奠定了他藏族音乐研究的地位,那么在后来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思路以及表述方式,与以往都大有不同:《窥商日本与西藏佛教传承及佛教音乐的异同》、《青海藏区民间与宗教舞蹈的田野考察——以玉树地区的民间与宗教舞蹈为例》、《藏传佛教临终关怀与亡灵超度仪式音乐研究》、《藏传佛教“死亡修行”仪式中的音乐思想》、《藏传佛教因明中的音乐学方法论》,在这些论文的研究中,他聚焦藏传佛教音乐仪式,透过研究的结构体系,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因素凸显出来,这首先是来源于藏传佛教对人的临终关怀,在社会结构中,挖掘仪式中音乐的功能,所属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深入到哲学层面的因明学的研究。作为一个具备“双视角”的学者,藏族文化从小的熏陶和之后严格的汉族文化学习与训练,以及西方研究“异文化”所采用的方法论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更好的应用,也更有独特的体会。
在《藏传佛教因明中的音乐学方法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比量智的对象是共相,而共相就是诸自相的共相。这种自相、共相,主位、客位的两种角度的变化,因明中称为‘所转境’。这种自相、共相,主位、客位的两种角度的结合,佛教称其为‘冥合性’,是为了认识主体置身于认识客体的内部,深入对象的内层,与之契合为一,从而彻悟世界的实相。其实就是民族音乐学中所说的局内与局外、主位与客位的辩证关系。”①嘉雍群培:《藏传佛教因明中的音乐学方法论》,载《广播歌选》2012年第12期,第74—75页。

这是一个对藏族文化,佛教文化浸淫多年的学者才可以产生的感悟。是一个思考着行走着的圣徒才有的感悟。似乎这已经是一个“会当凌绝顶”的孤独行者,但这就错了,了解嘉雍群培的人都知道,他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细腻的人,但又被他大碗喝酒、放生高歌的康巴汉子形象震撼,就是这么多元统一,就像横跨了汉藏两族文化。在局内、局外人身份的交替中,他学会了自如的穿越,也更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文化。他对自己的家乡和民族怀着醇厚的情感,深爱着自己民族的艺术,却也很冷静地看到经济大潮下严峻的社会现实,因此,就像在朝圣的旅途,一步一个脚印,既不失落也不抱怨,只是虔诚的坚守,冷静的支持。
在谈到藏戏时他讲:“藏戏是反映青藏高原发展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展现了西藏原始宗教艺术和佛教的形式,而且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彼此呼应、水乳交融。但研究藏戏的前提是收集失传的剧本,而这需要花大量时间和财力。因既无资金支持,又受到浮躁学风的干扰,这项工作很难完成。”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态度明确:“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不断进行创新,但创新的前提是要尊重历史和文化。”

在面对藏族风格流行音乐与创作表演繁荣的状况时,他呼吁藏音乐的创作者应在商业的浪潮中避免浮躁心态,加强对藏族文化传统的学习,将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融入藏音乐,保留民族文化精髓,运用现代化营销手段,让藏音乐真正地走向世界。
他的精神世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充满着入世的情怀,不是闲居一隅自成一体,而是积极传播与推动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也灌注在对学生的培养中,帮助自己的硕士、博士选定研究课题,为他们的田野工作给予最大的帮助。
在培养自己学生的同时,也不忘走出民族大学,去兄弟院校讲学,将自己心中的藏族文化,讲给更多的人。在河北高校的讲座中他讲:西藏地区有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神奇的文化现象,这些都使西藏地区有着自己特色的音乐起源论据,研究西藏地方音乐的起源对于建构西藏音乐的审美特色、音乐风格、理论阐述以及音乐的传承等有重大的基础理论意义。
这还不够,对于发扬民族文化,他还有更大的想法。在2003年“中韩第一届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会”上,他的宣讲题目是《藏传佛教乐舞“羌姆”中的中原文化》,在结论中讲:“羌姆中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是因为西藏早期是政教合一。”①嘉雍群培:《藏传佛教乐舞“羌姆”中的中原文化》,载中央音乐学院、韩国东北亚音乐研究所编:《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第15页。
在2009年“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 他做了《西藏死亡艺术》的发言:藏传佛教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要进入中阴,是新生的开始,是生命中最尊贵和最光荣的时刻。②见http://www.zhibeifw.com/fjgc/fjys_list.php?id=7253
在2013年3月31日,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赴斯坦福大学为该校音乐学院师生讲授中国藏传佛教音乐。
……
生命画上一个句号,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佛教皈依者的新生。
这是行进在大地阶梯上的朝圣之旅,就像作家阿来的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中所写:
就是这样
跋涉于奇异花木的故土
醇香牛奶与麦酒的故土
纯净白雪与宝石的故土
舌头上失落言辞
眼睛诞生敬畏,诞生沉默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