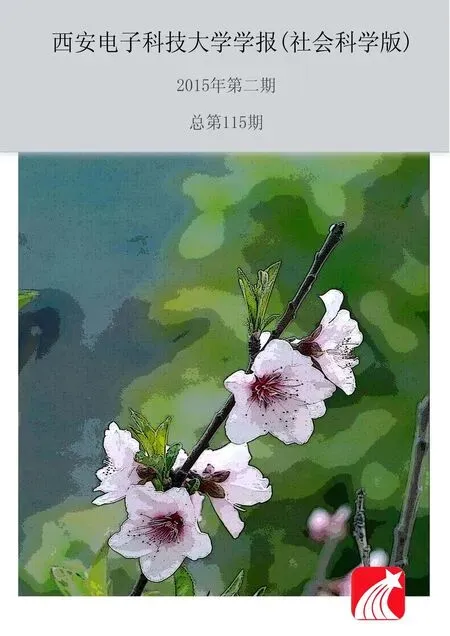隐含作者的全息考察和建构
姜 宁,牛亚军
隐含作者的全息考察和建构
姜 宁,牛亚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71)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应用很普遍,但是它的定义和所指一直仍然是学界的争论热点。本文结合当前此领域的主要学术焦点,对引进“隐含作者”的必要性,他和真实作者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这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隐含作者的提出有利于严谨的文学批评;隐含作者源于真实作者的创作又有赖于读者的建构,他和真实作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交叉关系,因此,隐含作者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在阅读中得以具体化的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借鉴语言学的两组术语——音位和音位变体以及语素和语素变体——的理解,隐含作者可以表示为:1+1+1+1+……1=1,所以,隐含作者可以是一个(抽象的),也可以是许多个(具体的)。有鉴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了对查特曼经典图示的修改意见。
隐含作者;真实作者;读者
虽然“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但是迄今为止,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存在方式或形态不时遭到质疑。在此期间,从 2000年4月召开的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年会的讨论及随后由莱恩·理查森引发的为期两周的网上热议[1],到2005年此提法的始作俑者韦恩·布思为复活“隐含作者”的再次撰文[2],再到2008年的叙事学年会上新的叙事模式的探讨[3],这些都表明隐含作者这一术语的理解和推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总的来看,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是否有必要引进隐含作者?2. 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3.隐含作者是一个还是多个?怎样理解?本文的探讨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一、引进隐含作者的必要性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将作者与其隐含于作品中的形象区分开来,我们才能避免一些无意义、无法证实的讨论,比如关于作家‘诚实’或‘严肃’的特性的讨论”[3]81。如果考虑到他这一提法当时的背景——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批评提出一切作品的意义来源于文本本身,尤其是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将作者完全排斥在文本意义之外——这一主张显然受到了新批评的影响[1]。但是,布思并没有因此“谋杀”真实作者,毕竟他认为这个隐含作者是真实的作者造就的:“我们把他(隐含作者)看作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提升;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3]84。可见,正是真实作者通过各种手段合成了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而且,布思在后来的“隐含作者的复活”一文中再次表明了他的立场:“怎么竟会相信作者的创作意图于我们如何阅读作品无关?诚然,批评家可以说作者在文本之外所表达的意图,可能会与作品所最终实现的意图大相径庭①。然而,难道这种差异不恰恰生动地说明了必须区分隐含作者和(有血有肉的)作者吗?”[2]30这一术语的推出是在文内作者和真实作者之间划出了界限,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评论中不乏以作品中反映的所有观点和思想统统强加在创作者身上的做法,因此区分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是完全有必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思的以上想法反映出一种本着对真实作者负责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只要证据充足,这并不妨碍(通过隐含作者)寻找真实作者的(思想和立场)可能;反之亦然。所以,那种认为隐含作者切断了与实际作者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有失公允的[4]104。不过布思关于隐含作者的必要性的思考似乎还只是局限于他与真实作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读者的需要。诚如伊瑟尔所言,阅读是一种交流活动,而且是不对等的交流,因为“阅读不是面对面的交流”[5]。既然读者在阅读中需要一个交流对象,他通过阅读勾勒出的假想对象就尤为重要,这个假想对象就是隐含作者。在对隐含作者的绘制中,读者所采用的线条、颜色、光影等都是由文本中透露的信息决定的。所以,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所还原的隐含作者也不同。对此查特曼有过清楚的表述:“他(隐含作者),或者说是它更好些,没有声音,没有直接的交流手段。它默默无声地通过整体的布局、通过他所选择的全部手段和全部声音指引我们”[6][7]104。或者说,任何阅读都是在一定的视角下进行的,这个视角的选择首先是由文本的结构(包括视点、时间、距离、反讽等所有创作技巧和成规)推导出来的,读者在其文学能力的指导下结合自身的经验对其中的种种暗示进行不断地猜测、证伪和完善,最终合成隐含作者的图像。尤其是读者于读某部作品之前根本对原作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这时的阅读就更需要有隐含作者的存在。借用布思文中不同版本的读者为例,如果布思甲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阅读作品A,他在此之前并不知晓其任何相关的信息,在未经查找真实作者相关的材料前,他所有关于作品的作者的(观点、思想等)推测都必然是那个想象中的作者——隐含作者的。即便有证可查的部分(思想)可归为现实中的作者,很可能还有一部分得不到佐证。就拿丹尼尔·笛福和其作品《鲁宾逊漂流记》来说。如果我们以后殖民的视角来看,文本的作者显然拥护殖民主义思想和行为,这是否可以说笛福就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呢?也许与其由此证明笛福是一个殖民主义者,还不如说鲁宾逊及小说中的隐含作者体现出了殖民主义的思想(压迫土著居民等),而这种思想是笛福这个实实在在的作家创作时毫不知情的,是一种社会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或许就是乔国强先生所说的隐含作者是由社会历史、环境构成的[8]25。
毫无疑问,隐含读者既源于作者的设计,又有赖于读者的建构。没有阅读,没有读者的参与,隐含作者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潜在的身份,只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解读文本内的空白、视点等所有修辞策略,才能使这种潜势转化为现实,构筑出隐含作者的形象。当然这种现实的转化首先是出于读者的需要,在真实作者缺席的情况下,作为交流活动中的信息的接受者,读者必然经由信息的汇总完成对那个隐藏在文本中的作者的塑造,并且因此赋予了隐含作者另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读者眼中的隐含作者[8]25。
二、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关系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真实作者创造了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不等同于真实作者,因为隐含作者包含了许多其他成分,除了乔教授所提出的三层含义外,我认为还应该包括读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对建构隐含作者的影响。正如前面的论述所提到的,作为读者,布思的阅读策略和理论受到了新批评的影响,尽管他并不完全接受其某些主张。同样,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读者,没有经过后殖民主义时代以及后殖民主义文艺思潮的洗礼,也不可能建构出一个殖民主义者的笛福的隐含作者。可见,隐含的作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体,似乎无法与布思的“第二自我”等同。“……他始终强调的是,作者的一个‘第二自我’,而没有在此基础上扩展为……一个既包含又独立于真实作者之外的概念”[8]24。虽然乔教授提出应该拓展隐含作者的概念内涵,但是这里的表述似乎可以理解为真实作者包含了隐含读者。此外,申丹教授在阐述她对布思这一概念的理解时也表明类似的看法:“‘隐含作者’是处于特定写作状态下的作者,而‘真实作者’则是处于日常状态下的作者”[3]31,无疑她也认为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如果仅从隐含作者的塑造是真实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一点来看,这种推论就值得怀疑,再加之构成隐含作者的多种成分,我们很难说隐含作者的内涵就一定小于真实作者的内涵。既然如此,我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他们交叉的面积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区域,下面用图说明。图1和图2中两个圆的大小并不表示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本身各涵盖的内容相等,只是表示二者有各自独立的空间。由图1到图2可看到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交叉空间的变化,它表明在一定情况下,二者有可能出现互相包含的现象,但很难说只有真实作者包含隐含作者的可能,而没有相反的特例出现。
图1

图2

也许是布思一贯关注文学的道德伦理价值的缘故,他的隐含作者在他看来是一个优于有血有肉的作者的自我(a better self),这是他在首次推出隐含作者50余年后明确进行论证的。他试图通过作者索尔•贝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及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例证明作者总是在作品中“努力寻求和投射某种更为优秀的‘自我’……”[2]35。此中的原因他认为有二:首先,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像贝娄一样,“抹去我们不喜欢或至少不合时宜的自我的痕迹”;其次,伦理上的精彩的面具(也就是最佳形象)可以帮助我们明辨是非,起到榜样作用。他的例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是不足以具有说服力的。而且,贝娄所不喜欢的自我很难说一定就是丑陋的或者说是不够完美的,在此他也有可能指按照创作的需要,或者说按照他对文学的理解,对《赫索格》中所反映出的隐含作者的理想状态(更具有立体感的、或者更加个性化)的追求,结合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概念的理解,或许我们可以说贝娄其实是对作品的整体设计和布局进行一种微调。另外,对于美好自我的定义也因文化、时代的不同而异。以D. H.劳伦斯和他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为例。劳伦斯的这部小说于1928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但直到1960年英国的出版商才赢得出版权。劳伦斯本人因为作品中的性描写受到迫害,直到他去世时还有许多人将他等同于一个色情作家。及至后来F. R.利维斯将他的许多作品纳入英国经典小说的“伟大传统”中,不但确认了劳伦斯的艺术才华,也肯定了他严肃的道德观。可见,对劳伦斯的不同的态度本身说明了不同的读者所建构出的隐含作者的不同,同时也引发了这样的思考:文本中表露出的某些观点是否一定是创作者的立场?创作者是否应该由此而受到惩罚?若某一个文化中视为不道德的观点是否就是绝对的不道德?或者说我们是否具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一般来说,艺术创作都是追求美的发现和创造,但是对于美的理解和标准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衡量。况且,面具不见得一定都是完美的!我们也从生活中来寻找支持的证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们可以畅所欲言而不用担心暴露身份,于是许多平素丑陋的言行得以在网上流行,这说明人们并不总是只选择漂亮的面具。另外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值得思考,在许多电子游戏中,喜欢扮演所谓的坏蛋或者反面角色的大有人在,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说明如果能够隐身,或者明知是在一定的虚假世界中,人们就有可能展示其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当然这种欲望的存在并不应使低俗成为文学追求的目标。文学创作是创造虚假世界的活动,诚如乔教授所言:“有的作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效果,故意‘降低’自己的情形也并不少见”[8]24。但无论如何,隐含作者不一定就是现实作家的优秀自我。
总之,无论是布思最初的“第二自我”,还是他的重新思考都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作者的创作总是反映出本人性格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隐含的作者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自我,隐含的作者也不仅限于真实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还包括了其他真实人物的投射。真实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性格、思想可以投射到作品中,但是一部作品中是否一定有而且仅仅只有作者的影子呢?也就是说一个作者的个人生活和观点只是他创作作品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我们有必要在二者之间划出界限。
三、隐含作者概念的理解
如果隐含作者是理解作品的必要成分,怎样理解这个概念呢?隐含作者是一个还是多个?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还是一种结构或者说是一套“隐性的成规”呢[7]89?理查森关于隐含作者的疑问源于不同的作者创作同一部作品的情况,而什洛米斯·里蒙-凯南的困惑是隐含作者作为一种建构体(a construct)是无法扮演交流中的角色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引入两组语言学的概念——音位和音位变体(phoneme and allophone);语素和语素变体(morpheme and allomorph)。
这两组语言学术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一组中的前者指示的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下面以语素为例加以说明。一般来说,语素是“最小的意义单位,是一个不能再继续拆分的音义相结合的单位”,如it、food、big等。语素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上的)单位”[9]313。“一个语素的具体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叫作语素变体[9]17。如果我们要讨论名词复数(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现象)语素,我们只有依赖一个个具体的语素变体来进行,也就是1. 在词尾加“s”,如book-book;2. 在词尾加“en”,如child-children;3.零变化,如sheep-sheep; 4. ……这表明名词复数语素是通过所有表示复数概念语素的具体书写形式及其对应的发音展示出来的,语素存在于每一个语素变体中,语素变体是语素的具体化存在,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式表示出来:1+1+1+1+……1=1。等号左边所有的“1”代表的是语素变体,等号右边的“1”就是那个名词复数语素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音位和音位变体的类似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理解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把握隐含作者的概念。所不同的是,隐含作者既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可以是具体的形象。在阅读中读者通过文本建构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隐含作者的形象是具体的形象,相当于那些一个个的语素变体,也就是等式左边的n个“1”,因为隐含作者一定要在具体的阅读中获得生命;但是每一个具体的隐含读者又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作者对隐含作者的创造,就好像我们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隐含作者。又因为隐含作者源自真实作者在文本中的所有安排,最终隐含作者的总数就是1001!还不止于此,如果像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将“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力量”也作为除所谓的“第二自我”之外的另一个隐含作者的话[8]27,那么隐含作者的总数就难以确定了,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有可能是一个政党、机构或某个团体。关键是,所有的这些难以计数的一个个的隐含作者仅是抽象的隐含作者的概念的具体表现方式,也就是说等式右边的“1”代表的是关于隐含作者的抽象的概念,这也许是查特曼在表述中用无生命的“它”it)代替“他”(he)的一个原因吧。
由此看来理查森等的迷惑其实只是囿于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一一对应的关系上,而实际上,隐含作者由于读者的构建变得难以统计,因而在没有针对任何作品及阅读活动所作的一般性的讨论中,我们的隐含作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我们此刻所做的一样。一旦涉及具体作品的具体阐释,隐含作者就真正“现行”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形象,就像哈姆莱特,他真的作为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过吗?但是,谁又能否认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呢?如果需要,你不会和心中的哈姆莱特对话吗?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床上的爱丽丝》()一剧中一样,主人公爱丽丝和艾米丽·狄金森讨论死亡的话题。我们是有可能和一个虚构的形象交流的,那个形象代表了某种思想或思维方式,我们通过假想对方的反应和逻辑推理使得心底的交流完成。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构建中,所以,交流是完全可能的。里蒙-凯南等认为隐含作者不是实体,所以无法参与交流。其实,一定要给予隐含作者以实在的形体,正是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障碍所在。在此,我也试图通过查特曼的经典的图表做一番改动,以便更好地理解隐含作者这一概念。
叙事文本

在查特曼的表中,突出的特点是所有的箭头都是单向的。另外,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都被实实在在地框在了叙事文本中,真正作者和真正读者与方框之间是用虚线箭头相连接的。申教授曾建议将两条虚线改为实线,因为她认为隐含作者和真正作者之间毕竟有割不断的联系;她还建议彻底去掉方框,却没有提供任何解释[1]13。马明奎指出申丹教授建议的模式非但放逐了文本和叙述,还使作者“最终消失于冷酷的读者之端”[10],他的这番评论是颇有道理的。有鉴于此,我认为她的第一条建议比较合理,但第二条需要再考虑。原来的实框表示隐含的作者和隐含读者只存在于文本中,也就是说作品一旦完成,真正作者和文本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原作者对文本的任何意义不再享有任何控制能力。只是这样一来也彻底地否定了隐含作者身上对真正作者的投射,故而我认为应将这个实框改为虚框,并增加一个从隐含作者发出指向真正作者的虚线箭头,表示隐含作者有可能反映出真正作者的(思想)形象;同时在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增加一个由隐含读者指向隐含作者的箭头,因为隐含读者建构了隐含作者。由于叙述者和叙述接收者不是文本中的必然成分,我的表中暂且删去。至于图中有关隐含读者和真正读者之间的变化,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再赘言。
叙事文本

仔细观察此表可以发现,所有的箭头都是双向的,这表明阅读文学作品的的确确是一种双向交流活动,正因为有血有肉的作者或读者的缺席,隐含的作者和隐含的读者才应运而生,使得交流得以完成。同时,还有一点特别的是,真正的作者的箭头在虚框之外,表示他对文本的影响止于创作完结之时;而隐含作者则是用一条穿越了虚框的虚线箭头指向真正作者,因为读者建构的隐含作者有可能穿越具体的文本折射出真正作者的影子。
综上所述,本文对隐含作者的必要性和这一概念的具体把握的探讨表明:隐含作者这一术语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有效地进行文学评论。他是一个既区别于作者又由作者创造的形象;既引导读者的阅读,又被读者建构;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他的意义和适用范围必将随着叙事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扩大。
[注释]
① 此处的强调符号为原文所加。
[1] 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与网上的对话[J].国外文学,2000(3).
[2] 韦恩·C·布思.隐含作者的复活[J].江西社会科学,2007(5):30-40.
[3] 韦恩·C·布思.小说修辞学[M].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 李建军.论小说作者与隐含作者[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3):103-107.
[5]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 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M].London:Methuen Co. Ltd,1983:87.
[7] 程锡麟,王晓璐.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8] 乔国强. “隐含作者”新解” [J].江西社会科学,2008(6).
[9] HADUMOD BUSSMANN.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10] 马明奎.对于“隐含作者”的反思与重释[J].文学评论2011(5):175-182.
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Implied Author and Its Construction
JIANG NING, NIU YAJU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ttemp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implied read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necessity of the implied auth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real author, and possible ways to perceive the implied author.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implied author relie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ader as well as the real author,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plied author to literary criticism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foster a responsible attitude in the field which in turn will ensure objective academic study. Moreove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al author and the reader determines the many-faceted nature of the implied author, who represents both an abstract concept and specific actu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The discussion comes to an end with a tentative revision of Seymour Chatman’s classical diagram of the communicative process in narration.
the Implied Author; the Real Author; the Reader
I0
A
1008-472X(2015)03-0117-06
2015-01-27
姜 宁(1970-),女,湖南宁乡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牛亚军(1963-),男,河北饶阳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本文推荐专家:
杜瑞清,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跨文化交际学。
杨纳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翻译。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