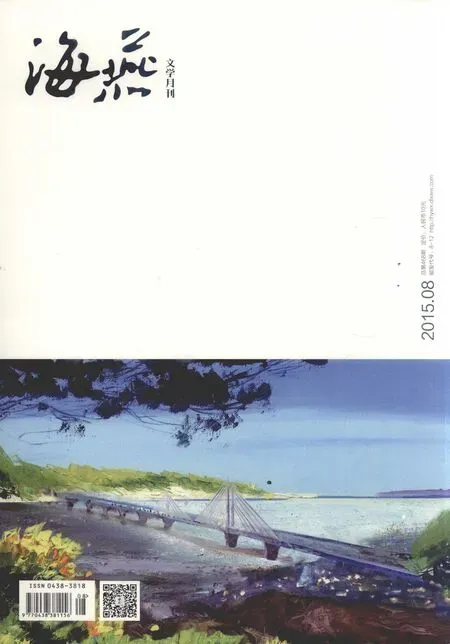绕树盘旋
□周美华
绕树盘旋
□周美华
在辽东半岛有个小镇,叫青堆子。1743年建港后,小镇里出外进之人渐多。我的祖人也从山东文登踏上这片土地,单从祖谱上看,已是13代人,只是不知从山东时记起还是到青堆子后记起。爷爷兄弟五个,行五,名周殿仕,行医为生。父亲兄弟四个,行四,1927年生于青堆镇。我生于青堆子周家已是1964年。这时的周家,早已于合作化时将爷爷的两处中医诊所和周家饼店参股合作了。大伯、二伯、三伯不愿在合作化后的商业口做店员,便到乡下种地为生。三伯做八一高级社会计。在青堆子,只有爷爷、奶奶、二伯家仁旭哥和我们一家,共住六间房。
仁旭哥的女儿早我一天出生,俩丫头都需奶奶哄,妈妈说累坏了小脚奶奶。爸爸在外地工作,大我13岁的仁杰哥,拉起风匣捅咕冒烟,担不起小家长的样子,妈妈只坐了三天月子。在周家和我同岁的还有三伯的孙子。我的叔伯姊妹中有两人小于我,即大伯家的妹妹淑荣、三伯家的弟弟仁平,他俩同岁,小我一岁。
至今,周家人口已有150余人,仍在青堆镇的只有仁平小弟,其他兄妹及后人大都在庄河。只是大伯家兄妹七人都在青堆镇外的乡下居住。他们1956年跟随大伯家到下河口,一去60多年,有的在那里出生。但是7兄妹的孩子全走出去了,在青堆甚至庄河以外的大连、沈阳、北京、上海,这不是偶然。
近300年来,青堆港由深变浅,由近至远,曾经涌入青堆镇的河南人、山东人,欧洲来的传教士、东亚来的日本人、朝鲜人,携带着中原文化及海外宗教文化,与当地满汉文化交融、碰撞,形成了多元、繁杂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在青堆镇绵延不绝。他们同在一个小镇上,谨慎经营,路数各异,却又将各自的观念规则留存于骨子里。那么,留存在大伯七兄妹骨子里的东西,就是他们用几十年积蓄于内心的力量,将他们的子女推得更远。这是去年大妈去世时我的感受。
爷爷与奶奶同庚,1890年出生,爷爷81岁、奶奶91岁老去。从爷爷算起,百多年的周家,从民国到合作化,一大家子人,长幼有序,过着殷实的日子。哥哥会走路时,就小皮鞋锃亮,分头溜光。爷爷沉默少言,好像时时都在给人号脉;奶奶勤劳能干快乐,她带领大伯父经营着周家饼店。饼店临街,坐在炕上做针线活的奶奶,看见窗上趴人,就招手,进来坐,进来坐。乡下上来赶集的,每天进来讨水喝的不下10人。奶奶从不闲着,媳妇们轮饭班,她不是帮这个烧火,就是帮那个哄孩子。奶奶近90岁时到我家,还一条腿上坐一个地哄哥哥的双胞胎孩子,瞅空帮妈妈缝补衣裳。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做通了妈妈的工作,让妈妈拿出些布角,奶奶给我缝了五个毽子,一大四小。奶奶走到哪儿,都是一屋子笑声。她耳朵不好,看人笑,就问,你们笑什么?把“笑儿”讲给她,她就接着笑,也让大伙重又哄笑起来。
合作化后,周家分家了,人分、财分、心分。听妈妈常叨叨,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这是不是母亲对周家分家时的感受?直到母亲88岁去世时,我也不得而知。父亲忠厚老实,不能出大力,做小买卖一套一套的,挣一分钱也交到伙里。别人点他,老四呵,家这么大留点小份子吧。他把那人的话告与爷奶,引起爷奶对那人的不满。周家秩序井然,没有犯上的,周家姑娘老少辈三十几个没与嫂子红过脸,在婆婆家更是贤惠有加。
改变周家人命运的是时代。因为有了个满洲国,把口才与长相都极好的二伯挑选去当了国兵,后当教官。国共拉锯时,二伯被抓,一个雪天晚上,二伯给看守他的两位农会会员讲“三国”。讲着讲着要去厕所,人跟着,之后回来再讲,讲到关键处,还上厕所,这回看守嫌风雪大没跟着,挥手说快去快回。二伯上次去厕所时瞄到门边有个杌凳子,将其挪到墙根底。回来人家又催着他讲,至关键处,说肚子坏了,再去厕所。看守说:快点儿呵。这一次,二伯翻墙而去,跑了。后来听说,那两位会员因为玩忽职守,腚蛋子都被打烂了。
几年后,二伯再次被抓,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获刑六年。这时还没有牵连影响到周家众人,待到文革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凡是周家子弟,参军啊晋升啊上大学啊等等,都过不了“政审”关,没啥指望。仁旭哥、仁杰哥及姑爷家五叔,蓄谋着一种改变和转机,三个人组织成立“风雷激”战斗队,表明向主流靠拢的姿态,自刻公章,自刻蜡板,油印材料一宿撒遍青堆大街小巷。第二天,老师查明三人团伙,劝仁旭哥,你出身不好,谨慎些吧。结果,脆弱的“风雷激”并未像它名字表现得那么强大,他们交出公章、蜡板、油印机,投降了。一次幼嫩的抗争胎死腹中。
1968年,仁杰哥18岁,下乡到立新公社(今仙人洞),第一个春节不让回家,过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他们十几个人,怀着奔家的巨大渴望,狼狼嚎嚎哭哭啼啼,从立新公社步行回家,走到大营子在同学姥姥家吃顿饭,睡一觉儿,天黑走回青堆。到家就扑到妈身上,眼泪巴嚓。哥是妈的心头肉,在哥身上丢了三个姐姐,在哥身下还丢了个姐姐。哥小时,妈妈干什么都不离手,仿佛那就是她的一个新器官。1969年农历正月十六,我们举家下乡到青堆公社孔家大队潘东小队。惟一的好处是:哥哥可以归户,不用再去青年点了。
一个合作化,将周家分家,大伯、二伯、三伯哥仨去下河口;一个运动,将哥哥下乡,将我们家搬到潘屯;一顶看不见的反革命帽子,将周家人压得老老实实喘不上气,并影响了一代人参军上学……二伯帅气、博学,即使因他让我们头上都有了帽子的阴影,整个家族依然对他颇为尊敬。惯于经商和外出游走的大伯、二伯、三伯,落于下河口,直到他们去世都不会搓草绳。我小时不懂,这有什么难,往一双小手吐上唾沫,搓出绳来,光顺劲道。还学会了扭网包,锁口也好看。爸爸在潘屯,弯腰的活不能干。后来我想,这是他们的一种姿态,或说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抵触方式吧。上几辈不抽烟不喝酒的周家男人,开始有了浪荡的迹象,仁旭哥和仁杰哥开始抽烟喝酒了,他们在广阔天地里找不到那些令人向往的图景。
生存环境逼仄也易使亲人间生出龉龃。大伯在青堆住院,奶奶把从医院带回的剩饭,喂给仁旭哥家早我一天出生的女儿,大嫂不悦阻止。大伯得知此事,立马将爷奶接到下河口,高声宣称,老人不是没有儿。仁旭哥对爷奶感情极深,二伯服刑期间,小二妈“走道”(改嫁)了,他便由爷奶带大。爷奶供其上学,找工作,18岁又娶妻生子。爷奶过世,仁旭哥想把老人用过的小炕桌留下作个念想,大伯坚决不肯给。
小二妈是区别于大二妈的,小二妈是大孤山人,今年已92岁,健在且十分漂亮。当年二伯做着教官,全副日式装备,呢制服,骑大马,佩洋刀。她在青堆绣房,和父亲表妹在一起绣花,表妹领她来周家,她便与二伯父一见钟情。当时大二妈已有两个女儿,爷奶反对娶小,他们就在外面租房,直到仁旭哥三岁。
妈妈讲,大二妈极有成儿(有本事、明事理),从不吵闹,家里活计从没撂下,也没给任何人撂过脸子。诸事得当,即便二伯进去了,大二妈也不会走。大二妈和二伯都办好离婚手续了,要回娘家那天,才告知大家。她领着四岁的淑兰姐回娘家了,留下了六岁的淑芳姐。淑芳姐也是爷奶养到18岁,嫁给远在伊春的两姨哥哥,后来她一直给爷奶邮粮票,直到1980年代奶奶去世。大二妈后来投奔其在伊春的姐姐,嫁一张姓人家,淑兰二姐便从周姓改张姓了。如此,大二妈娘仨也算团聚。2001年,离开周家56年的淑兰姐,在淑芳姐的陪同下,回到青堆,趴在二伯的坟地上长哭不起,她说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了。淑芳淑兰姐俩都戴眼镜,在遥远寒冷的伊春,她俩常跟母亲一起流泪,眼睛都哭瞎了。那次二姐走,我记她的电话号码,在手机上怎么也写不出个张字来,最后还是记成周淑兰。我想,原该如此。
小二妈走道时,领走了她所生的淑云姐,淑云姐长大后嫁在海边,还经常给爷奶送来她亲手编的苇席和晒好的鱼干、蚬干。2000年时,小二妈又透露,她走时还揣了个周家孩子,亦是个姑娘,生后送人,现在东沟,她们还有过认亲仪式。小二妈先后走了四家。后来见面,仁旭哥和我们都劝她,百年后和二伯并骨(合葬)吧。她却摇头不答应,说将来去公墓。她把青春丢在了周家,又几经颠沛,虽至老都是个漂亮老太太,但在我揣度,是不是她走到哪都没有做正室的感觉?一个漂亮却命途坎坷的女人,选择死后去公墓,其中或可透露出她漂泊无依、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青堆子天天望着大海,又渐渐没有了港口;周家几代人在青堆子生活,却与它渐行渐远,内心里有种不舍并生出深深的痛。
1975年拦海造田时,放炮崩起的冻土块要了二伯的命,那年二伯60岁。按说是事故,理应得到赔偿,但仁旭哥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摘掉二伯现行反革命帽子。这于我们几乎就像去了道紧箍咒——比起被管制的日子,连去下河口看爷爷奶奶都要持大队批的路条,真是要多舒畅有多舒畅。那之后,周家人凭着二十多年的扎实努力,渐渐走出阴霾。大伯家仁礼哥当上了下河口小队队长,并让下河口小队人喝上了自来水。三伯被安排看管水塔,按时提水。二伯去世后,周家摆事(主持家道)的活就落在三伯身上,此时的三伯,才情大显,就像他看护的自来水,源源不断。大姐找对象,父母反对,找来三伯说服;哪个媳妇和男人闹别扭了,找三叔评理。他不但给周家摆事,也给屯里人摆事。
大伯不声不响地侍奉爷奶,也以这一不声张的方式掌控周家。拨乱反正以后,政府返还合作化时期周家充公部分财物,用款项体现,大伯主持公道,按户均分。
1978年,大伯成为青堆镇第一个领个体执照的人,率领全家继续周家传统营生。这时已经没有周家饼子了,而专营豆腐。大伯每天赶着驴车,把新做的豆腐拉到青堆镇去卖,周家豆腐一出现,等着的人立即上前一买而空。暮年的大伯,或许还能找回当年周家饼店广受欢迎的感觉。至今,大伯家的仁茂哥还在做周家传统豆腐,我每每打起了馋念,第二天就有豆腐送来。周家豆腐入口即化,香嫩可口,炖起一碗端上桌,它在碗中颤颤盈盈引人垂涎,吞下一口周身舒适。做豆腐是个累人的活,起早贪黑免不了,大伯为人严厉,我印象中每次去他家,淑荣小妹总是在豆腐房拉着风匣。尽管她急着跟我玩却又不得脱身,把那风匣拉得乒乓直响上下撅抖,却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嘴里滴哩咕噜地发出些抱怨,又不敢张扬出声。
仁杰哥找了个八里庄媳妇,丈人家盖房子,本小队马车拉石头不够用,他拍胸脯,我去下河口弄,俺哥当队长。在山上找到当队长的仁礼哥时却碰了钉子,仁礼哥说春忙运粪派不出车,再说派给你,别人用车怎么办?仁杰哥没办成事,本想一去下河口,大马车就咵咵地来了,结果给杵了面子,一急眼,抓起泥块就朝仁礼哥身上撂,嘴里还不住声斥责叫骂着。直到三伯被人喊来才喝住。
2000年,龙凤胎中的男孩——兴威侄意外死亡,仅22岁。爷奶墓葬是仁礼哥家自留地,因为侄子是少亡,仁礼哥坚决不让进祖坟。想离祖坟远些,在大哥的自留地边上葬,仁礼哥还是一万个拨浪头。三伯极尽说事之能,与村屯沟通,将侄儿葬在大哥自留地边的另一块地。一年之后那块地被人包去养鸡,天天逼我们迁坟。其间,上坟也不让放鞭,怕吓着鸡。三周年满,家人前去迁坟,被养鸡户堆卸饲料压得铮亮的小土包,一直在此祭奠被认为是侄儿的小坟,往下挖,却根本不是。继续挖找,在养鸡户苞米仓下终于挖到侄儿的小骨灰盒。如果说仁礼哥对侄儿的拒绝,是因为仁杰哥抛去的那个泥疙瘩;仁旭哥不参加82岁大伯、91岁大妈的葬礼,是为爷奶那个炕桌,那么,当三伯家仁政大哥去世,仁礼哥又为何不让入祖坟,我一直很费猜解。亲人间别着的那些疙疙瘩瘩的劲儿,有时就像荆棘,堵住了通向生活原本的那条道路。
仁政哥65岁去世,晚上九点心脏病发作。当和我同岁的侄子从庄河赶到青堆医院,又挨家敲打寿衣店的门,买来衣裳给仁政哥穿好,运回下河口已是后半夜。第二天,兴安侄儿在先生的指挥下,扛着包了红纸缠了红线又滴了红公鸡血的镢头去茔地开圹时,路口站着被仁礼哥找去的队长。兴安呵,开圹呵?队长嗯嗯两声,似也觉难开口,兴安住脚。队长说你仁礼大爷不让埋呀,另找地方吧。兴安侄儿傻了眼,一下说不出话,明天就要下葬,现在上哪找地方?这时的周家,镇得住场的二伯、大伯、三伯相继去世,剩下不管事的爸爸,人称周家四少爷,即使去了,笨嘴拙腮也不会顶事。兴安扛着没沾泥的镢头回家,呜呜啦啦话不成句,脸已给气恼憋得紫胀。仁政大嫂听明白后,坐地拍腿嚎啕大哭,仁礼呵仁礼,哪伤了你?后找村屯人说和,仁礼大哥仍是不同意,只得另寻地方,仁政大哥如期安葬。
周家四少爷,我的老爸,一辈子就知道浪,18岁就骑着日产战狗牌自行车到处做买卖,在周家从来只知道服从而发不出指令。老爸今年88岁,患了脑梗起炕后,即使腿画圈儿不听使唤,也两天一双皮鞋地换,决不肯穿布鞋。每天早晨六点,雷打不动地出现在瀚林苑门口,依旧白裤白褂,眼镜礼帽,金镏子上手,锃亮的皮鞋。不知道他得脑梗的人,视他好人一个。曾有人问我,你爸在你家打更呵?对于一个从小在家里店铺劳作,常年跟街面上的熟客打招呼,退休后又逢集必赶,丧偶后不肯再续的老人来说,只要还能坐着,看着熙来攘往的人流和街景,几乎就是全部的活!
周家管事的祖辈父辈走了,那么秩序呢?长房长孙的仁礼哥想建立新的秩序吗?他没建立起来,一年后,仁旭哥,仁平弟将二伯、三伯、三妈坟迁走。那么仁礼哥想坚持什么又拒绝什么呢?
去年春天,91岁的大妈去世。周家祖辈父辈长寿,应该和爷爷的中医指导有关,还应和周家的豆面大饼子与豆腐有关。仁杰哥走了,大姐在外地,我和二姐前去,早晨五点动身,为的是赶在火化前去见大妈一面。大姐打来电话,带孝布了吗?咱老周家规矩,本家白事都自己备孝。二姐说知道,带了。和大伯家四姐妹真是久违了。她们嫁人后,在我的视野里基本不再出现她们的身影,谁家有事情她们也不去。在等大妈火化和下葬时,我们坐在一铺炕上讲话。得知家家都很好,孩子有在导弹旅的,有在石油研究所的,并且都在外面的大城市里买了楼。他们靠种地和打工,也靠孩子自己打拼,都能铺展出各自可瞩望的前景。淑香大姐两句话,让我理解了仁礼哥。大姐说,你们都有工作都有退休金,俺爸领俺到下河口,就一辈子种地。
这是一种因环境的落差而导致的心理落差精神落差吗?那么,仁礼哥是不是想将自己一辈子封死在下河口,不与任何人往来?他不缺钱,更不缺一盔坟所占的那几棵苗。可是,他们不知道,在我们心中,下河口,有爷爷奶奶在,有大伯、二伯、三伯在,因此,有周家的根脉在。当我们在潘屯,遇到哥哥架框草被人撅了满地怀疑中间夹石头时;当大姐干活休息空隙和别人一起下河网鱼,单她回来筐被踩扁并扣工分时;当别人挪了界石把地垅备到我们的菜根上时;当挨户收草木灰,硬说我们家的尿里兑水时;当很多人一声声饼崽儿饼崽儿骂不离口的时候,我们都擦干眼泪,我们有下河口。
是啊,我们还都有不由你选择的工作。1978年,仁杰哥按已婚青年分在道班,他整天一锨一锨地扬沙子护路,铺上油漆后,就一镰刀一镰刀地割着路边疯长的草。1979年,大姐按下放户子女分在建筑公司,整天从日出到日落,一勺一勺地给大工挖灰。二姐在棉织厂,三班倒,粗纱细纱将手勒满了口子。当我们下岗时,姐夫蹬三轮车养家,闪断了人家玻璃要赔,拉上个无赖故意摔了要赔,拉石棉瓦没赔过,却被玻璃纤维针刺得呲牙咧嘴。
我们在各自的路上挣扎着。二姐以工人的身份说,现在农民有钱吗?60岁以后有,才100多元,听说要涨,不知能涨多少。你们有地呀,我们用什么都得买,什么都贵。老三行,家里有企业。老三笑笑心想,当看到别人高时,有谁听到她行进中的哎哟声。老三开始搜肠刮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她们联结,她们坚强并脆弱。能用真丝巾换下她们头上的包袱皮吗?能用香水中和她们身上的汗水吗?能用化妆品驱除已浸到她们皮肉的尘土吗?终于找到一个角度,她们家家都有粳子。淑英二姐说,你们食堂不用吗?老三释然,拿起电话和食堂沟通,正好要买米了。107元一袋,50斤,卖吗?卖。得去拉,增添了运费,平常食堂一次买1000斤,还送货上门。老三就定,这次买2000斤吧。食堂却叫唤,现粉的米更容易焐,不好藏。老三还是定了2000斤。先拉谁家的?她们四个说先是淑英二姐吧。
安葬好大妈,第二天,老三就和二姐去淑英二姐家拉现加工的大米了。20天后,米吃没了,老三又打电话给淑荣妹妹。淑荣说,多钱?老三说老价,这个老价还真是老三现问了食堂的。淑荣说那我不卖了。老三在电话这边瞠目结舌,噢,好吧。老三还仿佛看到了电话那边淑荣翕张着的嘴。老三与大伯家四姐妹的联结戛然而止。老周家每个人都有通向公海的理想,而每个人都没丢弃小商人毫厘必争的本性。
老三找不到来时的路。祭奠侄子时,想给爷爷奶奶烧点纸,周家媳妇说,闺女禁入茔地,她们只能遥叩。给大妈圆坟时,老三走近祖坟,迁走的二伯、三伯茔地处栽着小树。由于仁礼哥的坚守,周家茔地分成三处。老三还会去下河口吗?老三去潘屯,当年生产队给四家下放户房子盖在洼处,冬天屋里地都是冰碴。而现在别人家基础垫高,已盖成宽敞的捣制房了。青堆子,周家店老屋还在,只是增高的路快接近老房房檐。
破旧的青堆子,散在的周家。就这样联结不上了吗?仿佛看到一棵老树,根脉尚在,枝叶喧哗,而栖息于树上的鸟儿,以各种姿态在绕树盘旋,啁啾不停。写到这里,老三不甘心,背着手在地上走。忽拿手机给仁礼哥女儿海燕发一微信。海燕,给周家建个群。海燕反应迅速,好的小姑。群名是:青堆周家。第一段:我是创建周家群的群主周海燕,诚挚邀请开通微信的周家人加入,望互相联系,方便沟通,我在群里向大家问好。第二段:收到邀请的都请冒泡哈。
这是周家又一代人的秩序与礼数,我犹豫再三,将哈哈二字发出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小姑为联结周家,还是冒泡了。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