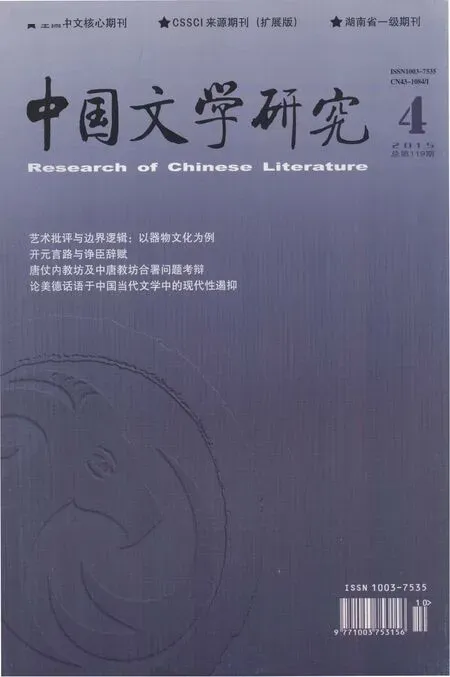礼仪与中国文学的“元象”——兼评王秀臣《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
杨 隽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01197)
笔者近日拜读王秀臣《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一书,深受启发。作者充分结合周代礼仪还原中国文学的元初形态——“元象”,沿波讨源,深刻解析“兴象”、“象征”、“文言”、“文质”等重要文学理论命题。这一研究的切入点决定了本书不是止于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本质的探讨,此其一。其二,笔者认为对中国元文学的研究仍可找到进一步阐述的侧重点,故撰文略述之。如作者所言:“仪式是艺术的原点,也是文学的起点。”穆穆皇皇、言语有章的周代礼仪孕育了中国文学的“元象”——“仪式形态的文学样式”,因此对言语之文的探讨必须结合礼仪之文,对中国元文学及其理论命题的探讨必然回到中国文学的“元象”及“元象”生成的礼仪空间。既是如此,笔者认为,对中国元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还应关注以下三点:第一,“演诗”是《诗》的礼仪形态,是周代礼乐流程的诗体话语,是周代礼乐精神的诗性言说,上博简《孔子诗论》云:“其言文,其声善”,《诗》是“文言”,是“善声”,周代礼仪赋予《诗》“文言善声”的审美特征,印证了“文言”理论命题的实践意义。第二,“立德”是周代礼仪的宗旨,是“文质彬彬”的人格标准向文学审美标准转向的桥梁。第三,“兴象”是“意象”的仪式形态,动态呈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立象尽意”的思想言说路径,是文学“意象”结构成熟的实践基础。
一、“演诗”与“文言”理论
据现有文献载,“文言”理论由孔子首先提出,但“文言”实践的展开显然要早于孔子。钱基博曾云:“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如钱先生所言,“直言”经过自觉的修辞而成“文言”,意谓孔子之前不仅“直言”与“文言”都存在,而且“文言”的修辞标准已很成熟。如孔子曾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思想传播的广泛与久远,这不仅说明“文言”实践是充分观照到接受环节的文化传播活动,同时意味着“建言修辞”的创作实践必然以可参照的成熟的话语范式为基础,即以符合“文言”标准的经典作品为范本,周代礼仪“演诗”正是促成重要的“文言”范本之一——《诗》生长成熟的空间。
进入西周,礼乐文化盛极一时,周代礼乐仪式空间活跃着歌、乐、舞统合的“演诗”艺术,“演诗”是周代礼仪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演诗”风格也伴随周代祭祀、燕飨、宾射等礼仪用途而呈现多样化的审美特征,“颂体诗篇基本上保留了青铜韵语的古奥庄重的特点,而风雅诗篇则带有灵动清新的艺术风格,其中《国风》与《小雅》的篇章尤其如此。”这种多样化的艺术特征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也曾论及,如简2、简3 云:“颂,平德”;“大雅,盛德”;“小雅,小德”;“邦风,其言文,其声善”。《周颂》为周王祭祀歌诗曲目,类于青铜韵语,古奥庄重,整体风格肃庸平和,谓之“平德”。如《周颂·有瞽》云:“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庸和鸣。先祖是听。”周代的祭祀仪式“演诗”是弦歌、乐奏合一的艺术表演,对此上博简《孔子诗论》有这样的概括:“乐亡隐情,诗亡隐志,文亡隐言”,诗乐合流的祭祀仪式“演诗”既是以礼乐、以“演诗”完成的宏大祭祀活动,传达孝道亲情、展现弘毅博大的政治志向,而且也是最具艺术水准、文学意味的“文言”实践活动,可见,周代礼仪“演诗”本质上决定着“文言”的思想内涵、艺术路径以及审美标准。其余如,《大雅》歌于周王祭祀仪式和大飨礼、大射礼仪式,语言风格隆盛典雅、豪气高韵,如《大雅·文王》有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歌着力显现王者的精神力量,故谓之“盛德”。《小雅》与《国风》用于燕礼仪式和乡饮酒礼、乡射礼仪式,明显呈现出和合自然、灵动明快的艺术风格。如《小雅·棠棣》有云:“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诗中洋溢着兄弟友爱、夫妇静好的室家欢乐,相比于《大雅》的“盛德”之风,谓之“小德”。《国风》则善以口语入诗,更为清新,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完全不是年轻少女暗送秋波的款款深情,而是直接进入向适龄男子求婚的模式,从择吉期嫁娶至撞日出嫁,最终只需招呼一声,口语化的“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谓之”三句使少女恨嫁的情态毕现,可谓“言文声善”。由此可见,《诗》所肩负的礼仪“演诗”用途是《诗》的体例结构、语言风格成熟定型的本质原因,礼仪“演诗”赋予《诗》——诗体“文言”不同的艺术表现特征,周代礼仪“演诗”是最大规模的“文言”艺术实践活动,大大促进了“文言”创作的自觉与理论的成熟。由此可见,《诗》是西周“文言”艺术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诗》是集中体现礼乐之文与言语之文的经典“文言”范本,印证了礼仪“演诗”对“文言”理论的实践意义。
综上可见,在周代礼仪空间生长成熟的“演诗”艺术即《诗》的“元象”,因此周代礼仪也是《诗》的“文言”形态生成的文化空间,这意味着《诗》是孔子《易传·文言》创作的重要范本之一,“文言”理论必然是对礼仪“演诗”艺术实践的总结。所不同的是,孔子独制《乾·文言》《坤·文言》,在语言表现形式上与礼仪形态脱离,这预示着真正文学意义的“文言”范本的确立,但仍不能否认周代礼仪“演诗”对“文言”的实践意义。因为“礼乐实践将语言纳入艺术的视野,语言艺术同其他相关礼典艺术相伴而生、同向而行,是中国早期语言艺术实践的特殊情形。正是这一特殊的形式孕育了中国文学最初的语言形态和最早关于语言是一门艺术的文学理论雏形”。因此,周代礼仪“演诗”实践对中国诗歌的“元象”生成与理论成熟具有重要价值。
但近年研究的实际情况是,“文言”理论的文学价值研究出现了断裂,如南朝刘勰的一句感叹:“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言”理论摆脱了与礼仪之文的初始对应关系,并由“文心”取而代之。自此,对于“文言”理论的系统探究鲜有学者问津,这与“文言”理论的实际价值极不相称,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而言也是不小的缺憾。相对于“文言”理论被长期忽视的研究境况,《礼仪与兴象》一书却能够将元典与“元象”相结合,充分关注礼义对于“文言”理论的启发意义与实践意义,以礼仪作为考察“文言”理论来源的切入点,回溯“文言”的理论元点,真正从中国文学的“元象”出发清晰透彻地厘清了“文言”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而重新评价孔子“文言”理论的文学价值与意义,这不得不说是“文言”理论研究的又一进展。
二、“立德”与“文质”关系
文学理论研究不仅是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而且还应注重理论命题之间的关系研究,《礼仪与兴象》一书不仅上溯礼仪空间对“兴象”、象征、“文言”等重大热点问题逐一展开微观还原、宏观阐释,而且注重理论命题之间的关系研究,如“文言”理论的研究就通过对礼仪之文的研究从而展开对“文言”理论的全景文化考察,并且对“文言”实践的考察没有局限于言语修辞方面,而是以“礼辞”为研究生长点诠释“文言”的道德、伦理品格,这种“文质”兼顾的“文言”研究深刻揭示出“文质彬彬”的人格理论转向文学理论的内在原因,作者对“文言”理论与“文质”理论的联系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但笔者注意到,作者对“文质”关系的考辨虽然也注重联系周代礼仪教化的“崇德”思想特征,但关于周代礼仪的“立德”宗旨与文学意义上的“文质”观念之间的联系仍待进一步阐述。
在周代,礼仪的“立德”实践及其秉承的“乐德”精神——“中和祗庸孝友”正是决定春秋时期“立言”实践“文质”关系的根本原因,孔子的“文质”观正是受到周代礼仪道德精神的直接影响而提出的。如《论语·雍也》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毋庸置疑,孔子的文质统一论起初是就君子人格精神而言,是对西周礼仪教化传统的继承。但殊不知,源自礼乐人格养成的“文质”传统也为春秋文化阶层树立了“立言”不朽的“文质”标准,为“文质彬彬”人格观向文学观转向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叔孙豹认为不朽之言乃成德、建功之言,而“立德”、立功都指向政治权力的确立。“立德”象征周代先王拥有功成天下、守成四方的精神力量,“立德”即王德确立。因此,叔孙豹所谓“立言”无疑是指以政治社稷、家国安康为主体的话语内涵的确立,其中蕴藉着一代圣德君王的品格精神与政治思想。
“立言”思想在春秋时代的影响很大,孔子多次表达“立言”思想,如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见,孔子是主张继承“言德”统一的文化传统的。但进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建立“言德”统一依存的文化一统局面日益瓦解,王权旁落,诸侯僭越时有发生,这必然导致政治话语权与王德精神的错位,甚至失位。鉴于此,孔子出于尊尚古礼而发出“言德”统一的呼吁,同时感慨“言德”失位的政治现实,可见“言德”能够代表孔子关于文学意蕴的规范和要求。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在礼仪传统与“立言”思想的影响下,“言德”进一步向“言志”转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相比出自《尚书》所描述的礼仪化的“诗言志”命题,“言以足志”明显脱掉了礼仪化的外衣,言语本身的缘情特质显现,“言志”的文学意味也鲜明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言”的礼仪道德精神的丧失,而是寓于所言之志中,以“志”涵容礼仪精神,即以礼仪精神统摄“志”的内容,这其中更能说明西周礼仪精神为春秋“立言”提供了道德文化传统,“言德”说与“言志”说充分反映出春秋时代对“言”的礼仪精神的追求。
不仅如此,以德统志的“立言”标准反映出春秋士人对言语内涵的自觉规范,规定了言语的艺术表达方式。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曾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孔子认为,饱含礼仪道德内涵的“言”必须经过文饰、艺术化而成为“文言”才能充分传达思想意蕴并流传广远。因此“立言”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言语内涵本身,还必须依赖“文言”实践过程,唯有“立言”实践与“文言”实践的统一,即完成“立言”—“文言”的实践过程,实现“文质彬彬”,才是春秋之“言”的完美境界。孔子所作《文言》即“文质彬彬”的典范之作,《文言》语句典雅,音韵和谐,结构严谨,总分有序,语言富有文采,而且都是言德行的文字。如坤《文言》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赞美柔顺之德是坤《文言》的主旨,柔顺之德涵纳万物、滋养万物,承顺天道运行,坤的柔顺使万物有主宰、运行有常态,这无疑是以大地的柔顺之德申明庸和有礼、孝顺友爱的礼仪道德精神。由此可见,文质兼美的《文言》印证了“文质彬彬”向文学转向的实践路径。
综上所述,周代礼乐仪式的“崇德”思想特征奠定了礼仪空间的文质关系:以礼仪道德精神为根本为灵魂为统摄,并以屈伸俯仰、升降上下的仪式化行为实践道德精神。不仅如此,周代礼仪道德精神深刻影响了春秋士人的“立言”标准与“文言”实践,以德统志的“立言”标准规定了“文言”实践的内容与形式,并预设了“文质”关系的讨论转向语言本身的可能。由于“文言”实践的目的是通过对语言文饰技巧的锻炼实现礼仪道德精神的传播,因此《周易·文言》堪称周代礼仪的“文言”实践成果,它不仅记录了周代礼仪道德精神的核心内涵,而且是中国元文学语言艺术的另一重要范本,印证了“文质彬彬”思想的文学意义。
三、“兴象”与“意象”结构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云“象生于意,故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王弼认为“明象”是理解《周易》六十四卦的关键,而且在“言—象—意”关系论述中明显突出“象”对超越“言不尽意”境况的重要性。但王弼认为语言符号的“明象”功能同样不容忽视,因为语言符号的实在性才使得“寻象以观意”变得可能。正是由于语言符号是“明象”、“观意”的唯一具体实在的依据,王弼在语言意义结构的分析中强调语言符号的“明象”功能,这对文学鉴赏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经刘勰一句“窥意象而运斤”的总结,创造“意象”成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优劣也成为评价文学成就高下的重要尺度,而“意象”能够转化为文学命题的文化原因及其最初的实践方式往往被忽视,进而“意象”的全景天地被部分遮蔽。“意象”研究的不完整使得对于文学“意象”的理解变得逼仄狭隘,这是文学“意象”研究的严重不足,因此“意象”的元生文化形态考察成为目前文学“意象”研究的重要生长点。《礼仪与兴象》的作者选择以“兴象”的礼仪形态研究作为联结元文化与元文学“意象”的契合点,客观呈现“兴象”在礼仪流程中以“言-象-意”为基本路径的实践过程,从而揭示元初“意象”命题隐含的文学意味及理论基础,弥补了“意象”研究中长期的缺失与不足。笔者在此仅就礼仪“兴象”对文学“意象”结构定型的实际意义略作阐述。
自漫长的史前时代迈进商、周时代,“立象以尽意”就成为先民传情达意的基本途径,立象达意的言说方式不仅体现在文字、语言,甚而体现在一切艺术形态中、哲学思想中,或者说“意象”思维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而存在于一切有关中华文明的记载中也不为过,因此对于“意象”命题的提出不是缘于文学批评的自觉这一点实在无需奇怪。而且实际的情况是:相较于“意象”命题,礼仪“兴象”更容易通向文学本身,这意味着礼仪“兴象”是发现“意象”命题元文学意义的关键。“兴象”一词源于孔颖达“兴必取象”的论述,揭示了周代礼仪之“兴”以象达意的具体实践路径。《说文》谓:“兴,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后人多从,但并非“兴”的本义。“兴”的甲骨文象众人举物之形,所举之物为“同”,“同的一个意义就是祭祀用的爵,即酒杯”,“因此“兴”字的“元象”描绘的是众人共同举杯祝愿的画面,透露出其元初意义与宗教祭祀仪式的密切关联。另《礼记·祭统》云:“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郑玄注云:“兴,谓荐百品。”上古祭祀仪式要按规定事先恭谨庄重地陈设各种荐品,包括模拟先祖生前穿着使用的服饰用具,以及祭祀仪式中必要的礼器,例如食器、乐器等,这些荐品统称“兴物”。不仅礼仪中的荐品百物称为“兴”物,仪式流程中的表演环节也称为“兴”,如《礼记·仲尼燕居》关于大飨礼表演环节就有这样的记载:
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据上述文献记载大飨礼的仪式之“兴”主要有两种实践方式:(1)悬兴:即入门鼓钟,亦谓之金奏,又因悬于簨簴(钟架)演奏又称金奏乐悬。钟鼓金奏是君王至尊威仪的象征,因此两君相见以“金奏”悬兴表示相敬之情,即以金奏之象“示情”。(2)“序兴”:即仪式正乐依序表演。升堂而歌《清庙》以清明祭宫象征文王盛德,即以歌诗之象“示德”;管吹《象》,舞《大武》、《大夏》,艺术显现文武功成天下的伟大事迹,以大舞之象“示事”。“兴”分别以乐奏之象、歌诗之象、大舞之象发挥着礼乐仪式“示情”—“示德”—“示事”的功能,礼仪之“兴”皆以“象”达意,“兴”遵循着“立象尽意”的实践路径,并且只需“兴象”而无需语言,仅凭“兴象”即可在固定群体内部顺畅沟通,这只能说明“兴”的象意在礼仪空间已获得集体的充分认同,“兴象”在长期的群体参与的礼仪活动中所生成固定的意义指向充当了语言的表意功能。换言之,礼仪作为“兴”与“象”结缘的原始语境而赋予“兴象”既定的意义,从而使得礼仪之“兴”融汇了语言与意象的双重功能。
“兴象”的仪式形态强调了“象”在意义传达上的优势,其沟通交流的优势甚至超越了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语言的弃置。相反,语言的意义在礼仪用诗中得到充分展现。如《关雎》首句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雎鸠合鸣之象兴发男女婚配,毛传云:“兴也”。《鹊巢》首句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以鹊巢鸠占之象暗示女子出嫁,毛传亦云:“兴也。”《诗》之“兴”所呈现的“言-象-意”的传达路径标志着“兴象”由礼仪形态向文学形态的转化,从而与《易》之“意象”表现出更多相通之处。如《周易·系辞》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孔子认为弥补语言表意缺陷的有效方法不仅是“立象”,还可以运用六十四种卦象符号模拟呈现人类的情感,并论述《周易》经文的义理,以三百八十四爻象动态呈现万物更新之象,这境界如同鼓舞娱神、神人以和的大乐之美。《尚氏学》云“意之不能尽者,卦能尽之;言之不能尽者,象能显之。”“卦”是尽意之卦,“象”为言之所立,尽意是语言的目标,可见,“象”与“卦”皆为虚象,“意”才是主宰,人类利用言语符号以成象、以尽意,表明对自然的能动选择,如乾象天,坤象地,《周易》选择天地之象是以天高地卑的自然景观言说君臣有位、尊卑有等、男女有分的主观判断,因此“成象”是自然主观化的结果,而语言记录了人类的这一重大精神成果,惟“象”如此才能“尽意”,才能弥合言意之间的隔膜。
“言—象—意”是《易》之象与《诗》之兴共同遵循的实践路径,展现了早期语言的“成象”实践过程,为人类情感发抒、思想传达积累了丰富生动的经验,言语成象而鸢飞鱼跃、活泼玲珑,“兴象”与“意象”会通交融的独特经验成就了中国文学的“意象”特征,重“意象”创造作为强大的文学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的创作与鉴赏。虽然周代广泛展开的“立象尽意”的实践活动不是为了文学,但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元文学的语言艺术、审美特征的生长成熟,“兴象”与“意象”所遵循的言-象-意的实践路径无异于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也奠定了文学鉴赏的基本层次。在礼仪“兴象”的引领下,回到“意象”的元初文化空间,联结文化与文学的桥梁,“意象”命题的文学意义才如此深刻透彻,文学的“意象”结构才如此完整清晰。
周代礼仪是中国文学“元象”生成的空间,“演诗”、“兴象”、礼辞、祭器、服饰,无不闪现着中国最初的文化群体对文学、对艺术的审美发现与理解,以礼仪为桥梁回到文明之初能够动态还原一幅穆穆皇皇、文思纷沓的元初文学世界,能够更为接近中国文学的“元象”及其理论元点,因此回到礼仪空间是一次去蔽的文化寻根,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由于它通向本真的中国文学与思想境界,研究成果必将是博大精深并有重要学术价值。
〔1〕王秀臣.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邢昺.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