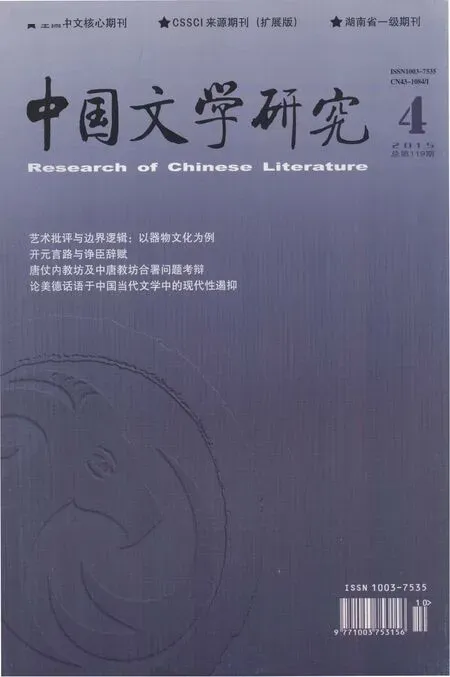消费语境下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透视
彭 丽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引 言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形态由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事实上,当下社会已步入一个消费社会,人们正在一个由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演绎着一种“没有规则只有选择”的消费文化。这种消费语境导致了视觉文化的欲望叙事,通过伪装和包裹催生新的消费,并觊觎建构一种图像消费的“乌托邦”;而图像叙事又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内涵。在此背景下,作为商品景观而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或视觉对象的女性,被“视觉狂欢的浪潮”推至视觉时尚前沿,其形象与角色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装备的媒介的建构与呈现,既折射和反映着社会之于女性形象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期待,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基于此,透视和分析消费语境下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理念,对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引领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塑造与呈现: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之特征
循着图像艺术的发展轨迹去审视,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之于传统的肖像绘画,还是之于当代大众传媒,女性形象始终是图像再现中的对象。虽然当代女性在政治参与、职业平等方面获得了历史进步,但在当代消费与视觉文化语境下,其形象却被当下繁盛的商业文化与大众传媒作为一种有效资源进行建构与呈现,流变成一种可被消费的“漂浮不定的能指”符号与视觉快餐,其中不乏刻板、扭曲、亵渎、异化甚至歧视。
当下视觉图像所呈现和表述的女性形象究竟具有哪些话语特征?其一,强化传统角色定型。一般而言,角色定型即是对男女两性特征予以归纳与概括,但由于这种归纳与概括是基于单一的男性中心文化视角的,难免充溢着传统的色彩。如就性格特征而言,男刚女柔;就智力能力而言,男优女劣;就权力分配而言,男主女从;就性别分工而言,男主外女主内等。在大众传媒中,男性往往充当着领导者、欣赏者、保护者、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而女性则表现为一种被领导者、被欣赏者、被保护者、问题制造者的特点。如长篇小说《白鹿原》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塑造了一个在男权社会中缺失话语权的女性群体,她们是传宗接代的机器,或是被交易与被利用的商品和工具;当女性以冠名为“祸水”的美去努力改变其社会地位时,却引来了一片“喊杀”,这些无不表现出男权至上伦理对女性自主精神的压抑与摧残。刘伯红等通过实证研究1197 个广告案例,结果发现33.7%的广告存在性别歧视问题,而在性别歧视的广告中则有71.46%的角色定型。这些定型的女性角色,不外乎“贤妻良母”与“风情妖娆”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均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理想范式与审美标准。对于前者的建构与表述,或把女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象征符号,或突出其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但却消除或掩盖了女性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而对后者的建构与表述,则通过包裹和伪装其身体,展现其光滑的肌肤或婀娜的身材,甚至通过探讨感觉、禁忌和隐秘领域的私性话题直视女性的内心世界等,由此,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完成了男性视觉欲望的载体”。
其二,热衷制造“美女神话”。在消费与视觉文化语境下,“美女”自身含义已被后现代文化抹煞,这一称呼已不再是仅仅指向女性的貌美,而是通用于整个女性群体。“美”似乎就是商品价值,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调查发现,国内现有的各大期刊杂志,以女性图像作为封面的达到90%以上,这些女性形象几乎均是外貌呈现,或妆容或装扮,而与其工作学习生活关系不大。纵观现代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的商品广告、影视剧中的主人公,还是各地层出不穷的歌舞大赛、选秀节目等,都更倾向于女性形象的建构与呈现。而在女性形象、“美女神话”建构与呈现的背后,则潜藏着一种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商品交换的美女效应。如当今不少热播剧虽情节乏味,但凭籍女主“傻白甜”的可爱形象和爆表颜值,其收视率仍可节节攀升。
其三,刻板女性形象。雅格布森的符号学理论认为,隐喻与转喻是传播意义上的两种基本模式,隐喻即利用两个符号间的相似性以一个类比另一个,转喻则是以小见大、以局部代整体。与生产与消费女性形象这一特殊商品密切相关的广告,或许正是按照符号学的这一逻辑,以一种特有的策略和修辞手法牵强地把美女形象与某种本不相关的产品或商品联系起来,并制造一种对受众所谓的“视觉冲击”。比如,将女性的皎白肤色诠释为饮料的清爽宜口,把女性的形体曲线拟同于汽车的舒适感,用女性的长腿喻成瓷砖柔滑的诱惑等。在这里,不管女性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具象的形象,还是被定义成“美”的隐喻,女性本应有的多样性形象均被抽离或抹煞,它只是一个被物化、商品化、空洞化的刻板形象。于是,女性的主体性或个体性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由文化诠释、规定或命名的女性形象,其价值也并不在于女性或者其形象本身,而是由传统价值观建构的“交换价值”。
其四,弱化女性作用。漠视或忽视女性之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否认女性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抽离或抹煞女性本应有的多样性形象,这对大众传媒而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全球媒介监测显示,1995 年、2005 年全球76 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中,女性占新闻总数分别为17%、21%,其对女性的刻画及其性别意识变化“令人沮丧”;刘伯红等在对国内电视广告中两性职业角色调查显现,从事科技职业的男性是女性的2 倍,从事管理和领导职业的男性是女性的3600 倍;全国平均在家务劳动时间上,男性是2.21 小时,女性是5.01 小时。可见,在视觉图像中,居于从属地位的传统女性形象依然大量存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状况“并无本质改变”;同时,由于两性职业生活的差别被传媒加以夸大,无形之中弱化或贬低了女性的作用与贡献,影响和制约了女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
综上可见,大众传媒之于女性形象的建构与呈现,在为公众提供观看对象以及看与评价的眼光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遮蔽和藏匿着视觉快感的意识形态、性别的不平等和偏见等问题——它以其敞开与遮蔽的双重功能,充当着贬损女性形象与传播传统角色定型的共谋,并以其隐性的话语霸权阻碍着女性的全面解放、发展与进步。
二、看与被看: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之消费
人们从人的包围之中步入物的包围,是消费社会中最根本的变化。鲍德里亚认为,消费语境下的人之消费不是物本身,而是一种“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的“突出你的符号”,因为消费已经成为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训手段。于是,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难以避免地沦为一种看与消费的对象。当然,这种看与被看并不是仅存于消费语境中,作为看的对象,女性裸像一直是西方造型艺术的基本母题,在中国也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只是消费语境下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因“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而“具有被看性的内涵”。而且,作为人的与生俱来的属性和自然行为,在消费和视觉文化语境中,看与被看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正如周宪所说,“人类看似自然的观看行为,其实是复杂的文化行为”。
女权主义理论往往把男性视为看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看的对象和客体。就自然属性而言,两性均是以“人”直接呈现的生命形态,在视觉图像呈现和突出女性之美为“他者存在”时,其实是在强调女性某些自然性别的特征,但经过男性“看”的过滤,女性形象往往只剩下“性”的符号。一般来说,相对于男性接触到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视觉图像中的女性更加完美一些,这种完美的女性形象成为男性因现实生活中的缺失而产生幻想的介质,从而获得法律不准、道德不容的某种欲望的满足和宣泄。比如,在“秀色可餐”和抹煞女性主体性的“香车+美女”的广告模式中,男性不仅可以置身现场获得视觉和心理上的满足,也可以因为消费香车获得一种驾驭和征服女性的快感。这种看的模式也被诸多电视广告生动呈现,即按照“惊艳-打量-性幻想”的逻辑表述和呈现广告中男性的心理,这可否视为男性在“看”视觉图像中女性形象的一般心理特征?毋庸置疑,在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女性难以获得男性尊重与平等的看,她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物而存在。如在一则电视广告中,男明星以劝诱的语气陈述其梦中情人,“我的梦中情人,一定要有一头乌黑靓丽的头发,相信我,没错的。”——在这里,真实女性形象的缺席与陈述中的虚拟存在,既表达出男性驾驭女性的一种自信,同时又因女性形象的某种迎合强化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在这里,男性不仅无视女性自身要求,而且把女性美的标准强加给女性——如果这种强加给女性的女性美一旦内化为女性的“圣经”,那么女性便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美的符号。
视觉图像中女性形象看的主体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如何“看”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女性之“看”也有幻想,但这种幻想较之男性是不同的。马中红教授认为,女性看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而产生的幻想主要有3 种:姐妹型,这类女性与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在年龄、生活条件、消费目的都较为相仿或相近,其幻想主要表现为羡慕与效仿的心理欲望的激发;邻家女人型,这类女性产生的幻想源自其窥视邻家女人怎样消费或消费怎样的物品,她们往往把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视作邻家女人,她们试图通过凝视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了解身边的女性,进而确认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方式;情敌型,这类女性即把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视作“情敌”,由于现实生活中某种缺失或攀比心理,她们往往带着一种羡慕、嫉妒的矛盾心理观看和幻想。相对于男性获得欲望的幻想与满足的“看”,女性的“看”更多是将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作为自身行为的参照与比拟,重点在于关注与效仿“美”——二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权力话语关系,男性之“看”,在于以一种欲望想像、塑造和占有她们,并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而女性之“看”,则颠覆了这一权力话语关系,她们将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转化为一种理想化的目标,并希望通过消费商品而改变自己。
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两性含义的不同来自不同的文化,两性的意识形态由社会文化操纵着。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社会话语权始终由男性操纵着,而女性则是被动的、附属的;历史的车轮驶入21 世纪,虽然女性在政治参与、职业平等等方面获得了历史进步,但却没有掌握审美权,美的标准依然由男权中心制造和推出,如果有悖于这一美的标准,便会遭到公众的冷落和排斥,甚至视为异类。在此背景下,女性被迫放弃或改变自我,顺应或者迎合社会对美的要求和评价。当女性“通过他人来激起对物化社会的神话的欲望”,以男权中心制造和推出的美的标准形象出现时,她们也许会得到一时的虚荣的满足,但付出的却是身心的疲惫——在女性为瘦身而被减肥药蹂躏得痛苦不堪时,在女性为获得胸部的丰满而注入硅胶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野蛮的施虐与受虐;如果达不到这种目标,她们便会产生一种自我敌视或嫉妒的心理——或许正是在这种奴性化的、自虐、自恋的人格扭曲中,女性成为了单纯的性别符号。
三、合谋与斗争: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之建构
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建构与呈现、消费与被消费的背后,折射着传统思想、社会观念和文化意味。事实上,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的生产与消费有着深厚的历史动因和现实背景。
基于历史的视角,东西方文化中之于女性的歧视均可谓源远流长。在西方,女性的歧视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文化之于女性的两个负面评价:一个是《圣经》把女性视为万恶之源,另一个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同时,诸多思想家与哲学家也助推女性跌下深渊,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些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指出,“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与女人”;尼采也强调,“女人身上藏着一个奴隶和一个暴君”等。在中国,对女性的传统贬抑则是通过礼仪、禁忌、话语方式甚至扭曲身形,把女性纳入男权话语体系与父系社会秩序之中。直至当下,这种传统文化依然潜在着,或者说我们依然生存于这样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中。虽然在当下的时尚界、娱乐界滋生并流行着“男色”或者“美男经济”的文化话题,但这是伴随着“女色”或者“美女经济”演绎和衍生出来的,我们从中既可看到女权主义的复兴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可看到“男色”与“女色”内涵与表现特征的不同,因为女性与男性“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还能看到制造“男色”与“女色”的一只无形的手——为了流行而生产东西的商业文化——媒体生产者与女性形象建构者不能也不可能不受到男女之间的宗教、伦理、道德、审美及风俗习惯的钳制,不自觉地传播着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基于经济背景的视角,趋向消费主义的以经济效益为终极目标的大众传媒,必然顺应或迎合“眼”驱逐“心”、“欲望”驱逐精神性“想象”、“表象快感”驱逐“内视审美”的潮流,以其敞开与遮蔽的双重功能和传播便利,持续制造和传播为男性所期许的女性形象,并建构一个“超真实”的“模拟”组合的世界,刺激和引领着大众消费;但其中的性别角色分工的夸大与不平等,又在客观上强化了性别角色的陈规定型。基于女性的视角,一方面,客观存在着女性特质,这些特质主要包括生理和心理、渴望无限、主导消费等方面的特质,或许正是这些独特的因子使得媒介在无意间形成了“性别刻板”;另一方面,在男权话语掌控的而无力与之抗衡的大众媒介中的女性,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了男权话语为其设定的女性形象和“性别刻板”,并潜移默化成一种女性自身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之于不公平的两性秩序不仅失去应有的批判力,而且在客观上维护着不公平的两性秩序。
基于这样的背景,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但这种必然引来多方面的反思与批评。从学术领域看,国内诸多学者对此作了多视觉的反省与批判,如吴飞的《媒介与性别政治》对父权制在塑造女性形象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有力批判;卜卫的《媒介中的刻板印象研究》批判了刻板印象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负面影响;艾晓明的《广告故事与性别——中外广告中的妇女形象》揭露了其中的性别偏见。从艺术领域看,艺术家采用多种方式予以嘲讽和斗争,如女性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以“游击女孩”的形式嘲讽男性世界的女性性感漂亮的标准;辛迪·舍曼采用自拍的方式,以摹仿反讽和揶揄解构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策略,批判了消费主义诱导下存在的男性意识;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通过对美术史中“教父”级的《蒙娜丽莎》改头换面,消解了大众传传媒塑造的谎言,解构了性别和权力。这些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与嘲讽,倒逼着视觉图像中女性形象建构与呈现者的反思与警醒。如何建构与呈现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女性形象,并从中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自然离不开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主动与他者文化的合谋与斗争——大众文化与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的合谋与斗争,这已是当下视觉文化格局中各文化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形态。基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大众文化在试图缓和疏解与他者文化的斗争关系,它一方面在主动与主旋律文化合谋,以主旋律意识形态包装通俗文化生产,不仅获得了宣传与资金支持,而且通过“共名”成功实现“正名”。如由影视公司这一大众文化生产方拍摄的《玉观音》、《永不瞑目》等影视剧,均是在主旋律题材的“宏大书写”中融入了青春偶像剧和情节剧的叙事逻辑,成功实现了青春偶像剧的“正名”,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具有正能量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也在寻找与精英文化的合谋,如《橘子红了》、《大明宫词》等影视剧,以“爱情与人性”、“权力与爱情”作为“正名”的“主题”包装,以精英文化的名义探求艺术、人生、社会等问题。
结 语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反省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视觉图像中建构与呈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形象?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就社会层面而言,一方面,应建构和引导性别文化,践行与发展以人为本、尊重女性个体的特殊性与多样性,给予女性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以平等的权力、责任、发展机会与社会资源配置,使其在平等和谐的性别环境中接收多元价值观念、发展各自潜能;另一方面应促进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展,并建立完善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法律保障,维护和发展女性的合法权益。就女性自身而言,当下,世界文明的进程因科技文明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加快,一些狭隘的偏见在经济全球化、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多元化文化的激荡中日益消解,这些都有利于女性本身价值的还原。女性在建构自身形象的过程中,应强化主体价值和自我意识,在破除传统桎梏中释放自身潜能,在融入公共领域中创造社会价值,在物欲横流中坚守精神高地,使外在之美与内在价值有机统一,赋予自身形象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蕴和社会意义。就大众传媒而言,应清醒认识自身在视觉文化中的扮演的角色、承载的社会责任,自觉从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和视觉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全方位开掘女性文化,以饱满、崭新、健康的女性形象传播先进的社会理念和美的文化气韵,准确反映当今社会的女性风貌和真实的内心世界,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周宪.论作为象征符号的“封面女郎”〔J〕.艺术百家,2006(3).
〔3〕郭培筠.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1).
〔4〕刘伯红、卜卫.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A〕.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张淑丽.解构与建构:女性杂志、女权杂志、女权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J〕.中外文学,1994(2).
〔6〕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戴韵.女性时尚杂志封面女郎形象解读〔D〕.苏州大学,2007.
〔8〕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温乃楠.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问题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8.
〔10〕刘伯红等.试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男女角色定型〔J〕.妇女研究论丛,1997(2).
〔11〕(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张红军.电影与新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3〕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A〕.文化研究〔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5〕陶东风.镜城突围:消费时代的视觉文化与身体焦虑〔J〕.中国广告,2004(9).
〔16〕丁怡.现代花瓶与贤妻良母——当代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综述〔J〕.广告人,2009(7).
〔17〕赵炎秋.生产与生存: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及其解决——重读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18〕道格拉斯.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与政治〔M〕.周宪、许钧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4.
〔19〕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20〕张晓凌.观念艺术——解构与重建的诗学〔M〕.沈阳: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