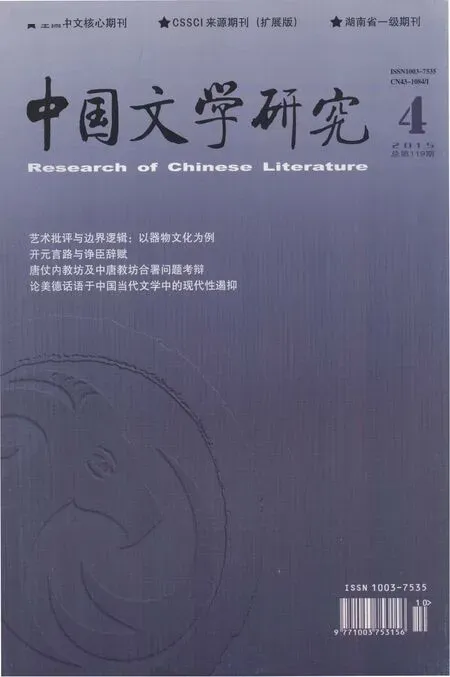论木心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以《文学回忆录》为例
刘 剑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北京 100876)
印象批评是一种创造性地表现批评家的主观印象和瞬间感受的批评方法。它依据审美直觉,关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它否认作者“客观意图”的存在,强调批评家的阅读感受,印象批评重视阅读印象,是一种斯坦利·费什意义上的“强读者”批评模式,实开后来接受美学的先河。印象批评在上个世纪30年代经李健吾等人的提倡,在中国“京派”批评中盛极一时,之后新中国文学批评史起伏跌宕,多为狂躁的政治潮流所裹挟,代表“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审美批评几成绝响;1980年代以来,批评界引进西方各种“后”学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文主义等等不断翻新出奇,纯粹鉴赏性的批评却因不具备“现代性”而难得专业学者推重。
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木心(1927-2011)的《文学回忆录》(上、下册,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脱颖而出,可以说在当代重新恢复了印象批评的名誉,堪称中西文学批评的一部“奇书”。正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人眼中的历史”一样,在《文学回忆录》中,木心自由出入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之间,让自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依靠个人颖悟大胆评点论断作家作品,其实抒写了“一个人眼中的文学史”。他接续了古今中外艺术型批评家(如艾略特、米沃什、昆德拉、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所树立的伟大传统,把批评建立在对文本真切精妙的感受和独特传神的表达上,其批评文字充满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从主体精神、话语方式、批评过程、价值定位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视作印象主义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回音。
一、批评主体:唯美主义的精神后裔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受到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柏格森等引领的哲学思潮影响,实现了非理性转向,开始重视创作和阅读中的直觉与非理性,欲望与潜意识,探讨审美直觉、生命冲动对作品形成的影响。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永恒变动的“印象”之中,没有可以绝对把握的客观现实。世间一切真实不过是一种感觉,人们只能相对地把握客观世界的某一瞬间。这一瞬间的“真实”是人的主观感觉和印象,一切推理无非是感觉的作用。因此艺术批评总是依赖于个人的趣味和感觉。
如果说“知人论世”的实证批评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批评的翻版,那么印象批评则是批评中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合流。唯美主义者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印象主义批评则主张“为批评而批评”。他们重视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发挥,把创作和批评一视同仁,认为“最高之批评,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木心在青年时代在“上海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追随刘海粟、林风眠等人学习中西绘画,上个世纪30、40年代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成长氛围对于日后他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回忆录》对中西文学的品评建立在个人感觉印象的基础上,其中体现出来的总体价值观也是唯美主义的。
木心倾心赞美的是一种诗意的、浪漫的、唯美的人生。在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谱系中,他认同讲求秩序的日神精神,更心仪迷狂的酒神精神。他赞美所有个体情调、生命意志,而对西方文化视为正统的基督教不以为然。他认为艺术精神是怀疑的、异端的、个体的,而宗教精神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的、集体的,两者正相背离。欧洲两千年艺术精华,都是表面基督教,内在核心却是异端精神。在他看来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骨子里都是异教的。他对西方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和兰波非常赞赏。他认为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是像尼采一样,在重估一切价值,因此王尔德彻底反功利,反虚伪道德。他喜欢尼采、王尔德和兰波,赞赏拜伦和雪莱;作为庄子和尼采的爱好者,木心的文学批评代表了真正的艺术精神和纯粹的文学趣味。
在中国思想文化中,木心喜欢老庄和魏晋风流,不看好孔孟儒家思想。木心认为中国杰出艺术家如屈原、苏轼、陶渊明,也和他们的西方同道一样,都是中国式日常生活的宗教——孔孟之道的异教徒。他常把来自不同文明的作者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眼中:
歌德是伟人,四平八稳的——伟人是庸人的最高体现。而拜伦是英雄,英雄必有一面特别超凡,始终不太平的。英雄和伟人是不同的,嵇康是英雄,而孔子是伟人。
无疑,相较歌德和孔子,他更欣赏拜伦和嵇康。顺着木心的思路不难看出,嵇康和拜伦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更具有天然的浪漫主义血液,具有敢于创造也敢于破坏的精神。嵇康和拜伦的人生不圆滑也不理智,而是充满了血性和激情,充满了悲剧崇高的美。木心仰慕这样个人主义的悲剧人生,钦羡这些“为艺术而艺术”、乃至殒身不恤的人物。
木心认为文学不是描写真实,而是创造真实,艺术的美高于生活的美。在他眼中近代逼真的文学代替了古代幻想的文学,并非完全是个进步。木心推崇的文学能将真实写到奇异的程度。与基督徒向往的神性相比,木心更着迷于对人性的发现:
我憎恶人类,但迷恋人性的深度。已知的人性,已够我惊叹,未知的人性,更令我探索,你们都是我探索的对象——别害怕,我超乎善恶。
他赞美激情,从不信神,读者在他身上无需再苛求还能找到有如高山和深渊一样的道德感,艺术在他心中充当了上帝的角色,他认为上帝是立体的艺术家,而艺术家是平面的上帝。艺术尽管不可能全息、全范围地表现生活,但是艺术是全部的生活感觉和经验,而经验是由各种印象构成的,印象的深浅决定小说的强弱。艺术家应该是真正的智者,对一切都抱着惊奇的态度,放纵自己的好奇心,尽情享受官能之乐,豁达大度,明哲而又痴心,对世间万物都有兴趣,却不迷恋。
木心的唯美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从不追随任何政治潮流。他总是人生的旁观者,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也是世界的边缘人,从不取媚于主流,而有自己独立的追求,那就是艺术。他对普希金关心和参与政治不以为然,坦言自己若是活在五四或者抗日时期,不会去写反帝反封建的诗。在谈到帕斯捷尔纳克、高尔基、索尔仁尼琴、肖霍洛夫时,他说“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都是写‘人性’,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的好朋友,他就是不服从‘党性’”。他认为诗人关心政治,写政治诗,事过境迁,终究难以留下来。现代的文学家应该聪明冷静。就像:
索尔仁尼琴和昆德拉,都是旁观祖国的大风大浪,一个在美,一个在法,很安静。这两位还不是灯塔型的人物,却能像灯塔一样,不动。
我不会弄“同胞们杀鬼子”这种调子,笔和小提琴一样,不能拿小提琴杀敌。
写永恒的诗,把作品留在人间,才是一个艺术家能为世界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木心一生经历坎坷,既没有被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戾气激怒,也没有被文革的人性深渊压弯脊梁。在文革那些困厄的岁月里,他也曾被捕入狱过18个月,在狱中,他自己画了钢琴的黑白键,弹奏钢琴曲。可以说对艺术的痴迷和热爱伴随他的一生,这种始终不渝的热爱使他足以抵御那些暗夜的寒冷。他总是自觉地与自己的时代保持距离,在精神上他是五四文化的“遗腹子”,雪藏了30年,一直到1980年代移居海外,他书写的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才破土而出,先是在台湾及海外出版,后来又墙外开花墙内香,经他的弟子陈丹青大力引介到中国大陆。精神上自由独立的品格,使得木心的书写习惯和阅读经验丝毫不受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和1979年以后的“新文艺腔”的影响,他的语言既有海外华人的现代气息,又有民国遗老厚重的传统文化味道。
作为一个精神气质上的唯美主义者,一位文学上的鲁滨逊,他既是独立的,又是漂泊的。民国时的旧中国,建国后的上海,1980-1990年代的美国,他的写作既“在地的”扎根于汉语口语,又流浪地带着天涯游子特有的反讽和感伤。他赞美张爱玲是一位“飘零的隐士”,其实这个称谓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完全适合。他曾经不无自嘲地说,
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
在他看来,现实中的欲望就像一座迷楼,而艺术家要飞出迷楼,他把尼采、托尔斯泰和拜伦,都看作是靠艺术的翅膀飞出欲望迷楼的伊卡洛斯。
他认为艺术和人生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把艺术、哲学、宗教,都看成是人类的自恋,认为应该适当与之保存距离,才有寻得真、善、美的可能。在西方的那耳喀索斯神话里,那耳喀索斯(narcissism)就是人的自我,他在时间的泉水里发现了自己的倒影。而这倒影,就是艺术。木心把艺术看作是超自我的自我。他认为:
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关照,你要沾惹它,它便消失了,你静着不动,它又显现。
整个人类文化就是自恋的文化,女人爱照镜子,男子、士兵、无产阶级,也爱照镜。那耳喀索斯的神话,象征艺术和人生的距离。现实主义取消距离,水即乱。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宿命。在他看来唯美主义者挑起的“为人生”和“为艺术”之争并无必要,一个文学家,只要把人生看透了,艺术成熟了,就不再纠结于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而是处处都是人生,都是艺术。也就是说人生和艺术,既要捏得拢,又要分得开。能做到这样,人生和艺术就都成熟了。
由此可见,木心是一个性情中人,真正的精神贵族。根据陈丹青先生的回忆,旅美期间在他周围俨然形成一个“布鲁姆斯伯里”式的艺术家精英团体。但是,他的批评趣味绝不保守,他将文学批评看成是一种艺术而非道德批评,他在精神上并非属于F.R·利维斯、T.S·艾略特以来“新批评”派代表的西方正统学院批评传统,毋宁说他的信手拈来、随意点染,“以己解庄”的批评文字,更接近《西方正典》的作者、富有浪漫精神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然而让他的批评趣味没有汇入浪漫主义批评而更接近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是,他并不喜欢过度的夸张和失控的梦境,他认为梦和艺术完全是两回事,“梦是失控的,不自主的;艺术是控制的,自主的”,在他看来,米开朗基罗的变形是伟大,威廉·布莱克的梦境抒写却走向浮夸,他既能欣赏尼采和瓦格纳将艺术推到极端的美,也能欣赏莫里哀和拉辛作品古典风格的宽容大度。总体而言,他更倾向从形式完美而非道德情感的角度去评价音乐、诗歌、绘画和小说,钟爱那些形相和灵智相结合的艺术作品。
二、话语方式:点评式的古典感兴批评
有学者认为,木心的这些批评文字,大多是对先贤哲人的转述和零星点评,是一些随想录式的生命感悟和佳言妙句的“串烧”,不成系统,虽然有可读性,在普通读者中有市场,但很难满足对文学阅读稍高的读者需求。我认为这种评价忽略了木心身上的古典因子。他成长于民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尤其深好老庄思想。他的只言片语式点评恰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感兴批评的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印象主义的批评理论,和中国感兴式审美批评在理论主旨上异曲同工。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金圣叹的《水浒》评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是这种点评式鉴赏批评的代表作。古典感兴批评大多是随笔的形式,集作、赏、评于一身,批评话语具有浓郁的艺术性,韵散相间,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批评和创作合二为一,用语大多玄妙,往往以意会体悟,以形象说诗,给人以暗示,资人以联想。
木心的批评正继承了中国古典审美批评的流风余韵。重视对文本的直觉和妙悟,重视批评语言的精妙和灵性。他一定不屑那些沉着、滞重的学术批评,而是甘心以中国古人为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追求“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让批评文本像艺术品,自成“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淡泊之美。比如他谈到自己喜欢不登大雅之堂的“三言”“二拍”,说这些短篇小说属于民间社会,里面自有民间的活气,可见那时代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调。自己有耐心看这类书,好比吃带壳的花生、毛豆,吃田螺、螃蟹,品尝大地的滋味、河泊的滋味。
木心认为,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可进可退,自由出入于中西古今之间,把这些中西的人文精神,都汇聚成自己的精神。他谈到:
中国和世界不同步,中国不会浪漫、唯美,给唐宋人浪漫唯美去了。写实倒是有过了,但鲁迅、矛盾、巴金,才不如陀氏、托氏高。
中国的共同点是大团圆,东方没有悲剧,东方人比较弱。西方人强,斗争,牺牲。东方人以和为贵,妥协是上策。
这样的点评非常个人化,随意点染,仿佛无心,又很到位。精彩之处如暗夜星子、溪涧山花,抬头可见,俯身可拾,与他一路同行的文学读者,可在这样的字里行间别有收获。
他的语言承接了“五四”以前生动睿智的古白话文传统,正如陈丹青所言,“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极少的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就像司空图和严羽这些古典鉴赏批评家一样,木心的品评全凭印象感悟。那些点评文字总是电光石火,三言两语,但往往能照亮读者,让人会心一笑。比如他把荷马史诗比作人类的童年:
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可列如下四个特点: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他的概括有直逼古希腊文学本质的精炼和凝粹。
中国古典的感兴式批评与西方印象批评都具有直观性、鉴赏性,但是它只是在比较的意义上具有印象批评的某些特征,因为它的批评术语没有严密的逻辑性,而是直觉把握批评对象的艺术特征和整体风貌。木心经常只是谈到某些作家作品给予他的笼统印象,但总能恰到好处,意在言外。他说:
嵇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轼、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来,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读木心的批评文字,就像走入司空图《诗品》中那种冲淡疏离、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命意境,“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文字的背后是思想,木心的点评论断并非机械借用别人的观点,而是将所有这些中西文学精神在自己内心融会贯通。也许他由衷向往唐宋古人宁静致远的审美生活方式,也许中国佛道家精神中的超然空灵已然在他内心长成一棵遗世独立的大树,他才能将这样的话语方式运用到极致。
三、批评过程:灵魂在杰作间的冒险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健吾追随法郎士等人提倡西方印象主义,也继承中国古典感兴式审美批评传统,强调批评中创造的心灵对文本的鉴赏和体味,主张批评是一种“自我发现”。法朗士很坦白地说“批评家应该声明:各位先生,我将借着莎士比亚、借着莱辛来谈论我自己”。他认为“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李健吾反感道德说教和政治审判式的批评,在当时党派之争的夹缝中,他试图尊重批评的个性,寻求一种“自由的批评”。在李健吾看来,“一个批评家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指,他不仅仅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的隐秘的关系”。批评家永远无法摆脱个性的影响去纯客观地把握对象,批评家对作家与作品进行批评的依据,必须是人生,必须以人生印证人生,以人性衡量人性。
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李广田等其他“京派”文人,在批评主张和实践上也受到印象主义的影响,提倡主观的、感性的、鉴赏式的批评,一时使得印象批评在中国蔚然成风。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涌入中国,文人批评家一时眼花缭乱,争相试用后殖民、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剖析文学,印象批评则成为批评不够学术、不够专业的代名词。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这些过于重视理论工具、轻视文本细读的流俗观念,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个性批评的魅力,让批评重新变成灵魂在杰作间的冒险。
首先,木心推崇批评主体的创造性与个性色彩,把批评视为一种自我表现的艺术,把批评家的自我作为批评的标准。他把文学史和美术史看作不过是天才的传记,他重视批评的主观性,总能力排众议,独立中流。比如,他认为中国中世纪的剧作家,没有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伦理。艺术家的永久过程,是对人性深度呈现的过程。他推崇莎士比亚戏剧,就是因为莎士比亚从不告诉我们答案,他只是呈现,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让人看出许多东西,这就是艺术的深度。由此可见,木心的批评观和李健吾当年的追求深为暗合。
其次,木心也强调批评过程中的印象和直觉。在谈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时,他充分运用艺术感受和统觉能力。他喜欢《封神榜》中的哪咤,认为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这些印象都概括得极为精准,凭直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谈红楼梦,也是凭着自己的阅读印象,认为《红楼梦》:
整体控制伟大,绝对冷酷。当死者死,当病者病,当侮者侮。妙玉被奸,残忍。黛玉最后为老母所厌,残忍。他一点不可怜书中人,始终坚持反功利,反道德,以宝玉黛玉来反。
这里的“残忍”、“冷酷”等都是作者读作品的直观感受,木心用自己锐利直捷的表达,激活了读者心中的这些感受,让读者引起共鸣。这和鲁迅当年对红楼梦的点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相映成趣。
再次,《文学回忆录》中的批评文字非常重视语言的审美特性。木心的文学评论语言,充满诗意,玲珑剔透,不黏不滞,脱口而出,随意赋形,如行云流水,也充满了美感和悲悯,让人读后见心动容。在谈到阿拉伯文学时,木心写到:
凡是纯真的悲哀者,我都尊敬。人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就是艺术家。悲观,是一种远见。他把悲剧精神看作是西方文化的重心,把悲观主义看成是东方文化的中心;他认为真正的悲观,不是逃避,沉沦,而是积极的行动,创造,追求属于自己的有声有色、敢爱敢恨、可歌可泣的人生。只有经历过人生的跌宕,有悲悯的情怀和透彻的智慧,才能对中西戏剧精神有如此深入浅出的理解。
最后,木心的批评也注重批评印象的比较与辨析。他自觉运用中西文化的对比,或者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不同个性作家的对比。比如当他谈到莎士比亚时,不忘和中国的戏剧相比较。他认为:
莎士比亚,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元曲,放之四海而不准。中国戏剧的唱词和念白,互不协调。唱有诗意,念则俗意。莎士比亚的唱词、念白,通体是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的对话,是世界上最美的情诗,全世界听得懂。
再如,他谈到《红楼梦》和《金瓶梅》:
曹雪芹的意淫还是唯美的、诗的,慢条斯理,回肠荡气。《金瓶梅》是肉淫,是变态的、耽溺的、不顾死活。分而论之,《红楼梦》是浪漫的,《金瓶梅》是现代的。
木心认为读《金瓶梅》要比读《红楼梦》仔细,因为《红楼梦》明朗,《金瓶梅》幽暗,一如托尔斯泰明朗,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一样。他以自己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批评洞见,能将古今中外这些文学经典中孕育的人文精神异趣沟通,才有这样精到深刻的比较。
四、价值定位:文学是一场盛大的回忆
木心把文学看成是一场盛大的回忆,他相信柏拉图的话,“艺术是前世的回忆”,是沉睡因素的唤醒,艺术要从心中去寻找。而对回忆来说,正如史铁生所言,“记忆是一个牢笼,而印象是牢笼外无限的天空”。木心的批评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质的表述,是用一个文学印象去阐释与说明另一个文学印象。他一个人独自面对着往古来今那些文学精品,如遇知音,如逢花开,信手拈来,性之所至,妙语如珠。他以直觉的方式进入作品,以瞬间“妙悟”、“体验”和“灵感”,凝定成批评的神来之笔。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一部分批评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印象批评,他们强调批评的主体意识,重视批评的独立品格,敢于书写独有的阅读印象。比如吴亮在《文学的选择》等批评文本中对当代名家余华、莫言、韩少功、张承志的点评,就是这种探索的代表之一。无疑,在当今的文学批评版图中,美丽而又睿智、偏见与洞见并存的印象批评,正得到越来越多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像木心这样从头到尾、有始有终,通篇以印象批评纵论中西文学史的大部头著作,可谓凤毛麟角。
自古及今,中规中矩、画地为牢的文学史数不胜数,文学欣赏中的个人颖悟却很难得;单就某一领域而言,木心也许不敌专业学者精深,但其可贵在于,以一个人面对古往来今众多流派、众多作品,所显示出的圆融、通透和识见,他的批评代表了纯粹的文学品味。从先秦诸子到希腊哲人,从但丁到尼采,木心选取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方式予以观照,而不是学者式的焦点透视。他说,哲学与思想只能作为文学的遥远的背景,推近到纸端,文学会烧焦、冒烟的……虽然木心反对“主义”。认为“文学,哲学,一入主义,便无足观”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颇具才力的批评,恰恰是接续了李健吾以来中断了的印象主义批评传统,他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情,以独特的审美眼光,为我们研究中西文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木心曾称自己“是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大雪纷飞是他内心的狂舞,而“黑暗”,不仅指他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更有那种经历人生千难万险“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孤独。他一生经历大风大浪,晚年因弟子的推崇得以被国人阅读。仿佛早预见到了自己在本土的接受会出现诸如“老清新”“格调不高”“文人气”“才子气”之类的曲解与苛责,在对老子的评述中,他曾经举重若轻地这样写道:
我爱老子,但我不悲伤,不绝望,不唱反调,不骂,不出鬼主意——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我不抱希望,所以不绝望;我自寻路,一个人走,所以不反激。我也有脾气要发,但说说俏皮话。诚然,所有自命很高的艺术家都希望被世人理解,但没有谁会奢求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不管是对于现当代文学过于感时忧国的沉重传统,还是对于新旧中国混杂着政治“左右之争”太多激进戾气的批评,木心文字的温婉深致、悲哀洒脱都显得像个异数。陈丹青曾经提到:“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应该怎样看待木心先生?他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中是怎样一种位置?这种位置,对我们,对文学,意味着什么?”单就《文学回忆录》来说,他的点评对文学批评——尤其是当代印象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木心之被当代发现是读者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无所谓吹捧,只有是否知音的问题;也谈不上被高估,因为至今在主流文学界,他的价值还没有得到正当评价。
〔1〕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收入《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转引自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张柠.木心:被高估的文学大师[EB/OL].羊城晚报,2013-03-11.http://book.sina.com.cn/news/a/2013-03-11/1046433156.shtml.
〔4〕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陈丹青.木心,一个无解的谜〔N〕.中华读书报,2006-1-160.
〔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美)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M〕.颜元叔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8〕李健吾.自我与风格.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9〕刘希渭.咀华集〔M〕.北京: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10〕史铁生等.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哲人〔J〕.黄河文学,2010(7).
〔11〕吴亮.1988年吴亮如是说:余华、莫言、韩少功、张承志.[EB/OL].“小众菜园”网站.
〔12〕陈丹青.想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EB/OL].凤凰《时代访》陈丹青2013年2月20日,http://blog.renren.com/share/330174065/1604644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