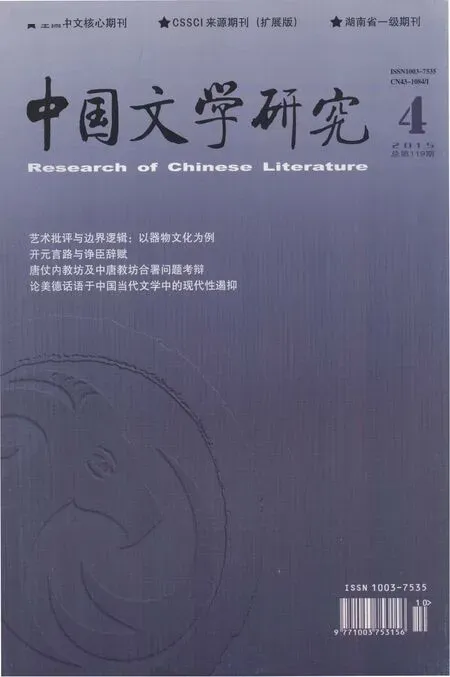艺术批评与边界逻辑:以器物文化为例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9)
“界限”意味边界轮廓清晰,即艺术主权独立,也意味边界的扩张与划分。对于艺术批评而言,“划界”与“跨界”是常有的事。“划界”是为了清晰艺术个性特征;“跨界”是为了拓展艺术的批评空间。前者是为了艺术自足性得以保障,后者是为了艺术自我与他者关系性得以显露。因此,当艺术遭遇到“我们”的时候,它必然“相遇”到各种知识之“界”。这样,“跨界书写”或“跨界批评”也必定成为艺术批评的工作方式。但在传统艺术批评史上,“风格”“形式”“美学”等批评范式一直被奉为圭臬,显然它们对艺术批评的发展是不适合的,尤其这些常规艺术批评范式在普适性上更值得怀疑。
一、诊断三种常规批评范式
1. 风格
“风格”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艺术范式,它能以最宽广视野和位移能力超越历史空间,去关注时间文化的潮起潮落。忠实于变化的“风格老臣”与它内在的相对稳定性的“形式君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立场。当器物遭遇到“我们”的时候,风格批评的“对立性偏好”容易被我们静止化。对此,风格批评的“诊断性思维”是有用的:
首先,“风格是技术的”。每种器物都具有技术性的,技术能以压倒性能力改变器物的风格,并使得风格带上时代的、地域的文化调性。风格的“技术第一原理”能适应于各种器物风格的变迁叙事。譬如在西汉中后期,人们对波斯引进的植物色彩加工技术以及本土装饰技术的改进,漆器的“错彩镂金”风格在技术庇护下显得格外耀眼。其次,“风格是有故乡的”。在形式、秉性、情感等维度上,风格的故乡性是明显的。“楚风”“秦风”“蜀风”“滇风”……它们在地缘意义及地域品质上具有很大差别;“中国风”“美式”“欧式”……它们在国别地缘意义及空间视象也是不拘一格的。再次,“风格是局部的,也是结构的”。风格秉性很容易表现在局部差别性上,即便是细微的,也是区分风格的重要差别点。最后,“风格不是精神隐喻”。器物的风格本质是自然的,工匠们的心灵活动也是自然的,而且是常年累月的自然形成。换言之,风格总是要走向现实的、社会的,并且永远是活着的,它与一般性隐喻修辞是格格不入的。
简言之,风格的外衣口袋里有技术、故乡、局部以及非隐喻等四件东西。显然,传统艺术的风格批评与器物文化批评有显著的差异,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
2. 形式
器物生命是很特殊的,它并不完全是工匠赋予的,而是由器物的材料及其技术本身创作的。如在漆艺行业,漆画并非完全产生于艺术家的构思。“人画一半,天画一半”。这是因为漆画的材料是独特的,尤其是大漆的黏性,不好控制,一旦落笔,往往只能“随性”,不大容易轻易改动。因此,漆纹饰图案或漆画是“随缘”的,并不与艺术家的构想准确对应。那么,器物文化批评语言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器物本身的形式词汇了。
对器物而言,形式的生命是流动的。拿瓷器来说,从揉坯、拉坯,到立坯、利坯;从荡浆、摧浆到施绘、上浆;再到进窑烧制,在这系列技术性过程中,瓷器生命是流动的,其形式甚或是多变的,其中“窑变”就是瓷器形式流动性的重要标志。另外,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各种器物的流通直接启示我们,器物的生命是流动的。被输出的中国古代器物不仅是艺术品的输出,还是一种文化与美的输出。器物文化在流动中彰显出它的世界性叙事特质,更显示出文化的无国界性。在异国他乡,器物文化坚守着国别性的理想,并非赋予“他域风格”,从而不但延续了器物的原来生命,更降生许多新的生命。器物形式的生命一旦被图像、材料、色彩等激活后,它在流动中一旦耗尽它固有的生命能量,则走向衰老或死亡,被另一种风格国王所取代。
器物形式生命的特殊性决定了器物文化批评的特殊性,形式批评绝不是风格的外衣,常规纯艺术的形式批评与器物文化的形式批评显然不能等同视之。
3. 美学
器物文化是具体的文化,它通常存在于器物的形式、色彩、质料等具体的视觉元素里。这些元素呈现出来的文化与美是造物者“心理景观”的外显与传达。那么,当我们遭遇这些“心理景观”的时刻,我们便进入了“美学想象”的心理活动之中。
对器物“美学想象”的目的在于获取器物的文化与美,或者说,器物美的文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美学想象”是关联的。就文化模式的地域性而言,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对器物的“美学想象”模式是有差异的。欧洲文化决定欧洲人对器物的美学想象是基于人为核心、比例为测度的焦点化和谐审美。希腊人的陶器造型及其图案在神与人之间获得灵感,来展示自己身体的美与文化。罗马人制造的玻璃器皿上绘制的图案最能说明他们的美学想象。印度文化决定印度人对器物的美学想象是基于宗教为核心、以化身特性为空间视觉关系的宇宙化审美。相对于欧洲人,印度人对在器物造型与图案的装饰上更注重宗教性元素的使用,即便是用玉石制作花瓶,也会多用“莲花”状金丝镶嵌,以体现他们的对梵天主神的敬畏。伊斯兰文化的宇宙中心是真主,宇宙、人以及万物均是真主安拉的创造物。由于伊斯兰人对偶像崇拜的谨慎,他们在器物以及其他艺术中一般放弃了生物形态的表现,多半采用非写实的植物图案。中国文化的宇宙中心是天地,并不是以人或宗教为中心。因此,中国器物的造型和图案的美学想象是“天地之心”与“自然之和”,并在太极、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中演绎对器物图像的哲学把握,在有与无、虚与实、少与满中实现对宇宙天地的美学想象。不同文化模式下的器物文化与美是独特的,有地域性的或国别性的文化特色是明显的。因此,任何偏离国别性的艺术文化史批评都将是一种主观化美学臆测行为。
很明显,器物的美学想象是基于文化模式下才能够实施的一种工作方式。器物文化批评必然借助“外在形式”与“内在生命”的完美整合或和谐契合,才能获得对器物美学想象的“入场券”。
二、开放边界:艺术批评发展的选择
以上三类器物批评的“问题话域”,迫使我们陷入深刻的批评困境之中。很明显,艺术批评的主要困境在于旧范式危机之时,没有新范式的崛起。但“范式从不暴死,它像动物那样,首先要经历一个逐渐退化和衰落的阶段。在范式上出现明显的裂痕时,没必要急着把它扔掉,而是首先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修好”。换言之,传统艺术批评范式不会自动死亡,而新范式又必须要崛起。为此,艺术批评的边界当以开放姿态接纳诸如角色、互动、情境、界限等批评范式的新生,以利于“修好”常规艺术批评范式的“裂痕”,从而拓宽艺术批评的话语疆域,使之与常规批评范式相互补。
1. 角色
在边界开放视野下,戏剧舞台“角色理论”与器物“角色分析”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作为角色化的器物及其文化批评,它有多种表现通道。譬如角色模拟、角色镜像、角色创造(或角色冲突)、角色扮演(或扮演角色)、角色仪式(或角色行为)等。下面以中国古代墓葬内的漆器角色化为例,从而分析它们的艺术表现通道。
在角色模拟层面,墓葬内常有舞乐俑、仪仗俑、人(奴仆)俑、士兵俑等墓葬偶人及其陪葬车马、庖厨、家畜等模型,还有各种镇墓兽之神物等。这些角色或成组的俑是象征殉葬奴隶的模拟品。从角色认知角度看,被赋予角色化的墓俑至少有模拟性、隐喻性、家庭化及社会化的功能作用。就角色模拟而言,它首遭孔子的批判。《孟子·梁惠王》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郑玄注释“始作俑”,即“与生人相对偶,有似于人。”俑是奴隶社会活人殉葬习俗的一种替代品,这是封建社会人性发展的一个文化标志。孔子之所以反对,是以为它“殆于用人乎哉”,这是不“仁”的表现。在隐喻方面,墓俑不仅能反映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水平,还能隐喻封建社会的各种文化,包括民族宗教、生活习俗、政治外交、民族性格等。譬如秦代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场景,地下静止的墓葬被它们激活,并被“告知”秦兵仪仗、军事制度、士兵风貌以及当时的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军事化角色认知。在家庭化及社会化方面,墓葬内多有家庭奴仆、侍卫、歌女、厨具、家畜、厨灶等具有家庭化角色替代物,这种墓俑的生活时间被移置在这样的空间里,明显是家居化角色模拟它们具有的生活感、现场感;这些墓俑也明显有“时间意义”“行动意义”“位置意义”“生命延续意义”“史境意义”等期待系统。
在角色镜像层面,器物角色是一种自我镜像的行为人或思想物。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Lacan Jacaueo,1901-1981)从儿童照镜子出发,阐释了“镜像体验”视野下的无意识图像语言的生成机制,并提出“语言镜像理论”的三个阶段: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被角色化的墓葬俑也近似拉康的镜像三个阶段或领域。因为,俑或群俑的文化象征界应当是现实界与“始作俑”艺术家之想象界的共同产物。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ooley)进一步发挥与继承了拉康的“镜像体验理论”,并在1902 年根据“自我”与“他我”的互动事实提出了“镜像自我(Looking-glass self)”或“镜中自我理论”。在库利看来,人的行为与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是通过与他人社会互动形成的。根据库利“镜像自我”理论,墓葬内器物应该处在“群物”之中的“镜中物”或“社会反射的器物”,作为“镜中物”器物,它是反射社会的产物。在批评墓葬内器物文化的时候,器物本身既是器物自我镜子,又是社会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镜子。常规意义上的器物风格、形式及美学的批评方法,往往只看到器物自我镜子,而看不到社会文化镜子与社会关系镜子,从而造成“见物不见人”的批评方法论之偏颇。
在角色创造层面,“角色冲突”是要被引入的。角色创造是基于角色冲突为条件的。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过木胎漆绘引魂升天的羽人,南朝壁画羽人画像在江苏、河南、湖北、四川等多地出现。在《山海经》中,被认为是汉族神话中不死飞仙称为“羽民”。道教将道士称作羽化升天的“羽士”。羽人、羽民和羽士的共同特征是“身生羽翼,变化飞行”,与不死同义。墓葬内羽人角色创造与出现是古人对界限性角色冲突做出的反映,它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生与死的角色冲突;二是天与人的角色冲突;三是有限之身与无限之能的角色冲突。古人对死亡的恐惧,对长生不老的追求,羽人是模糊生死的最有效途径;同时,对天的敬畏,对人生命的敬仰,羽人成为他们“天人合一”的最佳载体;另外,古人对自我身体的有限认识以及梦想升天的“技术无力”,进而用“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的角色创造,这就解决了有限之身与无限之能的角色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因为有生与死、天与人、有与无的界限冲突,因此,古人采取语图叙事或器物创造进行突围,从而消解了以上三种因界限而导致的角色冲突。
在角色扮演层面,墓葬内器物有角色扮演和扮演角色之分。角色扮演指生活中实际角色(如祭器或生器),扮演角色指向暂时性的替代角色(如明器或羽人)。角色扮演(Role-playing)是一种仪式行为,墓葬内的角色仪式是表明接纳与排斥的行为方式。譬如生器角色扮演是对生命或生活延续的接纳,从人到羽人是对天人分离的排斥;俑是角色营构或扮演角色的产物,也是对生的接纳与对死的排斥。因此,扮演是一种自我思想与创造的仪式行为,具有心理引导和思想意向的功能,并能获得或分享感知经验的效果。同时,扮演涉及到“化妆”和“服饰”及其道具问题,即角色装扮。因此,墓葬里各类语图叙事艺术诞生了。语图是构成角色仪式与情境的基本构件,也是复活与再现角色思想与情感的基本载体,被抽象化的语图为角色装扮提供思想形式与主观反映。为此,批评角色扮演,即要阐释语图的期望系统及其相应的扮演行为,将语图的抽象化复归或转化为思想的客观化,这种思维与批评的方法称为“角色转换”。
在角色仪式层面,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等逐渐将“潜在”情感仪式分析延伸到“功能”仪式领域。这为我们解读墓葬内各种角色仪式提供一种新思维:潜在的角色仪式均引向角色功能仪式,即角色仪式是一种功能性系统;它也为我们编织了角色所指向宗教、政治、经济、外交、习俗、审美等多向度反映文化的互动性功能。换言之,角色仪式是一个互动仪式,这样为我们研究角色及其背后的文化“互动”找到切入口。在本质上,仪式是一种角色体验过程,当角色聚集到一个地点就开始了“相互关注/情感连带”的场景行为。
将戏剧艺术的角色理论引入器物文化批评,能将我们的研究从一般性的宏观反思引向更为具体的微观艺术问题,尤其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器物的形式或风格的机械分析中转移到更加广阔的艺术生产及其社会文化上来,它包括与器物相关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物质文化及其意识形态。
2. 互动
在社会学视野下,器物系统可被视为一个缩小的社会空间及其各成员互动关系的模式整体。用威廉·詹姆斯与查尔斯·霍顿·库利的话说,个体具有“自我”或“镜像自我”的心理互动能力,即通过自我或他者的互动体验中认知自我的“心智”能力。
器物是个体创造的“心智”产物。如墓葬内的生器是“自我”生活的对应物,神器是“镜像自我”的宗教文化物,明器是模糊生与死的“镜中我”之物。如此,我们可以按照墓葬内器物将“自我”进行分类,大致有生器自我、神器自我(祭器自我)和明器自我三种互动的关联主体。生器自我是自我日常生活的镜像,神器自我是自我宗教生活的镜像,明器自我是自我未来生活的镜像。生器是直接用原来日常生活器物作“功能性延续”。明器是用符号方式标识墓葬空间中的其他日常器物,这是一种替代性的与“想象性预演”性质的行为方式。神器既是自身“形象典型化”的产物,又是自身宗教文化典型化的产物。它既是生器生活功能的延续,又是通向宗教功能的发展。基于“功能性延续”“想象性预演”“形象典型化”之后,器物文化的生活性及其社会性特质便能跃然纸上。
第一,在现象学那里,器物文化的生活性与社会性就是内在心理意向的产物。譬如墓葬内的生器指向“生”,明器指向“死”,祭器指向“神”。如此,生与神的互动、生与死的互换,死与神的互通就构成了一个微观互动的墓葬系统。作为功能性延续的生器,它的心理指向——生是可以延续到死的;作为想象性预演的明器,它的心理指向——死是生的另一种延续;作为形象典型化的神器,它的心理指向——神可以操持生死的。可见。器物的形象学文化偏向为解读创造器物的个体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线索。
第二,在符号学视野,器物作为符号的存在,它必然指向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互动模式”。1937 年,美国心理学家布鲁默在他的老师米德“互动论”思想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符号互动论”。在布鲁默看来,“符号”总是有指向象征事物的文化偏向。他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事物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相对于个体自我的一种象征意义。那么,对于墓葬而言,它内部的漆器、陶器、青铜器以及其他器具在微观互动中必然形成各自身份象征,或者在舞乐俑、兵马俑、乐器、兵器、漆奁、漆盒、漆冠等互动中,它们被赋予了某种文化的、社会的及宗教的客观意义。因此,在符号互动论看来,器物本身是不存在客观意义的,只有它们在互动中才被赋予特定意义的。
第三,在文化哲学视角下,器物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功能性延续”“想象性预演”“形象典型化”等的衍生物。因为,器物不仅是生活的伴侣,还是社会生产力及其审美符号的标志。石器、青铜器与铁器不仅是整个一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物,还是一代人的文化信仰的集体性符号。这些符号被阐释以及未被阐释的文化哲学指向了我们对这“一代人”或“整个时代”的认知与理解。抑或说,石器、青铜器与铁器等符号能言说其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它们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以上三种器物解读的开放视野,可以称之为“互动现象学”(意向的)、“互动符号学”(象征的)与“互动哲学”(语言的)。它们共同的立场是器物文化是“互动”的,器物自身的客观意义是在互动中被赋予的。它们的差异在于,“互动现象学”是基于心理指向的互动;“互动符号学”是基于个体象征指向的互动;“互动哲学”是基于文化符号指向的互动。因此,器物文化的互动理论是以“关系”为核心逻辑运转的。具体而言,“互动现象学”的关系核心组合是现象与本质,“互动符号学”的关系核心组合是主体与客体,“互动哲学”的关系核心组合是符号与语言。
“器物互动论”是鄙视“形式论”或“风格论”的,因为,后者所关注的文化是相对孤立的,只专注于器物本身的纹样、肌理、造型、胎质及其材料等视觉元素。器物互动论的核心问题是提倡一种分析哲学式的“家族相似”,即互动中的器物具有某种文化性的家族相似性。在阐释中,我们发现,器物互动论并非是以器物个体为出发点,而是以器物与器物之间的关系为研究中心,在关系互动中寻找器物文化的家族共性,并在器物的“功能性延续”“想象性预演”“形象典型化”等维度里探寻器物的图像与语境,从而实现器物文化的整体批评。
简言之,器物“互动”即器物“相遇”——它是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各种相遇器物之类型,也即审美现象的类型学展开。在各种器物审美现象中,器物作为对象结构与主体的意象性结构是同构的、互动的和同一的。因为,作为符号的器物所呈现出来的语言是我们认识器物的知识形态;作为主观思想抽象化的器物总是有客观形式与反映现象的期待系统。
3. 情境
在20 世纪70 年代,一批剑桥学者与伊恩·霍德(Ian Hodder)及学生试图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阐释社会制度及思想。他们的思想主要受惠于马克思、福斯太耳·库朗热、涂尔干和J.D.克拉克的社会学整体分析理论,还来自功能主义的“情境功能”分析理论,如埃文斯-普理查德和迈耶·福斯特等马林洛夫斯基的追随者基于部分非洲部落社群的有机整体情境系统分析。霍德认为,我们“必须注意相关性(Context)或整体背景的研究,相关性是考古学科的中心特征,一件处于不同背景中的器物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在此,霍德首次提出“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或译为“情境考古学”。霍德、福伦儒等学者试图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它背后的文化情境社会,并一致认为“情境”是弥合考古学与器物之间的关键性纽带。
器物的相关性或整体背景是情境论的核心批评指向,它与器物的基体、时间和空间相关。器物的基体是器物物质构成的基本相关性材料、装饰以及数量等可视性元素;时间是器物情境的历史性维度;空间是器物情境的特定位置及其环境。普希金曾经说,“在假定情境中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真”是戏剧作家创作的基本要求。器物情境首先是被假定的或设定的,即所谓的“规定情境”,它是个体身份与等级及其情趣决定的;器物情境也是“热情的真实”,即表现在对原生活的“模拟情境”,它受事实社会的时空性差异而定;器物更是情感的逼真呈现,即所谓的“意向情境”,它已然是一种社会知识状态——与情感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逼真意向性知识。
器物的“规定情境”是制度文化的直接呈现;“模拟情境”是生活文化的替代性复原;“意向情境”是一种朝向器物意向性的社会知识形态。因此,制度、生活和社会构成了器物的完整世界情境。当我们进入这样的“情境”,设身处境的体验或批评,这样的批评就能比较客观地复原器物的本来情境。换言之,“情境”是器物艺术的本真所在,抑或说,器物文化批评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情境”。
三、界限:艺术批评的边界逻辑
当角色、互动、情境等新艺术批评“名词”的入场,它们作为“新移民”便进入艺术批评的边界疆域。为此,我们要引入一个“移民活动”的概念,以期分析界限或边界的逻辑。法国学者卡特琳娜·维托尔·德文登(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在《国家边界的开放》中有关“移民活动”的描述:
移民活动长期以来在国际上被看做特例现象。然而今天,它参与着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建构,它在内部与外部、网络和领土之间引发了对国境线的干扰,并向国家主权发起了挑战。
除了移民活动引起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之外,国际移民活动还带进了一些新因素,如人权、环境、健康——在国家层面上,居然有这么多的流通因素。移民活动在国际体制和重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近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国家展开的国际体制建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日渐模糊,而其他决策中心日趋重要。如今,国家行为体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以移民活动为中心的一个全新的国际公共空间正在形成。移民活动也在国际秩序内重新引入了“漂流生活”的尺度,过去国际秩序是定居生活型,而如今的特征是“迁徙式流通”(Emmanuel Ma Mung),同时它还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在“国家理由”和人权之间,在“国民和世界公民”之间,播下了若干矛盾的种子(Stephen Castle)。
德文登对“移民活动”的建设性思考启发我们:艺术边界开放的关键词“移名”与国家边界开放的关键词“移民”,在很多“问题的向度”上具有相似性。或者说,国家移民活动与艺术边界“移名活动”在“特征”上存在有相互借鉴的共享区:
其一,国家边界移民活动“参与着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建构”。同样,艺术边界的“移名活动”也参与了门类艺术结构关系的建构,因为,被引入的“艺术移名”大大拓展了门类艺术的“行为空间”与“话语空间”。
其二,国家边界移民活动“引发了对国境线的干扰,并向国家主权发起了挑战”。与此相比,艺术边界的“移名活动”同样引发了对门类艺术边界线的侵扰,并向门类艺术的自足性主权发起了新的挑战,使“何谓艺术”变得更加模糊。
其三,“在国际体制和重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维度上的国家边界移民特征与艺术边界“移名”特征具有一致性。因为,“艺术移名”在门类艺术体制和重建中同样扮演不可小觑的角色。
其四,国家边界移民活动迫使“国家行为体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另外,“以移民活动为中心的一个全新的国际公共空间正在形成”。相比之下,20 世纪以来,“艺术移名”活动也迫使门类艺术中的许多概念重新界定,并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艺术公共空间。
其五,国家边界移民活动“在国际秩序内重新引入了‘漂流生活’的尺度”,“迁徙式流通”这种移民活动所带来的新尺度与流通方式在“艺术移名”中同样存在。“概念漂移”或“名词迁徙”是艺术界常有的事,我们无法阻止。
其六,国家边界移民活动“播下了若干矛盾的种子”,我们也不能否定“艺术移名”同样也播散了诸多与门类艺术互为矛盾的种子。当这些“矛盾”暂时还得不到缓解,它们正在朝向“庸俗”或“非常态”的方向发展。
以上诸现象与问题均关系到一个“边界线”的“界限”与“开放”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定义“界限”,将引发很多诸如体制再建构以及主权、角色、公共空间、生活尺度等“移民问题”。为此,我们要重点讨论艺术与国家在“界限”上的问题域。“界限”所涉及的语义学内涵应该有“边界”“分隔”“限度”等概念。器物文化的呈现及其批评均与这三个概念有关。
首先,“边界”不仅是空间及其内容有效性的标尺,也是任何文化自足的基本条件。论诗与画的边界是莱辛的重要工作,论仪式与非仪式的边界是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研究的核心。漆艺人、陶瓷人、竹艺人等群体的边界首先是清晰的,否者他们难以自成体系。
其次,“分隔”是划分空间的有效行为,也是厘清边界的必要尺度。在空间上,器物语图叙事的基本方式有在场叙事与不在场叙事。“在场”叙事,即语图所呈现的内容是“不隔”开的;反之,“不在场”叙事所呈现的内容是被“隔”开的。在场的语图只是“皮相之见”,而不在场的语图则是“思想内核”。或者说,“不隔”皮相是唤起“隔”的重要介质。不过,“不隔”与“隔”均是显露器物文化真理的可靠性标尺。
最后,“限度”是空间场域的范围规定量度,也是被“跨越”的对象。我们有对空间作限定性范围的控制欲,但同时也有试图突破空间限制的冲动。譬如建筑是我们划分自然空间场域为我所用的行为艺术,“天窗”或“门窗”是我们试图突破已有建筑空间而占有远方空间的企图。
对于研究者而言,“跨界思维”是必须的,也是常有的。否则,我们不能阐释器物文化知识的社会关联性。就器物文化的表现形态而言,器物关涉材料、色彩、装饰等多种知识领域。在材料层面,器物文化必然关涉材料物理学、材料化学等;在色彩层面,器物文化要关涉色彩心理学、色彩美学、色彩设计学等;在装饰层面,器物文化要涉及设计学、工程学、宗教学等。因此,当我们遭遇到器物文化批评的时候,我们必然“相遇”到各种知识之“界”。这样,“跨界书写”或“跨界批评”就必定成为我们的批评工具。
四、边界间性:艺术批评的内核
器物文化是人的文化,也是与他者共存的文化。那么,器物文化批评也应该是开放的,它必然摈弃抽象的,并要着力揭示人的文化以及“他力之美”。因为,器物文化不仅与他人或他者之间存有共享的开放间性区,还与批评者之间存在一个协同开放的间性区。抑或说,器物文化批评是介于主体与文本之间的“间性批评”。对于器物而言,它的“间性批评”主要指向“主体间性”,对于批评而言,器物文化的“间性批评”核心指向是“文本间性”。因此,“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共同建构器物的“文化间性”。就“主体间性”来说,器与人是不能分离的,器物文化在器与人的同一性与对话性中慢慢生成;就“文本间性”来说,作为文本的器物与审美主体之间的“视界交融”至关重要;就“文化间性”而言,器物文化是一种“他力之美”,它与其他文化之间是互动的,在情境中铸就属于自己的文化个性以及意义生成。
艺术批评的间性偏向,它决定了一种“间性批评”工作方式的降生。在时空上,间性批评已然超越时空,并在时间与空间交流中实现批评任务;在镜像上,间性批评是一种自我镜像的互文性写作,并体现着一种“他力之美”;在边界上,间性批评是一种开放性写作,在“移名潮”的建构与解体中批评文化史;在知识生产上,间性批评是一种知识创造,在知识边界的开放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进而为人类知识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
首先,间性批评是一种时空性写作。“时间”与“空间”在词源上均显示出它参与“间性批评”的偏向与倚重。因为,这两个词语构成均含有“间”字;另外,时间与空间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一对孪生兄妹。就器物文化批评而言,间性批评是在物质的时间与空间之间寻求交流,并形成稳定的“间性区域”的一种书写方法。
其次,间性批评是一种互文性写作。文化是网状的,并非是线性的。作为文本的器物文化必然是其他文化的一面镜子。因为,器物文本文化与其他文本文化之间具有“互文性”。也就是说,器物文化与其他文化是在互相接纳与吸收中形成各自的文化史。透过器物文化史的这面镜子,可以反射或映照出社会其他文化景观,这也是间性文本的互文性在叙事功能上的体现。
复次,间性批评是一种开放性写作。间性批评是一种发展性写作,文化发展是造成“学术移名”的根本原因。反之,“学术移名”又能推动文化发展。因此,间性批评必然要有边界开放的艺术政策,并以开放的心胸面对各类“学术移名”。尽管存在各种“移名问题”的争议与焦虑,但艺术边界的开放或“自由流通”已表现出在“间性区”的合作带来丰硕利益。
最后,间性批评是一种创造性写作。在“间性区”写作,那是一块“试验田”,被生产的知识已然是全新的。因为,它表现为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彼此尊重与吸纳,“自我”与“他者”均消失在“间性区”,即“物我两忘”的境地。所生产的知识是被创造的新知。
在传统批评器物批评上,“风格论”“形式论”“美学论”“知识论”等都不同程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在“间性批评”的视野下,器物不仅关乎器物本身,更关乎器物享用的人;器物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时间的与空间的;器物不是孤立的,也是流动的;器物不仅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为此,器物文化批评必须要实施三个重要转向:一是从“物本身”向“人本身”转向;二是从“静态物”向“动态物”转向;三是从“微/宏观”向“中观”转向。这三个器物文化批评的“转向”均指向“间性批评”。
五、初步结论
在诊断与阐释下,我们发现,用常规艺术批评范式分析器物文化极其容易走向形式论、机械论、玄学论等危险境地。为此,我们要开放艺术批评的“边界”,接纳角色、互动、情境以及界限等新“移名”,用“间性批评”书写艺术文化,它必将艺术文化批评带进知识合法化轨迹。因为,“间性批评”不仅尊重时间与空间的对话,还倚重他者文化,并以开放的立场实现知识的发展与创新。或者说,“间性批评”摒弃自我或他者的“宏大叙事”,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间性区域”实现艺术批评的应有任务。当然,间性批评也只能是作为知识叙事合法性的实验区,它也存在某些内在的“实验风险”,这需要我们“接着说”。
〔1〕(以)齐安·亚非塔.艺术对非艺术〔M〕.王祖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英)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M〕//钱耀鹏.考古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法)卡特琳娜·维托尔·德文登.国家边界的开放〔M〕.罗定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