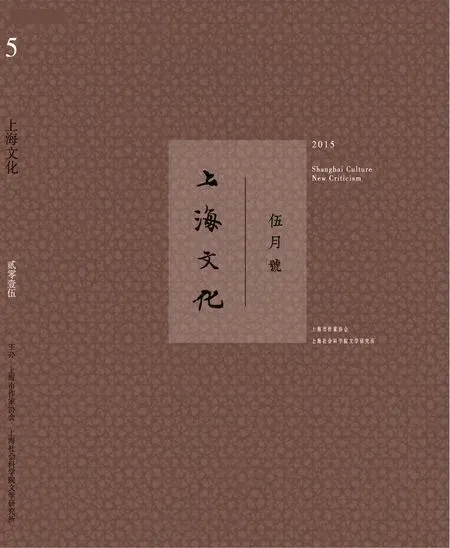真实的自己根本无从谈起关于《黑镜子》
汪功伟
真实的自己根本无从谈起关于《黑镜子》
汪功伟
1
谈及这部自2011年开播、迄今为止已然更新至第三季的迷你剧,《黑镜子》制片人查理·布鲁克说:“《黑镜子》每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不同的演员、不同的故事背景、甚至是不同的现实社会,但都围绕我们当今的生活展开——如果我们够傻的话,我们的未来就是这样。”看完《黑镜子》,作为观众的我们很可能会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下面这些问题:我们有朝一日会不会生活在一个无法逃离的科技梦魇里,无论这种梦魇是1984式的还是美丽新世界式的?科技是不是异化了淳良的人性,是不是已经把人类贬低为一颗死死拧在社会机器之上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渗透和入侵是不是应当有个界限,而在这个界限之外,人文精神可以、并且应当为自己的权利大声疾呼?如此等等。
这些尽管是现代社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大多数以反极权和反乌托邦为题材的类型片力图借用和反思的主要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黑镜子》所要处理的最根本问题。相反,作为《黑镜子》的观众,最好不要纠缠于那些关乎科技的细枝末节,尤其是,不要做一个廉价的现代科技批判者,一位把佩剑指向某种虚设的科技幽灵的堂·吉诃德。在我们身处的社会,激发某种道德感和批判意识易如反掌,但真正难能可贵的,反而是学会控制自己的道德感和批判意识。
那么,关于《黑镜子》,我们还能谈论什么?查理·布鲁克认为,《黑镜子》谈论的是那已呈黑云压城之势向我们不断迫近的未来。但或许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不妨认为,它所关切的,仍旧是那些关乎身体和心灵、关乎自我与他人、关乎个体与社会的古老话题。我们可以从这部剧集的第三季、也就是圣诞特辑开始,之后再回溯性地考察前两季。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激发某种道德感和批判意识易如反掌,但真正难能可贵的,反而是学会控制自己的道德感和批判意识
2
圣诞特辑中的男主人公马修是一位“超级人工智能”公司的职员,他的工作,是应客户的要求,通过追踪人类大脑的思维模式,从中提取出一个“意识副本”,并让这个副本为生活在物理空间中的人服务。这个副本有着清晰的自我意识,它可以指认出“我”,并且意识到自己已经与身体相分离。对于人类来说,这难道不意味着永生吗?灵魂的纯然不朽与肉体的可变易、可更改、可损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比。如果意识副本能够一直保留在某种介质中,这岂不是说,曾经必须在彼岸的天堂中才能实现的理想,在此岸也可成为现实?但是,《黑镜子》第三季向我们展现出的,恰恰是上述理想的反题。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但观众看到的反而是:缺失了肉体的灵魂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永生,便是对时间的超越;而死亡,则是对时间的臣服。在圣诞特辑中,意识得以永生的可能性,不仅在于它与身体的剥离,更进一步体现在,它可以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时间跨度却依然完好如初,后者在《黑镜子》中,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不朽的灵魂享受到的并不是极乐,而是永无尽头的沉沦与平庸,以至于那个意识副本向俨然做出上帝姿态的马修哀求着索要一份工作。
每一个体悟到生命有限性的人,似乎都会感慨此生中的某些缺憾,而所剩无几的时间已经不再允许他们通过行动对之加以补偿。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果真可以在时间中无限延宕下去,那此刻的一切行动,相对于那个被放逐在视野之外的终点而言,还有任何意义可言吗?正当我们向往完成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完成其一半,而若要完成其一半,则必须要完成其四分之一,如此这般,以至无穷。如果这个过程必须要历经无穷的时间跨度,那么我们甚至无法跨出第一步,因为任何一步都并没有拉近我们与那个不可见尽头之间的距离。于是,如果我们悬搁了肉身的死亡,获得了灵魂的不朽,所有行动的意义便被颠覆了,从此便只能混迹于天堂,像一位游吟诗人一样整日靠弹奏竖琴度日,而这也正是那些乌托邦作品所能想象的极限。
马修的工作不仅仅与那孤魂野鬼般的不朽灵魂相关,同时也与行尸走肉般的可朽身体相关,两者恰好互为对跖。由此我们获得了《黑镜子》中的核心对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圣诞特别篇视为这部剧集在主题上的完成。在象征着合法的白昼,马修的工作是制造无身体的意识,而在隐喻着非法的夜晚,他所从事的则是操纵无意识的身体:马修通过植入他人身体的远程通讯装置,向一位在社交场合不知如何表现的年轻人发号施令,告知他应该如何行事才能俘获芳心。肉身不同于灵魂的属性、亦即肉身的可朽,最终在年轻人所遭受的暴力和死亡中,得到了极端的表达。
在灵与肉的对立中,我们恐怕要反躬自问:对自我加以界定的到底是灵魂还是肉体?换言之,到底是什么确保了“我”的人格同一性?正是这个疑问,使我们在《黑镜子》第三季中看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设定。让我们回到那个意识副本所面临的困境。在缺失了有形肉体的情况下,意识副本对于自我的指认,以及它所感受到的痛苦、焦虑、百无聊赖,难道不只是一堆中性的信息而已么?我们向她倾注的同理心,不正是因为我们从马修赋予她的模拟身体中、从其姿态和表情中,辨识出失落和绝望的情绪么?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它与一个做工精细、内容逼真的电子宠物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即便我们不承认“我就是我的身体”,至少也不得不接受法国思想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论断:身体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相关项。
进一步而言,这一集中更大的悖论在于,两个意识副本与各自从中脱胎而来的母体之间,关系并不一致。那个被创造出来为主人提供服务的意识副本,由于已然从主人的身体中脱离,因而两者并没有人格上的同一性,甚至可以认为,她只是一个与人类思维极其相似的程序而已,而其所谓的自我,已经不能继续指向那个真实的母体了。但是,在该集结尾,我们发现,原来作为马修谈话对象的那个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意识副本。很显然,他依然与那个犯下杀人罪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当他在表述自身时,他连带表述了那个缄默的主人、他的历史与他的真相。最后,他甚至也必须为母体犯下的罪愆受罚。在此处的设定中,上一处被切断的人格同一性,却又不言自明地得到了恢复。与其把这种逻辑漏洞归咎于主创人员不够精心,毋宁说这不期然地透露了我们对于自身的思考所面临的极限:肉体和意识二者之中,到底是哪一个对自我做出了根本性的奠基?
在灵与肉的对立中,我们恐怕要反躬自问:对自我加以界定的到底是灵魂还是肉体
3
灵魂与肉体之间的错位,在《黑镜子》第二季的第二集《白熊世界》和第一季的第三集《你的人生》中,便在失忆与追忆之间得以呈现。
在《白熊世界》中,真正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并不是那种集体狂欢式的审判。换言之,这并不是一部关于惩罚与暴力之合理性的影片,不是一部关于人类的正义理想在付诸实际的过程中是否应当具有某种限度的影片,而是一部关于自我追寻、成长和破灭的生命寓言。影片开头,女主人公托妮从昏厥中醒来,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身处何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丧失了她的记忆,或者说,她丧失了从过去的一切线索中重构自我的能力。之后,随着猎杀的开始,她跟着两个偶遇的同伴不断逃离,直到最后,她奋起反抗。此刻,谜底揭晓,原来一切都只是一场残忍的游戏,是对她过去所犯罪行的惩罚。而在观众的辱骂和欢呼中,她从屏幕上得知了一个让当下的自己难以承受的真相:她是一宗虐杀幼童案的帮凶。尔后,她的记忆再度被清洗一空,她本人则被投入到一场新的轮回之中。
一个人对于自己所经历的命运加以言说,不仅是在呈现,同时也在勾勒、润色、修剪和掩盖
而在《你的人生》中,观众见到的则是《白熊公园》的反面。将自我推入困境的并不是记忆的含糊与空缺,正好相反,记忆似乎过于清晰、过于真实、过于锋芒毕露了,它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展现在其主人的视野之内,从而压垮了那个背负着这段记忆的自我。让我们重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认知心理学不同,记忆并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存储装置,以供更加高级的认知模块随时调用。记忆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自我在记忆,也在压抑。一个人对于自己所经历的命运加以言说,不仅是在呈现,同时也在勾勒、润色、修剪和掩盖。因而,我们的人生总是一种反身创造,它与我们在物理空间中的感知运动并不全然吻合。而与该集题名恰成反讽的是,被客观记录的、作为一种影像证据置于女主人公眼前的人生,反而是一段异己的、突兀的、无法被整合到当前自我叙事之中的人生。
身体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承担一段自己无法追忆、或者不想追忆的历史?我们似乎又回到在讨论《黑镜子》第三季时遇到的那个形而上学疑难,但更加具体:到底是灵魂中留存的记忆印痕,还是身体在客观空间中的移动轨迹,对自我做出了界定?如果是前者,那么在《白熊公园》中,对于女主人公托妮的惩罚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合理性,因为记忆的抹除不正好使她脱胎换骨,成为“新人”了么?为何还要继续折磨她的身体呢?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刑罚仅止于思想领域,即便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改造,最后不也在愈演愈烈中成了一台血腥的绞肉机了么?我们姑且克制一下自己的求知意志,暂时满足于摆出问题而不给出答案。
进一步而言,这两部影片在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之外,引入了“他人”的维度。身体不仅仅是那个与灵魂相对的惰性物质,同时也是处于他人凝视中有待捕获的猎物。他人只能通过他们所观察到的、“我”的身体运动去推敲“我”的灵魂,而这种推敲与“我”的自省往往并不重合。正是在这一点上,《白熊公园》和《你的人生》触碰到了经典电影叙事动力学的核心:他人的视野构筑了一面无法摆脱的镜子,“我”不得不从这面镜子中指认/误认出自我的理想形象,并通过一定的行动序列,或屈服于他人对自己的界定,按照理想形象的样貌对自我做出修正,或迫使他人认可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而悲剧的时刻则在于,无论主人公如何拚尽全力,试图做到其中之一,但终究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面目可憎的自我。
在《白熊公园》中,托妮在队友的凝视中终于开枪反击,这恐怕是这部影片中她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因为开枪的同时,她终于成为了他人欲望的承担者、他人目光中的行动者。但讽刺的是,这同时也是她最后一个行动。而在《你的人生》中,丈夫迫使曾经出轨的妻子面对那段不堪的记忆,使得那段原本应当被压抑于潜意识之中的记忆赤裸裸地展现在两个人的眼前。随着画面的播放,丈夫事实上是将他心中关于妻子的、但妻子却不愿承认的定义强加于妻子。一当主人公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视点中的自我形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弥合的沟堑,一当主人公不可能展开行动再去对他人视点中的自我做出承担或修改,那么叙事也就到此为止,故事亦在悲剧性的结尾中黯然收场。
4
在超级英雄类型电影中,最经典的片段莫过于,心狠手辣的邪恶势力已经把手无寸铁的大众挟持为人质,在屠杀即将开始前的几分钟,超级英雄突然横空出世,将邪恶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而在超级英雄亮相时,总有一些仰慕的民众翘首以待,用激动的语调呼喊超级英雄的名字。而《黑镜子》第一季第一集《国歌》适成这种经典套路的辛辣反讽。
与上一部分的视角相反,此时我们不考虑他人视点中的自我,而考虑自我视点中的他人,毕竟,相对于他人的自我而言,自我同样也是一个他人。希望这个绕口令式的句子不会造成什么困扰:如果说《白熊公园》和《你的人生》述说的是,主人公的自我因其与他人凝视中的自我形象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错位而最终走向崩溃,那么《国歌》呈现的,则是主人公在对他人凝视的自我献祭中成为了一件可悲的牺牲品。当我们凝视一个对象时,我们试图捕获的,并不只是那些直接给予我们的感性材料,更重要的是那能够填补我们内在缺失的不可见之物。可是,这种不可见之物并不隶属于实在的逻辑,而是隶属于幻象的逻辑,亦即,我们在客观的物理世界中找不到我们欲望中那块失落的短板,而必须要诉诸于对客体做出扭曲和加工的幻象,才能得到暂时的满足。因而,眼睛在观看、在凝视、在捕捉,在寻找那能够令自我陶醉的、幻想存在于他人之中的、却又并不总能得到他人承认的猎物。正因为如此,“我爱你”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爱语,其中也可能蕴含着某种原始的心理暴力。正所谓:“他人即地狱。”
超级英雄总是一种半神半人的存在,他们对于众人欲望的承担,具象化地体现在发达的肌肉、灵活的头脑、特异的能力和圣人般的情怀。以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电影,无非是为观众欲望的想象性满足提供了可能。而《国歌》的反讽则在于,它以最明白无误的方式,指认出那些超级英雄类型电影的叙事动力中潜藏的原始暴力,并象征性地体现在人与猪的交配中:在我们的幻象中,他人不再具备属于自身的心理深度,而是滑向人性与物性的暧昧交界,成为一件令我们的欲望获得完满的道具。
当每一个人都在电视机前观看首相和猪做爱的镜头时,也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被劫持的公主已经提前被释放出来。这个有些黑色幽默的吊诡场面,不同时隐喻了幻象对于现实粗暴的否定么?于是,这里需要拷问的伦理态度是:在对欲望的暴力保持克制而外(“有节制的醉”),我们是不是能逃离幻象为我们营造的陷阱,换言之,是不是能够做到不自欺?在《黑镜子》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回来》中,女主人公玛莎难能可贵之处,不正是在于,她最终拒绝了那个一步步逼近真实、试图取代真实的幻象,并学会接受丈夫的死亡这一确定的事实?玛莎采取的伦理姿态,是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创伤体验:一个逝去的丈夫,一个残破的家庭,一个孤独的自己。
正因为如此,“我爱你”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爱语,其中也可能蕴含着某种原始的心理暴力
5
关于“无意识的身体”,电影史上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可能就是《黑客帝国》中被囚禁在逼仄的灯泡型房间内的、为“母体”的运转提供生物电能的身体了。而凭借着生物电能提供的能量,“母体”能够为这些丧失行动力的身体,提供一幅秩序井然、熙熙攘攘的街景,以及自己走街串巷、忙忙碌碌的虚幻运动感。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看来,这种超乎于个体意识之上的、集体性的形式规则(例如礼物流动的规则、缔结婚姻的规则、商品交换的规则等等)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而个体,譬如在电脑前进行远程控制的马修,只是作为“大他者”、或者说是作为象征秩序的传声筒而滔滔不绝。恰如那位最后惨遭横死的年轻人只闻马修其声、不见马修其人,对于我们的意识而言,大他者并不现身、却又无所不在。我们只是在我们的所作所为中,不自觉地贯彻了大他者的指令。
反抗一台物理机器是容易的,而反抗一台心理机器,则是艰难的
进而,他人主观欲望的表达,事实上分享着某种无人称的、为集体所共享的“客观叙事”,这种“叙事”不单独属于任何一个确定的主体,但又为人类共同的生活提供了规范性的支持。是《黑客帝国》的核心设定:“母体”设置了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可和遵循、并且掩盖了大多数人悲惨的现实处境的客观幻象。正如在《国歌》的结尾,首相夫妇在大众媒体前相敬如宾的表演,掩盖了家庭已然分崩离析的事实;正如在第一季第二集《一千五百万》中,那个在屏幕前没心没肺地消费着电视节目的胖子,已然忘却了自己正日复一日重复着无聊机械的工作;正如在第二季第三集《瓦尔多的时刻》中,当门罗将杰米定义为一个懦夫和失败者时,杰米选择躲在瓦尔多的背后,借用一个虚拟形象表达自己的不屑和愤怒,但事实确乎是,他是一个懦夫、一位失败者,如果没有瓦尔多,他什么也不是。
穿越客观幻象,在《黑客帝国》中是通过一颗红色药丸实现的。就这一方面而言,《黑镜子》对穿越幻象之可能性的设想,则要决绝得多。本文的第一部分曾说,或许《黑镜子》并不是在预见人类的未来,反而辨认了我们的过去。如果可以把《瓦尔多的时刻》视为一部关于宗教的寓言,那么杰米不就是一位先知吗?他最早发明了上帝,发明了那个嘲讽和反抗现存秩序的偶像,但精神“扬弃”了肉体。真实的耶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具有神人二重性、能够把五块饼分给五千个穷人充饥的“耶稣基督”。而当瓦尔多从一个虚拟的反抗者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精神偶像时,一套权力机制便开始运转了,最后,针对瓦尔多的任何亵渎都是不被允许的,即便这个亵渎者是那个最早发明了瓦尔多的人。
但如果这无非是另一个江山易主的故事,那么其中的意蕴就要大打折扣了。事实上,在《瓦尔多的时刻》的结尾,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看见那些暴力执法者的真实面目,他们身上毫无生气的制服与头盔,使我们丧失了从中指认出我们必须要加以反抗的对象到底是谁、又具有何种身份的可能。因而,大他者在本质上与《黑客帝国》中的“母体”有着天壤之别,反抗一台物理机器是容易的,而反抗一台心理机器,则是艰难的。所以我们在《一千五百万》的最后看到,男主人公慷慨激昂的反抗,最后在观众的欢呼中被消解了,他的所作所为,似乎与那个急不可耐要求上台表演的女人毫无二致。大他者成功地将一位“越轨者”从歧途中解救出来,赋予他一个相对于那些没日没夜蹬着自行车的体力劳动者更加高贵的崭新身份。社会失范被解除了,“不幸的自我意识”将自己“竭力外化为”那片碎掉的玻璃,曾经用于反抗的武器,而现在则是他表演的道具。他小心翼翼地将这片玻璃供奉起来,仿佛通过这个动作,他可以向大他者表明自己拥有一颗珍视当前身份的忠心。
6
一份关于《黑镜子》的评论,绝口不提媒介的意识操控,绝口不提科技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绝口不提消费主义对人类家园的入侵,合适吗?诚然,或许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横流的物欲和非人的技术已经充斥着整个社会,人类已经踏入了大灾变前夕的黑铁时代。但是,如果这些关乎人类未来的判断,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的“黑镜子”式想象之上的,那么试问: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黑镜子》能够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模型呢?第一季的第一集符合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吗?而第二集又考虑到所谓的“消费者主权”了吗?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批判的合理性又源自于何处呢?我想,我们的理性还不足以让我们拥有上帝的视角,仅仅用一些诸如“消费主义”、“技术扭曲”、“意识操控”这样的术语,空泛地谈论社会、科技和媒体。相较于这些需要建立在翔实研究之上的问题,不妨认为,对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观众,《黑镜子》提出的更富有意义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亲人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逐渐忘记我们,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把他/她看作是与过去无异的一个人?当要求亲友对我们坦诚就必须要揭开他/她过去的伤疤时,那么此时此刻的无知是不是一种美德?当我们要求他人做出某种符合我们心意的行动时,这种欲望是不是应当有所节制?以及,在我们扮演的种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角色,以及卸除这些角色之后的自己之间,哪一个才是自我的本相,抑或,真实的自己根本无从谈起?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