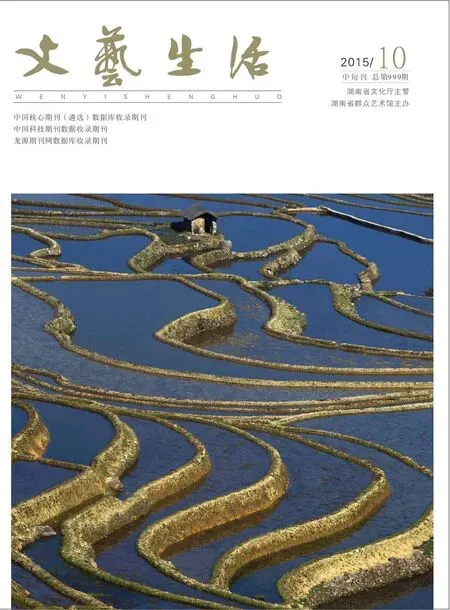浅谈《楚辞与原始宗教》
谢晓冬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浅谈《楚辞与原始宗教》
谢晓冬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楚辞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它以其悲壮激越的情感和独立不羁的人格力量大大冲击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楚辞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显示了文化在过渡状态之中文化因素的互相渗透和选择的规律。
楚辞;礼俗;屈原;祭祀文化
两千年来的楚辞研究其主导思想在于调和“发愤抒情”和“温柔敦厚”两种品格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用意是在维护传统礼教。楚辞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念政治思想和人格情操等理性内容,基本上体现了屈原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楚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楚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
楚文化,是以楚国的传统文化为主,以中原周文化为次,兼有其他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它形成于春秋末期,并一直保留到战国结束。战国各地有宗教,而以楚地为盛。《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文物考古则印证了历史记载。湖北江陵战国中期的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2700字有关卜筮﹑祭祀的简文,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儒家等学说的理性精神渐居上风,楚地却巫风盛行,楚人沉浸在鬼神的世界之中。
屈原是楚王的宗族,曾任左徒,后又称三闾大夫,知识广博,有较强的外交能力和政治能力,他职掌王族宗族长官,具有怀疑精神和理性品质。《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部作品。就其诗体形式而言,它一问到底的表达形式,十分罕见。对形式的过分执著往往意味着一种职业性在诗文背后起着作用。《天问》包括一百七十多问,一部分神迹巫祭之事,一部分述传说历史。各民族的史诗无一例外都要回答宇宙和人类起源的问题,《天问》也不例外。《天问》还有问及鬼神者,如风神“伯强”﹑水神“康回”等等,这显然是巫史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天问》亦有问及祭祀仪式者,如“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等,以上几个方面相当于《训典》的“序百物”,是巫师所必备的知识。《天问》实有似于《训典》,所以可以推断《天问》正是以屈原自己所掌握的巫史文献作为素材而创造出来的长篇诗歌。
屈原的职务与巫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问》是一部巫史文献的作品,屈原虽知识渊博,充满了时代精神和浪漫气质,但遭陷害流亡的不幸经历,使得他对社会历史有着深刻的反思。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悲其志。”《天问》和《离骚》一样,包含了属于屈原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并且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二百年以后的司马迁都为之悲哀。《天问》表达了屈原对天意的怀疑,这一思想来自两方面:一是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一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另一方面是屈原正直不屈,却为楚王所疏远直至流放,对于满腹抱负的政治家来说,简直是命运中的巨大打击。“王听不聪,谗言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由此表明屈原忠君的政治热情。
《周礼》曰:“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在屈原看来,夏启的“九歌”,不但是祭祀“帝”的,而且还充满着人情的放纵。“九辩”﹑“九歌”﹑“九韶”得自上的说法自然是神话,但可以相信这三者是和祭祀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为巫乐﹑巫歌﹑巫舞。因其本身的神秘性质,故被后人神化为夏禹窃自天庭,成了“天帝乐名”。屈原显然是明白原始“九歌”的真实含义,只是他对原始祭祀性质不能接受,故对夏禹颇多指责。
楚辞的“九歌”是如何产生的呢?王逸曰:“《九歌》者,屈原所为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笔者可以得出几点信息。(1)《九歌》原流传的地点;(2)《九歌》是当地土著祭祀乐歌;(3)现传《九歌》是经屈原改写记录的。屈原所作的《九歌》与原始“九歌”重名,相同的书名之间一定会存在某种文化联系,但是两个“九歌”之间相隔千年,虽出于一地,但不能说明就是同一体,“九歌”的祭祀礼仪的交往和传播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异。屈原所任命的三闾大夫之职,包含有宗教祭祀的内容,因此,屈原无疑对楚文化的祭祀一套十分熟悉。当他看见沅湘祭祀之礼时,为了满足“亵慢淫荒”,他对《九歌》进行加工改造。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出自屈原的情感需要和创作的冲动,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屈原知识丰富,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遭流亡,司马迁指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记录改造的《九歌》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创作肯定是包含了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不是对原始”九歌”进行还原;而且巫术祭祀在本质上也是想象的产物,它除了初民用以“控制”自然外,也是他们面对自然世界的莫测和恐惧所采取的自我安慰的形式。
楚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楚辞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显示了文化在过渡状态之中文化因素的互相渗透和选择的规律。楚辞对巫术宗教的自觉保护,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家园。
I206.2
A
1005-5312(2015)29-0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