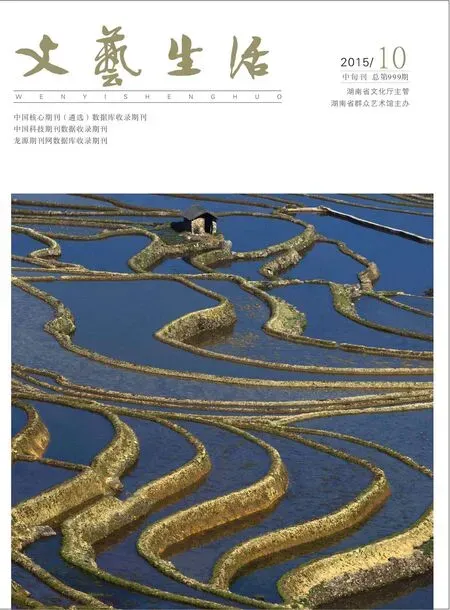初探翟永明诗歌中的身体意识与自我建构
——以《女人》组诗为例
朱音
(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初探翟永明诗歌中的身体意识与自我建构
——以《女人》组诗为例
朱音
(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1984年,中国当代女诗人翟永明首次以二十首抒情组诗《女人》出征文坛,凭借其独到奇诡的语言风格和坚定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一举掀起诗坛巨浪。本文以其《女人》组诗为例,试图从身体学层面发掘翟永明诗歌中蕴含的身体意识,从而分析其中体现的强烈的自我建构和女性观念是如何确立的。其诗歌拓展了与众不同的女性自我空间,超越了对生活的客观再现,因此极具女性文学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
翟永明;女人;诗歌;身体意识;女性自我建构
诗是生活、情感、思想的综合体,零碎的字句往往透现出诗人的内心真实。当我们怀着“索隐”的目的探入女诗人翟永明的组诗《女人》时,则会发现她的诗已不再满足于对客观生活的忠实再现,而是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表达主体——女性,使得“再现”上升到了“表现”的层次。通过对身体的不同表达,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女性自我世界的空间。
一、男性与女性
中国传统对女性的塑造是偏狭的,认为历史由男性书写,而女性只能沦为被书写的对象,丧失了自身应有的话语权。而经过文革的苦难挣扎,当妇女解放的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席卷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传统的“男性主导”定位被彻底打破,女性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正是在两性关系重新定位中诞生于世的。
因此,翟永明的思维方式中带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她为组诗所作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中提到:“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直觉。”她认为女性应开拓私人的情感、意识、自我空间,来与男性对话,尽管在情感关系中两者往往处在不平等的界地。
二、身体与自我
除了通过重新审视男女性主体的地位,翟永明十分重视身体表达来进行女性自我建构。这里的“自我”更多的是暗指精神意味上的“自我”。
(一)通过肯定身体的实在性区分自我与男性他者,并强化女性个体特征
如在《母亲》中,描写了母亲受孕、婴孩诞生的过程,实在性地区分了与男性他者的不同。“你是我的母亲,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你使我醒来//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借以血液、生与死、眼睛的表达,细腻传神地描摹了女性生产的不易。在诗歌中,翟永明不加掩饰地描写女性作为母亲在生产时的疼痛与撕裂感,通过“我”的口吻,从无知到苏醒的意识转变,来无比肯定母亲身体的伟大,并同时强化了女性特有的母爱光辉并暗示了生命的代代相袭。
(二)由身体感官传达女性的真实心理状态,强化身体与自我的融合
她在《渴望》一诗中有这样的表达:“今晚所有的光只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无法安慰,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梦中的墙壁发黑/使你看见三角形泛滥的影子/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带着心满意足的创痛/你优美的注视中,有着恶魔的力量/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淡淡的忧郁似水滴渗出,“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则暗示着女性焦虑、紧张的心理,显露出女性在自我认识过程中遭遇的迷茫与无助。无形的“喧嚣”物化为有形的身体,在这里,身体成为了一种可感的中介,每个毛孔都可以辅助反映出自我内心情绪的变化,反映灵与肉的融合,使得“身体”和“自我”合二为一。
(三)通过身体的感知来传达自我意识中的隐秘感
翟永明并不回避女性内心的私密空间,反而是直观地通过意象、象征来揭示痛苦,释放压抑,表达对男性对自我对生活的种种观点。她在《生命》中曾描写过对死亡的看法,“热烘烘的夜飞翔着泪珠/毫无人性的器皿使空气变冷/死亡盖着我/死亡也经不起贯穿一切的疼痛/但不要打搅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又害怕,又着迷,而房间正在变黑/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橙红灯在我头顶向我凝视/它正凝视这世上最恐怖的内容。”极具反差的对比,夜是热烘烘的,渲染了躁动不安的氛围。末句,不是人凝视灯光而是灯凝视“我”,在死亡与人类之间,强化了人类的渺小感与无力感,却在隐秘的内心空间之外增添了自我表达。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诗人翟永明借《女人》组诗,正是在男性与女性、身体与自我、这两组二元对立关系中重新审视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空间,从发现身体的实在、感知身体的意识到建构心灵的自我世界,最终完成了对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的新超越,为女性主义赢得了文坛的话语权。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I207
A
1005-5312(2015)29-0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