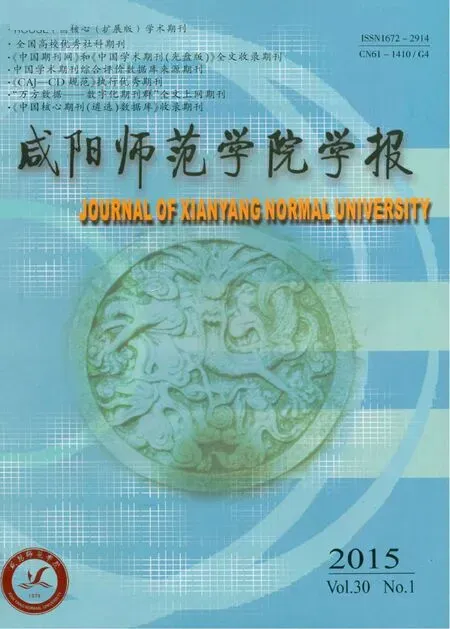先秦至两汉时期甘青藏区羌人的地理分布
李虹瑶,吴景山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先秦至两汉时期甘青藏区羌人的地理分布
李虹瑶,吴景山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藏族与古羌人在族源上有着极大的关系。甘青地区是羌人的原始发源地,先秦至两汉时期羌人在此地区的聚居范围多有变化。先秦时期羌人分布受自然影响较大,从战国后期开始,尤其是两汉时期,战争、政府行为等人为因素表现更多。研究这一阶段甘青地区羌人的分布,有利于了解该民族的时空分布及民族发展。
先秦;两汉;羌人;甘青地区
羌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藏人和古代羌人关系密切。先秦至两汉时期,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陇南及川西北等广大地区。这期间,羌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都是众多的分散部落,甘青地区是羌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关于羌人的分布,学者多有涉及。但关于先秦至两汉时期羌人在甘青藏区的地理分布,专门研究较少,未成体系。研究羌族的发展历史,掌握羌族的活动区域,对于了解甘青地区羌人的早期生活环境、探究藏族族源及其历史传承都是大有裨益的。
1 藏族与古羌族的关系及甘青藏区的范围
关于藏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但南来说(印度说)已基本上被摒弃,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说法为西羌说和混合说(藏族族源多源说)。不论西羌说还是混合说,均认为古羌人与藏族族源有关。费孝通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这样说过:“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1]
关于今甘青藏区的范围,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学者在界定时略有分歧。安世兴、杜生一与周伟洲讲述的比较笼统,认为甘青藏区广泛来讲是指今甘肃省和青海省境内藏族相对聚居区。但后两者又有所不同,杜生一把果洛藏族自治州同样纳入甘青藏区,[2]8周伟洲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说法,他将甘青藏区约同于安多藏区,在对安多范围的注解中明确说明:“大致包括今青海藏区(玉树地区除外)、甘南、河西等地藏区;不包括清代四川所属的果洛及松潘等安多藏区。”[3]即甘青藏区并不包括果洛。杨红伟在泛指上与上述三位学者一致,但在具体的位置界定上则有所区别:“所谓甘青藏区……为青藏高原北部及其边缘地区,包括青海全境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地。”[4]他将整个青海纳入其中。与之相对,李亚娟和陈柏萍二人均认为甘青藏区仅含今甘肃藏区(清际含部分临夏地区)、青海除玉树以外的广大藏族聚集地区和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5-6]
因民族杂居、融合的复杂性,在地理上进行定位确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出现了上述学者对甘青藏区的多重解释。但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甘肃、青海及其边缘地区的藏族文化带为中心进行描述,因而甘青藏区并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更是凝聚着藏族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另外,甘肃、青海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区,甘青藏区这一地理范围在不同的时期因政权更替、本土认同、民族的迁徙与汉化等因素,其外延有所不同。
2 先秦时期甘青藏区羌人的族源与聚居地
最早明确西羌地理范围并将其作为传记载入史册的是《后汉书》,其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7]2869南岳,即今衡山。①《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其余四岳均能与今地名相对应,唯独南岳出现差异。对此,《春秋左传注疏》解释为:“按三代以上衡山亦称霍山,是一山二名,如泰之名岱耳。”即霍山与衡山仅为一山二名。清代郝懿行提出质疑:“霍山在今庐江灊县,潜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以霍山即南柱,亦止得为汉武之南岳,而不得为《尔雅》之南岳矣。”《尔雅》中的南岳非今之衡山,之所以被后人误解,是由于汉武帝游览衡山并尊其为神。不管是一山多名或文字误解,历代正史均以南岳为衡山。如《史记·封禅书》载:“南岳,衡山也。”《汉书·郊祀志》注:“南岳者,衡山也。”《新唐书·礼乐志》:“南岳衡山于衡州。”可见羌族最早生活在衡阳附近,后迁徙到三危。历史上关于三危之地的地望所在记载多异,后人又各有所取,意见分歧,②李聚宝在《“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一文中总结了古今学者对“三危”地望的十余种说法:一是三危为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二是三危为西裔或西裔之山,但终究现指何地何山却无确切说法;三是三危为康、藏、卫三地;四是三危在今云南省境内;五是三危在今甘肃、青海境内;六是三危在今四川境内;七是山有三峰者就是三危;八是三危在洞庭、彭蠡之间的山地;九是三危在青海省东南部,并包括甘肃省西南部及四川西北部交界的西倾山、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巴颜喀喇山三山所在的地区,以及三山周围的一些地区;十是三危在今甘肃省陇西县西北。此外,也有主三危在今甘肃之天水、渭源和临潭者。此后的学者又持有其他的看法,汤洪、黄关蓉据先秦、汉初文献认为“三危”本意为模糊语义之大地极西之山,后世不断将语义阐释而发生讹变。参见汤洪、黄关蓉《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其中最为普遍的观点为“三危为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③杜预《左传·昭公九年》注、郦道元《水经注》、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以及乐史《太平寰宇记·沙州·敦煌县》均认为三危为今甘肃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本文以此为依据。河关,即汉代河关县,其县治史书记载不详,时断时续,亦难以确定地望。传统说法有大河家说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丁谦《后汉书西羌传地理考证》、梁份《秦边纪略》以及今人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辩》、马效融《河州史话》均认为河关县在今甘肃积石山县境内。(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长宁驿古城)与贵德说⑤龚景翰《循化志》、郦道元《水经注·序》以及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海历代建置研究》、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的“凉州”图均认为河关县在今青海贵德县境内。(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一带)。赐(析)支是古代羌族的居住中心,赐(析)支即赐(析)支河,“赐支河者,即青海南黄河曲处一部分之名”,田继周言:“赐支、析支,指青海湖至扎陵湖、鄂陵湖一带地区和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民族。”[8]267张广大据实地考证,证明赐(析)支河在今青海门堂至青海河南蒙旗县译曲河一带广大蒙藏地区(它包括今久治、阿坝、若尔盖、玛曲、碌曲、夏河、河南、泽库等县)。[9]二人表述大体一致,将赐(析)支锁定在青海东部地区。赐(析)河为黄河上游,河首,也就是黄河的源头地区,在今青海南部地区。车师初兴时居地在以吐峪沟为中心的今鄯善县境。
由此可知,在古代,羌族最初生活在衡阳附近,后经迁徙,聚居在以青海河曲为中心,东到今甘肃积石山县,西至甘肃敦煌市三危山,南到四川西北部、西藏东部,北接新疆鄯善县的广大地区。
关于商周时期甘青地区羌人的分布,文献记载较少。在甲骨文中,“羌”是唯一关于民族的文字,卜辞中对羌的记载最多,达937条,但有关羌人的地望却较为笼统。卜辞中仅有“来羌自西”(《甲骨文合集》6596)的记载,即羌人的活动地域大致在商的西方。
从考古资料分析,先周时期的刘家文化与商代羌族的分布空间极为接近。刘家文化极盛时分布在甘肃东部偏南一带,向西一度到达甘肃南部的渭水流域。羌族此时的活动范围大致如此。周初的卡约文化分布于整个湟水流域;周初的寺洼文化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县;西周中期的辛店文化分布于洮河流域;周厉王时期的诺木洪文化发现在青海省都兰县的诺木洪、巴隆和香日德。可见,甘青众多的文化类型与羌族有密切的联系。[10]195
春秋战国时期史料中亦鲜见羌字。春秋战国时,秦国强大,不断向西拓展疆土,并多次征伐羌戎部落,致使羌人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有的向西发展,“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有的可能到达天山南麓,有的迁至内蒙古西部,还有大量向西南移动。[10]202此时,在陕甘高原上还分布有不少的羌戎部落集团,其中比较强大的是居住在秦国西北边境的义渠国。关于该国的族属,向来争议较大。①有关义渠种族的归属问题,目前主要有氐羌、狄种、吐火罗族、允姓戎说和自为一族这几种说法。义渠属于氐羌的说法,古来有之,也是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本文以此观点为依据。马长寿从三个方面推断义渠人与氐、羌人相近:一是义渠人实行火葬之俗;二是义渠安国对西羌的熟悉;三是范晔在撰写《后汉书·西羌传》时将义渠置于卷首加以叙述。[11]86义渠国的都城,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义渠城在州西北”(州指宁州,今甘肃宁县)。[12]673义渠国疆域十分广大,《史记·匈奴列传》记:“秦昭王时……遂拔义渠二十五城……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13]2885据《后汉书·西羌传》,秦惠文王曾“伐义渠,取郁郅”,取其“徒泾二十五城”,后秦败义渠,遂置“陇西、北地、上郡焉”。[7]2874显见,义渠的分布除北地(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治所为今甘肃庆城县西南)外,遍及陇西郡(今渭水上游,治所为今甘肃临洮县南)、上郡(今陕西榆林市东南)。
战国后期,大部分分布于山西、河南、陕西的羌人已经融入华夏族,甘青地区的羌人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泾、渭上游和洮河、大夏河、湟水、河曲一带以及甘肃庆阳市西南、临洮县南。
3 秦汉时期甘青藏区羌族的扩张与迁徙
秦朝时,羌族范围扩展到今甘肃甘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西至临洮羌中”,临洮,即今甘肃岷县。汉初,羌人分布很广,但大部分仍聚居在甘青河湟一带。“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陇西外,大都仍散布在长城以西,特别是河湟地区,主要居住地是陇西(今甘肃临洮县)、金城(今甘肃皋兰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市东南)、西河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安定郡(今甘肃镇原县东南)。”[14]
秦汉羌族的分布,可以从地方羌的名称中窥探一二。根据《汉书·地理志》,可绘制表1:

表1 秦汉时期甘青地区以地方羌命名的郡县空间分布统计表
可见河西一带在汉初已有羌的地名分布,“羌族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分布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16]
影响秦汉时期甘青羌人聚居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迁徙。羌人的迁徙开始于秦灭西戎之后,羌人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开始迁徙。西汉时期,羌族迁徙的规模小、次数少,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也不大,基本上是本民族主动的迁徙。汉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7]2876汉武帝时,为了“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汉军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塞,先零羌纠集封养牢姐种,合兵十万,共攻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安故(今甘肃临洮县西),围枹罕。元鼎六年(前111),武帝遣李息、徐自为率军讨伐西羌,这次征战将羌人逐出湟水流域,退至青海湖、盐池附近。宣帝元康三年(前63),先零羌渡过湟水,到达金城郡北部。宣帝神爵二年(前60),赵充国平定羌乱,设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15]2993综观西汉一代,羌人或自行求附,或为汉兵破降,这些羌人皆就近安置在陇西、金城等郡。
东汉时期,羌族的迁徙次数较之西汉更为频繁,范围也愈加扩大,已深人到安定、汉阳(今甘肃武山县东)等地。与西汉迁徙相比,东汉羌族“以强迫性迁徙为主。羌族的迁徙,虽有少量主动或自愿性的,但大多是在战争中被俘或在军事压力下发生的”。[17]东汉建武九年(33),班彪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祍,而与汉人杂处。”[7]2878是时凉州已有羌人活动聚居。建武十一年(35),先零羌复寇临挑,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并被迁徙到天水、陇西、右扶风(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开创羌人内迁的先例。[7]2878-2879中元二年(57),烧何酋比铜钳为卢水胡所击,“乃将其众来依郡县”,[7]2880徙至临羌县。永平二年(59),滇吾复降,《后汉书·西羌传》言:东吾之孙麻奴“初随父降,徙居安定”。可知,滇吾部落降后,徙居于安定。元和三年(86),迷吾战败被俘,陇西太守张纡令其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洞北归义城(今青海贵德县东北黄河北岸)。永元九年(97),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征西将军刘尚等率军讨伐,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永元十三年(101),金城太守侯霸率兵于允川(即大允谷)击败烧当羌迷唐,降者六千余,分徙于汉阳、安定、陇西。永初二年(109),当煎、勒姐羌攻没破羌县,钟羌又没临洮县。东汉一朝,羌人的内徙相当频繁,到东汉末年,西北各地都已聚集大批羌人。经过迁徙,羌人除了原来在陇西、金城的聚居地外,在关中、凉州、上郡、北地、西河又形成了新的聚居区。
4 结语
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甘青地区是古羌人的原始发源地,即为今藏族的祖属地。自先秦至两汉时期,羌人聚居的范围伴随着羌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期间亦受到中原王朝政治经济形态的影响,这些对羌族、羌族文化和相关民族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羌人迁徙的过程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调节与适应过程,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融合,至东汉末年,汉羌民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此外,东汉后期西北民族疆域格局发生了新的改变,客观上促进了鲜卑民族的崛起并向内地扩张。
[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2]杜生一.甘青藏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周伟洲.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10-31.
[4]杨红伟.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4(1):110-121.
[5]李亚娟.略论明代治理甘青藏区的政治军事政策[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6(6):212-213.
[6]陈柏萍.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76-8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田继周.秦汉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9]张广大.析(赐)支河曲之地望考略[J].西北民族研究,1990(2):241-244.
[10]何光岳.氐羌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11]马长寿.氐与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0(1):117-152.
[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张力仁.地名与河西的民族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1):203-210.
[17]王力,王希隆.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48-60.
Qiang Peopl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an Qing TibetanArea Betwee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Han Dynasties
LI Hongyao,WU Jingshan
(Historical and Culture Colleg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20,Gansu,China)
Tibetan and ancient Qiang peopl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Gan Qing area as the original birthplaces of Qiang people,changed in inhabited areas between the Pre-Qin Period and Han Dynasties.The Qiang people’s distribution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na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The war,the government behavior factors played such greater role starting from the late warring states,especially between the Han Dynasties.Study on the Qiang people in Gan Qing area concerning distribution of this phase helps to underst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the Pre-Qin Period;the Han Dynasties;Qiang people;Gan Qing area
K289
A
1672-2914(2015)01-0040-04
2014-12-15
李虹瑶(1990-),女,河北沧州市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