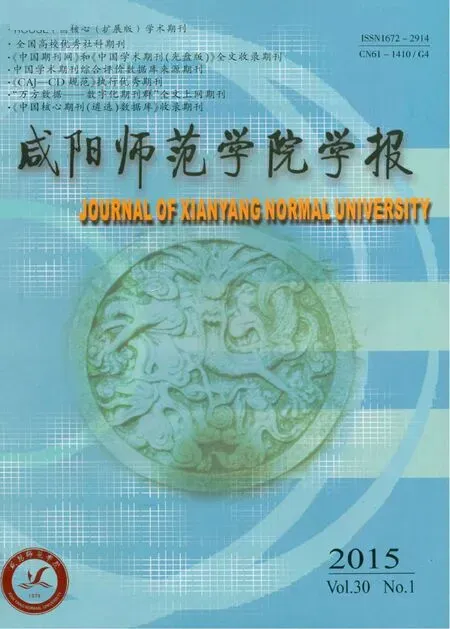以身份之名: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差异
傅美蓉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以身份之名: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差异
傅美蓉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以西苏、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者通过对女性特质策略性地运用,分别以身体之名、差异之名、母亲之名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女性写作的必要性,对性别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的诗性探讨,使原本被遮蔽的性别差异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无视、否定性别差异到重视、肯定性别差异,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所完成的这一转变凸显了女性主义批评鲜明的政治性与身份意识,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女性特质;性别差异
20世纪70年代,以西苏(Hélène Cixous)、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继续开拓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对菲勒斯文化的批评路线,提出各自的批评方法与策略,共同确立了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主体性地位。性别差异一直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焦点,女性特质则是其撬动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阿基米德支点。西苏、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不仅相信女性特质的存在,并且对其持肯定性的态度。不过,三者在具体的理论主张上却有很大的差异。西苏将女性“力比多”(libido)与女性特质联系起来,认为女性的身体、力比多与无意识一样,是四处弥漫、无边无际的,伊利格瑞则将身体各器官的感受、尤其是女性的性欲与女性特质联系起来。在性别差异问题上,两者均倾向于生物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立场,关注女性的身体及其生理特征,认为女性特质与身体密切相关。克里斯蒂娃反对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转而将女性特质安置在具有女性特质的“符号态”(semiotics)中。然而,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虽与生理性别差异无关,却也一头栽进了本质主义的陷阱。值得肯定的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特质的关注推动了女性主义批评对性别差异的探讨。
1 “阴性书写”:以身体之名
作为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西苏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e)这一概念和理论,《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宣言书。在此之前,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尚未引起关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不仅揭橥了语言结构、语言内容以及意指实践中的性别歧视,而且将矛头直指“男性”语言,试图打破该语言所设立的种种界限,将其改造成另一种语言。面对有性别的语言,女性主义批评何去何从?正如张京媛所指出的,女性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拒绝规范用语,坚持一种无语言的女性本质”,要么“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1]8对女性主义批评而言,第一条路无异于自掘坟墓,第二条路则大有可为。
如何才能有效地改造男性语言,这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共同面临的难题。对西苏来说,身体是一个位置(site),不仅设定了“我们是谁”的界线,而且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基础。[2]23在1968年之前,西苏一直以“犹太妇女”(Jewoman)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直到1968年之后的某一瞬间,她“突然感到自己已置身于女性的历史中”,开始承认自己作为女性的多重身份:“我是母亲,是女儿,我无法不让自己做一名女人……”[1]227-228从作为个体的“犹太妇女”到作为“置身于女性的历史”中的一员,西苏的身份意识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蜕变。这就为“阴性书写”提供了出场的契机。“70年代以后,身体既是女权政治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焦点,也成了女作家重新命名世界,认识他人与体验自身及表述自身的重要媒介。这些题旨都可在西苏的论著中找到。”[3]西苏从法语出发,将写作分为阴性书写和阳性书写,主张女性用身体书写。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明确提出“阴性书写”理论,强调“妇女必须写妇女”,[1]336这就为女性书写自我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坚持“无语言的女性本质”与接受“有缺陷的语言”之间,西苏选择了接受“有缺陷的”男性语言,进而对其进行颠覆性改造,“阴性书写”应运而生。在论及“阴性书写”的本质及起源时,西苏往往将其与女性身体关联起来:“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1]201对女性来说,这种基于身体的“阴性书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在西苏看来,甚至妇女的解放也需要借助这种书写来实现:“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1]195在此,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性的一个出发点。西苏虽然拒绝为“阴性书写”下定义,但在其书写实践中女性身体与女性经验显得尤为重要。“阴性书写”至少有两个目的,即“击破、摧毁”与“预见与规划”。[1]188在“阴性书写”中,女性身体以及基于身体的女性经验被置于语言之前,因此能够说出一切未被言说的可能性,再现真实、独特而具体的女性存在。
西苏所说的“妇女”真实、独特而具体的存在,是“在同传统男人进行不可避免的抗争中的妇女”,是“必须被唤醒并恢复她们的历史意义的世界性妇女。”[1]188在谈论“妇女”时,西苏虽然谈的是妇女的共同点,但更关注其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我们无法整齐划一地来谈论女性特征,在女性表达中也存在他者妇女(the Other Women),即处于学术界之外的“现实世界”或第三世界的妇女。[1]241“目前还不存在妇女独立的整体,不存在典型妇女。”[1]189如何才能使被菲勒斯中心主义遮蔽的妇女得以再现?西苏试图借助女性的身体、性与欲望,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本质观。“阴性书写”正是“西苏解构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后,为建立女性身体与语言的新联系而提出的策略。”[4]
西苏认为人类的天性中蕴含着“双性同体”(bisexuality)的特质,其“阴性书写”就是基于此提出来的。伍尔夫、克里斯蒂娃均对“双性同体”概念有过相关论述,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在此,“双性同体”是一种文化定位,追求“差异”与“多样性”,既尊重女性特征也尊重男性特征。[5]364西苏虽然坚持以女性躯体来写作,但她认为男女两性是可以交流的,“人类的心脏是没有性别的,男人胸膛中的心灵与女人胸膛中的心灵以同样的方式感受世界。”[1]232-233不难看出,西苏的“双性同体”以身体为出发点,为“女性特质”及“阴性书写”的合法性提供了诗性辩护。不过,西苏虽强调的是基于身体的“女性特质”,但其一头扎进去的却是文化上的本质主义。
2 “女人腔”:以差异之名
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人类”一词都是阳性而非中性的,因此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平等或中立状态的主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表达一种女性主体更不可能。据此,伊利格瑞主张建立一种非理性的女性话语——“女人腔”(le parler femme),进而凭借“女人腔”颠覆占主流地位的“男性”表达,再现女性自己。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语言概念,“女人腔”能够将对立的双方包容于一体的,不过男性一旦在场就会销声匿迹。身为后现代主义者,伊利格瑞从一开始就不打算给“女人腔”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其“女人腔”与“阴性书写”一样具有革命性,力图摧毁一切建立于菲勒斯中心主义之上的形式、形象、思想与概念。伊利格瑞认为,女性的目标如果仅仅只是推翻事物的秩序,即便实现了目标,也极可能是历史自身的一种重复,无法脱离菲勒斯文化的同一性;而“她们的性别、关于她们的想象以及她们的语言,都将不复存在”。[6]142-146
女性如何才能存在于象征秩序之中呢?伊利格瑞从女性身体与性欲的独特性出发,强调性别差异,认为女性经验比男性经验更具多元性、差异性与丰富性,肯定了女性特质的包容性、多元性与丰富性。在现有的再现体系中,人们所使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单向性语言非但不能再现性别差异,而且认为女性是“反复无常、不可理喻、狂躁不安、任性多变”[7]346的。在伊利格瑞看来,唯有借助“女人腔”(le parler femme)这种完全不同于男性话语的言说方式才能凸显女性特质。“如果想让女人为她们所说的话给出一个准确定义,让她们重复自己的话,以便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那将是徒劳的。”[7]347伊利格瑞拒绝用描述性的语言来定义“女人腔”,因此没有明确描述或精确规定女性特质的内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再现体系中,伊利格瑞并不可能为“女人腔”开辟新的疆域。尽管如此,“女人腔”不论是作为女性的自我言说方式,还是作为言说自我的话语体系,均可视为一种有效的身份标签与斗争策略。
为了进一步探讨性别差异与女性特质,伊利格瑞在《此性不是同一性》(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中重新界定了女性性欲,描述并肯定了性别差异,声称女性应该用“女人腔”来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性性征是以单数“一”为标志的,女性性征是复数的非“一”之性。男人性欲集中在身体的某一器官上,“女人却全身都是性器官”,[7]346其性欲是多重的、复数的。显然,菲勒斯文化对女性的想象体现出了强烈的中心主义色彩,女性往往被想象成单一的、雷同的。伊利格瑞借助女性经验的差异性,对女性性征进行了创造性的建构。女性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她在进行自我编造,她既能不断地拥抱词语,同时又要抛开它们,以避免使意义在词语中固定和凝结下来”。[1]347与女性身体/欲望的多样性相比,被描述的女性世界是单一的、匮乏的。不过,“女人腔”是一种非理性的话语方式,如果不借助第三只耳朵,甚至无法被听懂。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女人腔”的界定问题显得无足轻重,但其对女性身体与性别经验的关注,为女性的自我再现开拓了话语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伊利格瑞进一步强调了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美好愿望:“为了给两性差别定立一套伦理道德,我们就必须建造一个地方,使两性都可以在此居住,不管是身体还是肉体。”[1]373由此可见,在伊利格瑞看来,“女人腔”是性别差异的居住之地,倘若没有“女人腔”,人类语言便只能是单一性别的传声筒。20世纪末,伊利格瑞在《二人行》(To Be Two)中继续探讨两性之间的关系,又一次肯定了性别之间的差异,并开始以诗性的眼光观照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既非凭空创造,亦不容人无视。在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之间,存在着“无法超越的沉默”,[8]86因此对性别差异的关注仍是非常重要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再现系统具有某种盲目性,往往对性别差异熟视无睹,显然,“女人腔”诗意地再现了性别差异。在“女人腔”的基础上,伊利格瑞提出一种尊重性别差异的新女性主义:“它重视性差别,拒绝把我们看作无性的主体,把我们简化为先验(胡塞尔)或思想的变化(黑格尔)。”[8]152在伊利格瑞的努力下,女性特质以其鲜明的差异性特征闯入以男性为中心的再现系统,并获得了自身的言说位置。只有承认性别差异、尊重不同的主体性,性别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协作、相互交流,进而实现性别正义。
3 “母性空间”:以母亲之名
尽管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极易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淖之中,但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是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必然结果。伊利格瑞和西苏的女性写作鼓吹描写女性身体,肯定基于身体的女性特质,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女性特质与生理特征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阴性书写”“女人腔”本质上均不能脱离菲勒斯社会的象征秩序。克里斯蒂娃深受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aueo Lacan)以及文论家巴赫金(M.M.Бaxтин)的影响,试图借助拉康的“符号域”(Semisphere)打破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符号先于象征秩序而存在,在象征秩序内建构女性主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直接从符号学入手,把在柏拉图那里模糊含混的“chora”(空间、处所或容器)改造成具有女性特质的“chora”(阴性空间、母性空间或“子宫空间”)。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把宇宙生成之前的事物分成三类:被模仿者、生成者和接受者。①这三类事物分别被比喻为父亲、子女与母亲。第一类是有理智的、始终同一的模型;第二类是对原型的摹本,有生成变化并且可见;第三类则以一种类似保姆的方式承受一切生成的事物。(参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304页。)接受者是永久存在且不会被毁灭的“chora”,它为一切被造物提供存在的场所。“chora”容纳所有实体的宇宙本质,是宇宙生成之前以及万物被授予秩序之前的场所或空间。经克里斯蒂娃的改造,“chora”成为一种可以容纳一切运动、矛盾的母体,“富于滋养,不能命名,先于唯一、上帝,继而否定形而上学”。[1]352这一空间因以一种类似母亲的方式承受一切生成的事物而获得母性,故克里斯蒂娃称之为“母性空间”。
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中,妇女往往被排挤在时间之外,被当作空间来对待。伊利格瑞也曾表达类似的观点:“女性总是被当作空间来对待,而且常常意味着沉沉黑夜(上帝则是空间和光明),反过来男性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1]374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内,女性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自身的主体性,但女性主义批评不能抹煞女性自身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而寻求单一的女性话语。“母性空间”是身体作为主体形成过程的场所,是“母亲与孩子共有的躯体空间”,[9]61存在于每个女人身上。换言之,“母性”是性别差异的“真正载体”。[10]103与西苏的“阴性书写”、伊利格瑞的“女人腔”一样,克里斯蒂娃的“母性空间”也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是无形无性、不可言说之物,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纯推理的方式来把握这一空间。“母性空间”先于象征秩序而存在,不仅是建立象征秩序的基础,同时也是威胁象征秩序的破坏性力量。相比之下,克莉斯蒂娃走得更远,直接回到前俄底浦斯阶段考察语言的结构性与异质性,用“符号态”(semiotics)/“象征态”(symbolic)替代了拉康的“想象”/“象征”,试图建立反抗男性法则的颠覆性语言。“符号态”具有母性意义,与前俄底浦斯阶段的原始冲动联系在一起,“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性力量而活着”。[9]60在这一阶段,女性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认同母亲或认同父亲。认同母亲则将强化女性心理的前俄狄浦斯成分,使其边际从属于象征秩序;认同父亲则会创造一个从同一象征秩序中获得身份的女人。[6]164不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符号态”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克里斯蒂娃虽然揭露了拉康在语言中将父系律法普遍化的局限性,但只是“在某种豁免于挑战的等级框架里取得其独特性”,[11]107实质上还是承认了“符号态”在象征秩序中的屈从地位。不论是对母性身体进行自然主义描述,还是把母性划归为一种前文化的真实,究其实质都是对母亲身份的物化,使其对母性身体文化建构性之分析成为不可能。
如果说从镜像中观看自己的女人是“能指”,那么女人在镜像中所看到的形象则是“所指”,显然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和谐一致的。克里斯蒂娃对“母性空间”的探寻必然会造成“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松动与脱落,进而破坏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克里斯蒂娃拒绝在象征秩序内为女性确定某种单一的本质,而是通过“母性空间”这一范畴把女性身体还原到不确定的、原始混沌的状态,并把女性特质描绘为一种流动多变、超越了性别差异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特质并不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人。女人虽然拥有与男人不一样的性别身份,但这一差异并不意味着女性身份是由每一个“女性”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实现的。[12]300-301在“母性空间”里,克里斯蒂娃已经对单一的女性身份提出了质疑,并潜在地承认了女性身份的多元性,这就为女性主义批评今后的发展方向指明了出路。挪威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陶丽·莫依(Toril Moi)明确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宗旨是解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之间致命的二元对立”[13]239;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关注女性之间的天然联系以及菲勒斯文化对女性身体及女性差异的刻写,明确提了基于女性性别的“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斯密斯(Barbara Smith)关注黑人妇女的文学成就和同性恋因素,推动了黑人女性写作研究;美国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批判了女性主义研究的霸权意识形态,关注第三世界妇女的他者化地位,启发人们关注女性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因素。在女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女性主义批评逐渐走上了多元、开放、健康的发展道路。
4 结语
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再现系统中,女性从不曾拥有一种完全独立于男性的、清白的语言,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分裂以及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写作互相抵牾的态度。国外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女性写作是“来自男性世界内的妇女世界的建构”,是“妇女小说家对妇女世界的拒绝”,是在用“妇女的男性语言”歇斯底里地谈论女性的经验。[14]181一直以来,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因其所持的本质主义立场而备受诟病,通过考察其对女性特质及性别差异的关注,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和身份意识,就不会有女性主义批评的诞生与发展。简言之,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立身之本。“阴性书写”“女人腔”“母性空间”与女性主义批评等女性话语虽均具有异质性、杂糅性,但其通过对女性特质策略性地运用,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学界对性别差异的理解和关注,丰富了女性主义批评关于性别差异的话语实践,使原本被遮蔽的性别差异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1]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Kathryn Woodward.认同与差异[M].林文琪,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
[3]林树明.身/心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J].外国文学评论,2001(2):14-22.
[4]张玫玫.身体/语言:西苏与威蒂格的女性话语重建[J].外国文学,2008(3):77-83.
[5]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6]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2.
[7]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吕西·依利加雷.二人行[M].朱晓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孚卡,怀特.后女权主义[M].王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0]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论卑贱[M].张新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2]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3]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胡敏,陈彩霞,林树民,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Femininity: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yes of French Feminist Criticism
FU Mei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Shaanxi,China)
French feminists represented by Helene Cixous,Irigaray and Christiva affirmed the necessity of female writing through tactfully employing femininity strategicall,respectively in the name of the body,the difference and the mother from a different viewpoint,and held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on gender differences.The study of gender differences has enriched the practice of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on gender differences,and gender differences that is originally hidde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differences highlights political nature a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feminist criticism,which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criticism.
French feminist criticism;femininity;gender differences
I109.9
A
1672-2914(2015)01-0113-05
2014-11-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YJCZH040);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3JK0240);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2XSYK002)。
傅美蓉(1977-),女,湖北公安县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批评、性别与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