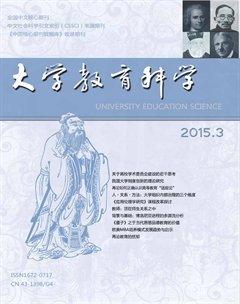教师:活在师生关系之中
刘铁芳 颜桂花
摘要: 教师生命的本质乃是活在师生关系之中,教师总是在师生交往的关系结构中来显明自我作为教师存在的价值,优秀的教师活在师生交往的优秀品质之中。为了使教师的行为产生足够的教育意义,教师必须站在与学生的关系之中,来选择合理的教育行动,由此而形成教师向着学生的实践姿态。最大限度地促成学生生命的自我成全,恰恰是对教师自身生命的成全。尽力地成全,尽力地解放,以促进生命与社会的进步,这是今日教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教师;师生关系;教师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3-0076-06
收稿日期:2015-03-12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厅2014年度重点资助科研项目“好的学校教育如何可能——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14A087)。
作者简介:刘铁芳(1969-),男,湖南桃江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学生是学校的中心,要促成学生的中心地位,切实地促成学生成长,还需要优秀的教师。如果说学生是学校的中心,那么教师就是学校的支柱。好的教师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怎么拔高,都不会过分。
一、活在师生关系之中:教师生命的本质
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名教师?拥有教师资格证,那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获得,是一种符号的合理化。但要真正成为一名教师还需要我们自身不断寄予我们所拥有的教师符号以内容。成为教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给教师之“名”以“实”的过程,所谓“名副其实”。如何给教师这个“名”辅以实际的内容呢?日常生活中,“老师”于我们而言只成了一种形式化的身份。只有当我们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发生一种社会所期待的教育交往的时候,教师才在真正的师生交往中显现自身作为教师的存在。师生之间的教育性交往就是使我们成为老师的时间和空间,是我们作为教师的实践“场域”,在那里,教师的符号获得了真实的内涵。换言之,只有在真实的教育交往中,学生才让我们显现为真正的老师,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师。
真正的教师形象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实践着的。真正的教师活在师生关系之中。作为教师,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显现自身作为教师的存在,就是要在真实的师生交往过程中显现教师生命的本质。教师之为教师的价值就是显现在鲜活的师生关系之中。教师之为教师,就是向着学生的生命显现。学生向着学习,教师向着学生,这就是好的学校教育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是先有父亲,还是先有儿子?就实际存在而言,当然是先有父亲,后有儿子;但从逻辑而言之,是儿子让父亲成为父亲,儿子赋予父亲作为父亲的内涵。我们总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显现我们自身,这意味着我们总是在实践对象的身上显明我们自身的存在属性。作为教师,我们总是在学生身上来显明我们作为教师的品质。优秀的教师活在师生交往的优秀品质之中。
2012年6月初,我参与学院教育硕士答辩时,有一位来自深圳的女老师,其论文题目是“网络环境下中学德育管理的困境与出路”,拿到手上,稍微浏览一下,感觉非常单薄,材料也不够充分。我是答辩主席,轮到我发言时,我开头就不客气地批评了她,说她的论文除了中间一部分有点数据外,其余的内容不够充分,几乎没有注释,然后表示,这样的论文是很难通过的。等几位答辩完,学员退场,我们几位老师讨论时,一位女老师提到,这个女孩很不容易,她的论文后记中写了,她得了癌症,能够坚持做完论文就算不错了。我连忙翻到后记,一看,果真如此,她2006年入学时就已经被医生确诊患有淋巴癌,需要进行化疗等治疗。“因为身体的缘故,毕业论文的撰写拖延下来,而且于2011年病情复发,完成初稿的论文因要重新进行治疗而不得不再次中断,幸运的是,学校和教科院并没有放弃我,为我保留了资格。”[1]在与病魔抗争的同时,是其导师和学院研究生班的老师鼓励她把论文做完,完成教育硕士阶段学习。我当即表示,尽管今后可能有抽查到的可能,但我们还是通过她的论文,只是请她尽量修改一下。后面宣布答辩结论的时候,我特意向她表示了祝福,同时也期待她尽力修改论文,圆满地完成教育硕士学业。
显然,站在学问立场上评价这位老师的论文,也许是没错的;但如果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来评价,则我的评价明显有失公允。前一种评价是基于教师自身,是作为教师的我单向地对学生进行评价,学生仅仅作为评价的客体;后一种评价则是基于关系,学生不仅仅是评价的客体化对象,还是生活中的人,我对她的评价应该置于她的生活背景之中,思考她的研究对于她自身的意义,由此来评价才能更好地引导她,激励她,成全她,而不是简单地贬抑她。
经历这件事情,让我对究竟应该如何做师生有了特别的感触: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任何时候都不是为了简单地向学生展现你的才华,而是为了激活学生生命,激发学生的才华——尽管教师的才华是非常重要的,但教师的才华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增进学生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如此,你对学生的判断是否就是准确无误呢?包括我对那位患癌症的女老师的论文判断同样有简单定论的成分。这意味着真正的教师,在任何时候都应把自己置身师生关系之中,活在师生关系结构中才是教师生命的本质。换言之,只要你作为教师的身份出场,你就应把你作为教师的生存置于师生关系结构之中,充分考虑你的每一个言行对于学生生命意味着什么。教师的职责,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成全学生的生命,而不是相反,抑制、阻遏学生生命的成长。
二、教师作为向着学生的实践姿态
教师生命显现在师生关系结构之中,真正的教师向着学生而生。教师之为教师,不仅是静态的社会身份,更是动态的教育实践。教育学(pedagogy)一词,源自希腊语。希腊语的Pedagogue最初的含义就是孩子的带路人,指引他们怎样去学校、怎样回家。当然,“引路”这个概念也许还有更丰富的含义。“希腊教育学最初的思想将教育学与‘引路的意义联系起来——陪伴孩子并与他们一道生活,以便为孩子指引方向和关心他们。”[2](P51)为了使教师的行为产生足够的教育意义,教师必须站在与学生的关系之中,来选择合理的教育行动。换言之,在每一个情景中,教师必须以立足师生关系来行动,以求得怎样对学生好,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教育行为意味着你应试图去分辨什么对孩子好、什么对孩子不好。正因为如此,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永远也不可能是‘客观的。抚养和教育儿童始终涉及到价值的判断。”[2](P59)
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不是耳提面命,而是随时准备聆听学生,聆听学生内在的需求,活在对学生的期待并且随时回应学生的期待之中。“只有当我们真正感受到教育作为一种召唤而激起活力和深受鼓舞时,我们与孩子的生活才会有教育学的意义。……父母必须聆听孩子的召唤并以适当的方式行动。毕竟,为人父母的含义就是保护和抚养孩子。做父母意味着生活中有了召唤——教育的召唤。同样地,做孩子就是与某个能注意和听到他的召唤的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召唤将这个孩子和他的父母联结起来,成为一体。教育的召唤就是那种召唤我们聆听孩子需求的召唤。”[2](P34-35)始终活在这种召唤,以及对这种召唤的回应与积极行动之中,這就是教师生活的实质。成为教师,意味着随时准备迎接这种召唤。正是这种召唤,让教师走出其个人自我,而活在作为教师的生命状态之中。
我们关心孩子,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孩子充满好奇,或者因为我们天性喜欢孩子,而是因为我们切实地关心孩子的成长。“教育学使我们(老师、父母、顾问,等等)心向着孩子、心向着孩子生存和成长的固有本性。”[2](P44)我们爱孩子,并且对孩子的成长负有责任,仅仅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更要意识到这种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的责任就是善于倾听孩子们成长的内在需要,爱他们的固有本性[2](P45)。教师之为教师的本质,就在我们每时每刻对学生成长的真实期待之中,这种期待弥散在我们的举手、投足、微笑的注视、亲切的问候、鼓励的话语之中。我们心向着学生,关心着学生,倾听、发现、理解学生的内在需要,并随时准备予以必要的扶持、帮助、指导,或者予以必要的陪伴。
范梅南在讨论“什么时候老师不成其为老师了呢”等问题时,提出教育学的基本条件:爱和关心,希望和信任,责任感[2](P87)。爱和关心让我们走近孩子,希望和信任让我们激励孩子,责任感则是对如何切实地促进孩子的理智承担。这些教师之为教师的条件,也就是内在质素,都是在与学生的关系结构中展开的,或者说都是教师朝向孩子的方式。向着学生而生,可谓教师的基本生命姿态。换言之,教师作为教师之生命的特殊性,正在于向着学生而生的教师生存姿态。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站在学生面前的每一个姿态,都激励着学生,向着学生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教育学首先召唤我们行动,之后又召唤我们对我们的行动作出思考。与孩子们一道生活以及反思我们与孩子们生活的方式,这两者都是我们的教育性生存的表现。”[2](P37)教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与学生相遇的每一刻,在聆听、回应学生的召唤之时,活出教师生命的精彩,在充分成就学生的过程中实现教师自身生命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2](P18),教师就是活在对学生成长的迷恋之中。
不仅如此,教师向着学生,不是向着抽象的学生,而是向着当下教育情境中的具体个人。站在学生面前,我们很容易以居高临下的教育者姿态,理所当然地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教他们如此这般。由于我们往往急于把我们的要求加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就想当然地省去了对他们当下的理解。我们对学生的判断先于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教育行动所需的知识应该是针对具体的情境而且指向我们所关心的具体孩子。”[2](P64)关注具体孩子,意味着要关注孩子生存的现实,关注他们现实中的生存,不以个人主观意愿来替代学生自我存在的现实性。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教师如何关切学生存在的现实性。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并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好的,而是告诉我们,存在的事物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导言中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3]这提醒我们,作为教师,面对学生时,任何时候都需要考虑到学生的现实性,避免个人的主观臆断替代了对学生现实性的考量。惟其如此,教师才能真正引导学生,促进学生,每个学生的发展只能建立在个人的现实性的基础之上。教师的意义就是把学生现实性中的各种力量调动起来,引导到合适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教育智慧,就是一种及时了解、充分理解学生自我存在的现实性,并积极加以引导的能力。教师的教育理性就是要对学生自我存在的现实性保持自觉,以求得教师的教育理想与学生存在之现实性的和解,而不是把我们对学生的简单构想强加于学生的生存现实之上。真正的教育意味着我们和学生一起进入当下,寻求与学生之间生命的契合。
三、进入与远离:师生关系发展的辩证法
大凡人世间的爱,不外乎两种基本形式:一种从施爱者出发,一种从受爱者出发。从施爱者出发,爱的表达式是“我想爱”;从受爱者出发,爱的表达式是“我能爱”。“我想爱”,爱是个人意欲的传递;“我能爱”,爱是一种理性的承担。“我想爱”更多的是自我想爱的意愿的成全;“我能爱”则是对爱的对象的成全。“我想爱”的人多感性;“我能爱”的人多理性。“我想爱”的人偏于浪漫,“我能爱”的人偏于责任。一个不成熟的人更倾向于说“我想爱”;一个成熟的人更倾向于说“我能爱”。“我想爱”的人,由于爱的意愿的强烈,更多地看到的是自己,很容易把对方爱的需要淹没。“我能爱”的人,由于爱的理智,更多地看到的是对方,会把自己不当的爱收敛。“我想爱”的人很容易陷于爱的放纵,“我能爱”的人更多地持守着爱的节制。“我想爱”的人往往会把以爱的名义做出的任何行动都视为理所当然,遵循的是一种类似韦伯所讲的意图伦理,即以意图善的名义来说明行动本身的善;“我能爱”的人则由于处处考虑到受爱者的需要,不是从个人施爱的欲望出发,所以遵循的是一种责任伦理,即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爱的意义。“我想爱”的人格特征在爱中往往渗透着对受爱者的控制,处处彰显爱者的主观意志;“我能爱”的人格特征由于在爱中处处考量受爱者的需要,以受爱者为目的,以成全受爱者为基本取向。
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而不是,或者说首先不是为了教师个人意愿的实现。虽然学生成长和教师个人意愿两者有相关性,但前者是客观性的,后者是主观性的,前者才是目的和根本,是后者的依据。深谙教育之道的爱,优秀教师的爱,总是能从孩子的需要出发,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积极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又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安静地回退到成人的世界之中,始终守住自己行动的边界。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堪称优秀的教师总是懂得分寸,进退自如。
这意味着教育实践的审慎。教育者的审慎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教育文化品性而言,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还远未习得一种师生关系的活生生的辩证法,即一种进入与逃离、肯定与否定同构的辩证法,也就是肯定教师对学生发展的作用,同时又要在学生的生命世界中去教师的影响,而让学生成为他(她)自己,成为会思考、会学习的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沦为教师的附庸,或者教师所代表的成人世界的附庸。
进入师生交往关系之中的教师,总是意味着某种影响施之于学生身上。这意味着教师影响对学生世界的进入。优秀的教师总是意味着教师自身影响力向着学生世界的深入,促成学生世界的转变。但如果教師的影响力发生仅仅只是教师对学生的进入,这必然导致教师影响对学生的有意无意、或隐在或显在的控制,学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影响的附庸。这在中国社会亲子交往中比较普遍。
显然,堪称卓越的教师,在以自身影响进入学生世界的同时,又显现出另一种倾向,即向着学生世界的远离,由此而让学生成为其自我,让学生自主自立,而不是作为教师影响的延伸。换言之,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并不是让学生成为教师的传声筒,而恰恰是要让学生走出教师的迷魅,也就是让教师从学生世界中退出,让学生成为他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教是为了不教”,这种“不教”之“教”不仅是作为“教”的结果,而且是内含在当下教的实践之中,辩证地统一在当下之教的过程本身。换言之,堪称优秀的教育人在任何时候,欲将自己的影响加之于学生身上之时,都应该有一种将自己的影响从学生生命世界之中拔离出去的倾向,以此来保持学生个体精神发展的真正的独立性,而不应该让学生的发展成为教师威权下的压迫性实践。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就深刻地显明了此种师生交往的辩证法。作为教师的苏格拉底确实影响了谈话的对象,但苏格拉底并没有灌输给另一方什么知识,他不过是在促成个体知识的自我显现。谈话的结果往往并不是另一方对苏格拉底的遵从,而往往是更大的迷惑,也就是唤起谈话的另一方对更高知识的向往,也就是让对方置于认识到自己无知,并由此而显现出智慧之爱的生存品质之中。
鲁迅曾经提出鸟导师的不敬之词,鼓励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4]从这个意义上,再来看鲁迅所批判的鸟导师,其用意就十分明显,那就是身为教师,任何时候都需要确保青年学生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促成个体精神的自主发展。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某些教育名家,哪怕他们把自己标榜得如何民主,其骨子里依然不过是威权下学生被成长的教育实践,换言之,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深深地扎根在学生的生命世界之中。
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再来看师生之间的恩情与学生的感恩意识。以进入为结果的教师影响力的发生,所带来的自然是教师之于学生成长的恩情与学生对教师的必要的感恩;而以进入而又远离为特征的教师影响力的辩证发生,所带来的是学生自我的独立与自由,教师对学生并无非报不可的恩情,学生的发展也无需对教师感恩戴德。教育乃是师生相互成全的活动,其间并不存在一种感恩的关系。日本知名教育哲学学者矢野智司先生所言的赠与的教育学,其中讲到的无私赠与,正是教师生存的最高境界的体现。
有人撰文这样评述意大利著名作家科尔维诺整理《意大利童话》:“它是本分的记录,保持着民间的质朴;质朴还在,一个民族的心理以及来自神话原型的看似简单实际古老的内蕴,就不会因艺术加工而丧失。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无比纯净的语言,这是寻常记录者不易达到的境界。如果说书中打上了大作家的印记,就是这几乎看不见的纯净。”[5]为师作为一门艺术,亦如卡尔维诺的整理编撰民间童话,尽可能多地保持并显现学生个体的质朴天性和他们自主成长的可能性,而尽可能少地打下教师个人刻意改造学生的烙印。最大限度地促成学生生命的自我成全,恰恰是对教师自身生命的成全。
四、儿童本位与全力的解放:走向教师精神的自觉
苏步青这样描写当时浙大数学系的生活:“由于当时浙大规模不大,数学系每个年级不足10人,所以,我们师生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春秋假日,我们跟学生一起登山远游,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黄龙洞,杭州四郊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和陈建功先生都喜欢喝酒,学生中能喝酒的也很多。在送旧迎新的‘吃酒会上,酒酣耳热,陈建功先生放开喉咙唱起绍兴的家乡戏《龙虎斗》,我则用法语高唱《马赛曲》,一闹就到深更半夜。”[6](P61)这段话可谓切中了好的教育展开的基础,那就是师生的平等交往与共同生活。
与此同时,当时浙大数学系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才,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从而在浙江大学数学系树立起严谨治学的学风。“记得当时有一个从上海到浙大念书的女同学,过不惯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学没几天就溜回繁华舒适的上海,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看电影,串亲戚,会朋友。后来在父母的催促下才回校上课。我知道这件事后,一进教室就点名叫她上讲台演算习题,算不出不准下台,让她一直在黑板前‘挂了一个多小时。从那以后,她全部心思都用到学习上,后来成了一位物理学家。”[6](P61)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苏步青作为教师的行为,也许有些不合时宜,譬如形容女学生花枝招展,中间略有贬意,在黑板前“挂”了一个多小时,也有体罚的痕迹。但其中隐含着重要的教育理念:我们强调教师要坚持儿童立场,以生为本,绝不意味着放任学生,更不是迎合学生,而是合理引导学生内在发展的要求。关爱学生与对学生的合理要求并不矛盾。“任何教育实践都不是随心所欲,有责任感的教育实践,需要站在儿童心理发展的高度,站在历史、文化与时代的高度。”[7]
不管是关爱学生,还是严格要求,都是有所指向的,那就是积极地促成学生发展。学生的健全发展乃是教师行动的内在准则和根本出发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时代的教师精神问题,换言之,我们时代需要倡导什么样的教育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孕育出了体现现代教育特征的儿童本位理念,鲁迅写于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谓儿童本位教育理念的代表。鲁迅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相信生命需要得到发展,年轻一代的生命应该胜过年长一代,这样社会才会进步,日新月异。父母对于子女有一种天性的爱,“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8]这里说的牺牲,并不是指的教师要如何埋头苦干、不知疲倦、带病工作,只讲奉献、不求回报,而是指我们在任何师生交往的过程中,始终能有一种切实的理解儿童、服务儿童、成全儿童的教育理念与行动。牺牲自我,乃在于尽力地教育,尽力地成全,尽力地解放,以促进生命与社会的进步,这依然是我们今日需要仰视的精神品格。我们在续接西方民主、平等教育理念的同时,其实也需要续接五四以来的教育精神血脉。
显然,这里的儿童本位理念,并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对儿童的溺爱,简单地顺着儿童,过度呵护,这样的结果恰恰导致儿童自我解放的不可能,也就是被过度围裹、保护起来的他们,无法独立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合理做人,幸福度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恰切地理解儿童的内在需要,引导这种需要,成全这种需要;面向儿童发展的可能性,让这种可能性逐渐成为现实。
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学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精选中外优秀人文作品百余篇,力图对学生们的“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9]。四川成都新都—中语文教师夏昆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脚踢开,告诉每—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9]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9]。这些教师的特点就是不是简单地面对现实而教,而是面对现实的阙如而教,也就是基于他们的敏锐心性和超越习惯之上的教育理念而教。如果说教育乃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那么教师的行动就是在培植未来。这意味着教师的行动应该立足儿童未来的发展需要。教师不仅向着学生而教,同时也向着未来而教。
朱自清1924年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这样写道:“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要认真培养起来,那却谈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21]以教育为信仰,尽力地成全学生,尽力地解放儿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教育精神。
五、结语:你就是你的教育学:走向教师人性的卓越
学生让我们成为老师,显现为老师。向着学生而生,可谓教师生命的基本姿态。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把我们跟学生相处的每一刻,作为展现教师自我人性、丰盈教师生命意义的平台。
你就是你的教育学,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你自身,你的整个姿态,就是课堂影响力的源泉。教育作为一种信仰,教师宗教般的虔诚乃是课堂感染力的基石。优秀的教师,能倾听教师职业的内在召唤,全力以赴,不仅是为了学生,也是为了自我,为了教师人生的幸福。
参考文献
[1] 黄娟.网络环境下中学德育管理的困境与出路[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 [加拿大]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3.
[4] 鲁迅.导师(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6.
[5] 张宗子.旧梦遗痕书还在(二)[J].书屋,2012(6).
[6] 苏步青.神奇的符号[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7] 刘铁芳.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2.
[8]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5.
[9] 曾鳴,袁幼林.钱理群“告别教育”[N].南方周末,2012-09-13(01).
[10] 朱自清.教育的信仰[N].春晖(第34期),1924-1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