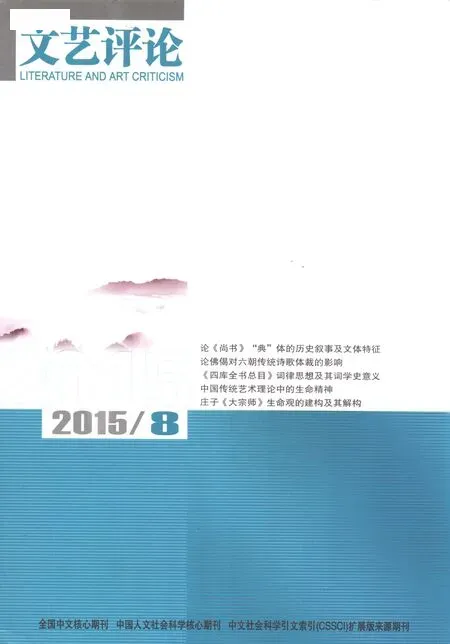庄子《大宗师》生命观的建构及其解构
李倩倩
文史新义
庄子《大宗师》生命观的建构及其解构
李倩倩
对《大宗师》的研究,前人多从天与人的关系方面入手,认为取法于“大宗师”的关键在于“以人合天”,即合乎“自然”,而反对“人为”。本文则认为庄子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其主要探讨的是认识论和存在论的问题,《大宗师》一篇亦是如此。本文试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来探讨庄子生命观的建构过程,并通过篇章结构的细致分析,指出庄子生命观又是一个不断解构的过程,因此,通过对《大宗师》的分析又有助于加深对庄子哲学思考方法的认识。
一
不可否认,庄子生命哲学的建立是由对人与天的认识开始的。《大宗师》开篇言:“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①对“知天之所为”和“知人之所为”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是知天、人这两者没有区别,皆为自然,故能任之,这是知之极至。如郭象:“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与众玄同,任之而无不至者也。”②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知天、人有分别,故能各尽其分,是为知之极至,如罗勉道:“知天之所为者,体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所为者,尽人事之当然也。”③显然争论的焦点是庄子的“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指什么,前者认为皆指自然,后者认为是分为自然和人事。其实庄子自己做出了回答,他说,“天之所为”就是“天而生也”,人之所为就是“以其知之所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也。”将这两句话中的“生”与“不中道夭”联系起来看,庄子在这里探讨的是生命为何存在与如何存在的问题,“天而生也”是说人的生命是因天而生的,人的存在是“天之所为”的结果,联系下文对“造物者”的描述,庄子是让人们看清生命的存在其实是很偶然的,人只不过是天地造化之一种,最终还是要归入造化中去。“人之所为”是对人的如何存在所提出的建议,那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努力养身保命使自己不夭折。因此,庄子“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是说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的由来与消亡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人却可以努力保全生命,使其过完这一生。故而罗勉道“体天道之自然”、“尽人事之当然”是符合庄子意思的,但是他没有说清楚庄子的“天道”与“人事”都是以生命存在这一问题为立论出发点的,不是抽象的,是有其具体内涵的,“天道”指向生命存在的根本原因,“人事”指向生命存在的责任,对这两者的认识是庄子生命哲学探索的开始。
保命养身由人来完成,而出生、死亡都有天来决定。庄子说认识到这一区别还是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是对天与人的联系的认识。他说:“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④“所待”指境遇。林云铭:“夫为知之盛,必待其终其天年,不中道夭之后,方见得是处。”⑤谓对生命存在的认识需要由死亡才能加以判定,而人的死亡又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怎么能判断我所说的天与人不是一体的呢,大概只有真人才能认识到要把生命的存在应与它的必然结果即死亡相联系起来思考吧。因此下文庄子用四段文字描述了真人的状态,其中最主要有两点,一是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⑥对于生与死这个由天来决定的事,真人只是安然的接受,从不用人为来干预。这是就人对天应有的态度来讲。二是真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⑦这是从人事的角度来看,虽然生与死无法选择,但是真人并没有否定生存的努力,因此不管他对刑、礼、知、德等世俗的好恶如何,他都能够做到与物无忤,与世谐行。“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天与人这两者各有其用,是同等重要的,清代陈寿昌说:“凡物偏用则相胜。真人任天顺人,妙协中和,性无偏执,故曰‘不相胜也’”。⑧这种“天与人不相胜”的认识论其实是为存在论服务的,庄子提醒我们,人类的存在必须与死亡相联系起来认识才是完整的。
二
庄子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进一步以寓言的形式形象的展开。每一个寓言都是独立的思想,代表某一种观点,这个观点不一定是庄子的,庄子只是将其作为反思自己思想的一个手段,但从不对这个寓言作判断,于是寓言和寓言之间构成一种相互消解的重言关系。重言者,“所以已言也”(《寓言》)。⑨就是在提出一种观点之后,紧接着又摆出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或是两行的观点,这两个观点之间是一种相互消解的关系。这是庄子表达自己哲学观点的主要方法,他从不在一个固定的立场上看问题,而是让寓言自己来说话,给人以深思。
“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四人”的寓言,提出了“物不胜天”的理论,它构成了对真人“天与人不相胜”的消解。这四个人都知道“死存亡之一体”,于是当子舆生病,子祀问他嫌恶吗,他说:“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⑩人之生是由造物者在其熔炉里铸成的,人的死是要归于熔炉里去重新融化,明白了这个道理,又怎么会嫌弃死亡呢,要欣然接受才对啊。但是偏偏有人纠结于死亡,不能做到安时处顺,由此带来命运的挣扎和痛苦,这是违背自然造化的一种表现。“且夫物不胜天久矣”,人事的努力是不能摆脱死亡的,这是被自古以来人类历史的经验所不断证明了的。这一理论消解了人全生保身的重要性,是对“天与人不相胜”理论的一种解构。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的寓言是对上一个寓言的再次发挥。子桑户死,孟子反和子琴张二人在丧礼上“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⑪。丧礼是人事的一个缩影,对丧礼的调侃对于儒家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庄子借孔子之口为自己的主张立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现。孔子说孟子反等人是游方之外的人,这些人是不遵从世俗规范的。原因有二,其一,在孔子看来“死生亦大矣”(《德充符》)⑫,生死是一件极大的事,而“游方之外者”视生、死如同一种病患的长消,这种认识消解了儒家对人的存在与死亡的严肃感;其二,“游方之外者”处于造物者的境界,逍遥于尘世之外,这种姿态是对世俗的一种超越。《天下》篇总结庄子的思想时说:“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⑬,孟子反、子琴张等“游方之外者”可以说是庄子处世理想的代表,他们这种违礼背俗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处世方式,毋宁说是庄子所构建的一种精神境界。因此当子贡问如何达到这种游方之外的境界时,孔子回答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⑭这种境界是通过对道的追求实现的。
人应该活在道中,这是庄子生命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⑮常感叹庄子思想的睿智,每当人生出现困境时就会想起这句话。我们太固执了,不愿意从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狭小的空间里走出来,还在做一些无谓的挣扎,这时庄子提醒我们:鱼本应属于江湖,生命本是属于道术,从现实中走出来吧,一转身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在等着你,那才是真正适于遨游的“江湖”。仅仅是这一转身的功夫就可以体会到道的存在,但对于人类来说何其艰难。上一个寓言所说的“物不胜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生命存在的执著,从而带来的对“道”的迷失。
庄子说能相忘于道术的恐怕只有畸人吧。“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⑯儒家以行仁义道德者为君子,而庄子说这些人按天的标准就是小人,真正的君子是孟子反、子琴张临尸而歌的违礼背俗的人,这些人是与造物者为友,对生死存亡了无挂碍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人与天之间,即世俗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庄子看来似乎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方内与方外、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同样构成了对“天与人不相胜”理论的消解。
三
庄子说物不胜天,生命存在的最好方式就是活在道中,使有限的生命进入到无限中去。但是,对生的欲求以及对死的恐惧似乎是人类的天性,同时也是他们的真情实感,怎么能克服呢?庄子在“颜回问仲尼”的寓言中,对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做了探讨。颜回对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的处丧方式表示质疑。⑰我们已经知道,庄子生命哲学是以“知天之所为”与“知人之所为”这一认识论为基础的,此寓言中孟孙氏“进于知”,就是说孟孙氏对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故而能做出这样的处丧行为。孟孙氏的“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世情抱有“简”的态度。儒家认为没有感情的守礼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孟孙氏“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的行为在颜回看来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伪装。但庄子却称这种行为是“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对于“简”字的含义,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从礼的角度来看待孟孙氏的行为,认为简是“省略、简化”的意思,就是说孟孙氏想简化丧礼却很难,但是他能做到不戚不哀,实际上已经对丧礼有所简化了。还有一种观点我认为更为符合庄子的思想,即把“简”理解为“不以小道害大道”的意思。⑱这是从情的角度来看待孟孙氏的行为,认为孟孙氏在死亡面前对自己的感情有所控制,从而不损害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不以情害道的表现,即能过做到“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也就是郭象注中说:“以变化为形之骇动耳,故不以死生损累其心。以形骸之变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为死。”⑲总之就是能坦然地接受死亡,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并不因过度悲伤而伤害到自己的身体。不因万事万物伤害自己是庄子人生哲学中重要的一方面,这其中就包括对由死亡带来的恐惧和悲伤的控制。在超越感情这一方面孟孙氏可以说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一个实践。
孟孙氏“知”的第二个方面是对生、死的看法是合于天的。庄子说:“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化已乎!”此处是说孟孙氏能够从“化”的角度看待生死,认为人生只不过是由一种存在方式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方式,即“孟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因此人不应该因生死问题介怀。林希逸:“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终始,不知端倪之意。顺造化而为万物,……听其自然,又安知将化、已化与不化哉?”⑳孟孙氏能站在造化的高度看待人世之生与死,所以他对丧礼也抱有超然的态度。
在孟孙氏这一寓言的末尾,梦与觉之间的区分又再一次出现:“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此又从认识论转化为境界论。郭象注:“所造皆适,则忘适矣。”㉑真正的适是不以之为适的忘的境界,即忘记梦与觉这两种方式,不去做区分,具体到存在论上就是不考虑生命从哪里来,又将归向何处,而是生命自然而然的存在,体验到所谓的“瞬刻永恒”㉒的境界。如果说“相忘于江湖”是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进入到无限,那么“瞬刻永恒”则是由时间中解放出来体验到永恒,这同样是一种合乎道的超脱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境界来说,孟孙氏所显示一种在人世而又超越人世的存在方式,并不是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忘记自己的超越,真正进入“入于寥天一”的无意识的状态。用梦与觉之不分的无意识状态来消解“孟孙氏特觉”,庄子在寓言的末尾对自己刚刚精心描绘的寓言进行了解构。
四
孟孙氏也许是庄子的一个理想存在方式,但是理想的并不一定是实用的,郭象在《庄子序》中评价庄子的言论说:“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㉓意思是说,庄子的言论超越了现实,虽然很高明,但不能实现。人的身体毕竟真实地存在于社会中,个体生命的完成必然要受到周围环境的制约,因此,真正做到孟孙氏这样游刃有余的人又有几个呢?阮籍就是一个“方外之士”,其母死“及将葬,食一烝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㉔就居丧而不拘礼教这一点来说,阮籍与孟孙氏相同,但是阮籍却因没有忘情,因此毁瘠灭性,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因此从形与神这两方面来看,阮籍都没有达到孟孙氏般保生的目的。
从梦与觉这一精神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说,旷达的苏轼亦感叹:“人生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㉕这三句是用孟孙氏寓言中“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之意。此日苏轼宿燕子楼梦盼盼,他日别人登临亦同样会抒发醒者对梦者的浩叹,因此古今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对爱情以及功名的执著是没有意义的。苏轼似乎从庄子这里得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梦的慰藉。但是“如梦”者,非梦也,人生如梦但毕竟不是梦,旧欢过去又有新怨,这一切多么真实,谁又能彻底摆脱和遗忘呢。人生就算是梦幻的,也是被深深地体验过的,庄子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孟孙氏的寓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寓言: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㉖
庄子发现他对人生存在的探讨还是离不开现实问题,就是说,认识到人还是在“有限”之内,而且进入“无限”的道的境界的方法好像也是终不能实现的。庄子的解脱理论在现实面前遭遇到了困境。因求之而不得,故庄子转向了对“命”的思考。在寓言的末尾子桑说:“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历来注者都认为“命也夫”是个判断的语气,因此觉得庄子是承认命的。如郭象认为:“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㉗林希逸:“然则使我至此极甚者,命也。”㉘林纾:“《大宗师》一篇,说理深邃宏博,然浅人恒做不到。庄子似亦知其过于高远,故以子桑安命一节为结穴,大要教人安命而已。此由博反约,切近人情之言也。”㉙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首先从语法上来看,要想表达肯定的语气,“命也”二字足矣,没有必要加一“夫”字,因此,“夫”字在这里不是句末否定,而是用以表达疑问语气的虚词,起到反诘语气的作用,可译为“吗”,因此,“命也夫”应该译为“这难道是命吗?”其次,从庄子思考的逻辑来看,他借寓言将所思考问题的各个角度都展现出来,但是不做判断,因为一旦观点被确定下来,它就会被作为和其他哲学观点相对立而存在,也就有了是非分别,这是与庄子哲学的整个言说立场相矛盾的。因此,对于命的思考也是一样,庄子不可能以肯定的语气表达出一种安命论的思想,而只能是通过反问的语气来提出这一问题,而它的解答则需要由读者来完成。故而,从反问的语气可以看出子桑是不愿意接受“命”这一事实的,因此庄子也是不接受命的,但是他没有下判断而是留给读者作进一步思考。
综观《大宗师》对生命哲学的思考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理论,明确了人顺天养身的责任,之后“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四人”的寓言打破了这一平衡,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以及道的无限性,紧接着又以孟孙氏的寓言通过体验“瞬刻永恒”对人走向道做了另一次尝试,仿佛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脱的希望,但是文章最后又用子桑的寓言否定了这一探索的可能性,对生命的反思竟是以“命也夫?”这样一种反问的语气结束,至此,庄子对生命存在的认识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思考生命的问题。因此,整个庄子生命哲学探讨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庄子以其特有的思想方法解决人生存在的问题,给人以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哲学启示,鼓舞着后人对生命的探索。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00089)】
①②④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⑲㉑㉓㉖㉗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9、229、231、234、239、941、265、273、195、1092、277、247、278、280、282、283、3、291-292、292页。
③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续修四库全书第956册,第158页。
⑤林云铭《庄子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⑧陈寿昌《南华真经正义》,光绪十九年怡颜斋刊本。
⑱李秀琴、黄笑山《〈庄子·大宗师〉“简”字释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
⑳㉘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9、124页。
㉒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8页。
㉔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1页。
㉕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7页。
㉙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