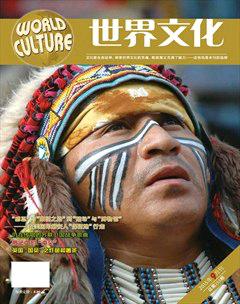为部落民抗争的女勇士
王春景
印度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独立后的宪法也规定了人人平等,禁止以宗教、种姓、民族、性别等任何原因歧视任何公民,废除不可接触制等,但现实是坚硬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痼疾很难被一纸条文治愈。在印度,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他们被称为贱民、不可接触者、野蛮的部落民,圣雄甘地曾称呼他们为“哈里真”(神的孩子)。在独立之后,宪法赋予其一个不带歧视色彩的称谓: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称谓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大部分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着主流社会的歧视,也忍受着极端的贫困。其中的表列部落,是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原住民,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都与印度教社会有所不同。独立之后,部落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他们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一方面不能再过打渔、狩猎这种传统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没有得到土地以及受教育的机会,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群。
独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在西孟加拉,出现了一位为部落民代言的女作家,她就是马哈斯维塔·黛薇(Mahasweta Devi)(1926— )。她了解到部落民生活的不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他们呼吁,在小说中让他们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她的文字使印度社会及政府再也不能无视这个边缘群体。马哈斯维塔为部落民的创作不是激情的一时兴起,而是坚持了几十年的事业。2013年印度斋浦尔文学节因为布克奖的介入受到广泛关注,马哈斯维塔受邀在文学节开幕式上讲话,她演讲的题目是《啊,再活一次》,体现了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经岁月洗礼依然浓烈的激情。
马哈斯维塔是著名的孟加拉语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走上创作道路,迄今已有20多部作品问世,其中很多作品被译为英语及印度各地方语言。知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她的英译者之一,她不仅翻译了马哈斯维塔的作品,还有大量的研究及访谈,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位孟加拉语女作家在西方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马哈斯维塔获得了包括印度文学院奖、莲花奖等多项重要奖项,2009年,还获得了布克文学奖的提名。
马哈斯维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斗争精神与她的家庭有直接关系。马哈斯维塔·黛薇生于达卡的一个富裕而开明的婆罗门家庭。她的祖父母是印度近代社会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曾与罗姆摩罕·罗易(印度近代之父)并肩战斗,她的父母都有较深的文学造诣,父亲玛尼什·戈塔克是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母亲塔里特里·黛薇是作家和社会工作者,叔叔瑞图克·戈塔克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马哈斯维塔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先后在维斯瓦帕拉蒂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在国际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在加尔各答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
马哈斯维塔的婚姻对她的生活及思想有更大的影响。1947年,她与著名的剧作家毕庸·巴达查理亚(Bijon)(1915—1978)结婚。毕庸是共产党员,他组织了进步的艺术团体,提倡把舞台搬到农村,其艺术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在独立之后,西孟加拉邦的左翼力量受到排挤的时候,毕庸失去工作,马哈斯维塔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她不得不为了糊口四处奔波。艰苦的生活锻炼了马哈斯维塔坚强的意志,也培养了她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65年,马哈斯维塔去比哈尔邦的帕拉姆(Palamu)采访,第一次接触到部落民。帕拉姆是比哈尔邦甚至印度最穷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基本上属于表列部落,历史上都属于猎户或渔人。印度独立之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他们不断被赶出世代赖以为生的森林、山区、河岸。而残存的封建的土地制度又使他们沦为地主的佃农或雇工,他们遭受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印度独立之后,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土地改革,1953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各邦也开始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制定本邦的土改法律。之后,各邦分别出台了保护佃农利益,废除租佃制度的法律。但是法律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很多地主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土地,钻法律的空子,而广大的没有文化的佃农根本无法保护自身的利益。
马哈斯维塔访问了很多村庄,还跟村民同住,看到了他们深重的苦难。马哈斯维塔在采访中发现,很多部落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向地主及高利贷者借钱,而他们又不识字,在地主及高利贷者们的操作之下,几年之后他们的借款就会成为一生都无法偿还的债务,很多部落民沦为奴隶(我国的印度作品翻译中曾把他们译为“白干”,一生为地主干活抵债)。很多村民没有土地,或者由政府分给了土地,却是非常贫瘠的山顶、林间的小块土地,仅供维持生存。在这些边缘的村落还存在着落后的租佃制度,大部分村民还被地主剥削,过着赤贫的生活。
部落民的悲苦生活感染了她,从此,马哈斯维塔走上了为他们呐喊的道路。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报道部落民的生活状况,创作小说《被占领的森林》《想象的地图》《乔迪·孟达和他的箭》《猎人之书》等,描写这些部落和贱民所遭受的来自高种姓的地主、高利贷者及腐败的政府官员的压迫,反思造成部落民悲剧的现实及传统根源。马哈斯维塔的小说以她的长期观察为基础,有着强烈的写实性,同时,又浸润了部落文化的神秘色彩。在《乔迪·孟达和他的箭》中,乔迪那如同被施了魔法的弓箭百发百中,象征着猎人部落失落的理想,也隐藏着被压迫者反抗的锋芒;在《稻种》里,杜兰那块巴掌大的田里长出的郁郁葱葱的稻谷,象征着即将在四处播撒的希望,也预示了那些埋葬在地下的斗士们以特殊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作为女作家,马哈斯维塔也非常关注部落民中的女性,她描写了部落民女性的非人的生活境遇。在存在种姓差别的印度,部落民的女性被当做高种姓地主及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她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任何保障,随时会受到侵犯。在这些村子里,地主家庭的成年男子,可以随意占有地位低微、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部落女性,她们若生下孩子,孩子依然是贱民。欠债的部落民,他们的女儿会被地主直接送到妓院抵债。地主家的孩子与部落民女性的爱情,给地主儿子带来的是一种谈资,给女性带来的是一生的悲剧(《多莉》);这样悲苦的生活,部落里的女人们却哭不出来,为了谋生,她们去地主家的葬礼上,为了地主家的体面,嚎啕大哭(《哭丧的人》)。马哈斯维塔以纤纤细笔,向不公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文化风俗宣战。在展示部落民的苦难生活的细腻和丰富方面,她的作品独树一帜。
除了以小说形式为部落民呼吁,马哈斯维塔还经常给当地政府部门写信,为部落民争取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斯皮瓦克和马哈斯维塔的一次谈话中,马哈斯维塔不无幽默地说:“每个部长那里都有我一二百封信。我对社会负有责任,虽然我并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但这种责任感是挥之不去的信念。而且我对我自己也必须保持这种责任感。我自问了千百遍: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吗?……在报纸刊物上的揭露非常必要。政府官员承认,他们害怕我。”
马哈斯维塔对部落民的帮助不仅仅停留在笔端,她亲自组织、领导了部落民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活动。首先她开展了对部落民的教育,因为长期以来,这些部落民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很多人都是文盲。她编写简单的课本,让这些部落民学习基本的书写和算术,使他们避免被地主欺骗;在她的帮助下,猎人们在1978年有了自己的组织“罗达组织”并进行了抗议活动;1979年她领导村民组织起来游行示威,争取土地权利,他们呼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废除土地租佃,土地属于耕种者,不属于游手好闲的地主!”政府迫于压力,逐渐地废除了土地租佃。她去德里为村民们联系一些经济项目,把村民们的手工艺品推向市场,解决村民们的经济问题。

马哈斯维塔把自己当做这些村民的一员,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那些部落的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大姐/迪迪”。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马哈斯维塔说:“我一有时间,就会为那些部落民、被蹂躏的人们、弱势群体战斗,为他们写作。”“我一直相信,真正的历史是由普通人创造的。我不断地翻阅那些普通人传承下来的不同形式的历史文本,那是经过岁月洗礼的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传说。我写作的理由和灵感是这些人们,他们英勇无畏,过去曾经失败过,但从不接受失败,对我来说,这无尽的创作源泉来自这些迷人的、高贵的、苦难的人们。当我开始了解他们,我何必去别处寻找创作素材?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他们的行为。”马哈斯维塔在整理部落民的口头文学,传承他们的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哈斯维塔用她的写作和社会活动,向祖国和人民表达着自己浓烈的爱,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为人人平等、丰衣足食这一朴素的人类理想而奋斗着。因为她对当代印度社会存在的政治、性别及阶级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介入,她成为备受关注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印度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马哈斯维塔出席了书展活动并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的创作》,她最后引用拉兹·卡普尔的电影《420先生》中的歌词作结,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是的,是这样的时代

鞋子是日本的,裤子是英国的
帽子是俄罗斯的
但心啊,我的心,
永远是印度的。
我的祖国
悲伤又破败,荣耀而美丽
她炎热,潮湿,阴冷,干燥
她就是灿烂的印度,
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