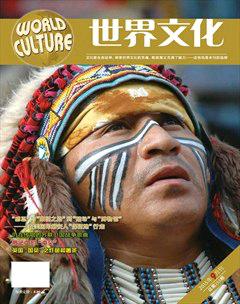慰藉平凡的生命
陈聪
华丽逆袭
1999年年初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一部名叫《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的小说在“游历”了法国大大小小十几家出版社之后,终于来到了它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Le Dilettante。一如它的书名,这部由不知名文艺女青年安娜·加瓦尔达完成的处女作终于“有人在什么地方等”它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小说出版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热销全法,之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二十七个国家发行,仅仅半年销售量就轻易突破了150万册。在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这部短篇小说集也博得了一向以挑剔苛刻闻名的法国文学批评界的青睐,安娜·加瓦尔达更凭借该书摘得2000年RTL读书大奖(Grand Prix RTL-Lire)的桂冠。从默默无闻的中学法文教师到法国文坛炙手可热的当红作家,安娜·加瓦尔达演绎的这场华丽逆袭才刚刚开始。

2002年,加瓦尔达推出首部长篇小说《曾经深深爱过》,此书一经问世便犹如一枚火种瞬间引爆全法,一股势不可挡的“加瓦尔达热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甚至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也公开承认自己是加瓦尔达的忠实读者。2004年,时隔仅仅两年,加瓦尔达的又一力作——长篇小说《只要在一起》惊艳亮相,并在全法国乃至全欧洲掀起了新一轮的阅读狂潮。这个围绕四个都市小人物展开,有关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平凡故事看似家常琐碎却暗含深意、感人肺腑。故事中的人物亲切熟悉得仿佛就是我们身边人:善良孤僻、蜗居阁楼的清洁女工嘉米烨,生活邋遢、情感放纵的餐馆厨师弗兰克以及口吃的菲利伯赫和多愁善感的老妇人波莱特,在同一屋檐下完美诠释了一个“只要在一起”就能互为依靠,相互取暖的温情故事。该小说经改编于2007年搬上大银幕,借助奥黛丽·塔图等一众电影明星的精彩演绎,加瓦尔达让很多从来不读小说的人“看”了小说。这之后,被法国出版界誉为“奇迹”的“加瓦尔达热潮”还在持续升温。沉积酝酿四年之后,2008年3月加瓦尔达携巅峰力作《慰藉》,再一次毫无悬念地轰动了法兰西文坛,总销量超过500万册的“传奇”让加瓦尔达稳稳地坐上了《费加罗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人如其名
1970年12月9日,安娜·加瓦尔达出生于法国上塞内省布洛涅—比扬古镇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计算机系统的销售人员,母亲从事品牌围巾的绘画设计工作。1990年,20岁的加瓦尔达就读于莫里哀学校,成为该校文科预科班的一年级学生,之后顺利考入索邦大学专攻法国文学。加瓦尔达毕业后执教于Nazareth中学担任法文教师。她曾嫁给一位不知名的兽医,离异后携两个孩子定居默伦小镇,单身至今无绯闻。一如“安娜”这个平庸又略嫌老旧的名字,加瓦尔达成名前的人生经历简单平凡,这让日后为她撰写“传奇人生”的编辑们感到头疼,曾有法国媒体捕风捉影地传出她再婚的消息,但是没过几天就辟谣说她仍是单身。后又有记者别出心裁地再爆“猛料”——传出“加瓦尔达已死”的重磅消息,之后谣言不攻自破,因为有人看见她“活得好好的”!
或许人们应该原谅媒体对加瓦尔达的穷追不舍,因为在法国文学界似乎有个悠久的传统:法兰西女作家们的血液里与生俱来就注满了反抗和叛逆。她们或荒诞不经或桀骜不驯,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会演绎出一段段令世人瞠目的戏剧人生。读者们会不自觉地有这样的联想,或许加瓦尔达会是法国文学史上另外一个“乔治·桑”:早在19世纪乔治·桑就借助其作品“妄言”婚姻迟早会被废除,并终日周旋于众多情人之间,肖邦、李斯特、福楼拜、缪塞、梅里美等数不清的才俊之士皆是她的座上客……又或许加瓦尔达会成为杜拉斯的“继承人”:才华横溢却又任性妄为,拥有离奇丰富的情史,终其一生饱受争议。然而,“对加瓦尔达抱有如此的期待,注定是徒劳的”。如果说法兰西文坛的众多明星女作家光芒耀眼恍若钻石,那低调谦和的加瓦尔达则触手温润犹如美玉。加瓦尔达面容清秀,却不施粉黛,并总以一袭旧衫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成名之后收入颇丰,但家中布置却极尽简朴,卧室里只有“一台能放录像的电视机”;因为“没有唇膏”,婉拒上镜,加瓦尔达以她特有的“法式幽默”一次次成功地逃避着聚光灯的关注。是的,她不是任何人的影子,她就是她——安娜·加瓦尔达。一个每日重复“写作——送孩子上学——购物”的寻常女人。从这一点上说,完全凭作品说话的加瓦尔达能跻身法国当红作家之列,当属实至名归。
文如其人
一如她的为人,加瓦尔达的作品文笔简洁精炼,语言朴实动人又不乏诙谐幽默。她将沉重的“人生真谛”寓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之中,凭借深厚的文字功底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悲喜剧之间。在洞悉人生无奈之余,加瓦尔达不忘借其作品向世人递送一丝温暖的 “慰藉”。

加瓦尔达擅长捕捉市井街头的小人物为原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着力解读普通人或可叹或可怜或可笑的悲喜人生。短篇小说《身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孕妇本来满怀欣喜地等待着小生命的降临,却在妹妹婚礼的前两天获悉胎死腹中,“但她不会把婚礼搅黄,为了别人,她自己的不幸可以再等两天”。在婚礼现场,她还不得不和别人客套,甚至在“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女人伸手摸她肚子的时候,“还挤出一个微笑”。是的,她能怎么做呢?打掉那个女人放在自己肚子上的手,对她说一个死胎是无法给她“带来好运”的,然后在妹妹的婚礼上放声大哭?小说的文字平实朴素,貌似信手拈来,却极富画面感地还原出人生最心酸尴尬的一幕。又如《年幼无知》中的德韦尔蒙太太,打电话的时候会故意把她姓氏的第一个音节“德”和后面的音节 “韦尔蒙”拆开来念,这样她的姓氏听上去就更像是“德·韦尔蒙”,以便使人误会她出身名门(因为在法国姓名中间的“德”多见于贵族姓氏)。透过形形色色俨然我们身边人的小人物形象,加瓦尔达轻而易举地拉近了作品和读者的距离,巧妙地触动了平凡人内心最隐秘柔软的角落,引发共鸣。
事实上,相比于那些惯用“骇人听闻的故事来哗众取宠的作家”,加瓦尔达更愿意于世人漠视的细微处落笔,穿过那些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小故事,透视现代社会浮华掩饰之下人们愈发暗淡灰色的灵魂。加瓦尔达的故事有着一种“观照生活的高远和穿透灵魂的力量”。比如在《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中,加瓦尔达这样不动声色地平铺直叙:男人念念不忘办公室秘书的胸部,但却从不越雷池半步。因为在出于好奇计算了离婚赡养费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女人知晓内情却无能为力,姿色尚存的脸上写满了对生活的厌弃。小说全文不见男人和女人的争吵冲突,两个人甚至没有一句对白。加瓦尔达本可以长篇大论这对名义夫妻的种种不幸,却反其道而行之,通篇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尤其末尾只淡淡一句“他们刚刚过了收费站,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此一句,我们就全然洞悉了芸芸众生身陷悲剧的无力感以及渺小人类在客观世界的荒谬处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瓦尔达的作品中故事的悲喜转化往往都在片刻之间,收放自如的加瓦尔达谙熟于这种悲喜剧的转换,既从容不迫又灵巧敏捷。其构思的“讨巧”之处就在于她知道在什么时候恰到好处地抖出“包袱”。在小说《跋》中她颇费笔墨地描绘一个无名作家“我”在接到出版社编辑邀约后无比激动的心情。然而突然降临的幸福转瞬即逝,编辑在赞美了几句“我”的小说之后,令人意外地抛出了“但是”两个字。剧情急转直下,“我”的小说纵有诸多优点却不能出版。失望的“我”甚至一度“瘫痪”,然后极具讽刺意味地被两个“跑腿”的人像抬轿子一样抬下了楼。小说情节在这里由喜转悲,相信这个貌似平庸的小故事在引发读者遐思的同时,更能轻而易举地唤起无数无名作家的“往事钩沉”。废寝忘食地写作,满怀期待地投稿,惴惴不安地等待,最后无一例外地石沉大海不了了之,这几乎是每个无名作家的必经之路。即使是被“法国出版界誉为奇迹”的加瓦尔达在成名前,也毫无例外地重复着这一命运,创作初期的她甚至连一封像样的“打印退稿信”都没有收到过。然而小说中的故事还没有落下帷幕,“我”被抬到楼下后“一跃而起”,因为幸运从天而降,“我”发现了一名美丽的女子!是的,即使被出版社拒绝也不妨碍“我”将“无与伦比”的文稿作为珍贵礼物,郑重地送给这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女孩儿。原本由喜而悲的故事在此峰回路转,可是加瓦尔达并未停笔,在距离小说末尾仅仅几行字的地方情节又一次逆转了,因为“我”猛然发现这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女孩儿竟然不懂法语!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加瓦尔达看似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将本不怎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写得格外曲折动人。
如果《跋》的故事止步于上文的尴尬结局,那无疑是个哀伤的故事。一部“无与伦比”的文稿,被明珠暗投给了完全看不懂法文的异国女子,总不免会令读者唏嘘。令人欣慰的是,作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加瓦尔达没有忘记在《跋》的最后一页上为我们留下一个小小的幸福的尾巴。文中的“我”本来想伸手要回自己的文稿,但是“后来……我又一想,那又何必呢……我的稿子今后将留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儿的手中……”行文至此,读者们不禁释然,最好的书赠予了世间最美丽的人,真可谓神来之笔,举重若轻地化解了“我”所经历的所有难堪绝望和郁结在读者心头的阴霾。一种“宝剑赠名士,良琴配佳人”的浪漫情怀从读者心底缓缓升起。故事以最美的结局于最动人处戛然而止……加瓦尔达早已优雅转身,留给万千读者的唯有她洒脱的背影,仿佛她就这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实则她早已俘获了万千读者的心,带走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潇洒结尾如穿透阴郁天空的第一缕阳光温暖了无数读者孤独无助的心灵,也照亮了平凡大众日益冷漠的灰暗灵魂。这个意犹未尽的喜剧小尾巴有别于自我麻醉的“阿Q精神”,实则体现了加瓦尔达在洞悉人生无奈之后仍愿以最大的善意,为世间孤寂心灵保留“希望”的美好愿望。
也许我们不愿正视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在现代生活潮流的裹挟下“阳春白雪式”的文学创作已呈江河日下之势。即使是在号称永不凋谢的法兰西文坛,纯文学创作也是高处不胜寒,很难获得大众读者的眷顾。而如火如荼的畅销书籍(诸如火爆全球的纪尧姆·米索、马克·李维等大众小说作家的作品),又往往会被自视甚高的法国文学界斥为“下里巴人”,归入 “次文学”(sous-littérature)之流。“littérature”在法语中意为“文学”,而“sous”在法语中意为“在……之下”,意思简单直白得不留任何情面,“次文学”(sous-littérature)是居于文学之下的,已非真正文学。更有部分热卖的类型小说被严苛的法国文学批评家直接冠以不入流的“快餐文学”的“恶名”。“高冷”的法国文坛对通俗大众文学嗤之以鼻,可见一斑。然而,加瓦尔达似乎是一道不一样的风景,在她的作品中既不见纯文学的“曲高”,也摒弃了大众文学的“媚俗”,在兼顾可读性与文学性上,加瓦尔达堪称当今法兰西文坛的一枝独秀。
入夜,辗转难眠。笔者又一次翻开了《只要在一起》,一行行熟悉的句子再度跃入眼帘。“很久以来,第一次,她(嘉米烨)对明天没有了顾忌……不是通常意义的明天,是今后,指未来的日子,将来的日子让她觉得……有想头”,“敞开了闸门,眼泪尽情倾洒在他的衬衫上……他(弗兰克)微笑着,生平第一次于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
有些书,我们一目十行,读了,忘却了……
有些书,我们一字十泪,读了,铭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