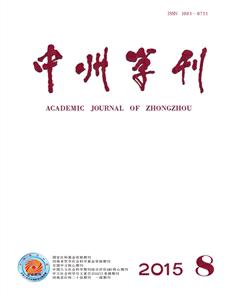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高 华 平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高 华 平
摘要: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荀子;诸子学;批评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和代表人物,历来都被视为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总结者。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但由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诸子”概念的含义,既非后来指称众多学者先生的“诸子”,也非如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指称与“六艺”(“六经”)相对的“诸子”著作的概念;而是或如《周礼·地官·司徒》中“对诸公、诸侯、诸伯、诸男言也”——指那些具有“子”爵爵位的贵族,或如《周礼·夏官·司马》“诸子掌国子之倅”中的“诸子”——指“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的概念①。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是如今人那样,将“诸子”理解为“众位学者先生”,由于当时的“学者先生”们是因其学术观念的不同而常被人分为不同的学术群体和门派(如儒、墨、名、法、阴阳等等)的,故当时他们也只有“百家”之名而不见“诸子”之称。可以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学者先生”虽众,但他们并未被称为“诸子”;因为他们是被分为若干学术群体或学派而出现的,故名曰“百家”。当时发生在中国学术界的激烈争鸣,不只是发生于那些单个的学者之间,而更主要是发生于一个个学术群体和派别之间,这就形成了中国先秦学术史上的所谓“百家争鸣”。而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所要总结的,就既是那些单个“诸子”们的学术思想,也是由他们所组成的学派或某“家”的学术思想。荀子思想的特点也因此可概括为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判与总结。
一、荀子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先生”们是分为若干个学术流派和学术群体的,故在当时他们只被称为“百家”,不被称为“诸子”,而后世则常常以“诸子”和“百家”并言,而“诸子百家”遂成为合当时“众多学者先生”和“学术派别”而言的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派别林立,“百家”显然只是言其多,而并非是对当时诸子学派的具体统计。《荀子·非十二子》是先秦时期批评诸子学派的名篇,它对它嚣②、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的学说,共分为六家进行了批判。后世或以为,虽然“《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之十二子,共分为六派:它嚣、魏牟为一派,陈仲、史为一派,墨翟、宋钘为一派,惠施、邓析为一派,子思、孟轲为一派”,“但如以后来所分家数核之”,则除“它嚣未详”之外,“魏牟即《汉志》道家之公子牟;邓析,《汉志》列之名家。子思、孟轲,《汉志》均列儒家……陈仲即《孟子》中之於陵陈仲子,史即《论语》中所谓‘直哉史鱼’……则仍不外‘儒’、‘道’、‘墨’、‘法’、‘名’五家而已”。③或以为,《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一为它嚣、魏牟……二子殆道家杨朱一派也。二为陈仲、史……近人谓陈仲、史,盖墨家、道家二派相兼之学,其说似也。(刘师培《国学发微》说)三为墨翟、宋钘……是二子皆墨家者流也。四为慎到、田骈……皆由道家入法家,所谓老、庄之后流为申、韩也。五为惠施、邓析,二子皆名家也……六为子思、孟轲,今世犹以为儒家钜子者……综荀子所非者六说十二子,所法者仲尼、子弓二子。以十家九流衡之,亦止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而已。”④其分别“家”数既有差别,而其所分别“家”数之根据仍在《汉志》“九流十家”之说,而非荀子本人对诸子学术的区分。
在荀子之外,先秦对诸子学说进行过全面分析和总结的,则要数《庄子·天下篇》和《吕氏春秋·不二篇》了。《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之人”道术“备矣”,但自道术分裂之后,天下便“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但《庄子·天下篇》中也没有说明所谓“百家”是指哪些学派。近人对《庄子·天下篇》所叙“周代之为道术者”进行分类⑤,但其所谓某人属某家某派之说,实乃后人贴上之标签,而非庄子其人之所固有。先秦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不二篇》有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诸语;《尔雅·释诂疏》引《尸子·广泽篇》有所谓“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囿”之说。后人以为,吕子将先秦诸子分举为“道、儒、墨、兵四家”;而《尸子·广泽篇》中的皇子历来无人知其解,料子顾颉刚等以为即是宋钘,《尸子·广泽篇》所论殆为儒、墨、道数家。⑥但这些亦非出于先秦吕氏、尸子旧说,而是后人所做的学派分类与归纳。
因此,我们可以说,凡言先秦诸子有多少“家”或多少“派”者,实际都只是后人的分析和归纳,而非先秦固有之观念。先秦学者只是统言其学者学派之多,而名之曰“百家”。在现有文献中,除《孟子·尽心下》称当时学术“逃墨必归之杨,逃杨必归之儒”、《韩非子·显学》曰“今之显学,儒、墨也”这两处所说“儒、墨”或“儒、墨、杨”有指学派之义外,其余皆无指称学派之例。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给先秦诸子分“家”分“派”者,实际要等到西汉初年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一文的出现。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此文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给先秦诸子分“家”的。它首次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派”,并对它们的思想特点做了初步的概括和说明。但严格地讲,司马谈此文虽然将先秦诸子分为了六“家”或六“派”——似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皆为诸子百家之一“家”,但他其实只是把法、名、道(德)明确称为“法家”“名家”和“道家”,而阴阳、儒、墨三者则被称为“阴阳之术”“儒者”和“墨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尽管2000多年来学术界从未有人对此做过说明,但我认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司马谈可能认为法、名、道(德)三者属于比较固定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而阴阳、儒、墨三者虽也有些人结成为学术派别或群体,但它们其实更主要是某种职业身份⑦,所以他就明确地称法、名、道三者为“家”,而称阴阳、儒、墨为“术”或“者”。
而在我看来,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者名称上的这一细微差别,至少还说明了另一问题,即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在春秋战国之际最早出现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然后则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然后才有法家、名家和阴阳家,以及以稷下黄老学派为代表的道德家等。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所谓诸子百家,其先可能只有儒、道、墨等少数几“家”,然后才涌现出许多新的诸子学派,而旧的诸子学派则或解散,或消沉寂灭,其学说则演变为社会上零散学者所习之“术”或一种身份。⑧
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的“六家”,还是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中的“九流十家”,既不表示这些学术派别和学术人物曾同时出现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更不表示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每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派别都不多不少,正好是“九流十家”(甚至多至“百家”)。同样,《荀子》一书中的所谓“百家之说”,既不表示当时的诸子学派真的多至“百家”,也不表示整个先秦中国的诸子学派(或至少其中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就是后人所归纳的“儒、道、墨、名、法五家”或“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而已”;而只是说,中国先秦诸子的学派虽然众多,但在荀子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乃是十二子所代表的六种学说。
二、荀子对先秦诸子的批判
《荀子·非十二子》最集中地反映了荀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和总结,历代研究荀子思想及中国学术批评史的学者,对此都非常重视,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前人多认为荀子是将诸子分为“六派”(“儒、道、墨、名、法五家”或“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加以批判和总结的。但经过对《荀子·非十二子》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正如荀子在此篇中所言,他批判的实只是诸子之“六说”——六种观点或学说,而并非学术流派或学术派别意义上的“六派”(“五家”或“六家”)。
其一,在《荀子·非十二子》开篇,荀子即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⑨云云。这已表明此篇针对的重点是“邪说”和“奸言”,而不是某“家”某“派”。而且,荀子在批判了十二子的学说和观点之后又说:“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大顺……六说者不能入,十二子者不能亲也。”“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皆只是明确地将十二子的学说归纳为六种观点(“六说”),而不是“六家”。
其二,从《荀子·非十二子》对“六说”中每一“说”所举的两位代表人物来看,这些人物本身的时代和思想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不可能形成为某个学术流派或学术团体;后世对这些人物的学派划分也往往存在矛盾。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存在所谓“家”或“派”,而只是因为他们在某一观点上相同或相近,《荀子·非十二子》才将他们合而“非”之。
《荀子·非十二子》所“非”的,首先是它嚣、魏牟。其言曰: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它嚣、魏牟也。
它嚣,尽管郭沫若以为他即是关尹,亦即环渊⑩,但其实并无什么根据;因而学界一般相信杨倞所谓它嚣“未详何代人”,是更稳妥的看法。而魏牟,当即《汉志·诸子略》道家“《公子牟》四篇”(班固原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之公子牟,属道家人物。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嚣、魏牟的观点应该是杨朱、詹何、子华子一系“尊生”“贵己”,以至于放纵情欲的观点。但因为后人对此处荀子所谓它嚣其人的时代都不清楚,所以对它嚣、魏牟二人是否属于同一“家”或同一学派是无法讨论的。
《荀子·非十二子》又说:
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
《荀子·非十二子》接着批判的,是墨翟、宋钘。其文曰:
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荀子·非十二子》接着说: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众,反紃察之,则倜然而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慎到、田骈二人之书,《汉志·诸子略》一在法家,一在道家,故也不属同一“家”或同一学派。《庄子·天下篇》叙慎到、田骈之学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法然无决,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齐万物以为首。”《汉志》法家的“《慎子》四十二篇”,现存辑本;《汉志》道家的“《田子》二十五篇”,则已完全亡佚了。从现有文献记载和现存《慎子》辑本来看,一方面《慎子·佚文》中主张“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臣》中说“官不亲私,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但另一方面,《慎子·佚文》又说:“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一断于法”的思想主张。所以荀子在此批评他“尚法而无法”,“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听于俗”,“倜然无所归宿”。但问题是,这些可能只是慎到的思想主张,而不等于田骈也是如此。《庄子·天下篇》在说慎到“齐万物以为首”之后,只是说“田骈亦然”,即只是强调了他们都有“齐万物”的思想,而无一言及于“法”。《吕氏春秋·不二》曰:“陈(田)骈贵齐。”《尸子·广泽篇》曰:“田子贵均。”也都只是强调了他们有“齐万物”的思想,而无关乎“法”。所以似可以说,先秦学者之所以将慎到、田骈合于一处加以评论,全因为二人“齐万物”的主张,至于在“尚法”问题上,则二人未必一致。荀子也不过沿袭了当时学术界的惯例,而将二人合而“非”之。但正是在其所“非”之点上,二人恰恰是并不能视为同一“家”或同一“派”的。
《荀子·非十二子》接着又说:
不法先王,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惠施、邓析二人书,《汉志》虽同列于“名家”,但惠施略与庄子同时,为战国中期学者;而邓析当生活于春秋子产时代,早于孔子——此时诸子学派尚未产生——二人不可能成为同一“家”或同一学派的学者。故荀子只是从惠施、邓析二人都喜欢“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多事而寡功”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学术批评。因为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惠子多方”,其学术本相当驳杂,其核心概念是“大一”“小一”“大同”“小同”之类,“徧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所以荀子对他有“好治怪说,玩琦辞”的评语。《荀子·不苟篇》并把《庄子·天下篇》惠施与人辩论的“山渊平,天地比”(《庄子·天下篇》作“天与地卑,山与泽平”)、“钩有须,卵有毛”之类“说者难持者也”,以为“惠施、邓析能之”。但《庄子·天下篇》及现存先秦文献并没有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作“无用”之辩的记载,因为邓析虽如刘向《(邓析)叙录》中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非常明确,是为了教人胜讼,故《吕氏春秋·离谓》说当时“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而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固春秋末期法家先驱也”。这就说明,荀子在此合惠施、邓析二人“非”之,只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存在“好辩”“善辩”这一点。
《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十二子”中的最后两位,是儒家的子思、孟轲二人。其言曰: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世俗之沟犹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子思、孟轲可以说是“十二子”中独有的两位确属同一学派、并且有师承关系的学者。《汉志·诸子略》儒家类有“《子思》十三篇”(原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可惜多有亡佚。《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以为《礼记》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后世《子思子》辑本也主要依此辑成。但如依今存《子思子》辑本和《孟子》七篇而论,“在哲学上,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孔丘的‘中庸之道’”,“提出‘率性’以行的方法”,“以‘诚’为核心”而“使‘天道’和‘人道’相通,并把二者统一起来”;孟子思想则主要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以性善论为中心的“仁政学说”。这也就是说,其实荀子在这里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并非思、孟哲学思想的全部,甚至可能还不是他们的主要哲学思想。荀子之所以在此将思、孟合而“非”之,也并不是着眼于二人同属于儒家学派或二人是否存在师承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二人所提出的“五行说”在当时有太大的影响,“误导”了世人,以至于“世俗之沟犹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引起了荀子对“郑、卫乱雅”的担心,故荀子才对思、孟大加挞伐。
正因此,我们似可以得出结论说:《荀子·非十二子》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共分六组加以批判,都并不是由于他们在学术上属同一“派”或同一“家”,而只是着眼于其行事或思想主张上的某种相同或相似点而立论的;如果某二“子”具有相同的思想主张或行为特点,即使他们的时代相隔很远,也不属于同一“家”或同一“派”,荀子也会将二“子”合而非之。
也正因此,《荀子·非十二子》除了对十二子及其观点进行尖锐批评之外,对儒家的子张、子夏、子游之徒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懦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引郝懿行之说称荀子对子张氏、子夏氏和子游氏之儒的批判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张之貌而不似其身,正前篇所谓陋儒、腐儒,故统谓之贱儒,言在三子之门为可贱,非贱三子也。”这实际也证明了我们上文所说《荀子·非十二子》所“非”并非其人及其学派(“家”),而只是他们所代表的某种思想主张或观点。
除《非十二子》一篇之外,《荀子》书中对先秦诸子点名道姓加以批判的,还有《儒效》篇对慎到、墨子、惠施的批评,《富国》篇和《王霸》篇对墨子之术的批评。《臣道》篇曰:“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议兵》篇曰:“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前者之“所谓篡臣也”,皆见于《战国策》,当属战国纵横家者流;后者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实乃后世所谓“兵家”。这说明荀子批评的锋芒所及,已至于纵横家和兵家。《天论》篇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信(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多。”《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两篇所批评的先秦诸子更多,而且同时指出其“所见”和“所蔽”(或者说其所长和所短),很具有“二分法”或“折中”的意味。《解蔽》篇又曰:“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空石之中有焉,其名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又曰:“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涉及儒家的曾子、孔伋、有子(若)、孟子。《成相》篇曰“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祥)”,“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又涉及慎到、墨翟、季真(王先谦引韩侍郞曰:“或曰:季梁也。”)、惠施等。《正论》篇批评宋钘“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之说;《礼论》篇批评墨者“薄葬”使人于礼、义“两丧之”;《乐论》篇批评墨者“非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性恶》篇批评孟子的“性善”之说为“无辩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岂不过甚矣哉”。这些都明确地批评了诸子的学术观点,立场鲜明,针对性很强。在《修身》《荣辱》《儒效》《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中,则分别对名家的“坚白、同异之察”“无厚、有间之说”以及“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等“用名乱实”“用名乱名”或“用实乱名”的“治怪说,玩琦辞以相挠滑”的行为和“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作了不点名的批判。这还不包括《大略》《宥坐》《法行》《哀公》《尧问》等篇中,记孔子及其弟子事迹时所包含的对先儒的“点赞”和评价。
三、荀子先秦诸子批评的时代特点及其成因
从上面我们就荀子对先秦诸子批评的回顾来看,荀子的诸子批评是与其所在的时代诸子百家之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一,荀子的学术批评虽然几乎涉及当时诸子百家的所有学派,但他的批评实际上又是有所侧重的,即使是对同一诸子学派的批评也是如此。对于道家,他同时批评了老子、庄子、它嚣、魏牟等众多学者,但对老、庄则只有“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伸)”和“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两句批评。而对道家学派或道家思想史上可能并不十分重要的魏牟等人,则有专门的批判,对他们的“纵性情,安恣睢,禽兽行”,反复地予以抨击。对于儒家,荀子对孔子、子弓不遗余力地进行歌颂,而把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了子思、孟轲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贱儒。如果结合《韩非子·显学》篇所谓“儒分为八”之说来看,尽管荀子时代儒家的派系很多、学者甚众,但荀子其实只是选择了其中的某些派别和某些学者进行批评的。
其二,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六组十二位诸子学者的思想观点与行为时,虽然在批评开头毫不客气地抨击了其“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或“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不可以为纲纪”等,但在抨击之余,则必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肯定自己的批评对象亦有其合理之处。《天论》《解蔽》二篇在批评诸子之学时,也采用“有见于”“无见于”和“蔽于某”“不知某”的形式评判诸子,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学术批评中的独断论和以偏概全。在当时,这都是独一无二的和难能可贵的。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之所以会形成上述特点,既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是与先秦诸子学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战国中后期思想史和诸子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决定了荀子诸子学术批评的基本特点。
尽管学术界对齐国稷下学宫创立的具体时间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却都承认,齐稷下学的第一次兴盛应该是在孟子尝游稷下的齐威、宣时代,即《风俗通·穷通》所谓“齐威、宣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齐稷下学的第二次兴盛,则应该是在荀子活跃于齐国的齐襄王时代,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用胡适句读——引者注),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卿之后,则为战国的终结期,荀子之学由韩非、李斯演变为纯粹的法家。
荀子所生活的年代,诸子之学较之其前后皆有很大的差异。在荀子之前的孟子时代,诸子之学最为兴盛的是儒、墨、杨(道)三家。《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尽心下》又曰其时天下学术:“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乃是孟子所在时代稷下学术的基本面貌。孟子所说的儒,自然是指孟子本人所属的儒家。孟子在当时势力很大,《孟子·滕文公下》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车食于诸侯。”但此时的儒家除了以道统自任的思、孟一系之外,同时还有与之在人性论上立异的告子一派。《孟子·告子上》载告子曰:“生之谓性”;“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王充在《论衡》中曾说:“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分于善恶,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无分于善恶也。”而朱熹所说“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如荀子性恶之说也”则是有失偏颇的。但由朱熹的看法我们也可看出,儒家学者是倾向于把告子与孟子在人性论上的区别看作是儒家内部关于人性论的争论的。而由孟子与告子的辩论,又可见儒家确乎属于当时的“显学”。
儒家之外,则为杨、墨。杨,指杨朱;墨为墨翟。《庄子》书中亦多称杨、墨,并多将杨朱写作阳朱或阳子居。《庄子·骈拇》曰:“骈于辩者,纍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唐成玄英疏:“杨者,姓杨,名朱,字子居,亦宋人也。墨者,姓墨,并墨徒,禀性多辩,咸能致高谈危险之辞,鼓动物性,固执是非。”这是把杨朱也归入墨家。《庄子》中《应帝王》《山木》《徐无鬼》诸篇则称阳子居,世人皆以为即是杨朱。钱穆认为“杨朱辈行较孟子、惠施略同时而稍前”,生卒年约在公元前395年到公元前335年之间;而蒙文通则从道家思想发展演变历史的角度,认定杨朱之学当由北方列子道家而来:“则杨氏之学,源于列御寇,而下开黄老。”由此可以看出,杨朱学派应属先秦道家的一种特殊形态。《孟子·滕文公下》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同书《尽心上》曰:“杨氏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和《吕氏春秋·不二》“阳生贵己”、《淮南子·汜论训》“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诸说完全一致。可知杨朱的“为我”乃是“贵生”,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私自利,而实际是对老子所谓“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之养生思想的极致发挥,即《淮南子·汜论训》所谓“全真保性,不以物累形”——不使自己的本真受到丝毫的损害,从而实现养生的目的——而这明显是属于道家养生派的主张。所以成玄英所谓杨朱属墨徒的观点是不对的,孟子时代“盈天下”的,实为儒、墨、道三家。
在荀子之后,以稷下为中心的诸子学中兴盛的则主要是儒、墨两家,这从《韩非子·显学》对当时学术的评述中可以见出。《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这就是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之说。很可能当时道家杨朱一系演变为它嚣(或即詹何)、魏牟、子华子之流的“纵性情,安恣睢,禽兽行”之后,因受到荀子等人的猛烈批判已走向衰亡,而道家的主流则与法家合流,成为慎到、田骈直到韩非等的黄老之学。(亦即所谓“道法家”。《史记·韩非列传》称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正以此。)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在孟子与韩非子之间。由《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之先秦诸子来看,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如果按后世“九流十家”的观点进行分类,实为儒、道、墨、法、名“五家”或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而已。《荀子》一书当然有很多批判“小说家”的地方,如《正论》中批评“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等。但“小说家”乃不入“流”之一“家”,实不在诸子百家之列;且如宋钘其人,《荀子·非十二子》将他合墨翟而“非”之,谓其学术“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易、县君臣”,故学者多将其归于墨家。而刘《略》班《志》所谓“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定义,则为诸子思想传播之纯形式特点,与其思想内容实无必然联系。故可以说,荀子所批判之诸子百家,如果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实只有儒、道、墨、法、名五家而已。
而且,在这五家之中,至少道、法两家之间已明显具有合流倾向,故自古即有“黄老道家”(或“黄老”)和“道法家”之名。《荀子·非十二子》合慎到、田骈而“非”之,但在《汉志·诸子略》中“《慎子》四十二篇”(班固原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在法家;“《田子》二十五篇”(班固原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在道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则曰:“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将他们同时归入“黄老道德家”。而近代郭沫若也认为:“慎到、田骈的一派是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的。”
综合来看,荀子时代的诸子之学的发展出现了两大特点。其一,当时的“显学”较稍前的孟子时代或稍后的韩非子时代都有不同。孟子时代的“显学”是儒、墨、道(即杨朱),韩非子时代只有儒、墨两家,而荀子时代则有儒、墨、道、名四家;而且此时的道家已由早前的杨朱演变成“黄老”或主要为道家与法家合流的“道法家”;“名辩”则已由一种辩论的方法而独立成“家”,变成了名家。《荀子》一书除了《非十二子》中合惠施、邓析而“非”之之外,还在《修身》《儒效》《正名》等篇反复批评了惠施、邓析的坚白、同异之论,特别是《正名》一篇,历代注家皆认为该篇乃因为“是时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故作《正名》篇”,即是为了批判名家而作。其二,当时的诸子百家各家的学说之间界线日渐模糊,明显有走向综合的趋势。从宋钘学说或归于道家、或归于墨家,慎到、田骈学说或归于道家、或归入法家,以及诸子皆有名辩倾向,就可以见出这一点。
荀子时代诸子学发展的新的历史特点,也正是荀子本人诸子学术批评之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此时儒、墨、道、名四家是学术界的新的“显学”,故荀子也就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他们;而于其他诸子学派,如农、杂、纵横、阴阳之类,则很少置评。又因为此时诸子百家之说有明显走向综合的趋势,特别是在稷下学宫中“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德之术”盛行,各家各派的边际日渐消融,有时很难分辨一位学者思想属于何“家”何“派”,所以荀子在开展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时,主要并不着眼于学派或“家”的划分,而是针对某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论——即使某两位学者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派(“家”),如果他们有某种相同的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荀子也会将他们合而“非”之,放在一起进行批判。
注释
①参见罗焌:《诸子学述》及其所引《周礼郑注》,《诸子学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②它嚣,郭沫若以为即关尹,亦即环渊,都是老聃的学生。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36页。这是不对的。学术界一般以为它嚣“不知何时人”,而环渊与关尹、老聃都没有关系。参见高华平:《环渊新考——兼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及该墓墓主的身份》,《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③蒋伯潜:《诸子通考》,岳麓书社,2010年,第9页。④罗焌:《诸子学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⑤罗焌:“首为墨翟、禽滑釐。禽为墨之弟子,则皆墨家也。次为宋钘、尹文。《汉志》载小说家《宋子》十八篇,名家《尹文子》一篇,则二子盖形名而兼小说家也。次为彭蒙、田骈、慎到,《汉志》《田子》列道家,《慎子》列法家,惟无彭蒙书。据《庄子》云:‘田骈学于彭蒙。’则三子者乃由道家而流为法者也。次为关尹、老聃,皆为道家。次为庄周,则道家之别派也。又次为惠施,附以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皆名家也……然则《庄子》所陈,凡十四子,实止儒、墨、小说、名、法、道六家而已。”见罗焌:《诸子学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⑥参见萧萐父总编、李德永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93—496页。⑦前人早已指出“儒”“为有学识之士之通称,不专指儒家而言”。见蒋伯潜:《诸子通考》,岳麓书社,2010年,第10页。故刘向《孙卿书录》曰:“秦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进城后半部,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韩非、李斯为法家,亦得称儒。可见“儒”乃职业身份。阴阳、墨亦可类推。⑧蒋伯潜曰:“诸子之派别家数,乃后来评述者各就其主观的见解所分析之异同,归纳而得者……诸子之家名亦后人所定,非各派开祖先立一学派名以资号召者。”见蒋伯潜:《诸子通考》,岳麓书社,2010年,第10页。⑨“文奸言”,原作“交奸言”,但依上文“饰邪说”看,“交”当是“文”之形近而讹,“文奸言”即“饰奸言”,作“交”者误。⑩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52、141、233、144页。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91页。《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淮南子·道应训》都载有魏牟(中山公子牟)与道家詹您可论养生之事。《庄子·让王》载:“中山公子曰:‘在江海之外,心居魏阙之下,奈何?’瞻(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不能自胜也。’瞻(詹)子曰:‘不能自用于则纵之,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纵,此之褢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学界一般以詹何所论“自纵”,即是魏牟所持“纵情性”爬坡说。参见高华平:《同詹何看先秦道会众思想的发展演变》,《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关于慎到、田骈的学派归属,历来看法多有歧异。《庄子·天下篇》以彭蒙、慎到、田骈为同一派,郭沫若认为:“慎到、田骈的一派是把道家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的。严格地说,只有这一派或慎到一人才真正是法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314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索隐》曰:“王劭以‘人’为衍字,则轲受业孔伋之门也。”但不管孟轲“受业子思之门”或“子思之门人”,思、孟之间存在师承关系是可以肯定的。参见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5—151页。郭沫若认为“空石之中”的“觙先生”,“所影射的正是子思”。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27页。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4年,第284、695页。蒙文通:《杨朱学派考》,《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687年,第267页。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411页。
责任编辑:涵含
作者简介:高华平,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中古代中国哲学资料分类辑校与研究”(11AZD0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11BZX049)。
收稿日期:2015-04-03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8-0102-08
责任编辑:思齐
【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