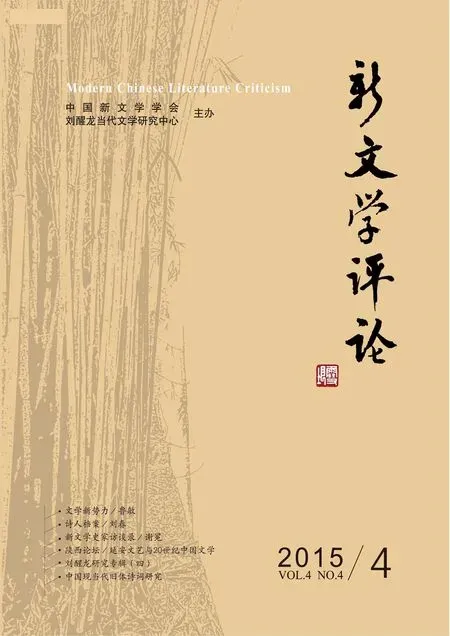鲁敏的“记忆”叙述和“70后”的文化语境
◆ 王 军
鲁敏的“记忆”叙述和“70后”的文化语境
◆ 王军
集体记忆,是留存一个时代独特性的重要方式,类似的经历、情感和价值把一代人捆绑在一起,并塑造出他们的存在形态共同体。在文学领域,集体记忆是很多作家共有的思想资源和生活积累,正是在集体记忆的旗帜下,我们区分出了作家不同的代际和群体。但是,一个代、群的集体记忆,必须也只能通过个体来呈现,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却与集体记忆形成了错位关系,它至少表现为两种不对称现象:首先,集体记忆不是由个人记忆按照简单的加总原则构成,而且即使是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记忆也各不相同,因此二者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相等,个人差异很可能导致集体记忆的离散化而缺乏核心特征;其次,由于语言内在的局限性,个人经验的语言叙述不仅不能书写出确定性的集体记忆,甚至可能会是对集体记忆的改写。这两个方面的“错位”让我们对集体记忆和个人体验的同构性产生了疑问,我们现有的记忆叙述模式能够把差异化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融合起来吗?
对鲁敏来说,个人体验和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构成了鲁敏文学实践的核心内容,对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鲁敏也有非常个人化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和很多“70后”作家类似,鲁敏的个人记忆叙述一方面被认定为其价值之所在,一方面又成为这一代人“集体记忆匮乏”的证明,这样的结论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错位关系的疑问,因此,探究鲁敏小说的记忆叙述方式,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解开这个纽结,并发现“70后”作家代际特征的一个渠道。
一、“人物”和“叙述”:个人经验的独特化
在物理性空间的意义上,鲁敏已经相当成功地在小说中给我们展示了两个地域环境,一个是她的故乡“东台”,一个是她十四岁后的生活地“南京”。相对而言,鲁敏似乎有意识地弱化了时间性的代际身份和公共经验,而试图凸显空间性的个人经验,并由此来达到一种超时间的境地,她的思考颇为辩证:
个人的体验和记忆,寒无疑问,是局限性的,但这局限,我想正是其价值与力量所在。我不认为,在某个时代,人们共同经历了革命与杀头、改制与下岗、买房买车或是离乡打工,这就是公共经验与公共记忆,就会唤起读者的呼应、就代表了所处的时代与人心。那换一个时代呢?换一群读者呢?我想这是一种媒体化的、所见即所得的思路,而不是文学价值或特质所在。我所理解的广谱化的公共经验,既代表了时代又超越时代的,其实正是一些最基本的人类体验,比如,新旧交替、物质与精神、宿命感、撕毁美好之物、性、死亡、信仰的幻灭、对阶层与身份的追求或拜托,等等。
按照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出鲁敏的写作意识定位,在个人、时代、超时代人类经验三个因素中,个人和超时代各执一端,地位凸显,而最具有代际特征的时代境况最为漂浮,个人通过体验和记忆,穿过时代的漂浮之境,抵达超时代的目的地,那里有最普遍性的人类体验。
这种思路并不鲜见,以审视的姿态保持与飞扬现实的疏离,寻求人生的永恒,是沈从文和张爱玲在革命和救亡之外开拓出的新路,也正因为那对于“恒久”和“安稳”之望,他们才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历史韵味。在他们之后,这条道路有很多跟随者,能够不被湮没而另辟蹊径的关键,在于个体如何通过各自的方式到达那些普遍经验之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是鲁敏最具有个人特征的选择,那么,她是怎么完成个人经验道路叙述的呢?
《墙上的父亲》发表于2008年,但是这篇小说却可以看作鲁敏小说的“核”。基本上,鲁敏小说的母题之一,就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羽毛》、《死迷藏》、《六人晚餐》、《此情无法投递》等作品,和《墙上的父亲》一起,构成了“父女”关系(或稍有变异的“父子”关系)的相关性文本。因为个人的独特经历和内省意识,鲁敏在“父亲”和“女儿”这一主题上的感知投射极其巨大和深入,所以她能够写得格外酣畅淋漓,不断通过新的细节来丰富并推动这一主题,最终把它变成了自己小说中的一个基本情节模式,虽然父亲的缺席或在场可以随机变化,但“我”的世界却因为父亲而被改变和塑造。
这个情节模式无疑属于鲁敏个人体验的叙述之一,但是更有鲁敏特征的,是在这个情节模式中展现出了两个相配合的层次。首先,由于经历和理解父女关系中的个人创伤经验,鲁敏对创伤性人物给予了集中性的关注。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鲁敏小说中很多人物似乎是弗洛伊德心理体系中的“期望病人”。这些“病人”的主要病症是“恋父情结”:在《墙上的父亲》中,父亲在世时对家庭的背叛和对女儿的忽视,给渴望父爱的女儿们制造了巨大的阴影,父亲死后,妹妹王薇无限执着于吃,而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物,姐姐王蔷的自卑感,转化成了对邻居女孩的痛恨,以及对婚姻的功利主义立场,在她们身上,时间停滞在父亲照片挂到墙上的那一刻。短篇小说《羽毛》写青春期的“我”窥探到了父亲对女同事郝音的秘密感情,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去诱惑郝音的丈夫穆医生,来推动父亲完成他的表白。斯佳对继父的迷恋,成为长篇小说《此情无处投递》故事的原动力;《六人晚餐》里的“父亲”时隐时现,牵动着晓白和晓蓝的一举一动。更加弗洛伊德化的因素,是小说对性意识的微妙展现。向母亲献殷勤的男人,有着运动员式的体格和浓密的汗毛,它们引起了少女王蔷的性想象;斯佳和继父之间的肌肉游戏,成为斯佳的性启蒙,因为接近于乱伦而被继父的理智所拒斥时,斯佳在另一个男人的手指中感到了性报复的满足,而看到做爱的继父和母亲时,斯佳对继父的爱慕解体了;晓白对丁伯刚家床的想象和试图一探究竟的欲望,唤起了四个小辈共同的破坏冲动。有关心理疾病、性想象、梦的几乎每一个情节都好像在为弗洛伊德的案例提供样本,分毫不差。但是,鲁敏小说中的心理分析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那就是这些心理病症都不只是呈现出来然后交给读者去体验的,它们已经在作品中被有意识地当作了病症,成为一个“被返观”的对象,人物对这些精神异常状态在读者之前作出了解剖:王蔷让她的妹妹去看心理医生,K医生条理清晰地解释了王薇的病症,顺便也把王蔷解剖了一遍;陆仲生一直相信儿子是纯洁的,在暗中发现斯佳同性恋趋势的时候,终于把这个结果想象成是他儿子的罪孽;“我”意识到自己就像一个导演在主宰父亲和郝音、我和穆医生的关系,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了详细的心理注释。
在这个情节模式的基础上,鲁敏小说的人物世界也在发展和扩张,创伤性人物的面孔不断丰富,比王蔷、王薇更具有心理、精神乃至人格特殊性的人物频频出场,他们已经不再节制地躲藏在种种温情的遮挡之下,年轻的东宝无比实诚地照顾半身不遂的痴子兰小,并让兰小怀孕了;朴素的乡村最终扭曲了裁缝师傅和徒弟的同性关系;晓白身上的模糊性意识;斯佳则似乎陷入了“性”的漩涡,她在性的搅拌机里无所依傍……“于是,在笔下遭逢那样的人物,那些极端的、变异的家伙,有着去社会化的举止与行动,孤意追寻人性深渊里的阴影,逆流而上的,去往冷僻的黑洞……”,这些极端和变异的人物如此密集地出场,仅仅用鲁敏关于父亲的单一个人经验,已经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了,它表现出的,是鲁敏的一种美学意识,是对极端性人物价值的集中确认,鲁敏和这些人物不是偶然巧遇,而是有意相逢并互相深入。从个人经验的根基上生长出来,通过思维和情感的扩张代谢,鲁敏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人物世界,也获得了自己的审美关注和发现方式。
其次,和人物选择相配合的,是鲁敏的“叙述”选择,对于这些极端和变异的、去社会化的人物,几乎只有一种方式去接近他们,就是通过最微妙的心理、情绪和无意识。在这点上,鲁敏把个人体验再次凝结提升成一种成熟的认知和写作方式,她承认,自己对于个人记忆有着执着的偏好:
对这些皱褶里的幽暗处,我一直是存有贪念与野心的。我总想着,要尽其所能地触碰、搅拌、逼视,我喜欢临近人性的深渊,看那崎岖的风光——不是因其美,或者只是因为其中有酷烈与温情、绝望与妥协。
这种对记忆的偏好自然地融入了小说,可以发现在《墙上的父亲》和《六人晚餐》等作品中,非常明显地出现了时空上的双结构,现在/过去,现实/回忆,穿插回环,过去的回忆向周围蔓延,向深处推进,它要抵达的是鲁敏的目的地:对人性的审视。而从叙事的角度来说,丰富的回忆还发挥了一系列的功能:它建构了一个心理发展的逻辑线索,从对父亲的回忆里,王蔷感受到父亲对家庭的忽视和逃离,从而解释着母亲和王蔷姐妹一切行为和情绪的源头;它也制造出了浓郁的氛围,在回忆小时候玩镜子反射阳光的游戏时,王蔷感受到了巨大的荒诞感和孤独感;它还形成了对照和起伏,老温和女儿,是方甜和她爸爸的翻版……回忆,不是现实之外的第二个世界,而是整个就和现实搅和在一起,不分你我。假如没有回忆,这些小说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关于父亲的记忆,是鲁敏小说的起点和基础,但如果仅仅只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其局促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个人记忆和生活无论如何幽深,也必然会显示出它的末端,它的有限空间无法容纳一个优秀作家的思想栖居,突破这个空间局限,就意味着向外在社会空间扩张。在鲁敏的小说中,这个趋势也逐渐显现,父亲和女儿的形象虽然没有迅速弱化,但更广阔的社会性事件频频出场,它们附着在家庭故事之上,成为很多小说重要的背景,比如《此情无处投递》中1984年的“严打”,《六人晚餐》中的“迈皋桥爆炸”。但是,这种突围是否意味着叙事方式也必须同时转型,用一种客观叙事来代替心理叙事呢?这个问题对鲁敏很重要,因为一直以来,由于父亲和女儿的宿命性关系,以及通过内省提取的经验,鲁敏小说最擅长的,是深入大脑“褶皱里的幽暗处”,通过变化万端的感官去把握和体验世界,她甚至表达过对感官能力某种类似崇拜的感情:
相信我一次:感官是万能和无所不知的。……情人们的暧昧床笫,诡计者的复杂手势,绝望者的清澈泪水,这一切的一切,只要发生了,存在便是告知,他们便会产生气味与声息,使空气颤动,使光线交映,他们将被他者的感官在偶然间捕获。秘密不复是秘密,它会开成一朵繁复的花——这便是感官的表达方式和控制手段,它让世界透明,变形,危险。
鲁敏不是没有意识到,记忆和感官是一把双刃剑,很刺激,也很危险,既因为个人的记忆和感官能力有限,又因为人类意识和无意识的世界无限广大而且漂浮不定,作家在创作中稍有感官捕捉的失败感,以及世界稳定感的丧失,就会对小说和作者都带来难以想象的虚无影响,所以,弱化记忆、感官和心理叙事,对鲁敏来说可能会更少曲折和迷失,但更大的可能是,鲁敏也会因此而抛弃了“自己”。
虽然经历了自我否定的痛苦,但鲁敏几乎没有多做犹豫,她选择的是执着于探究这个无限世界,并找到自己的道路,一方面鲁敏更多地进入外在空间,关注更多具有社会性的事件和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延伸回忆和感官的触角,继续深入个人的内在世界,把个体记忆推进到群体记忆和更多样的人性世界。而鲁敏的小说叙述,也在逐渐完成独特化的进程,她经常采用的一种“多棱镜”式的多重叙事方式将第一、二、三人称视角纠缠在一起,将每个故事、每个人物的心理纠缠在一起,在这样的融合中,鲁敏小说的心理描写显示出了一种极致之美。
独特的人物世界和叙述方式两个层次融合在一起,构成了鲁敏最重要的个人经验叙事,也确立了鲁敏的美学立场,她在谈到她笔下的人物时,引申到对小说本质的思索:“这也许不能算是‘自然’和‘可爱’的小说……写小说又不是做生意,不必投机于固定的审美,也不必循着旧传统四平八稳。冒险、自由、乖张,这难道不是我们选择小说的理由之一吗?”小说不是满足或迎合,而是冒险和自由,这样的人物和叙述给读者带来的一定不会是愉悦感,但是鲁敏的关注和追问,对于当代小说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一块意义拼图。对于鲁敏来说,这也是她确立自己道路的根基。
二、“独白”和“对话”:价值调适的文化语境
除了地域空间,鲁敏也构建了人物和叙述两个文本空间,如果把这两个方面都想象成一种空间化存在的话,那和这个空间世界同时存在的时间性,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把鲁敏放到一个更开放的代际背景中,它首先被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内容:鲁敏是如何通过个人叙述完成集体记忆书写的?她的个人叙述如何显示出“70后”的代群特质?
如前所述,相比空间的明确性,鲁敏小说的时间代性身份是较为模糊的,辨识度并不高,她似乎不仅不想凸显自己的时代身份和公共经验,反而对此形成了略带抗拒的态度,这种姿态有时甚至渗透到情节中:
——一些往事就是这样,一个人时只会自斟自饮,成了苦酒;而一旦变成集体记忆,事情就滑稽起来,就会笑场。哈哈哈!她们相互取笑,毫无良心的添油加醋,并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闹中迅速而愉快地失去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墙上的父亲》)
个人经验的内在独白被扩张成一种“共在”的集体记忆时,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形成互相融合的“同在”,没有完成对事件反思和情感融合的推进,而是解构了独白的内省意义,解构了记忆和事件本身。在这个情节中,个人经验被集体记忆分解了,个人时间被集体时间融化了。这些,正是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之间错位现象的表现。
然而,在同一篇小说中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细节,它似乎摆脱了鲁敏的控制,进入了人物自身的经验里:
王蔷闪闪烁烁、欲扬先抑地跟对方谈起父亲的事情……对方的惊讶与感叹从不会让她失望,并且,父亲的悲剧与玄虚开始转移到她身上,她好像就此获得了某种特别的气质,与家世有关,与成长有关等等……王蔷相信,在对方眼中,她会被另眼相看,她的一举一动会显得异乎寻常。
很难说这算不算一种对虚荣的追求。王蔷认为,一个人,为了取得与众不同的特质,为了在人群中“出挑”,任何手段都可以谅解,况且她并没有撒谎。她没有父亲,只有父亲的故事。(《墙上的父亲》)
这里揭示了个人进入集体之中,完成集体性的精神“同在”的过程,个体原有气质被集体记忆的化学作用所改变,个人经验迅速递进到一个时间的新阶段。当然这个过程不是简单顺利的精神“同一”,而是充满了障碍,但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使个体与他人、个体与自我交杂在一起,既形成了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又建构出了一个对话的语境。在王蔷的内心活动中,失去父亲是一个悲剧,但是因为叙述悲剧而获得关注则使悲剧变成了喜剧;追求虚荣的行为虽然不够高尚,但是作为人的本性,为了一个合理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谅解的;只要不撒谎,利用一个故事,用怎样的方式利用又有什么紧要呢?在和集体记忆的相互进入中,个人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方在无言地审视,另一方则在井井有条地辩解,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著名分析,在这个情节中似乎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再现。通过自我对话,达成价值调适,去社会化的个人体验找到了进入集体记忆的合理渠道,反过来又赋予了个人体验以新的内容。在独白的对话性转换中,个人时间摆脱了封闭状态,进入了一个整体性的循环系统。
作为现代小说的核心特征,意识和无意识的呈现成为比故事更重要的部分,“向内转”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方式,独白无疑是其中之一。从本质上说,独白是为了呈现自我而存在的,它指向孤独感。但是,在鲁敏那里,独白改变了它的本质,成为对话,成为理解。从王蔷的心理和解,从“我”在犯下幼稚的错误之后还在想象郝音的原谅和父亲的宽宥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更典型的是《此情无处投递》,小说写1984年“严打”时期,大学生陆丹青组织了一个舞会,在那里他遇见了斯佳,两个年轻的身体试探着深入接触的时候,邻居带领公安破门而入,陆丹青被当作流氓逮捕并枪毙。以此事为转机,他的父亲陆仲生和斯佳开始了不同的人生。鲁敏有意尝试用两种字体设置了两个文本系统,一个是主要人物的故事和心理活动;一个是死去的陆丹青和活着的陆仲生的各自独白,两个系统穿插进行,互相推动。在第一个系统中,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打通了外在故事叙述和内在心理叙述,而第二个系统中,本来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的自我心理过程,却不断地转向了对第二人称“你”的关注,“我”和“你”完全融合在了一起,陆仲生失去儿子的痛苦,转化成对儿子为什么会这样的询问和探究;陆丹青描述自己心路历程的过程,则不断地进入对父亲的回应和对斯佳的爱中。展现自我的独白,变成了关注对方的对话,“我”变成了“我”和“你”,而孤独感也最终获得了某种宿命般的人性升华,陆仲生寻找斯佳,斯佳感应着陆丹青,并意识到陆仲生对她的寻找,最终她和已经失忆的陆仲生坐在了一起。《六人晚餐》的结构同样进行了精心设计,小说围绕两个残缺的家庭,六个各有心思的男女来展开,在两个家庭互相结合又分离的过程中,纠缠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小说分别以六个人物作为六个章节叙述对象,每个人物都在叙述圈里被叙述,叙述自己,也叙述他人,每个人的叙述都在丰富、推动着属于集体的整个故事前进和深入。这种多棱镜式的叙事不是把每个个体分离开来,不是强化每个人的孤独感,而是把他们聚合在一起,互相补充和流动,让每个人的孤独变成被理解的孤独,变成了“对话”式的语境和个体时间性的“同在”。
除了理解和“同在”,对话的功能还表现为自我反思性的存在,在鲁敏小说中,极端性人物不是不自知自身的极端性,她们往往意识到了自己的无意识病症,并有目的地进行着调适,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精神病医生的出场,《墙上的父亲》王薇和王蔷都得到医生的诊治,《六人晚餐》里的晓白也多次与医生交流,这些细节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改变了人物的命运,而是显示出了一种对话的意味。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由医生诱发的病人认识过程,可以理解为病人的自我反思过程,医生的分析具有直接的治疗效果,从而唤起病人重新占有了那一部分生活史,并取消分裂过程。医生作为自我反思的符号出场,代表着孤独者走向了对话和敞开。
这种把独白和对话融合在一起,把个体时间放置到集体时间中去认识和调适自己的意识,是一种具有“70后”代际特征的因素吗?我们尝试着做一个对比,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是同性别、相似创作阶段、类独白式叙述方式,而以文学传统、对话性为重点的代际差异则是我们要描述的目标。50年代的王安忆和残雪,60年代的陈染和海男,都是相对比较擅长于心理独白式叙述的作家。她们之中,残雪的独白体最为抽象和极端,即使是在最密切的父母和子女亲情关系中,也充满了隔绝和疏离,可以看到残雪与存在主义思想、卡夫卡式现代主义文学的紧密联系;王安忆的现实主义心理叙述非常复杂,独白话语更具多样性,尤其是《小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对“性”既渴望又抗拒的态度,《叔叔的故事》里“我”不断进入并试图理解“叔叔”的叙述,都非常接近对话语境,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走向自我调适,而是分离和不妥协,王安忆绵里藏刀式地坚持着她的意义立场,所以,《小鲍庄》多线索之间隐藏着反讽结构,《小城之恋》双独白叙述中显示着对抗性,《叔叔的故事》中“我”对叔叔的观望姿态,把叙述者有效地和人物分离开来,这种多重独白叙述是一种主体对另一种主体有距离地审视;海男《人间消息》独白的自我程度接近残雪,区别在于更具有抽象和象征意味弱化,而个性和女性性别特征凸显出来;陈染的很多故事有稳定的人物共同体式结构,比如《无处告别》中的缪一、黛二和麦三,但在这种类女性情谊情节中,独白主体只有一个,其他人则是被叙述的客体,“我—她者”的意味是明显的。在王安忆和残雪的小说中,焦点是个人背后的人类历史境遇,是文化和人生的总体意义以及普遍性的孤独感,集体时间的大框架中包容了个人时间,但独白主体各行其道,并立而不妥协;而在陈染和海男的小说中,焦点在前景,在个人身体、意识的自我性,独白叙述视角是单一化的,个体时间拒斥着进入集体时间。从代际特征来说,“50后”女作家关注普遍性,其文学传统和80年代之前强大的现实主义和经典现代主义有关;“60后”女作家是个人化的,其文学传统受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影响巨大。
和她们相比,“70后”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是差异、对话、反思,这些语词进入了鲁敏们的内心,进入了她们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是那些她们偏爱的极端性人物,即使她们喜欢采用接近孤独的独白体,也写得和前两代作家不一样,通过自我对话、多重视角叙述、个体和整体之间的价值调适等等,去社会化的人物走向了社会化,差异走向了融合。如果我们把鲁敏小说和“70后”代际特征描述为独白中的对话和自我反思精神,描述为个体时间进入集体时间的调适和妥协,她们似乎脱离了普遍性和个人性的绝对主义,进入了相对主义的文化语境。这些经验并不是在鲁敏一个人身上存在。卫慧的《上海宝贝》写的也是在“性”意识上具有非社会化的人物,但“我”对性的非道德化立场、与母亲从对立走向和解的状态,以及心理医生的出场,也许能够说明价值相对性和对话语境的在场;此外,李洱的《花腔》采用了三个人物叙述同一个事件的叙事方式,和鲁敏的“多棱镜”叙述异曲同工。如果把这些“70后”的小说和卡夫卡《城堡》的主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时间变换、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的叙事方式作为一个文学系统放在一起,我们是否看到了“70后”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更多元化的文学资源和传统,“50后”、“60后”比“70后”更早接触到这些庞杂的东西,但是在“70后”身上这些东西融化了,“70后”的作品和人物不仅仅只用一种声音说话,他们已经开始习惯多种声音的“同在”,这是属于多元性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语境。
三、缺席和在场:“70后”的集体记忆问题

得出“70后”没有集体记忆的结论,可能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上都稍微简单了一点,但是如果把集体记忆当作某一代际内部高度认同的、以一些核心意象为中心、有某种确定性价值追求并得到了完整“叙述”的整体性,那么“70后”确实缺少一面鲜明的旗帜,就像“50后”的理想主义、“60后”的个人意识那样。但是“70后”表面上的“集体记忆匮乏”,是否也可能是另一种获得?在他们成长的经历中,虽然受到80年代的流行文化、90年代市场经济、文学边缘化和作家队伍的流失等多种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共同价值没有成为一个确定性模型,但是,对多元性的渗透,对相对性的领悟,却使人数有限的“70后”作家队伍,慢慢展现了外形分散而内在包容性非常强大的气质。以确定性缺席作为包容性在场的符号,这是“70后”的文化事件。在这个文化背景中,我们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的理论张力,理解鲁敏小说的人物、主题、叙述和精神,并找到对“70后”作家的把握渠道。



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空间和时间,人物和叙述,独白和对话,普遍性和多元性……这些二元对立因素呈现出一种结构主义式的张力,在鲁敏小说中存在,也作为我们理解鲁敏以及“70后”作家的文化背景而存在。在鲁敏和很多“70后”作家的小说中,我们能够感知到一种共同的温情,在那些极端的、变异的、去社会化的人物和故事的对面,还有一种体悟和触摸;在那些现代主义和符号化了的叙述中,还有一种传统性的情怀。这种温情来自于差异、对话、反思和理解,它们可能会因为多元包容性而缺乏终极性意义、确定性魅力和批判性力度,但它们也可能是鲁敏和“70后”作家对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集体记忆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②鲁敏:《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9页。
③鲁敏:《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8页。
④鲁敏:《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⑤鲁敏:《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⑥鲁敏:《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⑦[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一、李黎译:《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⑧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11页。
⑨刘莉:《70后、80后新锐作家创作综论》,《大家》2013年第5期。
⑩谢有顺:《“70后”写作: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单位: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