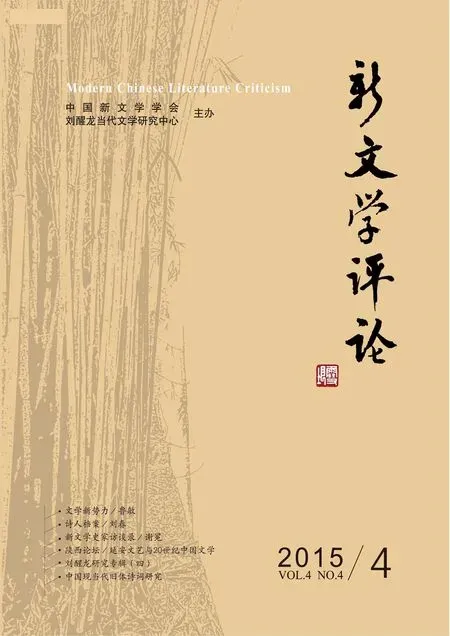情爱·窥视·话语
———关于鲁敏都市书写的三个关键词
◆ 张光芒 杨有楠
情爱·窥视·话语———关于鲁敏都市书写的三个关键词
◆ 张光芒 杨有楠
鲁敏曾多次表达自己欲以“小说之虚妄”来抵抗“生活之虚妄”,这似乎是在表明,本性即为虚构或者天生就在撒谎的小说是虚妄的,另一方面,外表真实的生活其实亦是虚妄的,而鲁敏的写作就产生于两者的博弈之中。这种类似于“负负得正”的欲念是否已经实现,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鲁敏创作文本及其话语流程所流露出的审美旨趣已然显示出,两种“虚妄”在剧烈的对抗中所产生和积聚的能量的确赋予了鲁敏巨大的创作热情。自1998年开始执笔为文的鲁敏,其作品不仅数量多、体裁多样,而且内容也展现出较大的包容性。正如程德培所言,鲁敏是一个“‘胃口’很好的作家”,“她好像什么都想写,什么都敢写”,因而“她的创作总有点庞杂”。但综而观之,其“庞杂”的故事倒也有脉络可寻,基本上离不开两个场域,即作者“托生的乡野”和“寄居的都市”。尽管以故事背景作为作品分类的依据显得过于传统,但在鲁敏的审美世界中,城与乡实在是相差甚远的两副模样。如果说“东坝”是鲁敏建造的一个人的乌托邦,那么都市就是人性幽微的展示厅。显然它们是鲁敏用两幅笔墨叙述而成的。已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东坝”那些美丽得接近谎言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服人,最得益于作者用心讲究、不苟且的叙述方式。相对而言,都市故事中的深刻思想则往往更引人注意。这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鲁敏都市小说书写方式的鲜明特色与创造性。通过细读文本,我们认为鲁敏对都市故事的形式构建与思想挖掘同样重视且着力甚深,这里拟以提取关键词的方式发掘鲁敏都市书写中故事与叙述互动的独特性。
一、 情爱:“在场”的缺席者
对于爱情,鲁敏直言不讳地道出自己的不信任与幻灭感,这甚至曾导致一篇关于“爱”的长篇小说的夭折,因为她深感“我没法去写一个我不确信的东西”。不过,在我们看来,鲁敏因不确信而写不下去的应该是那种“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式的完满爱情,而爱情的存在形式和可能性显然并不只此一种。因之,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鲁敏那些以都市为背景的故事中,就会发现情爱非但没有退场反而几乎是常驻的角色。即是说,情爱成了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所谓“在场”是指它是鲁敏都市书写中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对象;而所谓“缺席”则意在强调鲁敏对纯粹的、真正的爱情的怀疑态度。因而她笔下的爱情大都带着相似的假面,即虚无、脆弱、无所附丽。
电影《推拿》中的都红曾说:“没有哪个女人是看不见爱情的。”爱情,作为一种生命本能和精神需求,在那个与所谓“主流社会”相疏离的空间里实现了素朴的流淌,人人都有追求爱的需求与权利。鲁敏在自己的都市故事(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渴望“看见”爱情的女人,如《李麦归来》中的李麦、《爱战无赢》中的中年女人姚一红、《镜中姐妹》中的小双、《细细红线》中的“她”等。然而,她们无一例外地在鲁敏的审美世界中走向失败的终点,并最终无奈地意识到所谓“心心相印的甜美爱情”,“或许,那本来就不存在”(《细细红线》)。如果说十七岁便为爱而死的小双还能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伤怀、悲剧之美,那么其他那些逐爱失败的女人则更让我们看清爱情终究缺席的尴尬。在叙述这类故事时,叙述者的感情流露出既矛盾复杂又清醒理性的双重性。一方面出于对爱情的渴求和幻想,叙述者将同情流露于笔端,甚至还时常与故事中舔舐着伤口的女人一起唏嘘、喟叹;另一方面对爱情始终怀疑、不信任的态度又促使作家主体从不忘记在已然灼痛的伤口上撒下粗粝的盐巴,逼迫她们直面可怖的真相。如此看来,或许对爱情浅尝辄止便倏然而逝的小双才是受到鲁敏恩赐的人,因为她终不必像“她们”那样在挣扎过后仍退回到无爱的宿命里。
爱情是注定缺席的,无爱是当今生活的常态,这几乎成为鲁敏都市故事的底色。于是,两种背离也就在此基础上顺其自然地生长出来。首先是爱情与婚姻/家庭的背离。相较于以上那些渴望、追逐爱情的女性,鲁敏塑造了更多委身于现实的人,他们或是在千疮百孔之后终于看透了爱情的泡沫本质,或是从一开始就笃定爱情的虚无,抑或是出于纯粹的物质需要,最终都殊途同归地奔赴一场无爱的婚姻、一个畸形的家庭。《墙上的父亲》里的母亲、姐姐王蔷、妹妹王薇坚信“任何与爱情有关的念头都是天真的罪行”。她们是没有爱情,也不奢求爱情的三个女人。父亲去世之后,家庭随之陷入困顿,如何填饱肚子,早日摆脱十九平方米的小房子成为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主题。于是母亲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容貌和寡妇身份,适时吸引男性帮忙解决生活中的不便;妹妹王薇则依赖一段段恋爱满足自己对“吃”的欲望;姐姐王蔷更是渴望借助一场婚姻将整个家庭带离困境。需要注意的是,王蔷选中的结婚对象——那个能够在物质上获得母亲认同的老温,同样是出于现实的考量而接纳了王蔷以及她的母亲。于是男人和女人各怀鬼胎地一起投入一段无爱的婚姻里,而且彼此心知肚明。因而在通往婚姻的路途中,爱情不是必需品,各取所需的便利才是。
同样,《六人晚餐》中渴望逃离旧厂区的晓蓝最终舍弃与丁成功的朦胧情爱而与建筑公司老板黄新结婚。如果说丁成功试图以玻璃屋的建立圈禁并坚守自己的纯情还能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些许暖色,那么当丁成功在因爆炸而破碎的玻璃屋里绝望自杀时,我们就分明而清晰地接收到了作家主体试图传达的意旨:爱情不过像玻璃,简直脆弱到不堪。
这种没有爱情做黏合剂的家庭和婚姻在鲁敏的都市书写中几乎随处可见,《白围脖》、《取景器》、《百恼汇》、《镜中姐妹》、《转瞬即逝》……尽管多数家庭表面上尚还留有一口气,终不至分崩离析,但是作家又以另一种方式披露了它事实上的溃败,即婚外情和出轨的普遍发生。可以发现,鲁敏的都市故事中似乎存在着一场由爱情主导的没有止境的“逃亡”,先是因为爱情的虚无(如《转瞬即逝》中的田荷所言“如果没找到爱情,那就索性现实到底”)而躲进婚姻/家庭,然后又因不甘于此而逃出婚姻与家庭的围城。不过,这仍然不是鲁敏爱情叙述的终点,随之而来的是与爱情相关的另一种背离。
其次是爱情与性的背离。《细细红线》中的“她”是一个陷入荒芜婚姻的女人。人到中年的她渴望扭转年轻时功利的婚姻观念,于是决心重新出发寻找爱情,从而发展出一段婚外情。然而“她”爱上的“他”却只同意以“不搞恋爱”为前提进行交往,并直截了当地宣称“肉体至高无上,应当直接抵达,无需以精神为导线来曲径通幽。直线,即是最正确的方式”。逐爱失败并最终重新退回到无爱泥潭里的“她”终于看清,就像通往婚姻的路上可以没有爱情的出场,性也同样不需要爱情。如果说“她”的出轨还缘起于对爱情的奢望,那么鲁敏笔下的大多数婚外情则从起步之初就与爱情无甚瓜葛。长篇小说《百恼汇》简直可看作是一副婚外情的荒唐浮世绘,姜宣、姜墨、姜印三兄弟的出轨皆非出于形而上的爱情渴求,在这里性仅仅是三人逃离当下生存困境、发泄精神烦恼的渠道和出口:姜宣借其摆脱强势妻子的压制,姜墨借此治好了自己的性功能障碍症,姜印则不仅借以发泄多种不满,最终还戏剧性地靠一场出轨表面上修复了与妻子的婚姻关系。
《转瞬即逝》中的田荷和林海也都坦诚彼此之间“没有点滴的爱恋”,他们所投入的只是偷情本身。特别是《白围脖》中忆宁与崔波之间的婚外情明显带有游戏的性质。表面上看来,与丈夫王刚之间的沉闷关系、母亲对私生活的多加干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忆宁从婚姻/家庭中的出逃,但细读文本即可发现,对已逝父亲越轨行为的有意模仿似乎才是忆宁出轨的更重要的导线。而崔波出轨的原因则更加荒谬,仅仅是为了报复同样出轨的妻子。这样游戏化的,或者说宣泄式的性观念不止发生于婚外情的关系中,甚至普遍地存在于生活的多个场域。《正午的美德》中的大四女生圈圈渴望借性打开烦闷生活的缺口,《亲吻整个世界》中的女大学生将性作为交换工作机会的筹码,《杜马情史》中的杜马则以性证明自己的男性尊严……性与爱的分离已经昭然若揭,“大家都不会爱了。只会做爱”(《白围脖》)。这显然与“肉体的肉欲化的禁忌”在当下时代的相应松弛有关。这可以看作鲁敏对社会现象的部分捕捉,但又不止于此,她的小说叙述更进了一步,不留情面地刺穿了这种性关系的脆弱性。例如,在仕途之春终于到来之时,《百恼汇》中的姜印和《转瞬即逝》中的林海都果决地切断了自己与情人的关系。如果说“爱及其要求的持久的、可靠的关系以性欲与‘情感’的联合为基础”,那么这种情感缺席下的性欲的解放终究与爱无关也注定短暂易逝。于是那些从婚姻/家庭中逃出的人必将再次触礁。性不是无爱的出口,也终究不是“逃亡者”可久居的飞地。
需要注意的是,作家主体对待婚外情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是颇值得玩味的。“直到现在,对各种此起彼伏、大同小异的出轨情状,我有着不太确定的心态,像是根本无所谓,偶尔也会来点道德洁癖,更多时候,觉得那根本就是落在人生之上的灰。生而为人,完全的不落灰,或许也是不真实的吧。”这种在主流价值观看来颇有不妥的态度也时常流露在文本之中,而与之相关的往往是鲁敏小说中另一个较为突出的关键词:父亲。如果说情爱是“在场”的缺席者,那么父亲显然就是“缺席”的在场者。在《墙上的父亲》、《和陌生人说话》、《盘尼西林》等作品中,消失的父亲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起点,甚至还逐步深入地影响着事态的走向。但父亲显然还有另一个象征的可能性,即逝去的爱情。《六人晚餐》中晓蓝的父亲过世了,母亲故意和与父亲形象相差千里的丁伯刚维持纯粹肉体上的关系,期望借此守住与父亲的爱情。而在更多的作品中,父亲经常是婚外情的参与者。最有代表性的是那篇与鲁敏个人经验多有重合之处的《白围脖》。故事结尾,忆宁的那句哭诉“爸爸,我想你”,与其说是女儿与父亲的和解,不如说是女人对爱情的招魂。在性禁忌如此严苛的“文革”时期,父亲尚能冲破无爱的婚姻与“小白兔”一起奏响爱情悲歌;而在性欲已得到较充分解放的当下,爱情却几乎无迹可寻。以此为观照,《此情无法投递》、《墙上的父亲》等作品中时常出现的“恋父”倾向似乎又有了另一种阐释的可能。可以说,鲁敏对婚外情的“不确定的心态”更多地生发于对真正爱情的渴望和期待,而绝对不是对婚外情的无限度接受。
二、 窥视:故事人物与创作主体的双重姿态
如上所述,情爱是鲁敏都市书写着力逼近的对象,但又不止于此,在对两性关系的细致观察和精心描画中,都市这一带有空间、时间意义的生活场域及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浮现。即是说,情爱还是作者管窥都市情状的一个渠道和凭借。基于此,我们不妨聚焦于鲁敏都市书写的另一个关键词:窥视。如果说鲁敏都市故事中的情爱更多地表现出相似的面相,那么窥视则显然是一个有着更多维度的关键词:它不仅出现在文本之中,表现为故事人物的一种动作行为,也高蹈于文本之上,作为作家主体的创作姿态统筹着故事的呈现和讲述。
在精神分析学派看来,窥视并非一种纯粹的变态心理,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窥视他人的欲望。同样,在鲁敏的都市书写中,窥视首先是故事中的人物表现出来的一种普遍行为。当然,对窥视行为的文学书写由来已久。与一些现当代作家对窥视行为的描写相对照,鲁敏笔下的窥视行为也可作简单的归类分析。首先是与性欲望有关的窥视。《白围脖》中表面上保守、圣洁的母亲通过不断窥视女儿忆宁的个人隐私、偷偷翻看黄色光碟等行为宣泄个人欲望。《盘尼西林》中母亲也借由对妓女私人细节的窥探纾解个人的性压抑。其次是好奇驱使下的窥视。《百恼汇》中的严晓琴怀疑丈夫姜墨对自己不忠,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跟踪,不动声色地窥看到了丈夫的秘密。再次是接近于窥视癖的窥视行为。《百恼汇》中的姜宣为摆脱沉闷压抑的家庭时常在周末到单位翻看同事的桌面、垃圾桶等,从窥视别人的秘密中获得快感。《小流放》中的穆先生透过前任房客留下的旧迹不可遏制地窥视他人,甚至以假扮别人的方式逃脱固有的生活。《墙上的父亲》中的王蔷则以对别人父女关系的频繁窥视填补父亲缺失带来的情感漏洞。
在以上几点中,鲁敏小说中的窥视行为延续了其他作家的一些书写方式,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其独特性。与刘心武、残雪等作家相比,鲁敏笔下的窥视似乎慢慢磨平了极端、病态的棱角。相较于冷冽的格调,鲁敏小说窥视的眼睛中流露出来的有时更多的是温情。《六人晚餐》中的晓白即是如此。他年幼失怙,甚至也不能从相依为命的姐姐和母亲那里得到渴望的爱与关注。当母亲带着晓白介入另一个残缺的家庭,他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两家可以真正融合到一处。这不仅可以填补父亲留下的空白,也可以帮助晓白借由丁伯刚和丁成功确认自己的男性身份。于是敏感的晓白开始以窥视的方式寻找并增加两家结合的可能性,而周三沉默的晚餐时间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他窥看整个丁家甚至厕所,从中探寻自家没有的男性化气质;他仔细观察并分析丁家每个人的表情动作,以便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偷看到丁伯刚对自己吃相的欣慰,便更加卖力地吃来讨好众人……而当窥视到晓蓝与丁成功之间的特殊目光,晓白不惜耍一些小手段撮合二人以求两家更加黏合。可以看出晓白的窥视中倾注着对家、对爱、对亲情的巨大渴望。然而他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两家仍然毫无预兆地分手了。这无疑更为晓白温情的窥视蒙上了一层酸楚。
除此之外,《此情无法投递》中陆仲生与斯佳之间互相不打扰的窥视也染上了些许温情的色彩。丧子的陆仲生原本怨恨斯佳,但在一次次的窥视之后,谅解、宽慰、忧虑甚至自责的复杂情绪最终将怨恨消解殆尽。而斯佳也在对陆仲生的反窥视中慢慢袒露了自己对老人的担心,对丹青及其家人的愧疚。于是当窥视结束,面对面的两人似乎终于可以将所有纠葛都遗忘,或者假装遗忘,流着眼泪拥抱着抚慰彼此的伤痛。故此,偏于温情的窥视,可以说是鲁敏笔下窥视者的一个独特之处。
与窥视者形象一样,作为故事的创作主体,鲁敏也可说是一个窥视者。如《取景器》中的摄影师唐冠所言,她“需要一下子发现拍摄对象与众不同的东西,那隐藏着的缺陷、那克制着的情绪、那屏蔽着的阴影部分”,于是她选择以偷拍的方式,借由可以放大一切的取景器窥视被粉饰的景象背后的细枝末节。写作者鲁敏亦是如此。在一篇创作谈中,她道出了自己与小说交情的缘起:某个黄昏,她从写字楼里向外俯瞰,看到了正下方全都行色匆匆、方向坚定的人们,一种焦灼感突袭心头。鲁敏渴望凭借某种隐蔽和有效的合法工具穿破表象,去窥视人的心肠,“感知他们的哀戚和慈悲”,于是小说这样“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变形和癫狂的望远镜和取景器”就自然地为她所用了。当然,作家的“创作谈”常常和他们编写的故事一样不能尽信,但是在都市书写尤其是“暗疾”系列的都市故事中,鲁敏确实是一个站在取景器背后的窥视者。
所以,在这里,“窥视”还是一种写作姿态,即作者以一种隐藏的视角探测目光所及外表背后的情感身世、精神伤痛和人性幽微。借助窥看者的眼睛,鲁敏窥见了都市情爱的时代特质,也发现了都市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暗疾”。所谓“暗疾”大都来由不明,症状更是千奇百怪,它显然处在主流社会圈定的合法秩序之外,自是不能轻易示人、为人所知,于是“窥视”的姿态就更显得关键和必要。借由小说这一取景器,鲁敏无限聚焦并放大了都市人的私人病症和细节,甚至有意识地将其投放在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暗疾》以梅小梅的婚事为主线,借助细致的镜头般的语言展现了梅小梅一家的“暗疾”:母亲记账成癖,父亲会间歇性地呕吐,姨婆热衷于讨论大便,梅小梅则沉迷于购物、退货的游戏中,而那个表面随和宽容正常的黑桃9的病症则更加深邃……人人皆受“暗疾”所困,这是鲁敏窥视下的都市。可以说,这样一种瞄准式,甚至有些极端化的窥视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探测人性幽微的便捷路径,并逐渐凸显了作家创作的个人风格。
作为叙述主体的窥视者,鲁敏十分老到地拿捏了“窥视”这一写作姿态。在《暗疾》中,特别是对“暗疾”故事结尾的处理更是十分自然合理:作为窥看者,她只是呈现,而不意在提出治愈的方法和出路。所以大多数“暗疾”患者只在故事结尾处留下一声呼喊或喟叹,然后继续裹挟着各自的“病症”前行。饶有意味的是,《不食》的结尾,一向拒绝性和食物的秦邑在“我们”的步步窥探和劝说下终于攻克了自己的“暗疾”。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回到主流的队伍,而是以更惨烈的方式(植物人)存在于主流之外。这是否意味着鲁敏所强调和认同的更多的是一种不介入的“窥视”呢?
然而,鲁敏的“窥视”并不是哑然无声的,即是说它是一种“窥看+审视”的表现方式。如果我们将鲁敏的都市小说比作剧情片,那么画外音可以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和特色。综而观之,在鲁敏的都市书写中,一个可以随时、随地、随意讨论评述事态和人物的声音经常出现。如果借鉴相关的电影理论,它应该属于非剧情画外音的范畴,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于故事世界以外的声音,并不为故事中的人物所知,只有观众(读者)可以知晓它的存在。此外,它不是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即时收录的,而是后期制作时增添的声音,因而不对故事的发展起直接影响和作用,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隔着“屏幕”的介入、预告或评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六人晚餐》,此外《墙上的父亲》和《此情无法投递》中也时有出现。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作者经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发表对爱情、人伦、道德或者人物行为的看法,而这些评论的画外插入一方面使得鲁敏的讲述并不表现为零度情感的纯粹呈现,而是一种带着温度和个人判断的叙事;另一方面又恰到好处地分开了作者的个人解说和人物事态的本来面目,使得客观叙述和主观议论得以产生别有意味的审美张力。除此之外,这样的“画外音”还有另一种插入方式和功用,如《跟陌生人说话》中的“顺便说一下丁冬,因为刚才忘了说他”,《杜马情史》中的“本文开头的那次新年聚会后不久……”,《暗疾》中的“我们前面说过”等。显然,这些画外音的插入在增加过度的流畅性的同时,更分明地向读者传递了一种距离感,它让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鲁敏认为写作不是与现实的“贴身肉搏”,而“应该有个‘隔’的东西,比如,通过时间来隔,通过视角来隔,通过手法来隔”。我们认为画外音亦是一个有效的“隔”的手段,而这恰好又与鲁敏“窥视”的写作姿态相契合。
三、话语:时代与日常的文学互渗
出生于1970年代的事实使鲁敏不得不面对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命名:“70后”作家。许多以代际划分作家的研究者认为,“70后”作家大都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彼时转型期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基本从“宏大叙事”的模式中跳脱出来转而投向对世俗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细致呈现,进而,日常生活得以进一步冲出时代、历史的宏大雾瘴,在文学书写中竖起异常鲜明的大旗。但研究者也认为“过于强调个人化记忆和碎片化的经验,也使小说从另一方向上流失了它的社会功能”,甚至质问“文学难道要成为日常生活垃圾的搜集筒吗”。如果我们暂且搁置代际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仅仅从结论出发即可提取出一组矛盾的文学话语类型,即“时代话语”与“日常话语”,前者往往紧密贴合时代主潮,诉诸勾勒历史的宏大风貌;后者则基本聚焦于个体生命的普通生活,竭力探寻其蕴含的平凡诗意和日常审美。而如果回顾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纠葛其实由来已久。

我们认为鲁敏的都市书写就部分地体现出寻找这种文学话语的努力。回顾她早期的都市书写即可发现,与许多女作家相似,彼时的鲁敏也基本拘囿于对个人日常经验、“小情小爱”的讲述:长篇处女作《戒指》围绕姐妹俩和母亲三个人的爱情展开、铺陈;《爱战无赢》则关注了母子之间、兄妹之间、夫妻之间的情感之战,勾勒了爱情与亲情,欲望和坚守之间的比拼;2007年出版的《博情书》虽然仍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主线,但已显示出一定的开阔性,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当下时代的性爱、婚恋特征,以及网络时代的真实与虚假……而诸如《转瞬即逝》、《冷风拂面》、《镜中姐妹》等早期中短篇小说也同样致力于传达作者对爱情的个人思考。中短篇《方向盘》、《秘书之书》,长篇小说《机关》等则可以视为鲁敏对都市创作题材的开拓,她开始将眼光从爱情中的男女扩展至机关生活中的小人物,而《笑贫记》、《致邮差的情书》、《超人中国造》等则展现了城市底层人物日常的悲欢苦痛。
在以上这些作品中,鲁敏的创作视野和格局逐渐从个人扩展至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从“小情小爱”的私人经验蔓延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卫慧、棉棉等私人写作中被遮蔽的日常百态在以上作品中得以复现。但是需要承认的是,在鲁敏的这些创作中,日常话语仍部分地对时代话语造成了挤压,这一方面是说日常细节和个体经验基本上仍是一些都市书写的全部着力点;另一方面则是说,在作者有意纳入时代话语的篇章中,时代与日常之见的隔阂可以说十分明显。如在《白围脖》《取景器》中,由于作者对“文革”历史经验的陌生和疏远,“文革”的复杂性显然被剔除了,更多的只是服膺于作者个人的创作观念。即是说,时代话语与日常话语在这些作品中并没有实现十分有效的文学互渗。


鲁敏曾言,她希望自己的小说呈现的是一幕幕“小而软”的景象。可以说,这些“小而软”的景象即是作者精心选取并工笔描绘的日常生活,它可以是闲谈杂语,可以是情爱甘苦,可以是南京街头的桂花香,甚至可以是超市货架上的价目牌……但是当作者有意并尽力将对时代、世界的感知和体认蕴含其中,诸如时移世易、人群分化、生活变迁等“大”的问题也就以“小”的面目出现在文本之中,时代话语与日常话语由此得以实现互渗。
本文从鲁敏都市书写中提炼出的三个关键词——情爱、窥视和话语,分别构成了鲁敏审美世界的三个不同层面。情爱是就都市故事的内容而言的,我们认为创作主体鲁敏对爱情所持的怀疑态度使情爱在文本之中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窥视则跨越文本之中与文本之上,是故事人物和创作主体的双重姿态;话语则处在一个更宏观的位置,其可谓是一种写作努力,即在文本中实现时代与日常的文学互渗。可以说,这既是鲁敏小说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也是考察鲁敏小说的有效视角。我们希望循此思路能够对鲁敏的都市书写有更多的独到发现。
[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13ZWA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程德培:《距离与欲望的“关系学”——鲁敏小说的叙事支柱》,《上海文学》2008年第10期。
②鲁敏:《爱的最后一口气——关于〈取景器〉》,《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③[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④鲁敏:《以父之名》,《人民文学》2010年第3期。
⑤鲁敏:《青春期:闪电前的闷热时光》,《回忆的深渊》,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⑥韩作荣、施战军:《从心灵走向现实——第五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人民文学》2007年第1期。
⑦由于“70后”作家这一创作群体自身的复杂性,需要先对本文所引入的“70后”作家的命名作特别说明。一般说来,卫慧、棉棉、周洁茹等是“70后”作家中最早声名鹊起的,他们疏离于历史、时代经验,而沉迷于对个人尤其是女性自我内心、身体等的探寻和揭示,其创作中基本看不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以鲁敏、徐则臣、乔叶等为代表的后起的“70后”作家则不再仅仅局限于自我的狭小空间,整体上表现出异于前辈的创作风貌。本文所提及的“70后”作家就是后一种。
⑧张清华:《镜中的繁复或荒凉——关于鲁敏的〈墙上的父亲〉》,《小说评论》2008年第3期。
⑨周立民:《可疑的“个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阅读札记》,《山花》2009年第17期。
⑩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