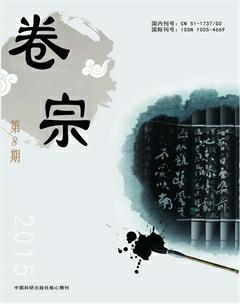《古诗十九首》隐女形象分析
杨静
摘 要:《古诗十九首》是产生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东汉后期的一组五言诗,其作者不详。从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多写游子仕途的失意和游子思妇离别后的相思,以及写弃妇的哀伤;从形象上看,诗歌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较之唐宋文学对女性形象“神”、“形”具备的描绘而言,东汉文人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则重“神”轻“形”。因此《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隐蔽性与不确定性,多数的女性形象则是通过神态与心理特征表现出来。故把《古诗十九首》中模糊朦胧的女性称之为“隐女”。
關键词:《古诗十九首》;隐女;形象分析
《说文解字》中,隐,蔽也。藏匿,不显露之意。古往今来,在文学作品当中出现众多与“隐”有关的人士中,以东晋时期的的“隐士”陶渊明最为出名。在中华文学璀璨的历史长河中,“隐士”众多,“隐女”却甚少,以《古诗十九首》中的“隐女”最为显著。《古寺十九首》作为五言诗发展成熟的标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钟嵘先生曾评价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再有刘勰誉之“委婉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古诗十九首》着力于刻画思妇这一独特美感的文学形象,塑造了众多风格迥异、真实感人的思妇形象。通过塑造思妇形象来展示人生随想,表达对生活的领悟和审美的追求,是“古诗十九首”的特色。[1]我国传统美学一向重视“神形兼备”的审美原则。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在诗歌中创造出神形兼备的艺术形象,传统美学要求把写形与传神结合起来。写形是对客观事物外在形貌的摹写,传神是对客观事物内在本质的揭示。[2]这些女性形象同前代《诗经》和后世唐诗宋词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古诗十九首》中的各类女性形象与之相似之处,更有与之相别的特色。相同的是,两者都描写了女性的各种外貌特征及心理活动,不同的是,前者的女性形象塑造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女子,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是东汉时期的失意文人,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生活中原型的塑造,也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是巧妙的隐藏在诗人的诗歌里,其朦胧之姿,绰约之美令人发思。
东汉中后期,幼子临朝,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统治者内部斗争异常激烈。当时文学的潮流是由名门世族所把持的,寒士即便是偶然因文学有名,也就是说明他已经变成华贵的附庸:“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的。因为当文化和政治经济同样的为他们所把持保有的时候,不只他们在学习的环境地位上方便,而且诗赋文笔等的风格和内容,也都是适应着他们的生活需要的。[3]因此他们不仅不只是握着经济政治的特权,还是社会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加之汉代自汉武帝以来奉行养士政策,东汉质帝时代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而他们的出路就是通过选举,由中央或州、郡征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游学”,或者说“漂泊”。营求功名富贵的人日益增加,而能官僚机构容纳毕竟有限,幸进者少而失意者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下层文人长期在饱尝求仕的艰难和在“君臣僚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历尽心酸与屈辱外漂泊,长期远离亲人,怀才不遇,心怀不平,郁结于心。在诗人全国游学漂泊之际,感之自身境遇与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女子境遇相似,遂将自己饱尝忧患人生体验与凄凉身世融入其中,用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批风格迥异,形态清晰的思妇形象。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文学大家的赏识,摆脱穷困境地,因此在女性形象上的塑造多采用神态动作与心理活动描写。如果在诗歌中的女性形象重“形”轻“神”或者“神形兼备”便会“宣兵夺主”,使读者们更注重女性外在形象的描写而忽视文人们在诗歌寄予的愁苦情感,就违背了其创作初衷。因此,我们在赏析诗歌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诗歌形象塑造本身,而是通过这些模糊的“隐女”形象去挖掘其深刻的情感内涵。
《西北有高楼》中,“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首是写一位男子听曲感心的故事。诗中的这位女性弦歌者并未露面,她只存在于男性听曲者的想象之中。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位听曲者对弦歌的解读,将这位弦歌者的形象解读出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诗歌开篇就介绍了弦歌者弹奏的所在位置。“西北”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曹魏修建的邺城以及铜雀台,其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铜雀三台正在邺城的西北方向,是故曹植《登台赋》说:“连飞阁乎西城”。据潘眉《三国志考证》说:魏铜雀台在邺城西北隅(见《邺中记》),邺无西城。所谓西城者,北城之西面也。因此,西北的高楼应该就是铜雀台。此外“上与浮云齐”并不是一般的建筑物,是只有帝王贵族家族才有可能居住,加之高楼上的弦歌者是有乐器伴奏而歌,这只是宫廷贵族的音乐消费方式。可见此弦歌女子并不是平常普通百姓家的女子。“音响一何悲”弦声传到听者的耳朵就一个感觉“悲”,这样悲哀的哭声就如杞梁的妻子,犹如哭塌城墙之势。高楼上的女子的琴声婉转哀怨,曲中的愁怨正往复萦回。“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那女子弹奏时一唱三叹有相应的和声,传达出了失意的愁苦和无尽的哀伤。那她是为何而伤?“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告诉了我们答案。如此美丽,有才的女子,却终无得到伯牙与子期式的知音,内心愁苦无人能懂。就像诗人一样,自己满腹才华,却因社会现实,无人赏识,也不曾有人懂得他内心的悲哀,接着诗人道出了他的志愿:“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但愿我们能像一对美丽的天鹅,奋力鼓翅在空中结伴而飞。至此,这位遭遇不幸、独处深闺、孤寂无助并深感知音难觅的贵族女性形象已清楚浮现出来。她的苦闷、悲哀和期待,定会激起许多被压力的女性的共鸣,更是诗人被残酷现实压迫的真实写照。
芙蓉,是南方之花,其花八九月始开,耐霜,因此也被成之为拒霜花。苏轼也曾使用这一说法,如其《和陈述古拒霜花》:“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涉江采芙蓉”之“江”,指狭义的长江。这时南方芙蓉已经盛开,花香色溢,引得诗人忍不住要涉水过江到长满兰草的沼泽地里去采摘。“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说明这时的诗人已经漂泊到长江以南,看到如此清新可人的花朵,就如妻子娇俏可爱的脸庞,情不自禁的想要把它采来送给妻子。无奈“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诗人回头遥望故乡,道路又是那么辽远漫长千里迢迢,可谓是“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这时,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同样登上高处,凭栏眺望女子,时而抬首望那天边绵延的黄云,时而低头看那河畔葱绿的青草,丝丝缕缕的情愁彷如香炉袅袅的熏烟,挥之不散,萦绕心头。诗人回望故乡,那里不只是故乡,那里还有他深爱的妻子;此时妻子,决眦眺望,远方有他许久未见的夫君。夫妻二人的目光被无情的山川遮挡了,无法交汇,相思之苦无法传达,只好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纵然“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但也要在梦中相见,互道相思。
《东城高且长》中苦闷忧郁的诗人在看到洛阳东城景色萧瑟凄凉,听到《晨风》、《蟋蟀》唱出怀人的苦心,感伤人生的短促之声,更增内心的苦闷忧伤。正值伤心情感无处派遣之际,忽逢一“佳人”,便不觉将视线转到声色之娱上面。诗人紧闭双眼,佳人的英容面貌渐渐地浮现在脑海。“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诗人此时正处燕赵之地,而历来燕赵之地盛出美人,最著名的就是燕赵四大美人。第一位是甄洛,也称甄宓,曹丕的妻子,曹植的梦中情人,并为之做《洛神赋》,引起曹氏家族的纷争;第二位是汉朝第一后窦漪房,出身贫寒而天授漪媚的她备受命运垂青由民女到宫女最后成为辅佐文景武三位帝王治理大汉江山的杰出女性。第三位是秦始皇的生母赵姬,赵国都城邯郸人;第四位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李妍,天生丽质,精歌舞,擅音律。“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使人难再得”便是指她。因此诗人不觉的把“佳人”当成是甄宓、窦漪房之类的倾国倾城女子。“佳人”“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这些女子面容俊俏、身穿绮丽华服,但却对着窗户弹着清商曲,乐曲的声音竟是这样的悲伤,弦音繁急便知弦柱调的这么的紧促。从她们悲伤的曲调中便知她们生逢乱世,并处于被玩弄的地位,醉生梦死的调令生活令她们的内心日渐空虚与寂寞,以至于经她们纤纤细手理出的曲子也蒙上了悲凄的色彩,使人心生怜爱。“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佳人”手中的琴弦越发急促,使诗人全部的感情都在翻腾奔驰,不觉得整理衣带,一面徘徊,一面沉吟踯躅,犹如两颗孤寂已久的心瞬间苏醒以至于萌生了想同佳人化为一双比翼齐飞的飞燕,共同衔泥筑巢同宿于美人的华屋里。通过诗人婉转细腻笔调,一个当户弹琴、梨花带雨、孤寂、忧伤、的佳人形象全方位的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
《古诗十九首》中这些隐女存在于诗歌始终。她们是温柔贤良的妻子、俊俏孤寂的才女、倾国倾城的佳人,她们是真善美的象征,寄予了诗人艰难的仕途命运与丰厚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在把握这一类隐女形象的时候,决不能停留在诗歌形象本身,而要结合诗人曲折的生命历程去感悟和领略潜藏其中的隐女形象,体味东汉后期文人通过诗歌字里行间与形象塑造中传达出来的精神苦闷与人身感受,领略其朦胧隐约之美,感受其痛苦失意的灵魂。即使千百年后,《古诗十九首》中的隐女形象依然是一道凄美哀怨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彭庭松.论《古诗十九首》之感伤情怀及审美特征[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6):12-95.
[2]吳思敬.诗歌基本原理[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