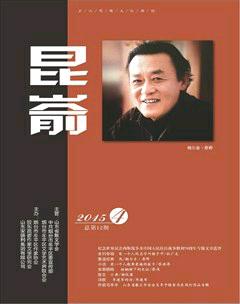小龚
一想到小龚,就会掂量一下人之间的情分,压在心里的分量只有自己清楚。小龚是我青年时期的同事,那时的交往,充满信任和深深的情意。
可是,我和小龚第一次密切接触,到现在想起来都心跳。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国科协机关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揭发”什么的都有,很快分为两派,闹得正常工作也无法进行了,对立了两年多。我随着本部门的同事参加了其中的一派。“大革命”也不是天天“革”,没有事的时候,年轻的同事们也常凑在一起“侃大山”,我藉此结识了其他部门的年轻人,其中就有龚维忠。我们那个机关大多是40、50、60岁的人多,所以我们这些30岁上下的人都是“小”字辈,我也就跟着叫他“小龚”。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们匆匆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后面有个人抓住我的肩膀,平和地说:“赶紧跟我回去。”
“怎么了?”我回头一看,是小龚。
“谁把你的脑袋啃成这样?这能见人吗?”
他硬是把我拉回他的办公室,很快把我的头发重新理了一遍。我说,是我们普及部的老李给我理的,人家说好是拿我练练手,我同意的。他笑道,你们普及部没有人能干这活儿。他说的对,我们普及部的干部年龄偏高,中年以上的人大多有点身份,理发都是到理发店去,像我这样年纪刚分来的大学生没几个。而他们出版社那几年分配来二三十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互相理发,许多人都有这种本事。小龚给我理完了之后说,你先去食堂吧,我收拾一下马上就去。
我先下楼了。
我刚从楼门走出十几米,突然听见身后“嘭”的一声惊人的闷响,回头一看,吓出我一身冷汗!原来是一个人从三楼的厕所窗子上跳了下来,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离我只有一米多远。一看,是出版社的人。
有人自杀了。
吓得我不由自主地大喊:“快来人哪!有人跳楼啦!”
此刻,人们都在食堂吃饭,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看着他还在抽搐,头上的血不断地流到地面上……我要前去扶他,这时靠近院子的办公室的人听到我的呼喊,都从窗子中探出头,看到我要去动这个在不断流血的人,就大喊:“小杨!你别动他!”
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
这时,小龚从楼里出来,一看这场景,也惊呆了!但他很冷静,说,别动他,看着点现场!我去叫保卫科的人。
等保卫科的几个人跑来之后,那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小龚跟着跑回来,我们看着他们忙乱了一阵子之后,他就拉着我去食堂。路上对我说,这人是他们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就是因为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有历史问题,害怕了。这些日子情绪就不正常,没想到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买了饭,可谁也没有吃,坐在那里,心还在怦怦乱跳。
他在低声自言自语:触及灵魂。
从出了这件事,我们两人就下意识地常常在一起,开会都坐在一块。
我和小龚不在一个部门,他在科普出版社,我在普及事业部。他是1964年分配来的,我是1962年分配来的。他是学物理的,我是学美术的。他是安徽人,我是山东人。年龄相仿,个头一般高,一个楼里上班,一个食堂吃饭。当时,小龚和20多个新来的男大学生就住汽车库临时改造成的集体宿舍里,我常到这里找他们玩。大家一起聊天时,我发现他不爱多说话,说上一句就耐人寻味。
我对他的真正信赖,是在一次机关里偶然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们单独在一起聊天时,我过于随便,无意中说了一句有点犯忌的话,他听了以后,便用手悄悄指指自己的嘴。我明白了,在运动的非常时期说话不小心就会出事的。这事总有点后怕。那个手势让我学会了慎重,对他的信任也是由衷的。
文革中两派要“大联合”的时候,我被本派派去和对立面谈判,对立面中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很是难缠,谈好的东西第二天他就能拿出个理由推翻,又得重新开始。我去找小龚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他就告诉我这个人的弱点——当他自己说到一定状态会突然跑题,让我注意他在什么时候一出现就把他截住。这招果然有效,两次下来,这个人就不再胡乱纠缠了。我这才发现小龚是个很细心的人,能够观察人的一些细节特点,平时虽然不多说话,可心中有数。
1969年我们去干校了,虽然不在一个“连队”,因为都是年轻人,干活是绝对主力,凡是干校的一些重活,都会见到我们的影子。
在干校动荡的政治运动依然在进行。难得的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反而得到了运动以来少有的愉快,因为干校是在群山环抱的水库淹没区,遇到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就相约去山里散心。周日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进山踏野,有时小龚还会陪我去写生。
我画画的时候,他就坐在我身边看。我问他:“我画得好吗?”
“挺好!”他说话总是很“节约”的。
“奉承我!”我说。
“真的!”
“喜欢吗?”
“不喜欢。”没有一点虚假。
深秋进山,看到野柿子树顶端上有些熟透的红柿子。我在树下使劲晃,柿子一掉在地上就摔烂了。小龚看着我笑。
我说,你别乐,你也弄不下来完整的。
他说,你再摇吧。
他走到树下,把随身带的一个军用挎包张开了口,伸到身前,我摇下一个柿子时,他就迅速地用书包迎上去接住,他手上有一个很微妙的动作,就让柿子稳稳地完整地落在了书包里。他说,这和踢球一样,用脚接球时一定要在接住前加一个用来缓冲的动作,球才能停在脚下。我们在学生时都喜欢踢球,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用这个办法我们居然把剩下几个红柿子都完整地拿到手了。
我在干校日记《四五六○部队》中记录着和小龚在一起的事情。
一次是1972年元旦,是这样记载的:
昨天贯台大队的大队长到这里来要请“徐克思”徐克明到山里去吃野猪肉,今天老徐便叫上我和龚维忠同去。
新年第一天,天气并不好,晴不晴阴不阴的。通向肖沟的大路上,两排杨树挺立,几只喜鹊站在梢上不时地叫着,我们三个一边走一边说着干校三年来的变化,原来眼前是一片林苗地,现在树苗移去形成百亩成片的沃土,拖拉机耕种的小麦,苗儿青青,匍匐在地上。
我随口唱了一句:“麦苗儿青来菜花黄……”
小龚马上说:“那还得等几个月。”
“什么意思?”我问他。
“现在还没有菜花呢!”
也是。
他们两人都是细心的人,为了来吃野猪肉他们还带上了花生、买了一斤糖和半斤瓜子。
社员们今天上午干活,下午休息,十二点时都回来了,他们炖了家猪肉蒸了馒头,也欢欢喜喜过新年了。吃饭前大队长把人们召集起来,来了一番“讲话”,说我们三个来了,是对他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还说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干校对他们的关心,好好干。把我们三个请在屋子里坐在炕上,本来我们是来吃野猪肉的,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如坐针毡,十分尴尬。
他们盛了一碗野猪肉给我们,可是和家猪肉混在一块,我们尝了尝,没尝出什么特殊味道。
下午回来时,他们硬是要我们带回一大块生野猪肉。
晚上徐克明在宿舍煮好带回来的野猪肉,又去请来了刘文铎、周铮、孔祥瑾,加上小龚和我嘻嘻哈哈地吃野味了。
一次是1972年1月9日,是这样记载的:
从昨天开始下雪,今天又下了一天。
清晨起来雪下得有近半尺深了,我拿了一把笤帚把院内的通道扫了一遍,然后一直扫到马棚门口。上午我喂好了牲口(1972年我被安排在马棚养牲口半年),龚维忠约我进山到姜庄去买檀木,我们就带上绳子踏着满地积雪向南河走去。本来想从大路通到河边的地方过河,小龚说那里不好过,所以顺着河滩又折向东南走去苗圃的小桥。本来雪地走起来就不大好走,又是在沙滩上更觉得困难,不一会儿浑身都冒汗了。小龚摘掉了帽子说:“不行,受不了啦!真热。”两个人心情都十分愉快,在中原的深山里能遇上这样一个雪压大地的景象,又特别是我们跑到这大自然中去吸吮少有的新鲜空气,更觉得惬意。
小河水照样潺潺地流着,不管你下了多少时间的雪,也不管积水的地方冻了多么厚的冰,桥下的水总是彻夜不停地冲刷着沙石,刚落下的雪花立即被吞噬了。小桥上也是厚厚的雪,我们小心翼翼地过去了。
说到山,我便抬头南望,不知怎地,大雪盖了山上的一切,那种平时威武雄壮的姿态却消失了,我极力想找出被大雪压住的大山的可爱的地方,谁想脚下一滑,扑通就倒下了,差点滑进沟里。
“妈的!”我脱口骂了一句。
小龚大笑起来,想过来拉我他自己也摔倒了。
“妈的!”他也骂了一句。
我也笑起他来了。
进马庄的山谷,一条大路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次的了,虽是白玉满地,但是闲不住的社员(农民,那时叫做人民公社社员)仍在忙着他们的事,这条大路上早已被来去的人踏出一条小路了,我们两个却硬是走那积雪的地方,听着那沙沙的声音,也觉得怪有味道的。
过了马庄就是姜庄。
“快到了吗?”我问。
“早着呢,刚走一半!”
“噢!”我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因为他上次和刘文铎来过一次。前边就是村庄,走到村头一个高坡的房子前,我照直向前走,他却上了高坡上的小路。
“怎么搞的,你怎么拐弯了?”我问。
“嘿嘿,到啦!”
“这小子!诓我。”我跟着他上去了。
找到了队长,小龚拿出了刘文铎写的信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说:“木头早就准备好了,现在去拿吧!”他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小村里,到了一个院内,里面放了不少木头,找出了一块檀木。
“要多少钱?”小龚问。
“咳,要啥钱,不要钱。老刘在我们这里呆了一阵子,怎么能要钱呢!”
“不,公事公办。”小龚说话不会那些客套,急了就抓一句,说了半天,队长说一元钱。我们就给了一元钱,两个人抬着出了村。
回来时身上有了负重,但是走得却比来时快多了。
小龚买檀木是要做木工用的刨子,想学做木工活,这引起我的兴趣,我又拉他和徐克思进山去找檀木棍,想给我的父亲做个拐杖。
到深山里,我终于找到了一棵根部往上被野藤缠绕着的檀树,缠绕的部分有将近半米,树干直径有8公分,多年的缠绕生长形成的螺旋状特别好看,若做个拐杖,一定很有情趣。没想到,檀树长得也很高,木质很硬,我从根部硬砍,每砍一下,树干就好像有意躲闪一样,有劲使不上。
小龚说,你这样干不行。
“怎么不行?”
“第一,树木的上半部分重量压在下面,你要花费更多的力气。第二,你在下边使劲,上边树冠跟着震动摇摆起来,也抵销了你的力量。”
“有道理。你真应当得物理学诺贝尔奖金。”
说着,他就从一米二的部位,先把树冠砍了下来。说:
“你再砍吧!”
果然,每下一斧,都实实在在地落在根部,不一会就砍下来了。
砍下来,我掂了掂,又大又沉。小龚看着我大笑。我莫名其妙:“你又怎么了?”
“这么沉的拐杖,你父亲拿得动吗?”
从干校回北京之后,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仍去做编辑工作。
自分配到我们机关工作之后,小龚一直没有机会谈恋爱。回京工作之后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北京女孩。但那个女孩患有一种不治之症,人看上去很好,但日后将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情。和小龚关系好的同事都劝他放弃,我也劝他慎重。他却说,既然认识了又知道了这种情况,这样分手就有点不负责任了,我身体好,正好将来可以照顾她。不久就真的结婚了。
有趣的是,那个女孩的弟弟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并不是因为觉得小龚不好,而是觉得这个人太好了,不能让自己的病姐姐耽误了这样的好人。后来,这对姐夫内弟极合得来。
凑巧的是,他们结婚的新房,就是我刚分配到机关时住过的那间集体宿舍。是在机关办公楼的顶层,楼道两侧的办公室腾出来当作宿舍用,好在楼道比较宽大,家家在门前放着杂物和煤球炉子,是典型的北京“筒子楼”生活模式。
婚后,妻子常常回母亲家,小龚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多。
因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着,彼此见面的时间少了。
有一次,我担任一个激光科技展览的美术总体设计,遇到一个问题找他帮忙,他带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把我的问题解决了。看到他既专注又熟练地翻查资料的情形,很是佩服他特有的专业素质。
展览开幕前夕进行审查的时候,我请他到展览现场来看看。
展览是在一个大型博物馆的展厅中,规模和内容以及我们美术设计的精彩之处都让他感慨,称赞我说,你很有成绩。我说,这可不是我的成绩,选题是领导们定的,内容是20几位科技人员编写的,版面是30几位美术人员设计的,施工是各工种数十位师傅制作的,我这个总体设计不过是从中协调,只有别人没想到的欠缺之处我来管一下。
他说,这不是很好吗?
我说,在我的心中说不上好还是不好,这是工作,任何人都必须做的,就像一台机器,只要运转起来,所有的部件都得一起转,只要有一个小器件掉下来,就有可能影响机器运转,在这个展览中,我的任务是保证所有的“部件”都正常运作,包括我在内。可作为学油画的人,内心的渴望是进行艺术创作,我来科技口十几年了,除了在干校抽时间画过一些,眼下这种工作干起来,哪有创作的时间呢?
他说,我也是。学生时期梦想着去搞科研,却来做了编辑,为人做嫁衣。出一本好书,我虽然也很高兴,可毕竟是作者的成果,我不过是个编辑,天天在尽心尽力地做案头之事,有的书稿还不是我的专业范围的,还得去学,去弄明白。
说的深了,我们都感到了各自专业和心理上的难言之隐。
我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做,谁让我们摊上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我们想法是一样的。后来细想想,当时和自己同行都没有透露过心灵深处的惆怅,我们之间却能够畅快地沟通。
之后的一个冬天,突然听一个消息,说小龚中煤气了,万幸的是被抢救了过来。
我赶紧去看望他。他已经恢复了,真是死里逃生,代价是永远失去原来的健壮。
事情就出现在筒子楼的煤炉上。
一天下班后,妻子说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回家晚一些。那时供暖不足,小龚吃晚饭后,怕屋子凉,妻子易患感冒,就把火烧得正旺的煤炉搬到房间里烘一下,打算待房间暖了再搬出去。之后他就躺在床上看书。
晚上,可巧他妻子那天回娘家有事不能回来,就托人转告小龚,别等她了。转告的人去敲他的门,敲了几次没有回音,门上的小窗子上里面挂着帘布,看不见里面的动静。邻居也没当回事,以为他有事跑出去了。
到第二天上午,他的妻子又给熟人打电话,让找找小龚,熟人去敲门还是没有回音。告诉其妻子说屋子里没有动静。
妻子急了,说,你们看看我们家的煤球炉子在屋子外面吗?
一看,没有。妻子说,你们赶紧破门吧。可能出事了。
人们破门而入,发现小龚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他跟我说,真是捡了条命。按说自己是学科技的,不应当出这种事情,在床上看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突然醒了,觉得头疼得很,手脚动不了了,知道是中了煤气。他立即想到房间的门底下缝隙很大,有凉风吹进来,地面上的煤气浓度会小,就努力从床上翻滚到地面上,开始脑子还很清醒,想喊,喊不出来。后来他想努力向门边爬,可是没有力气,爬了一段,后来昏迷了。
这场煤气中毒,对小龚脑部损伤很大,从此,他变得有些木呆呆的了,加上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躺了那么长时间,身体有些部位也不听使唤了。那时,我在西郊双榆树的友谊宾馆北馆上班,下班回家正好路过老机关,有时就上四楼去看看小龚。我们面对面坐着,他总是看着我傻笑,很少呼应我的话,原来那个活泼、诙谐的小龚,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看着他,心里很难受。
更不幸的是,后来,他的煤气中毒后遗症发作,不能工作了。他的妻子反倒是每天伺候着他。
又过了两年,我调到了中国美协工作,和科技口和老机关的人来往少了。
一天一位老同事到美协来告诉我,说龚维忠走了。
惊愕中跑回老机关宿舍去,急急上到四楼后,房间已经空了。邻居说,他的家人因为悲痛,哪里还能在这间房子里住下去?
时光无情地把小龚带走了。
我特别想知道小龚的身世。
他在世的时候,大家都身强力壮的,觉得来日方长,谁会去刨根问底?可是一旦失去了他,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他曾经是如何从农村出来和我们走到了一起。一个30多岁的人故去,在社会上会见到不少,可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那几年,我外出办事,骑车若从老机关的楼下走过,从远处就会看着那个我熟悉的窗子,似乎那个留着寸头、瘦瘦的脸、嘴上有稀疏胡子的人,就站在窗前。
有一天,我刚到这里,恰好一只大雁从高空飞过,洒下孤鸣,异常凄厉。
大雁南去,斯人西行。终了,离别,如此而已……
杨悦浦,著名书法家,193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招远东曲城村。擅长书画、美术评论。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并被表彰。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八)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