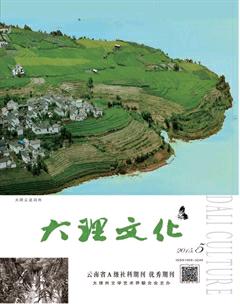剃头记
张旗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什么事难办,就说这个头难剃。白已有难办的事,就说白己的头还得别人来剃。那时,乡间俗语,理发不叫理发,叫剃头。理发匠就叫“剃头匠”。乡村里没有专门的剃头匠,县城里才有。县城里的理发匠还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待诏”(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待诏”这个称谓的由来),理发铺就叫“待诏铺”。村里一般没有谁会为剃个头跑一趟县城。进待诏铺花钱不说舍不得,这一去一来大半天,耽搁了田里的庄稼活计。反正一两个月,你就得剃一次头,是家庭生活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大多都是邻里互相帮助解决,或是白家一个给一个剃。小孩子头发太长,就会有人嘲笑说“像个小毛贼”,说得很难听的。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上县城去上高小(小学五六年级那时称之为“高级小学”,简称“高小”),我的头就是母亲给剃的,剃的就是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男主人公“骆老师”的那种发型。现在的年轻人看到“骆老师”的这个发型,觉得很土,很傻样,很搞笑。我一看,心里却一热,想起了那个逝去了的并不遥远的时代,想起了给我剃头的母亲。那时这种发型却有一个很时髦的名字叫“东洋头”。城里的待诏铺剃的也是这种东洋头,中间梳成“两分水”。有身份讲究一点的男子,每天早上洗完脸,仔细把头梳成两分水了,还要抹上发蜡固定发型,让头发亮丽有光泽。母亲给我剃的头就是这种发型。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前,或者说三十多年前,中国男人的发型大抵就是这个样子。但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个两分水,更不喜欢抹得油头粉面的男人(那个年代银幕舞台上演的脸谱化了的汉奸、狗腿子多半就是这样的人)。剃完头站起身,我总是揸开五指伸手往头发里一抄,抹平了头上两分水的那条“沟”,才往外走。
那时,小男孩剃头除了两分水,也有把头发全剃干净了的“光光头”,开玩笑叫“亮蛋”,叫“和尚头”。大人也有愿意剃个光光头的,那多半是在夏天,图凉快。不用剪刀,只用剃头刀,三下五除二就“刮”干净了,不说省事,还说这不生虱子。而且周期长,一年“刮”三四次足够了。因此,有人还把剃头匠叫做“刮刮匠”。
常见的发型还有“锅盖头”和“马掌头”。也不用剪刀,用剃头刀把头顶四轱辘团转的头发剃光了,头顶留下网网一圈头发的叫“锅盖头”,头顶前脑门囟上留一帘头发的叫“马掌头”。剃锅盖头、马掌头也不太麻烦。先洗头,把土碱化了水浇在湿漉漉的头发上,头皮被土碱烧得热辣辣的。小孩嘁痒痒痒,大人说杀痒才好呐,虱子这下该死光了。一边说,一边使劲搓揉,反复冲洗,顿时洗下了一盆酱油汤。这才拿了早前那种老式的剃须刀,蘸点水,在袖口上正反来回荡几下,啧啧啧一路剃下去,该留的留着,该剃的剃去。现在早已不见这样的发型了,只有在过去那些老照片和影像资料里才能见得到。近年城里又有个别小青年剃了这样的发型招摇过市,还以为又是一种时髦。
头是一个人形象的焦点,发型就是包装头颅的品牌,是一个人文化品位和身份的认证。母亲从来不给我剃光光头,也不剃锅盖头和马掌头。她不嫌麻烦,她一直坚持给我剃东洋头。我想,除了她不愿他的儿子像个小和尚外,她一定是嫌锅盖头和马掌头太农村太土包子了,她也不愿他的儿子像个小放牛像个马锅头。她是要把我塑造成一个读书人城里人形象的。她的这点心思,或者用当下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她的梦(做儿女的谁不是母亲的梦),她是不会说出口来的,是多年以后我咂摸品味出来的。这就不是一个农村妇女审美价值观的问题了。
母亲坚持给我剃时尚的东洋头,这对她来说太不容易了。城里待诏铺用的是推剪(现在用电推剪),即使修理厚密的长发,也是理发专用的条剪。母亲给我理发,用的却是她缝纫裁剪用的条剪和父亲的剃须刀。咔嚓咔嚓剪下去,难免会有一两根头发没剪断,顺势逮了一下,扯得头皮生疼。那种刀背很厚的老式剃须刀,尽管磨得锃亮,其实并不锋利。啧啧啧剃过之后,头皮脖颈针扎一样,火辣辣的疼。围布就用她的围裙,难免有一两根碎头发掉落在颈脖子上,钻进前胸后背,粘在身上痒得难受。我白小多病体弱怕疼怕痒,母亲每次给我理发,我本能地常用手去护着头,母亲不得不给我手上几巴掌。理着发,我咧着嘴,不时把头扭过来扭过去,忍不住了又伸手去护头。母亲又继续打手,打了再接着理。理一次发,要扯皮好几次。晚年有一次母亲还当笑话说起这个事,说我不像几个弟弟乖,理个发给她那样淘气。
尽管如此,母亲给我理的那个东洋头,还是像模像样的,得到乡党邻里审美的认可。如果头发修剪得七缺八丫的,头发根梭得不整齐,一埂一楞的,该剃的没剃干净了,就会被人家笑话,说这剃的是“马啃头”。补救的办法,只能把它剃成锅盖头或马掌头了。这样的事,母亲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在那个僻远的山村里,母亲是怎样学会理发的,为人之母她有多艰难!旧时待诏铺门前,就有一联语称这行道:“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想想也是。
十岁那年,我考上钟英完小(即今州城完小),离开老家进县城上高小,接着又在宾川一中上中学,理发就进待诏铺了。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给我理过发了,我从此再也没有享受到母亲那双饱经生活磨砺的温暖的手,给我的这份特别的抚爱了。我也遂了母亲的愿,一介草根,拼搏大半生,成了城里人,跻身于知识分子行列。只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再也没理过那种两分水的东洋头了,理的一直是板寸小平头,很平民也很青春。在别人眼里我是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要的是普通人的白在、轻松和白由,追求的是任性随缘,道法白然。我坚信,有内在,白从容。这却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实在话。以上个世纪至今一百年做观照,1919到1949是30年,1949到1979是30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这期间的三个30年之变均是天翻地覆式的。就说这理发店,前三十年叫待诏铺,后三十年叫理发店,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叫做“发廊”,现在又大都改叫美容美发店了。有的理发师已升格为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美发师了。
一切都远去了,走进美容美发店,眼前晃动的是奇形怪状的飞机头、子弹头、蘑菇头、超酷菊花头,是五彩缤纷的红头发、黄头发、绿头发、棕色头发。理发不仅仅只是一种生理需求,而是成了普通人张扬个性、展示魅力、塑造形象、提升白身品位的心理需求。
而且,做母亲的,抚爱儿女白强如我母亲者,也无须要有剃头理发这等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