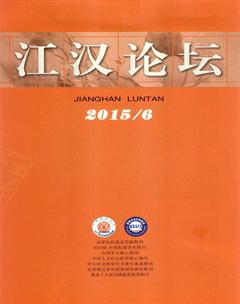晚清铁路论争中的文化意蕴
许启彤++张卫东
摘要:19世纪60、70年代和80年代末,围绕着铁路建设问题,清廷臣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喋喋不休的论争中,清廷错失了发展铁路的大好时机,使中国社会的进步额外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代价。对于这场争论,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铁路,为什么在清廷如此命运多舛?克服思想观念的束缚及依附于这种观念上的重重阻碍,打开思想进步的阀门,是我们的社会真正取得进步的不二法门。
关键词:晚清;铁路论争;思想观念;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100-07
一、引言
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期是真正的铁路时代。列宁说,“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从19世纪30年代利物浦一曼彻斯特铁路开通起,到20世纪初,铁路建成已达百万公里,很少有哪个国家还没有铁路。”源自英国的这一石破天惊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铁路将这个世界从大部分人仅仅只到过他们的村子之外或附近集镇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在一天而不是一个月就能跨越一个洲的世界”。尼古拉斯·费思说:“现代社会以铁路的到来开始。它们颠覆了已知的世界。它们带来比以往任何机械或工业创新都更大也更直接的影响。它们是影响到任何建设了铁路的国家里每一个人的第一项技术发明”。铁路代表了19世纪工业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当时世界的潮流。
英国伟大作家狄更斯在其小说《董贝父子》一书中对铁路的种种描述,更让我们宛如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铁路给当时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铁路刚开始向这里(巴巴多夫——笔者注)伸展的日子,附近的居民还没有打定主意该不该承认它,如今他们变聪明了,知错必改了,他们现在热烈宣扬铁路的巨大力量和与它相关的光明前景。……那些了不起的国会议员们,仅仅在略早于二十多年以前(19世纪20年代——笔者注),对于由几名工程师提出的关于建造铁路的疯狂设想,只是取笑而已,他们还在质询中对铁路计划使劲阻拦;如今这些议员却把怀表拿在手上,乘火车到北方去旅行:他们行前还发了电报,通告自己的北行日程。火车机车像个征服者,日以继日地隆隆作响,奔向远行的征程;或者,它平稳地到达旅程的终点,像一头驯服蛟龙,滑进指定的角落,供它停车的地点刻度精确到以英寸计。它在那里站住了,浑身震颤,让大地也随之抖动,它似乎在宣示一个秘密,那就是自己身上蕴藏着前所未料的巨大力量,将要最终成就那坚定不移的目标。”
然而,铁路——这一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物,在晚清社会却命运多舛。围绕着铁路建设,清廷经历了太多的纷争,而就在这种喋喋不休的论争中,错失了发展铁路的大好时机,使中国社会的进步额外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代价。本文在梳理晚清两次主要的铁路论争的基础上,探讨这些争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二、两次铁路论争
铁路在晚清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同治初年至甲午战前、甲午战后至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至清亡三个时期。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铁路知识传人我国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太晚。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如郭士力、高理文、马礼逊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就将有关铁路的知识零星地介绍到中国:而道咸时期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则从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中初步了解到了铁路的知识,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当然,无论是传教士们的介绍,还是林则徐等人的理解,其中都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都不是铁路方面的专家。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19世纪60、70年代,清廷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铁路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器物象征,亦开始被提上洋务日程。由此,在19世纪60-70年代及80年代末,清廷臣僚中关于要不要在中国修建铁路发生了两次激烈的争论。
19世纪60-70年代的争论,主要是清廷官员与在华欧美外交官和商务人士之间的论争。1865年,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递《局外旁观论》称:“凡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人行。”1866年,英使馆参赞威妥玛上《新议略论》称:“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欣悦”。英国驻京外交官密福特说: “上星期(1866年4月一笔者注),我们去了总理衙门,过得挺痛快。铁路、电报、违反条约等老话题,已经谈了上百次。恭亲王十分紧张,坐立不安……”1875年,德国公使巴兰德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称,铁路是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的关键因素,最后说:“当今之世,如尚有一二不以电气蒸汽为救时急务,以为别有道以制胜于他国也,吾诚不知其将果操何道也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希望中国速开铁路,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但上述建议无一例外都被总理衙门婉言谢绝:“其开铁路一事,屡经各国公使晤时提及,均经本衙门理阻各在案。原因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至铁路一节,并非谓其无益,实因与中国地形不宜,前已历次布闻”。就连清廷当时最开明的官员李鸿章也认为:“查铁路费烦事钜,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至于其他枢臣疆吏,更是极力反对修建铁路,其原因大抵如下:“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洋人于内地“可任便往来”、使中国门户洞开、险要尽失、洋人可长驱直入……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连篇累牍的呈递到总理衙门。据统计,1867年10月至1868年1月,“各省将军督抚共18人纷纷专折各陈其说,其意皆在阻止洋人在中国建造铁路。”
应该说,当时清廷大臣对铁路于国家的富强功用多少还是有所认识的,但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历,使清廷对其怀有深深的戒心。对于铁路所具有的侵略的能力,满汉大臣从一开始就“是不予置疑的”,因此,当时人们的心态,多少有着可以理解的方面。由于大臣们的集体反对,各国要求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建议也就只有束之高阁的命运。
但英国商人并不死心。英商怡和洋行,在1874-1876年间,瞒着上海地方政府,以修建普通道路为名,偷偷修建了一条从吴淞口到上海租界总长为12英里的铁路一淞沪铁路,试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迫清廷接受铁路。但路成之后,清廷与英国及怡和洋行经过近一年的交涉,1877年10月花费28.5万两白银的代价将其收回。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收回由中国商人自己经营,但南洋大臣沈葆桢则说不能让后人觉得开铁路是由他而起,于是下令将其拆毁。对于沈葆桢拆毁铁路之举,实在让人觉得难以理解,而李鸿章则直接说他“识见不广”.此举意在“邀取时俗称誉”。固然,当时在中国民间存在着不小的反对建设铁路的声音,但人民并不十分排斥铁路、轮船、电报等先进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守旧派动不动以民间的反对作为说辞,实际上只是拿来做幌子罢了。“今闻华民多有愿设火车者,惟朝廷尚未准行。”英国媒体也报道说,“这个国家的面积要比整个欧洲都大,然而目前还没有铁路或电报把这个广袤帝国的一端跟另一端连接起来。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等贸易口岸之间有一些外国轮船在航行,这些轮船上总是挤满了中国乘客,这说明中国人并不反对现代旅行方式”。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人,都对铁路对于中国富强的重要意义有十分明确的阐发。但王韬等人由于当时地位还比较低微,其主张尚无由上达天庭,因此对决策层不能产生作用。至于更下层的民众的声音,就更没有渠道使朝廷知晓。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关于在中国建设铁路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一方面是清廷加强国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洋务运动继续推进的需要。在前者,随着沙俄蚕食我国新疆边境地区,英国深入云南地区探险传教,法国在中越边境蠢蠢欲动,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及其对琉球、台湾的侵略,使清廷感到了巨大的威胁,迫切需要加强海防与陆防安全。而在后者,随着煤铁等洋务事业的持续推进,对大型、快捷的新型交通工具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以满足生产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醇亲王奕譞的主持下,清廷终于在古老的的中华大地启动了铁路的建设,决定“试办铁路”。1881年12月,全长11公里服务于开平矿务局煤炭运输业务的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是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这条铁路通车不久,朝廷中的反对派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由,朝廷为其蛊惑,乃下令禁止使用机车,而改为驴马拖曳。在李鸿章的呼吁下,1882年复改为机车牵引。这条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开始,构成了今天我国铁路网中最早的一个区段。
虽然唐胥铁路建成了,但清廷对铁路建设仍然疑虑重重,因此,尽管李鸿章等人一直主张延伸唐胥铁路,以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直到中法战争失败后的1886年才开始了这条铁路的展筑工作。1885年,清政府迫于中法战争的失败,鉴于海军力量的薄弱,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指挥海军,并由该衙门兼管铁路事务,从此把铁路和海防联系起来。此后,在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海军衙门大臣奕譞的主持下,唐胥铁路分别向天津、北京及山海关方向延伸,1887年延伸到芦台,称唐芦铁路,长45公里:1888年秋,该路完成了芦台到塘沽和天津的一段,至此,东起唐山,西至天津,全线130公里通车运营,该铁路也改称唐津铁路。
唐山天津铁路筑成后,按照原定计划打算向东延伸至山海关,向西准备延伸至北京附近的通州。天津通州之间,客货运输都十分频繁,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对于拱卫北京的安全,以及商业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津通铁路的修建,虽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可是正在勘探、购地和招股的时候,反对筑路的声浪突然兴起,于是筑路派与反对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从1888年12月到1889年2月间,余联沅、屠守仁、吴兆泰、张炳琳、林步清、洪良品、翁同稣、孙家鼐、尤百川、文治、奎润、恩承、徐桐、孙毓汶等人,纷纷上书极论铁路之害。他们的主要反对理由如下:“自外交上言,谓洋人遍布宇内,易滋事端,穷民迁怒,或且铤而走险。自国防上言,谓尽撤藩篱,洞启门户,不啻为外人施缩地之方。自经济上言,谓自办则库空如洗,借债则利息太重,少造无益,多造耗费。且购买洋料,损己益敌,漏税可虑,国课不供。自民生上言,谓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水手车夫负贩,将均成饿殍,且物价以流通而益贵,生活以便利而愈难。自礼教上言,谓田庐坟墓,系祖宗所遗,谁肯轻迁徙,且习奢侈、染邪教,有伤古风。其甚者,且谓穿凿山川,必遭神谴,变更祖制,大祸将临。”总之,铁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不能修建。上述官员大多任职中央,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故而空谈有余,时务则不足。因此,李鸿章对他们的言论极为反感,曾辛辣的讽刺他们说: “翰林为较有影响之阶级,多半无事可做,为失意之穷儒,喜劾论而无力,习性反外,尤其对外人之近于推翻孔教者为最反对。然翰林为中国最宝贵之读书分子,任何人欲改革中国,欲在中国有所行动,必得翰林之士人赞同而后行”。
针对守旧官僚对修建铁路的攻击,奕譞、李鸿章等人也从各个方面予以了反击。虽然李氏百般解说,但仍然无法遏止反对者的攻击。最后海军衙门和军机处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奏请沿江海各地督抚将军也参与讨论,结果地方督抚也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派。支持或基本支持的主要有: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修筑从陶城埠到临清的漕运铁路:两江总督曾国荃,极力支持李鸿章和海军衙门;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坚决主张修建津通铁路,江苏巡抚黄彭年亦主张兴修津通路;江西巡抚德馨主张修建保定至王家营的铁路: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修建芦汉铁路。反对的主要有:湖北巡抚奎斌、安徽巡抚陈彝、闽浙总督卞宝等人,盛京将军安定在复奏中,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清廷在综合了各方意见后,认可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缓建津通路、改建芦汉铁路的建议,张的这个建议经海军衙门上奏并得到清廷批准。从这个结果看,主张修建铁路的大臣占了上风。
应该说,此时清廷决策层对铁路建设的心情是较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铁路对于维护清廷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对如何修建和先从哪里修建铁路则拿不定主意:另一方面,清廷对于铁路的所谓“弊端”也感到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守旧大臣的种种说辞,尤其是建铁路会导致“门户洞开”、以及由此引发社会动荡的种种说辞,深深触动了最高统治者惧怕洋人侵略和下层民众动乱进而危及政权能否存续的敏感神经。基于上述矛盾心情,清廷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以芦汉铁路代替津通铁路。
三、晚清铁路论争中的文化意蕴
什么是文化?据说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500多种,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200多种。可见,给文化下定义是如此的容易,又是如此的困难。文化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化差别是人类群体之间的真正差别,“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型和肤色。”这个观念,中国古人也曾经反复予以阐发,其中唐人程宴说得最为明白:“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也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华夷之辨”或者说“夷夏之辨”。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以文化划线来区别“华夷”,其潜在的心理是“中华文化优越论”。“中华文化优越论”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是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周边、领先于世界在文化上的突出反映。“按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2000年内如果不是惟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中华文明本来就是上古华夏各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产物。因此,包容性与开放性原本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特征,所以,中华文明并不惧怕异质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成功消化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因素,如草原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最典型的则是佛教文化,这就使得中华文化愈加严整精微。
近代以前,在长期与异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从未被任何外来文化击溃,总是能够化外来文化于无形。在一次次成功化解外来文化的冲击的过程中,中华文明逐步走向成熟,也越来越自信,自信到认为中华文化就是全部世界。到了清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达致峰值,清王朝号称“天朝”。柯文说:“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自身就是世界,认为可以环抱世界。直到1840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但到1900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这是历史事实。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1792年,乾隆帝傲慢地对远道而来的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戛尔尼使华的失败,“颠覆了西方对中国的传统认知,直接影响了英国对华政策”。
即使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仍然没有警醒中国土大夫的文化优越感。这里可以以19世纪60年代,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来说明这个问题。1860年,英法联军来到北京,在摧毁了圆明园之后,逼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允许欧洲列强在北京设立公使馆,而且可以觐见皇帝,到了这个时候,清朝统治者依然认为,外国公使和历史上的“朝贡者”没有什么区别。“中国的皇帝不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可以具有跟他同样的权力——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表达天意。所以中国人有一个成见,认为所有来见皇帝的人都只能作为附庸者前来朝贡。关于这种礼仪,中国的文人或是官吏阶层拒绝对现状作任何改进。他们曾经坚决反对铁路和电报。”这里,“中国人有一个成见”中的“中国人”,即指中国士大夫。因此,在觐见皇帝的问题上,清廷仍然试图令外国公使行“三跪九叩”之礼,在马戛尔尼时代都是不可能的事,过了将近70年,满清贵族还没有把事情搞明白。
回到本文讨论的铁路问题。很多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大都经历了疑忌——试用——高扬三部曲。清廷对待铁路即是如此:最初满朝官员都反对在中国建设铁路(19世纪60年代),继而决定试办铁路(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接着决定“毅然兴办”铁路(19世纪90年代),最后掀起了建设铁路的热潮(20世纪初)。这一时间跨度恰好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历时整整40年。建造铁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对声音?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一向是最流行的解释。近代来华著名传教士林乐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深的研究,他对中国文化中今不如昔、尊祖法古的历史观、文化观提出了批评:“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
对于中国文化“敬天法祖”的保守性,不仅是林乐知,很多来华的西方人士都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性提出了批评。早在利玛窦来华时代,他就对中国人昧于世界大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后来的来华西人,一直在不断地指出这一问题,1844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说:“(在中国)文章的优劣是根据古代圣贤的风格与情趣来判断。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文人追求的是儒教的传统思想。西方以独创性为主来评判文章的优劣,中国却恰恰相反,遏制独创性,把改革创新扼杀在萌芽之中。因而,中国的学者把精力浪费在维护知识一成不变上。”20世纪初,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写道:“朝廷的诏书和清国官员们的说法都极富于哲学意味,他们认识到重组国家政体已成当务之急,但是……帝国里的每一个满清官吏,都决意不会去做‘将自我否定的条例付诸实践的第一人。在司法程序、金融……铁路、矿山与工业的发展上,方方面面的改革莫不如此;他们都在理论上认识到立法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却无人迈出脚步”。中国文化的这种空谈论调与脱离实际,一直是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文明过程中的最大阻力之一。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刚刚兴起时,针对守旧官僚对洋务事业的攻击,恭亲王奕?就曾十分犀利地批评了大学士倭仁等人夸夸其谈、不谐时势的迂腐之气:“该大学士(倭仁——引者注)……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祷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后来主持铁路事务的醇亲王奕譞也说:“窃查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譞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指中法战争——引者注),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奕譞能够转变思想,并大力推行铁路建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固然是铁路建设的阻力,但并非事情的全部。一些来华西人对于晚清的铁路争论,提出了颇为值得关注的看法。如英国外交家密福特曾指出,中外交流的“所有障碍都来自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与外国人任何方式的交往都会引起清朝官员无端的恐惧,觉得是对他们的统治及特权的永久威胁。而在他们的特权中,巧取豪夺与残酷无情是最重要的两项。”再如1898年12月至1899年3月,到中国来负责勘测粤汉铁路线路走向的美国铁路工程师柏生士说:“我认为,在中国反对建造铁路的最重要的意见主要来自官僚阶层。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采用现代交通手段之时,在全体国民必将随之破除迷信、接受新思想之日,中国官僚阶层的政权定会土崩瓦解,他们的特权也会受到大大的削弱。当然,中国普通百姓中间还存在着对革新的强烈偏见,但是只要这种革新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与鼓励,偏见就不难消除。”在密福特、柏生士等人看来,晚清统治者并非不清楚铁路所带来的利益,但更担心铁路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即便利的交通,使人口和信息迅速流动,会使人们更多更快地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促进社会转型。事实上,“铁路可以使社会转型”,日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轮船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人员、思想、机械和跟现代文明相关的其他任何东西。中国的闭关锁国不可能长期抵制这种人侵。”因此,对于一贯秉持愚民政策的统治者来说,是十分可怕的威胁,无怪乎一部分守旧派官僚这么卖力的反对铁路的修建。
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时期运用权力的杠杆启动现代化事业进程,是集权国家的一种共有现象,如日本、俄国等国早期现代化运动就是如此。”而且,“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己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因此,对于清廷统治者而言,假如能对俄、日等周边国家活生生的发展实例,能够及时了解、学习、吸收、引进,或许近代中国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然而,历史没有假设。面对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最高统治者显然缺乏应对的手段。
著名学者赛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他还引用托马斯·库恩的话说,文明和文化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那么,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头等重要的思维模式究竟是什么?“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仁和群体优先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价值理念。”和上述价值观相表里的则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以及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设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观念、准则、制度和思维模式塑造了每一个中国人,上至达官贵人等精英群体,下至贩夫走卒等普通大众。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十分感叹李氏所处的境地,认为李氏实为世所罕见的人才,在满清大臣中最具世界眼光。梁氏说:“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这是说人们的思想为社会环境所制约而难以突破, “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这种“习俗义理”之所以会如此禁锢人们的思想,其原因一是长期教化的渗透,二是历代雄主之布画。无论是“教化”,还是“布画”,都有国家机器制度层面的配合,恩威并施,从而将统治阶级的意图深深注入每个人的骨髓和血液,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只有服从顺应这种文化与制度安排,才能在这个社会立足。
任何社会的发展,精英人士都发挥着引领作用。晚清以降,当西方文明携其先进科技与思想加速东来之际,中国士大夫集团发生了分裂,保守主义者严守所谓夷夏大防,试图抵制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污染”以维持中华文明的所谓“纯粹”:但与此同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也使一些开明的士大夫认识到,西方文明代表了中华文明从未碰到过的强大力量,于是他们开始接受这种文明,并试图用西方文明弥补中华文明之不足。包括铁路论争在内的洋务纷争正是士大夫集团分裂的一个明显标志,这种分裂是思想观念的分裂,这种分裂为思想观念的进步打开了一个通道。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然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其中所蕴涵的深刻哲理则不容置疑。笔者想说明的是,克服思想观念的束缚及依附于这种观念上的重重阻碍,打开思想进步的阀门,是我们的社会真正取得进步的不二法门。葛兆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衡量:一个是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维度,另一个则是思想发展的维度。工业革命以来,知识与技术的更新速度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随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进化。但是,“一个历经数千年确立起来的,在中国已经拥有足够历史资源,并且自给自足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它的整体倾覆并没有那么容易。”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我们对于中西文化,仍然充满了疑惑。何时、如何跨过这个“历史的三峡”,人们都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