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我是五四“新传统”的鼓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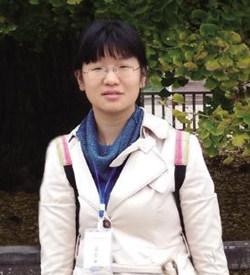
卢欢,80 后,湖北某媒体文化记者。关注出版动态,遍访文化名家;喜好阅读,“为了让所有的善意颗粒归仓”;带着谦卑、耐心与好奇心,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丰富的过渡色彩。
很多人知道刘川鄂是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而了解他的人会想到他的网名叫“浪子阿川”。
自称是“浪子”的他,格外推崇自由。这可能与他从小就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长大,又较早地进入社会有关,天性中有野孩子的成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谈到自己所理解的自由,道出心声:“我一直提倡做一个浪子,不是做一个孝子。所谓孝子人格就是听话、服从的人格,所谓浪子人格就是一种自由、飞扬的人格。”
毕业留校后,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成了刘川鄂的主业。二十多年来,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从事同一份工作,对于他来说,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大的毅力,而是因为慵懒、怕折腾。即便是没占到好位置去争取话语权,或被人视为不上进,这些他都不在乎。他只是在想:“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作为教师,在北大教书与在湖大教书的幸福感是一样的。”

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中,刘川鄂对这些年的文学研究做了一番总结。从现代到当代,从文学史到文学评论,从理论探讨到文学时评,从纯文学到大众文化,大致算得上他的学术轨迹。
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他很早就下决心,从事学术研究,要出于对人类的关切和热爱,要有探寻真理的热情。“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爱到处宣扬自由梦”,最初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就融入了他的人文理想和艺术美学。从青年到中年,与现代作家鲁迅、张爱玲为伴,他更是用心写下了大篇幅的“看张”文字,也成就了张爱玲研究专家的又一头衔。
在当代文学评论上,刘川鄂更多时候都在紧贴着湖北基层作家的步伐走。他新近发表了评论文章《新世纪诗歌的互联网传播特性》,把湖北钟祥诗人余秀华走红事件称为“仿综艺选秀事件”。他较早琢磨在电媒时代如何对优秀的作品进行有效宣传的问题。正如他所言:“一个好的作家,如果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的话,除了传统期刊、出版方面,还应该注意到新媒体的方式,利用网络等平台,扩大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一
刘川鄂自称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且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进行综合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他在大学里读了四遍《鲁迅全集》。从天性上来说,鲁迅那种清俊甚至刻薄的性格,跟他这种温和、散漫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隔膜。所以,他写鲁迅的文章不多,但鲁迅对他的事业、精神气度影响却很大。“鲁迅通过批判传统文化来改造国民性弱点,这是他一生的伟业,也是我的文学活动的重要精神支柱。”
五四以后开始张扬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卢欢:您在文学研究上最初起步于“现代”和文学史,是什么契机促使的?
刘川鄂:今天的60后和50后中很多人都有文学情结,倒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多么发达的文艺细胞,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知识资源、精神资源非常匮乏。经济上極度贫困,精神上反倒是高度亢奋,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找书看,但又没有什么书看,因匮乏而渴求,因渴望而热爱。
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看大字报识字,看《毛主席语录》,偶尔翻翻连环画,都觉得很新奇。那时候,被允许的文学读物就是毛主席诗词、鲁迅和浩然的作品。再加上那时最主要的学生活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宣传队创作、表演的诗朗诵、对口词、三句半、样板戏等,是我们最早的文学训练。
上大学后,据我观察,农村来的同学多钟情古代文学,城市来的同学偏好外国文学,像我这样县镇来的同学,往往在这两种夹缝中间,多喜欢现当代文学。因为小时候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底子差,又在高中阶段读过一些鲁迅的作品,导致我很早对现代文学怀有兴趣。我大学的一个老师徐福钟是同乡,也是搞现代文学的,我经常去蹭饭聊天,自然朝这方面靠得多一些。我做现当代文学研究大概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有个缺憾,那就是我过早地涉入现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的知识准备不是很充分,也妨碍了后面的发展。
卢欢:您也是喜欢文学写作的,有没有可能像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於可训那样又搞创作又搞研究?
刘川鄂:我从十六岁读大学开始,经常为我将来到底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的问题苦恼纠结,不能自拔。直到现在,我的大学同学王兆鹏(武汉大学教授、著名诗词研究专家)还记得我当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不要做研究的人,要做被研究的人。心高气盛,天真可笑。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的价值从整体上来说高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它更体现文学本身的价值。郭沫若讲过,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我加了一句:“评论是长舌妇”。那时候,我是不太在意搞研究、评论的。
大四那年,我二十岁生日的那天,给一个创作杂志和一个研究杂志各投了篇稿子。我想,什么东西发表了,我就搞什么,就像今天掷一个硬币来做命运的选择。很不巧,《青春》的编辑给我回信说,我的爱情小说写得很清新、抒情,但社会含量不够,退了稿。而另一篇《关于加强新文学资料建设的建议》被《新文学史料》刊载了。于是先就这么定下来,我就踏实地做研究了。
评论家大多有一个破碎的创作之梦,当今中国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可能先是想当个作家。此后,我也虚构过小说,有时也写诗,但我始终对我的语言不满。我不乏想象力,不乏琢磨人的能力,但是我的语言过于平实、平白、平淡,所以没有在创作的路上走下去。
於可训教授最早是搞文学创作出身的,现在退休了,又回归创作。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这样。搞学术是规范的生活,搞创作是反常态的生活。一个人要做到一辈子的反常态,很不容易。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俗的生活和世俗的幸福的一种拒绝,要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气质和决绝的态度才可能写出佳作。也有既搞创作又搞研究的人,但这种人一方面的成功总会被另一方面的所掩盖。除非钱锺书这样的少数,但是他也就写了几部作品嘛。
卢欢:您自认为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受益于五四的‘启蒙情结”这样的话也出现在新书的自序里。能谈谈您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吗?
刘川鄂:要感谢改革开放,要感谢那样一个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的年代。鲁迅曾经说过,旧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五四时代,因为是从旧营里来,所以反戈一击最为有力。我也是在极度物质贫困和政治高压的环境中成长的,在从少年到青年的思想活跃期,恰逢那样一个全民疯狂阅读、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我的思想能量也被大大激发了。
古代中国人只知道尊崇父亲,偶有埋怨,但只有从鲁迅开始、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开始审判父亲。五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关节点,即是从家国天下到个人本位的转变。古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整体上是家国天下。到了五四以后,就开始张扬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像李大钊说,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像胡适说,国家之上是人类;像鲁迅怀疑我们中国人要被世界开除球籍;像周作人说我们中国是人的沙漠,要辟人荒;像郭沫若站在现代个体人的视野来爱国家……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把我们传统中国的文化,把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家国天下式的、泛政治泛伦理的文化否定了,要张扬一个现代的、民主的、自由的、个性的文化。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延续,而是对传统的否定、颠覆。五四用价值重建来代替社会改造,重建一种现代的、更人性化的、更值得肯定的价值。我觉得五四是跟古代划了一个界限,开启了一个现代文化,我肯定这种改变,所以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
什么是一个人的终极价值
卢欢:就学术研究而言,您是最早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进行综合研究且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曾以自由主义文学这条线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主流意识所遮蔽的、更接近文学本质的另一文学发展支流。您解释说,对此的研究源于您的自由梦?
刘川鄂:这跟我的人生价值观有关系。我认为,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很偶然的,没有谁规定你要出生,那么,个人就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价值。人生本来就是没有地图的旅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是社会的外在規范,而是来源于并服从于自己对人生的体悟。
中国古代社会宣扬人的幸福是立德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主要是对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而言的价值观,对普通人来说,则是福禄寿喜。古代的哲学不考虑个人幸福,而现代社会更强调个人的价值。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内心是否充实。一个人要充实,肯定要读自己想读的书,做自己爱做的事,跟自己心爱的人无忧无虑地在一起。这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自由应该是一个人的终极价值,虽然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就像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中国人的死脑筋不太懂这个,怎么还有比生存、家庭、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呢?当你的生存、家庭、爱情限制你的自由,就走向了人的生存价值的反面。
我在1993年夏天上课的时候,上午讲了不自由的闻一多,下午要讲崇尚自由的徐志摩,中午午休时,我就梦见我跳上了一辆开往成都的火车。当时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预选赛在成都开打,当时我和朋友约好去看球的。车厢之间有阳台,可看见外车厢标识始发地和目的地的标牌。阳台上站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长发飘飘的女子,我不知道她是谁,就像李金发梦到的金发女郎。我问她,火车开往哪里?她指向标牌上的两个惨白的正楷字——自由。
当时,我内心非常震撼。这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一个梦。如果要我说出我认同的人生价值的话,那一定是爱、美、自由这样一些精神层面的价值。
卢欢:相比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其他文学派别,自由主义作家艰辛地在夹缝中生存、选择,他们的主张及其作品更能触动您?
刘川鄂:我的人生追求跟我研究的自由主义文学有精神上的契合之处。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写出了传统的制度、文化对人的精神上的奴役。郁达夫的作品,宣扬知识我不要,地位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只要异性的爱情的人生,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对个人幸福的肯定。郭沫若的诗歌《女神》,是民主和平之神的象征。还有如施蛰存的小说《石秀》。《水浒传》写的石秀就是道德石秀,对朋友之妻,只有道德,没有更复杂的人性感受;而施蛰存写的石秀,既谨守叔嫂之防,同时对美女又有内心的喧哗与骚动,写出了人物内心的丰富性。这可以看得出来现代作家和古代作家在认识人、认识道德上的差异。读这些作品对我有很大的触动。
卢欢:您同时也发现,比较一下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人力车夫题材,便可看出自由主义作家对民众苦难普遍较为隔膜,也难以充分贯彻甚至难以坚定文学独立、人性中心、自由创造的原则。所以,在您看来,它的总体成就并不高?
刘川鄂:是。中国自由主义作家主要是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大多是留学欧美的。当时有几个政治力量相互较量,所以有很多的空隙,反而促进了思想繁荣。不过,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鲁迅形容他生活的时代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当面对内忧外患,连生存权都没有解决的时候,谈到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有时未免奢侈。所以,中国自由主义作家,相对于其他流派来说,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较高的成就。但是,应该说,在整体贡献上还是有局限的。
举例来说,我认为作为民主主义作家的巴金,他的小说的技巧成分是很弱的,心理描写缺乏深度,但就因为他表现了民众的反封建情绪,所以比同时代很多自由派作家的影响大得多,光《家》这部作品在1949年前就印了四十多版。那些自由派作家,后来有的转向了更加激进的立场——“左翼文学”,有的终止了探索,难以为继。
文化不是越长或越特越好,而是越优越好
卢欢: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看来,《新青年》乃是自由言说之始。今年恰逢《新青年》诞生100周年。您怎样看待这本杂志在当时横空出世的意义?
刘川鄂:《新青年》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自觉,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确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它之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还应有待更充分的认识。
当时还有好几种鼓吹新思想的启蒙杂志,比如《新潮》、《新妇女》等。也有些杂志,过去认为是反动的,现在宽容点的认为是文化保守派的,比如学衡派、甲寅派、林琴南等。
《新青年》毕竟是在整体上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立的表达。所以,它的出现受到旧势力的打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历史毕竟走到了现代。中华民国至少是形式上已经建立了民主政體,学校教育也注重对新思潮的接受。1920年,教育部明令学校要用白话文教学。此外,都市的繁荣、新闻出版业的强势增长,使得知识分子可以不依赖官方,教学、写作等成为独立的职业。新的刊物和它表达的新思潮,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卢欢: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前不久提出,我们纪念《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需要重新思考和彰显“新传统”的价值。在您看来,《新青年》留下了哪些“新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刘川鄂: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其实还有一个研究现代文学很有名的教授王富仁提出过“新国学”概念,跟温儒敏所说的“新传统”意思相近,但“新传统”的含义更加明确。他们看到了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合理成分,所以提倡这样的“新传统”是很有意义的。我本人也是“新传统”的鼓吹者。
我认为,五四最大的发现是人的发现。关于五四文学,我的博士导师易竹贤在胡适的基础上概括为: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活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就是关于个人价值的探讨、肯定个人自由的文学。所谓“真的文学”,就是鲁迅所肯定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所谓“活的文学”就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一种更民主更大众更晓畅的表达。
从文学而言,“新传统”就是“人的文学”的传统,“真的文学”的传统,“活的文学”的传统,的确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珍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繁荣、腾飞,有人希望从文化层面上证明自己,证明我们这个产生经济奇迹的国度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怎么证明呢,显然只能用从属于自身的文化来证明。但是,提倡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人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今天中国的进步是吸取了世界政治、经济经验和优秀文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带来的。从整体上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带来了中国人精神的解放,尤其是个人的解放。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个核心的事关人伦的价值观念,比如孝、忠、义、贞洁,是不能进行现代性的转换的。所以,抛开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直接拥抱老祖宗,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卢欢: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新青年》和五四一代太“激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您觉得呢?
刘川鄂:这要看你的价值立场怎么摆。跟民族情结重的人不同,我这些年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文化不是越特越好,也不是越长越好,而是越优越好。文化长和文化优是两个概念,长不长、特不特,没有优不优、好不好重要。怎么判断文化的优越呢,就是看人的幸福感。虽然我们说的幸福感包括很多主观的东西,但是一个人要衣食无忧,有尊严地活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应该说今天的社会条件比古代好得多。如果你真心认识到现代文化给人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古代家国天下的幸福感,如果这个共识可以达成的话,就不必过分在乎文化是否断裂。
二
米兰·昆德拉说过,如果小说放弃了人的探索,小说就死亡了。在刘川鄂看来,通过形象的、审美的方式探索人性,用虚构的语言揭示出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是文学尤其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如今有了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像化文学,文学与影视攀亲的越来越多,承认多元,宽容对待复杂多样的创作现象,注意审美创造的多样性,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作品,应是今日评论家的基本素养。“在一个充满审美差异的艺术伊甸园里,批评家尽的是浇灌沃土、培育花朵、剪除杂草、驱逐蚊虫之责。”
投中五部完全可能,但我投了另外三部
卢欢:您今年以专家的身份加入到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阵容当中。这次评奖过程是怎样的?面对参选的两百多部长篇小说,当一个专业的批评家、评委与当一个普通的读者有何不同?
刘川鄂:这次“茅奖”评选活动在今年5月确定评委名单后,让评委先分散阅读,然后赴京集中阅读和开会,从7月29日报到至8月16日投票结束,共十九天时间,住在八大处一个封闭的、没有挂牌的单位。
有人质疑,入围的252部作品评委们都看完了?其实这不成问题。因为,第一,评委大部分都关注近几年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从评奖开始,而是从作品发表的时候就关注了。参评之前,我就关注过几十部名家名作。另外,阅读和讨论的机制保证了不留死角。每一部作品有好几组的好几个人都同时关注到。六轮讨论,六轮投票,在程序上是合理的。真正的好作品都在其中,不会轻易被漏掉。因为最后一名是并列的,第一轮投出81部,第二轮投出41部,后面几轮分别投出30部、20部、10部、5部。期间都给评委补充阅读时间,评委随时可以调阅作品。如果有分歧,有的评委还重读了部分作品。
这是我第一次做“茅奖”评委,一下子读那么多的长篇,有时觉得很沉闷,两眼发花脖子酸痛也要硬着头皮读下去。一般来说,读文学作品比读学术著作难。学术著作以观点、材料和论证取胜,有常规的体例,容易作出评判,但面对一部长篇小说,如果语言不错的话,不读完很难说它好不好。不过,像我们这样的评论家和期刊编辑,作为专业读者,对一个作品的整体判断能力和对那个作家的整体判断,应该说比一般读者要容易一些。一般读者缺乏对中外优秀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的整体性参照,往往是凭兴趣阅读,比较随意,个人喜好色彩过浓。
卢欢:六十多名评委在各轮评选投票过程中出现过哪些分歧呢?
刘川鄂:一般来说,讨论时,大家会对各自肯定的作品做出明确的表态,对别人肯定但自己不太肯定作品,也会婉转地提出不同看法。有人比较喜欢充分表达意见,有人喜欢用投票直接表达自己的评判和选择。进入第二轮第三轮投票后,比较有共性的问题,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曾经获“茅奖”的作家要不要继续投下去?由于大家有个共识,“茅奖”带有终身成就奖的性质(除了张洁获奖两次外),已经获奖的作家在进入第四轮的时候,都掉下去了。大多数评委认为,还是要给其他有特点的作品和有贡献的作家更多机会。除非你的作品好到众口称赞、无人可及的程度。
第二,“茅奖”到底是中国作家奖,还是汉语文学奖?这里牵扯到一个重量级作家,严歌苓。大家对她的《陆犯焉识》评价非常高。很遗憾的是,她因为国籍问题而没有被推到最后一步,但这也确实引发评委在这个问题上的考量。
第三,围绕王蒙的《这边风景》的分歧。从1950年代至今,王蒙对当代文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1950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基层官僚主义的批判,1980年代复出后又写了一系列现代派小说,至今一直在探索、写作。这次申报的作品写于1970年代,2011年出版,他作出了修订,力图减弱或者淡化那个年代的写作印记,并增加了“小说人语”部分。评委们充分肯定王蒙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贡献,也肯定这部作品在表现边疆多民族生活的鲜活、真实、丰富。但它仍然留有极左思潮时代的痕迹,这也是某些评委没有投这部作品的原因。
卢欢:都说每一届“茅奖”获奖作品是代表了最近四年的长篇小说作品的最高成就。此次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这五位作家获奖,这个最终结果是评委们趋于保守而作出的么?
刘川鄂:那倒不是,前面所说的因素排除后,留下的遗憾应该不是太多。评委们在投作家和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联上,应该是有一个综合考量的。没有进入前十名但有实力得奖的作家和作品是有的。比如韩少功的《日夜书》,这应该是他写知青的集大成作品,但確实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结构有部分的游离,写得有点“干”。我也很关注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他在这部小说中把人物写得那么鲜活,语言有抓人心魂、欲罢不能的魔力。但也有个小缺憾,他着力描写的有贪腐行为的男主人公,缺少谴责和忏悔的成分。
我和部分评委对70后、80后作家也很关注。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表现70后的生活场景和精神状态非常丰富充沛,人物很鲜活,细节很有吸引力。80后作家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写贞洁坊、节妇、缠足,通过好几个女性的悲剧表现传统中国野蛮、落后的文化,应该说是很有历史感和精神厚度的。但他们的作品都没能进入提名名单,因为还没达到一个无可挑剔的程度。另外,同等条件下,那些知名的50后60后作家,受到的肯定可能会更多。
卢欢:从最后一轮的实名投票看,您只命中了两部获奖作品:李佩甫的《生命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加上林白的《北去来辞》、红柯《喀拉布风暴》、阎真的《活着之上》,可否对您心目中的这五部作品进行一个点评?
刘川鄂:我要投中五部是完全可能的。因为20进10的时候,最后获奖的五部作品的得票率远远高于另外五部,在这种情况下,一两个评委的投票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是要一个满堂红,还是个人化?我纠结过。出于肯定和鼓励一些新的写作要素的目的,我投了另外三部,虽然明知道它们很可能得不了奖,虽然这样看起来我的中榜率比较低。
从女性主义的个人化写作到底层写作,林白一直是个非常勤奋有创造性的作家,写作的路数很宽,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默默写作,不太理会写作之外的人和事。《北去来辞》写转型期里中国女性从乡村到都市的生存状况,通过一些相关人物生活、命运的变迁,反映人们心灵的变化,很有深度。这个作品刚开始结构比较散,不过读下去会发现她是有意这样写的,但这可能有点考验读者的耐心。
红柯的《喀拉布风暴》表现了一种爱情至上的游牧民族的精神气质,对汉民族家国天下的文化来讲是一种异质。这是一部浪漫的、有血性的、有灵性的作品,虽然某些细节上还显粗糙。在如今写实为主导、先锋退隐的文坛风向之下,他的浪漫主义冲动值得肯定。
阎真之前出版的《沧浪之水》对读者影响很大。他的《活着之上》写大学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窘况,写得非常真切细致,有人性批判和体制批判的锋芒,但诗意和文采还不够。而我肯定的,就是他的这种现实反思和批判精神。
评论家要重视对审美价值高低的评判
卢欢:就此次的阅读情况,您觉得可以怎样去总结近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状况?
刘川鄂:这样的概括其实比较困难。以前我的整体阅读量不够,这次集中恶补了一下。如果说我们既要有文学高原又要有文学高峰的话,那么在我的心目中,还没有出现高峰作品。它们都不无缺憾。比如这次获奖作品中,《江南三部曲》,三部的质量是不整齐的,写当下的第三部比较弱;《这边风景》极左化文笔是一个明显的硬伤;《生命册》写乡村都市,写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变化,都很有力量,但是关于大学、商海的细节好几处明显不合情理,这对写实主义手法的长篇来说也是硬伤。《繁花》可能是评论家和读者认知最一致的作品,但它用吴方言来写,强化地域色彩,也可能失去对这种方言不太熟悉不太认同的读者。也有读者认为它过于琐碎。《黄雀记》可读性非常强,但里面的核心细节即1980年代的那件强奸案,铺垫不够,妨碍了作品的可信度。
自现代以来,中国作家写农民和写知识分子两大题材的成就比较高。而都市书写在近几年已经开始有出色的表现。与此相关,中国作家擅长写乡村百年历史、写家族的争斗和几辈人的变迁史。随着全球化、都市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生存价值的凸显,那些以个人或者相近的几个个体为主人公为主题的作品涌现,也是这些年的新变化。
近些年有的长篇小说作家在结构上做出新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就是采用正文加某些注释的方式,效仿学术著作的真实性,又不妨碍整体的艺术表达。《生命册》一章写乡村一章写都市,用关键人物来联接,也是在结构上有突破。
卢欢:关于优秀文学作品的甄别,您是否还在坚持如作家邱华栋所强调的“没有精神深度的文学没有价值”的类似观点?
刘川鄂:整体上说没有变化。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大致有三块:主旋律写作、纯文学写作和大众商业化的写作。对不同的写作,不应该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想写出心目中伟大的作品,还是要以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为参照,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在整个文学表达上有所追求。我一直赞赏那些丰富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相统一的作品,也就是有精神高度的作品。所谓丰富的人性含量,就是通过作品来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来丰富读者对人之为人的理解。这种表达是和谐的、完美的,通过语言、情节、结构来创造性体现的。
卢欢:之前您有个感慨是,在中国大众读者目前这种阅读水准、阅读趣味面前,反媚俗是批评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您觉得在这方面,文学批评家这些年做得怎么样?
刘川鄂:现在有三种批评,一种是文学爱好者、读者批评,主要是通过网络方式,往往是无意为之的;一种是媒体批评,包括传统媒体、网站、杂志,往往是以文化、文学事件为关注中心;还有一种是专业批评,包括学院派的大学教授、作协系统的批评家。从总量来说,今天的作协会员有十来万人,而稍微有点名气的批评家全国也就一二百人,而且还青黄不接。北京三五十个,南京上海的也就十来个,其他省的就几个人。文学评论更加小众化,对社会的参与度更小。说在反媚俗、引导读者方面,评论家严重失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次正式入会当评委之前,我把国内对那些知名作家的研究论文尽可能找来翻了翻,算是提前做点功课。我注意到,大多评论文章都是阐释性的,重在阐释作品内容和社会影响,很少能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充分的分析评判,更鲜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作品的不足之处。这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大问题、大缺憾。
我觉得,评论家应该重视对审美价值高低的评判。所以,我比較欣赏李建军、王彬彬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够勇敢地指出知名作家作品的不足之处。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太少了,凤毛麟角。我也算是这类吧,但我涉足名家的比较少,涉及基层的、未成名作家的比较多。最近刘慈欣的《三体》因获雨果奖又大热起来。我记得三四年前和女儿逛北京王府井书店时,她跟我推荐这部作品,我有意买来看过,觉得这部小说虽然有很多新意,有宇宙意识,但文学因素不够,能炒到那样的程度,令人咋舌,不可思议。
卢欢:作为湖北的学者、批评家,身兼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您很多时候都在湖北文坛现场,也为湖北文学写下了很多文字。就您的尝试来看,一个文学批评家对地域文学建设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
刘川鄂:没人能决定一个作家的层次。作家就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不满的人,通过自己的表达来表达对新的世界,表达对生活、对美的热爱。作家是最难培养的,也是不可能培养的。评论家对作家的帮助是有限的。当两者有共振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提高。我以评论家的身份参与湖北省作家协会的活动,是为了湖北文学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为了活跃地方文学的气氛环境,对基层作家有一些帮助和鼓励。
湖北是农业大省,包括武汉在内的城市都市化程度不高,湖北作家大都是凭热爱、凭生活感触来写,依附于土地、依附于个体生活经验,写实的风气比较浓,但缺乏提炼。湖北有一些出色的70后、80后、90后作家,像李修文,语言能力很不错。但整体上说,跟50后、60后作家比,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是在下降。湖北省作协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但需要很长时间去改变。
责任编辑 向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