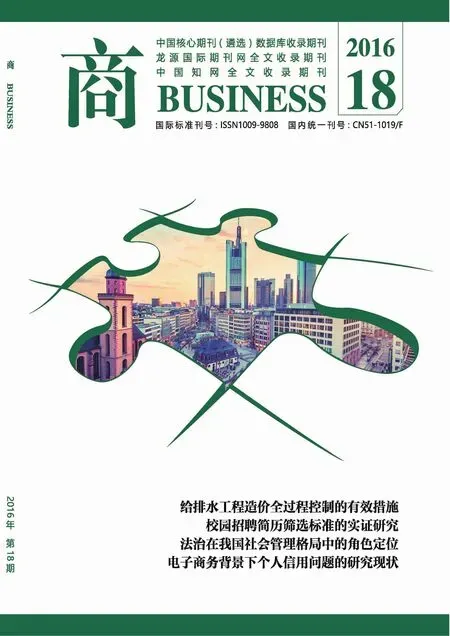论周朝罕见青铜酒禁的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郭兴(1990-),女,陕西西安,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摘要:铜禁是西周开始出现的新式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出土较少,就其使用范围和文化意义也有较大争议。出土于宝鸡石鼓山的铜禁对这种青铜器的进一步研究带来了可能。通过对出土文物“酒禁”的形制以及相关文物、文献资料记载的研究,讨论殷商末的饮酒风气和周朝初期禁酒令的颁布、推行和演变过程。
关键词:西周墓;铜禁;禁酒令
一、宝鸡石鼓山出土罕见铜禁
2012年6月22日,陕西宝鸡渭滨区石鼓镇石头村四组村民在开挖房屋地基时发现青铜器,随即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渭滨区博物馆组成石鼓山考古队进行发掘,出土文物多达101件,品类齐全,经确认这是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相比较其他器物来说,青铜禁是此次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并且也是宝鸡历次出土的铜禁中第一次得到科学发掘的,是宝鸡地区目前为止出土的第五件铜禁,是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第七件铜禁。①
二、“禁”的源解和历史背景概括
禁是古代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和宴飨时用来承放酒器的几案。《仪礼· 士冠礼》注:“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铜禁的发明是商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西周在商代青铜器技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创制的一种新形态的礼器。
宝鸡——也就是古时的殷镐地区,是西周的先祖的发源地之一,周族公亶父迁居岐山周原之地以后(也就是武丁时期),开始进入商人的势力范围,成为商王朝的附属方国。发展到武丁时期并且在进入到渭水流域后与姜姓部族结合,周人迁岐之举在在周代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关中水土丰茂,周人的势力从此发展起来。周文王之际,周人已经占据渭河流域,黄河中游之半,再加上晋南和汉江。而殷商占据黄河下游和东夷所在的淮上到海边②。并且殷商为东方夷族的叛变而牵制,国力消耗严重,再加之政治腐朽,统治阶层贪图享乐,可谓内忧外患。孟津观兵后两年,武王率军对朝歌发动攻击,战争过程已不可考,战争的结果是商纣兵败自杀身亡,商王国解体。
然而战争的胜利不代表政治的胜利,周武王只是一蹴而就地成为这个庞大帝国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战争胜利之后,还需要巩固统治安抚人心的政策。因此周武王进行了大型的分封活动以稳定政权,分封了大量同姓、异姓诸侯,给功臣分赏战利品。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的还有大量殷商晚期和西周初期的兵器和武器,结合墓葬形制、随葬礼器的级别和精美程度等因素判断,这座西周墓的主人应为西周初期的高等级贵族,墓主人生前可能曾为武王征商时立下过汗马功劳,随葬的殷商兵器皆为战利品,其余随葬的精美礼器以及两件铜禁足以证明墓主人战功之显赫。
三、酒禁和禁酒令
1、商末的饮酒之风和周初的禁酒意识
商末代统治者纣王酗酒乱德,统治阶级风气淫靡,国力日渐衰微,商末纵酒的风气,各种文献和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和生动的描述。最为出名的当属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描述:《史记·殷本纪》云殷王纣:“好酒淫乐,嬖於妇人。……大勣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诗经·大雅·荡》当中也有假托周文王的口吻感慨殷商灭亡的诗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③还有《商书·微子》云:太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表现了殷商时期清醒的大臣对于国家的命运深沉地忧虑。这些文献资料生动的描述也反映出商末统治阶层酗酒乱德到了怎样的境地,原本用作礼仪之用的饮酒成为了影响生产发展、政权稳定的严重社会问题。
商周文化有“青铜文化”之称,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主要代表。然而这两个时代的出土的青铜器也有所不同,殷商代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中占了很大比重,并且大多都是成组出现。到了西周初年,青铜器的数量虽然远远多于殷商,但是西周对殷商青铜器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技术制造层面,并且沿袭商代的酒器数量有了明显的减少,而且在在酒器的大小对比也有明显变化,大中型酒器明显减少,小型酒器开始增多④。器物形制的改变反映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传承和革新,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统治者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意志,是周代禁酒意识有力的佐证。
2、禁酒令的颁布
取代了殷商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如何稳固政权薄弱的新生政权,加强统治,避免重蹈殷商覆辙——尤其是西周以小邦的力量逐步发展起来而战胜了大国殷商,周初统治者可谓如履薄冰。周武王之后的西周第四代领导人周公旦(周武王胞弟)对于前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在封康叔到卫国(卫为殷商故地⑤)主持政事时——当时是已平息了管叔、蔡叔、武庚(商纣王子)叛乱之后,以成王之名颁布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载于《尚书》)。“酒诰”就是关于酒的命令,诰:告诫之文,帝王任命或者封赠的文书,上告下之字为诰。关于《酒诰》颁布的历史背景,《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中是这样记载的: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
周公告诫处封与殷故地的康叔,让康叔不要饮酒误政,意在警戒西周夺取政权和平息叛乱胜利后的高级贵族,怀有“鉴古知今”的精神,时时警醒自己,借鉴朝代兴亡的教训,改变不良的作风和习惯,才能够使周的统治长远。
《酒诰》⑥节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
从《酒诰》中我们可以看出,禁酒令的颁布是以维护国家稳定、巩固政权为目的,以上天和文王的口吻教导卫民有节制的饮酒。周公对卫地的殷商遗民和受封的统治阶层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饮酒的场合也进行了细致而明确的规定,只有父母高兴,或者参与祭祀时才可以饮酒,而各级官员也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过度饮酒。
3、禁酒令和铜禁的关系
通过研究反映周初禁酒意识的文献和禁酒令,我们不妨猜测,酒禁是配合禁酒令的一种礼仪用品,在天子分封、祭祀等场合作为礼器来使用。考古研究人员在考古报告和后期研究当中曾经提到:“周初曾经厉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禁酒的考虑。”⑦这种说法有失妥当。因为酒在商周时代是一种奢侈品,而非一般平民日常可以享用的,民众饮酒的机会仅限于参加重大节日的时候,如祭祀等场合。在祭祀用酒方面,殷周两代一脉相承,祭祀在上古时期是统治阶级重要的日常工作,酒被滥用是因为商纣王从各方面破坏了商先王时期的用酒制度,并且随着统治的日渐腐朽成为统治阶层纵情享乐的载体,即便如此,饮酒风气的盛行也仅限于统治阶级,所以《酒诰》包括酒禁的使用对象针对的也应为各级官吏。
四、禁酒令未能大规模且持久有效的原因
既然周初曾如此严肃地对待饮酒问题,并且也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证明统治者的态度,酒禁的出土情况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却只有七件而已,文献的记载和文物的佐证为何出现了脱节?
1、酒在统治阶层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依然扮演重要地位
商周二代的礼仪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各种重要的礼仪场合中,酒都是必不可少的,在统治阶层的宴会当中,酒也是随处可见,《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述:“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所以所谓的“禁酒”不可能是完全禁止,并且随着政权稳定,经济逐渐恢复,饮酒变得更为惯常。《诗经》中描述统治阶级宴饮的篇章随处可见,《大雅·既醉》中就描述了周天子和诸侯国宴饮的场景:“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既醉以酒,尔肴既将。君子万年,介尔昭明”⑧。还有诸如《小雅·鱼丽》:“君子有酒,旨且多”⑨;《小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⑩。并且随着文王时代的远去,社会逐渐稳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殷商亡国的教诲也逐渐被统治者淡忘,饮酒之风又日渐盛行起来。这些作品生动表现了王室贵族饮酒的状况。这也就是说从周文王开始禁酒意识萌发到周公摄政期间发布明确的禁酒令,随后逐渐淡去。统治者有禁酒意识只有七十年左右,而有效的禁酒令大概只维持了四十年左右。酒禁作为一种新式礼器,没有大批量生产和扩散也在情理之中。
2、颁布禁酒令的地域和阶层有限
关于西周的政体历来各家众说纷纭B11,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种分封制是相对比较松散的。相对于夏商两代,西周的政体显然要统一的多,但是和秦汉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相比,所谓“天子”的集权则要弱的多。周天子看上去更像是联盟盟主的身份,国家整体看上去是周邦和万邦并存的局面,全体贵族共同掌国政的性质。
已知的七件酒禁当中,有五件的出土地点都在镐京(今宝鸡)附近,这证明酒禁只是在距离统治者较近的范围内,虽然统治者有面向全国禁酒的主观意向,但是并没有达到全国响应的客观效果。《酒诰》所针对的是殷商故地的遗民所颁布的禁令,本身就有一定的地理限制性,其余地区更多为警示作用。
五、结语
综上,西周初年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吸取殷商灭于酒的教训,教导官员和百姓勿耽于酒色,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创制新型礼器和颁布禁酒令来达到改变社会风气、控制饮酒之风的效果。但是这种礼器的使用具体方法还有待于更多的实物出土和更加丰富的史料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刘军社:《宝鸡石鼓山惊现西周铜禁》,《博览》2013年09期
②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简明版),中国地图出版社,商及西周时期全图,1991年版
③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295页
④陈全方,周亚,罗忠民《商周文华》学林出版社,2008年8月,47-109页
⑤卫康叔之封及卫国所在地,《史记·卫康叔世家》:“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⑥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酒诰第十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372-383页。
⑦刘军社等:《陕西省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⑧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282页
⑨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178页
⑩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182页
B11参考李学勤《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3月,第九章,西周政体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