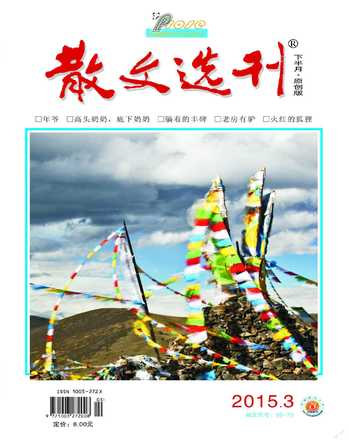小村
韩卫贤
我的故乡是个很小的小村,朴素得像一个乡下泥孩子。
我曾在朋友那里借来地图,趴在桌子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我知道,知道它名字的人,很少。
小村的四周是站立的庄稼,它们生生不息,正如小村里淳朴的农民。
小村没有迷人的风景,实在得像一捧黑土。走出小村的我,却走不出小村散发的泥土清香。
每当我回到小村,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总会看见村口的老树下,正在劳作的娘。
我知道,每一个从乡村走出去的人,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村,都有一棵树,都有一辈子也走不出的乡情。
我也一样。
小村是我永远的家。
很小的小村,其实很大。
风过河面
风过河面,我小小的心思,正水草样疯长。
少年时,我爱思考,常常站在女儿河边,望河水。
那时,我想象着把自己站成一株植物,迎风而立,仿佛自己成了女儿河的一部分,须臾不能离开。
我还发出了声音。我用孩子气十足的声音,高声吟诵课堂上学来的文章。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就是想也想不清楚白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安排。
也许这样的细节是极普通的。但是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它其实一点也不普通,是我悠长童年生活中的最夺目的一抹亮色。
现在,我站在女儿河边,恍惚中看到自己仍在朗诵抑扬顿挫的诗歌。我朗诵得很投入,也很动情,惊得日子像水鸟样疾飞。
风过河面,吹皱了河水。
仿佛吹皱了谁的脸。
山枣
丰腴的山冈一熟透,山枣那圆圆的小脸,就涨得红红的。
不让秋风收藏,蹦蹦跳跳,滚下坡。
是有什么喜事要来临吗?
乡下人的喜事可是不多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人办喜事,大都选在秋天。
真的有喜事呢!我听到了那久违的音乐正从小村中蓦然升起。
那是喜庆的音乐,粗犷、直率、实在,仿佛整个小村憋足了劲,大声喊出来的一样。
唢呐声像一条红线,牵出了迎接新娘的花轿,牵出了合不上嘴的新郎官。那急匆匆迈动的脚步,让小村此时无比生动。
再贫瘠的乡村,也有天空般明亮的爱情。
圆圆的山枣,就是最好的见证。
堆满衣襟。
撒上婚床。
雨下得太久了
雨下得太久了,飞鸟的翅膀已湿透,怎能驮来太阳暖暖的笑脸?
当阳光越走越近的声音一点点涨满,云聚云散中,传来一声谁的轻叹?
我知道,那不是轻叹,而是一种朴素的仪式。
我也该做点什么。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努力地弯下腰,做中农妇拾麦的姿势,同雨作最后的告别。
告别了,事情还不算完。乡下人做事情是讲究礼仪的,别看他们说话有时粗声大气,但做起农家院里的事情,却完美得像小村在舒缓匀称地呼吸。
我在爹略显浑浊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
我礼貌地目送雨季渐渐远去,然后推开柴门,戴上爹破了边的草帽,走过村街,走出小村。
我在女儿河边走过,来到田间。
我把自己的身体伸展开,与阳光亲亲热热地拉手,兄弟般促膝而谈。
一只鸟
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我就走出了家门,走过村街,走到女儿河边。
春天的清晨,每一个角落都荡漾着生命萌发的绿意,每一缕空气都弥漫着比爱情还要甜蜜的气息。我在走动中被这种气息感染着,心中生出些许感动来。
让我感动的还有一只鸟。我看见一只鸟在我的头顶飞过。那是一只不大的鸟,飞得悄无声息,它没有呜叫。它不能呜叫,因为它的嘴里衔着一根小小的已经枯干的树枝。我不知道这只鸟是什么时候起身的,但我确信它一定起得比我早,飞过依然沉睡的天空,飞过日夜流淌的女儿河,飞过一片田野或者一座村庄,才衔回这根小小的树枝。
衔着树枝的鸟是要建巢了,就是说,它恋爱了。它要每天早起劳作,用一栋漂亮的新房迎娶自己漂亮的新娘。
我真的感动了,目送小鸟那渐渐飞远的身影,直到消失。
我继续向前走。我觉得我走路的脚步声有了变化,似乎在一下一下溅起的声音里,蕴含着什么。
一只鸟因爱而奔忙。
一个清晨因奔忙而明亮。
一天因这样一个清晨而变得意味深长。
桃花盛开
桃花盛开,让寂寞的小村发出充满活力的笑声,清清爽爽的。农事蓦然醒来,愣愣地打量着田野。
你可以听到大人的谈话声高了八度,孩子们嬉戏的喧哗声溢着掩饰不住的快活,就连拉车的马儿喷出的响鼻也传得远远地,村路般悠长。
一切都是清爽的。
是谁,被坚硬的冬季划伤了?去找桃花吧,那氤氲的气息,是促进伤口愈合的最好药方。
邻家的六奶奶推开窗子,高声地咳嗽几下,嘴里少了一颗牙,脸上却多了一层笑。在六奶奶眼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唯有这盛开的灿灿桃花,总是在这样一个春意萌动的中午悄然而至,叩动心扉。
六奶奶笑呀,笑得“咯咯”响,仿佛看到自己情窦初开时那张灿若桃花的脸,仿佛看到整个小村因这悠然而至的约会而满面羞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