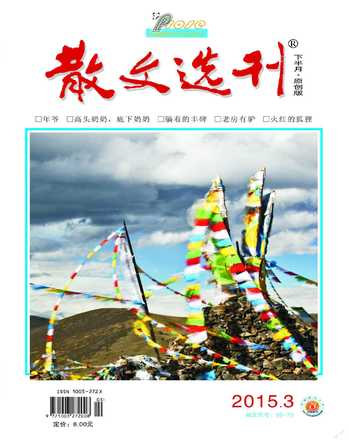抹不掉的记忆
时磊英
一
那时,三奶奶不到40岁,一米七的个子,皮肤白嫩、细腻,微微泛着红润,一头乌黑的过耳齐发用黑线卡卡在耳后,柳叶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如一汪碧水,是我见过的女人当中最俊俏的一个。
三奶奶娘家是地主成分,是大户人家走出来的女子,她是我们村唯一一个识字的母亲。那个时代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她和三爷爷的婚姻就是当时典型的门当户对。虽然三奶奶品貌出众,但三爷爷却个子不高,相貌平平,是一个憨厚淳朴的庄稼人。在现在看来,他们实属那种看起来很不般配的夫妻。不过他们夫妻俩几十年来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是典型的模范夫妻。
三奶奶一生中,生育了三儿四女。娘家早年就移居山西,父亲早亡,唯独三奶奶一人留在山东。
二
三奶奶家和我们家是五服边缘的本家同族。
我和三奶奶的三女儿——素素同岁,她大我两个月。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初中都是同班同学。上学、放学的路上,步行时,我们肩并着肩行走;骑车时,我们并排行进。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没有秘密可言,并且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哪里有我的身影,哪里就有素素的存在,就连晚上睡觉我们也会时常凑到一起。1983年秋天,菏泽大地震的那天晚上.素素和她二姐、四妹都睡在我家里。以至于后来三奶奶多次和母亲说:“幸亏地震时房子没有倒塌,否则,我的四个闺女就砸死在你们家三个。”
我们家因为有了当村支书的父亲的一份工资和祖父母的扶持,相对来说,生活要比一般人家好些。村里人吃黑面馍的时候,我们就能吃到包皮的花面馍;等别人家吃到花面馍的时候,我们家就能吃上白面馒头。素素每次被父母训斥或和姊妹吵架之后,都会哭着在村西的路口等我,每次我都从家里偷偷拿出来一个大大的白面馒头给她。30年过去了,每当我和素素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她都会说:“那时候,爸妈稍说我一句,我就不吃饭,哭着在村西路口等你给我偷来个白面馒头。我真希望你能天天都给我偷个白面馒头吃。”
我从来都把三奶奶当成我的家人。
三
三奶奶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子,裁剪是她的拿手之技。她的剪裁方式与众不同,裁剪时的用具只有一把剪刀。她用眼睛和手作为尺子,随便找来一个随处可得的土坷垃作为画粉。她见过的人不用到场,把布料铺在床上、桌子上,抑或是地上的苇席上,伸手张开虎口,很随意地柞几下,用土坷垃画出几道粗略的线条,几剪子下去,一件裁好的衣服就在她的巧手下诞生。看似很简单的裁剪,做出来的衣服却合身得体,无不让人惊叹三奶奶鬼斧神工的绝技。本村乃至外村的妇女,只要家里要做衣服,就会掂块布料去找三奶奶裁剪。她即便再忙,也从来都不推辞,在她的人生字典里好像就没有“不”字。
三奶奶还有一个绝活——剪花,也就是艺术上所称的剪纸。三奶奶的剪纸方式与众不同,她不需要准备工具和原料,家里常用的一把剪刀和几张废弃的破书纸或废本子纸,她信手拈来,无需画,凭着想象很随意地剪上三五下,用时一两分钟,一幅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的剪纸便在她的巧手下诞生了,无不令人钦佩叹服。我们小时候,还很时兴穿绣花布鞋,本村甚至外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或孩子,无论谁家穿出来的花鞋,花样都是出白三奶奶之手,绣花更是三奶奶的拿手绝活。
村里的喜忧大事,三奶奶便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有喜事,三奶奶会忙不停地去帮忙做被子。有嫁闺女的,她去帮忙做嫁衣,为使做出来的衣服平整而好看,在当时没有电熨斗的情况下,就用茶缸装上热水或炭火,慢慢地把做好的衣服或绣品烫熨平整;等嫁出去的闺女生了孩子,她还要毫无保留地使出自己的绝技:剪花、绣花、裁剪、做小衣服,让主人在祝酒时把三奶奶的辛劳化成风光和体面带去。要娶媳妇的,儿女双全的三奶奶要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其铺床、接新娘、燎车、唱喜歌、祝福……村里有了丧事,三奶奶要按照当地丧事的风俗做孝衣、糊孝鞋、发酵发家面、烙制打狗饼、净面、唱挽歌送行……
四
三奶奶像一棵老树,她把自身的营养都无私地输送给了枝叶。
三奶奶的儿女们大都在城里工作、经商和生活,有车有房有存款。他们让她和三爷爷到城里居住,可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依旧和三爷爷守着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在三奶奶最后有病住院的日子里,儿女们让她住城里最好的医院,他们知道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为孩子和家庭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们想用孝心把母亲的生命无限延长,可是美好的愿望并不能改变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她这棵苍老的大树最终还是倒下了。
料理了一辈子丧事的三奶奶,而此刻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了小村人为之忙碌的主角。
五
三奶奶走后,儿女们不能天天守在三爷爷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通情达理的儿女们按照母亲的遗嘱,帮三爷爷找了个小他十几岁的女人,照顾他的生活。
我去娘家时,续娶的三奶奶到我家去串门,母亲见我对其无语,一次次打圆场给我介绍,可我不听话的泪珠总在眼眶里打转,泪光里,三奶奶的高大形象总会清晰地重叠在那个女人身上,将其遮掩,将其覆没。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试图喊她,可话到嘴边却一次次地又咽了回去,怎么也喊不出她一声“三奶奶”来。有时,我甚至还会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
三爷爷续弦之后的春节,我和姐姐、妹妹一起到三爷爷家去拜年,可每当我走进他们家门里的时候,我都会流着眼泪退回去。在我心里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三奶奶,该我去拜年的三奶奶已经走了,她家里的那个女人不是我的三奶奶,我固执地不能接受这个活生生的现实。
续娶的三奶奶在嫁给三爷爷之前与我素不相识。我很清楚,她是无辜的,她是一个和三奶奶同样善良的女人。我之所以不肯开口喊她“三奶奶”,并不是因为对她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三奶奶已成为我生命里抹不掉的记忆。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已浸湿了纸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