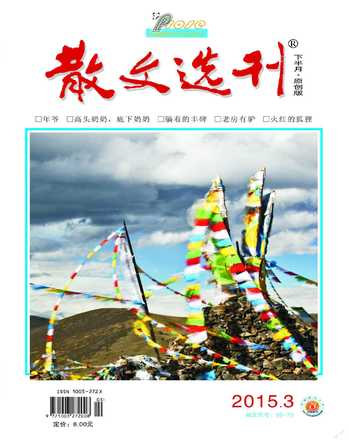南墙根
窦坤
老家在一条山沟里,整个村子南北长约二里多,东西不到一里;大多院落在靠东的山根,西边山根也就十几家,中间一条宽窄百米左右的沙河;自北向南分布着几个泉眼,只有两个大的泉眼蓄水修了涝坝。依据风水,靠东的院落主房也背靠东,大门向西;靠西的院落主房则背靠西,大门向东。地势高的人家,出大门就能看见沙河对面人家院里的动静。至于街巷,当然是南北为街,东西为巷。三个队各有各的麦场,一队、二队的麦场基本在靠近沙河的院落中间,大小有足球场一般,三队的麦场有两个,都较小。三队有公路东西向横穿而过。老家冬天多西北风,即便有太阳,高原山地的风也冻人厉害。但有一处地儿可以享受阳关的温暖,这就是南墙根。家家东西向南边的院墙外,背风朝阳。在冬天里,哥三哥四抑或二姐五姐、张家老汉、李家奶奶的凑在一起,拉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甚至谁家最近有秘事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在村子里流传。南墙根是整个村子里信息的集散之地,也是是非不一的流言发源地。
南墙根最理想的地方是麦场北面某家的南墙。一是眼界开阔,见谁路过,就近叫过来闲聊,不漏人;二是,带了孩子来,孩子们正好在麦场滚铁圈、跳房房、踢毽子,看得着、好照应;另外,孩子玩翻脸了打架也就近好拉架喝止,防止娃娃们手下无轻重,一个把一个防不着给打坏了就糟了。至于三队,多是在公路北边的人家南墙,正好闲聊,瞅着谁要出门了、谁从外边回来了等等心上没事却要打听的杂事儿。有时候也就是自家送人等班车来,大伙儿有事无事地抬会儿杠。那个时候人闲啊,冬天外出补贴生计的活儿也少,不是背煤,就是挖石膏去,而这活有危险,还是个苦力活。所以,大部分人闲散惯了,尤其一上五十岁,就以老自居了,乐于清贫地享受冬天无聊的闲适。每天早饭吃过,只要天气好,就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了。见面先问:“吃过了没?”这一“国问”同样在那个年代流行于我偏僻贫瘠的家乡,这边答道:“吃了,将儿吃了两碗搅团。”这样寒暄问候着靠墙而立,老一点的掏出烟袋锅子,就着煤油火机抽上旱烟,滋儿滋儿地冒着呛人的温暖。年轻一些或是不讲究的掏出报纸裁的纸条儿,顺长折成一指宽窄,另掏出烟叶袋子,一溜儿倒上烟渣子,沾上唾沫,一头包着细细的烟渣子撵紧了,一头卷成细细的吸口,火柴“哧”地一下点着,一样冒出青白的烟来,眯上眼睛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张家长李家短的烂谷子事来。女人们则在不远的另一处纳着鞋底儿,高一句低一句地打探秘事、谈论隐私。有时候常常是男人这边声高起来,原来是抬起杠来;而女人那边早笑成了一团,一个天大的窗户纸秘密又被揭发出来了。所以,女人们的笑声不但放肆,还会夹杂放浪。男人们往往不屑地吐一口口水,继续抬杠。男人们抬的杠不离乎谁的绰号怎么来的、哪个人的丑事是怎样发生的、谁落了好事是什么原因、谁家倒霉是否是前世的报应等等。这边说得活灵活现、如同亲临;那边打断了,说出又一个版本来。就为一个版本谁是真的可信的,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弄到高叫着对方的绰号,狠狠地损对方,目的只是迫使对方放弃个人的版本,承认自己的版本。这个时候,往往老成持重的人一句话就会敲定某一个版本的正宗,落了下风的人会说“不信了打听啥”作为委婉的认输,便不再争论。女人们则挤眉弄眼地说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聊以解闷,谁也不会追究来源,只是添油加醋地议论,直到没有心肺不负责任的言论发展成是非流言,又会在当事人面前指天发誓地辩解清白。最后是狗改不了吃屎,还是拿杜撰的流言蜚语继续传播损人不利己的这事那事。凡事总是离不开南墙根,尤其是没来由的让人兴奋的大家都知道是杜撰的事,却是说的人有天有理、唾沫飞溅、引经据实、滔滔不绝而无头无尾、终归流言的;听的人却也津津有味、故作萌态、假意奉承、顺势接话,成为流言自觉抑或不自觉的扩散者。事情有真有假、事件有小有大,大部分都借助南墙根这个小舞台无意间生成、有意识地流传。像风一样,说来就来了,说走也就倏忽一下走了,连注意的心和操心的人都没个准头。
乡里人的无聊时光和闲散生活,在每天南墙根的唠叨和无聊里慢慢过去,孩子们也在南墙根的唠叨和无聊里耳濡目染地慢慢长大。南墙根就像一个小型微缩的戏台,演绎着老家那个时代贫瘠但幸福感满满的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