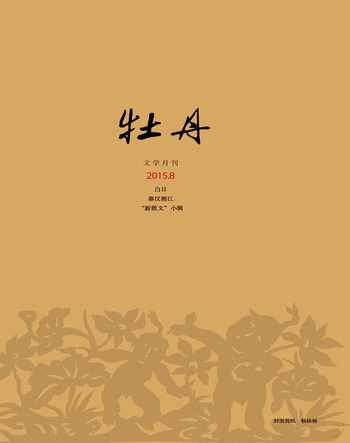蓬头者,他站在另一个世界向你招手
慕眺
春夏之交,雨水变得充足,天空变得喜怒无常,刚才还是春光明媚,而现在已是大雨滂沱。晚上一场阵雨袭击了小镇。驱车路上,一切都裹进水光和灯光撑起的世界之中,令人容易产生幻觉。
掐指一算,他从一个地方迁移到这里,一呆就是九年。日子就如老家居住多年的厅堂,哪里摆旧皮沙发,哪里是水泥楼梯,闭目可知。必经之路旁边的荒草杂地已经摆上楼房、公园、广场、商铺、人群。
一到晚上,城东的广场上横七竖八泊着许多小车、摩托車、自行车,几处广场舞的音乐此起彼伏地响着。道旁树郁郁葱葱,个别枝丫疯长,犹如许久未理发的头颅。生活的经和纬织就的平面,犹如海面。海水渐渐淹没头颅,不知从何时起,他试图不呼喊救命,而在水中呼吸——但这仅仅是奢望。虽渐至沉没,却还清醒,他一直在等待另一扇天窗被打开的时刻。这个时刻曾经隐约来临,但又倏忽不见,犹如坠入海中的网索。曾经捕获的星光,是否脱网而去?日子压折了枝枝蔓蔓的感觉庄稼,只留下空荒的田野、麦茬,以及枯萎的稻草人。
雨时下时停,车子的雨刮发出呜呜的响声,和着滴滴答答的雨声。眼前的视线变得模糊,这让他变得有点谨慎,不由地探头盯着模糊的街道,深怕有车或者人从两侧蹿出——冷不防,真的从左侧绿化带中探出一个蓬头——一个瘦高的男子,头如结痂,疑带假发。原来,对面是一条窄胡同,这里的绿化带被人开出个口子,白天众人从绿化带横穿而过,进入胡同,此刻黑暗布满其间。他心里一惊,不由地踩住刹车,车仍旧往前滑行两步,车底发出沉闷的摩擦声“哧哧哧”,在“蓬头者”面前停步。
那个“蓬头者”,对此险情似乎并不为意,侧对着他,朝着路的对面,使劲地摇手,嘴里还说着什么,最后,还嗔怪似的笑了一下。他从对“蓬头者”的厌恶和愤怒之中开始惊愕——“蓬头者”旁若无人地招手。怪异的动作。他想起小时候看见的一个村人——一个因为高考失败而精神失常者,人家都叫他“大学生”。“大学生”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从他家门口经过,拿着赶牛的细竹鞭或者断树枝,边走边打着道旁花枝招展的野菊花丛,口中嗫嚅,俄而呵斥着什么。奔跑的狗会被他挥起的细竹鞭或者断树枝吓一跳,躲在一旁汪汪汪地叫,觅食的母鸡则咯咯咯地闪开了。“大学生”眼中无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破碎的(或者是完整的)世界里——极少的时候,“大学生”会朝他这边瞪一下,但是,暑期负责看守父亲小卖铺的他无聊而安逸的心会突然一阵紧张——沉闷无趣的水里掉进一个恐惧的石头,溅起水花。现在,他已并不感到惧怕,更多地觉得,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某只手曾经伸出,活生生地掐断“大学生”显得不堪一击的神经。
眼前的“蓬头者”使劲地招手,面对黑色的胡同,仿佛里面有需要唤醒的人。
我们把“蓬头者”、“大学生”放在“精神失常”的盒子里——人一旦被打上标签,他基本上就在那个盒子里了。但是,反过来看,从这些“狂人”的变形窗口往外看,你是否被触动,就如看车子后视镜一般,一切总归远去,一切成了陌生的反面?曾经固若金汤的秩序、程序,在“蓬头者”那里,是否一文不名?事物的固若金汤和灰飞烟灭之间只隔一道念想之藩篱?从这个角度看,看似正常的一切将变得破碎不堪、荒诞不已!
他又想起网络上那个组建“联合国部队司令部”的农民骗子,他拿起自己铸造的欺骗之矛刺向恐慌的街头,流出真实的脓血,让人看到污秽腥臊的肠子露在外面——善良的人们总是不愿意看到血淋淋的场面,认为明日太阳还得升起。“蓬头者”、“大学生”,骗子像一扇被打变形的窗,时刻提醒我们,固有的秩序、程序之外还有未知的世界。而曾经纤纤如玉的我们只知参与此地的庸常乃至罪恶,且沉溺其中而不自知。
他下了车,居然有和“蓬头者”握手的冲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仿佛都可以听见两侧楼房里酣睡的声音。他上前一步,“蓬头者”眼睛直直地对着他,他也盯着“蓬头者”——他似乎要去握住“蓬头者”内心的世界。而“蓬头者”的目光已越过他,依旧使劲地往黑暗的胡同里招手。他有一种挫败感……
雨夜易于致幻。等他回神过来,他的车已停在家门口了。雨已停歇,街上空无一人,他似乎听见整栋高楼打鼾的声音。